的是如何建群
如何建群 时间:2021-02-26 阅读:()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二六年五月號總第50期2006年5月30日曲徑亦望通幽讀王斑《歷史與記憶》⊙張慧敏王斑:《歷史與記憶全球現代性的質疑》(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這是一部纏綿於幻想之作.
纏綿裏不乏憂鬱,憂鬱裏更顯執著.
將一部理論著作用纏綿喻之,似乎有不妥之嫌.
但是,我卻認為找不到更好的詞來表達一個對當代歷史、特別是立足中國當代歷史的學人之筆,這思考、這努力.
當代歷史不僅與現代歷程相系,而且無法避開一種以指導實踐為旨規的理論、或者可以直接指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可這理論又以社會主義國家實踐的徹底失敗變得使闡釋極為困難.
而立足於中國當代更是難中之最.
因為在當代,中國人的記憶裏有那麼多被自己國民信任的政府強迫的傷害,這歷史的創傷、那靈魂的疼痛是可以讓幾代人驚搐的.
可作者卻要以自己的理論素養立足中國與世界對話,帶著一個理想主義的無畏和樂觀,企圖找到縫合歷史與記憶的曲徑.
也許作者難以苟同,但卻是我閱讀的感受,以作者自己對王安憶《紀實與虛構》的評述來概之:「這個歷史其實是傳奇和神話,敘述者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因而作品的基調是憂鬱哀傷的.
」但是王斑的筆有一種憂鬱般的沉重卻不哀傷,是如中提琴般的厚重,但不乏昂揚;這是因為,批判現代的立場始終立於對「幻想」的堅持,而我開篇定論取此二字亦是來自文本自身的理論引用(見頁177),其是指史詩的魅力與詩意.
《歷史與記憶》(下簡稱《歷》)似乎是由九篇可以獨立的單篇論文構成,由一線貫之凝成專著,即為作者在導言中指明的:「本雅明歷史批判的啟示是,必須發掘現代性進程中另類的蹊徑、層次與想像,質疑中國現代性歷史的程式化敘述.
」本雅明猶如智慧的精靈閃爍於整部著作中,每一篇、每一章以警句般的形式亮出作者對中國現當代歷史敘述的思考.
一《歷》的思考方式屬對話、探討、或者說辯論型,有一個先在的話語場,作者對這樣的場境發出探討,以理說之.
作者首先強調的是「歷史並沒有終結」(頁8),這是對「歷史終結論」的回駁,而且作者要強調的還有這歷史意識和觀念不僅僅是古代型的「寫作或關於過去的文字記載」(頁26)而是現代型的「既是一種寫作方式又是人們的社會行動,既是一種敘述的表達,又是重構社會秩序、理性自覺的世俗實踐.
」(頁26)作者更進一步地以梁啟超之言來明確古代歷史觀與現代之不同:「現代歷史是由某種目標所推動,而過去的歷史只是記錄.
」(頁27)其實作者要堅持的仍然是「民族-國家」歷史的建構.
因此,作者認為:「歷史的眼光不僅前無古人,更是創造來者,展望未來.
」(頁26)於是,作為閱讀,就必然需要對這樣的語境對話做些辨析.
以「歷史意識」對話與「普遍主義」對話場域裏,「普遍主義」認為:在世界真正的大問題都解決了之後,構成歷史的最基本原則和制度可能不再進步了,因為在「自由民主」的樂土裏,以現代自然科學為代表的歷史機制、以及闡釋都趨於雷同.
所以歷史走向終結.
多半針對此論,反駁者堅持「大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比如「九一一」,比如伊斯蘭等宗教紛爭問題.
對此,「終結論」始作俑者福山區分為兩點憂慮:一為經濟發展的失敗,如中東;二為東亞的經濟成功與傳統的家長專制的結合.
但是,福山在闡釋特別是第二點憂慮時並沒有很好地深入東亞的傳統文化機制,其例舉的集體意識、集團意識,個人對多數人的認同的非理性的順從和依附,是不符合其欲批判的東亞儒家意識的,因為儒家意識並不在於「多數」,多數有可能產生的暴政恰來自反思民主機制存在的負面因素.
而儒家服從和依附的是一個建制,其在東亞傳統文化裏千年來以「禮」單字概之,在「禮」之下沒有多數投票之說,其「群體」意識在於對這個建制裏的人人都有益,屬於理念品格而不是現實的人多勢眾、投票表決.
人確實在禮的建制裏上至周公下至百姓皆為工具,以現代理念審之,其削弱個人性;但這個「禮」本身是滿懷抱負的,其構建的層層等級更是將這抱負散散於各極,事實上最大的挑戰正是有可能阻止平等意識裏「沒有理想、沒有抱負」、平面的「最後的人」的出現.
也就是說福山憂慮的挑戰絕對不來自於習慣的「東亞封閉的傳統意識」,而是東亞的現代歷史進程裏,不會全盤否論西方的引借,但是也不會完全歸功於西方文化的引借,而是傳統的現代轉化,借用後殖民理論的概念是「交互與雜糅」,這可能是歷史機制闡釋的別樣性.
王斑的《歷》屬於上述對話場域裏的討論之一種,只是作者採取的立場是屬文學性的隱而不露、卻又處處針對的方式來進行表達.
首先,作者表明自己傾向「歷史的意識」有別於相對論的「歷史性的意識」,作者借用美國歷史哲學家羅斯的分辨,前者是「有能動性,希望發現過去的發展能賦予今天以意義,為現今指出方向.
」於是,顯現歷史延續性的必要,而且使某種歷史敘述合法化.
按傑姆遜所說:歷史自身不是一種文本,除非它以文本形式或敘事形式出現,否則,我們便無法接近它.
1《歷》恰是將中國現代歷程作為多個文本現象,而且採取不同文體的分段闡釋來接近歷史.
第一章作者從《魯迅的批判歷史意識》入手.
切入的是中國現代歷程的初始形態(當然中國的現代歷程具體時刻當然可以推向現代之先的近代),也就是說民族國家話語建構的最初狀態.
中國的現代民族國家意識的產生確實伴隨著西方的煙槍大炮,且是一個民族最脆弱急需現代科技給予新活力的時刻,也確實在魯迅那一代產生對中國傳統最嚴厲的批判形態,但是,若以「歷史終結」論者的極端西方中心論的對話語境為前提,來「再現」中國現代民族國家最初的歷史情景,就自然有了王斑如此篇的闡釋了.
作者明示,此篇希望勾勒出一種朦朧中的「批評的歷史意識」軌跡,其「試圖從兩個途徑來討論.
一是簡要地評論法國哲學家福柯的系譜學歷史視點在中國語境的作用,分析其對中國現代文化批評的適用性和局限性.
二是分析魯迅對於西方現代性的反省和批評.
」(頁18)首先來看其第一條途徑分析.
其中隱含了後現代思潮對啟蒙話語的質疑語境,從福柯的譜系分析法入手是相對啟蒙的宏大歷史話語有可能掩蓋或者「霸權」了其他邊緣的、歷史橫斷面間如民間、社群等敘述,《歷》著重的是將歷史返回到當時民族危機的情境中來探討.
對此,本文不予重敘.
我更有興趣的是因了當下思潮碰撞而凝成的辨析,這可以引出兩個思考點,一為,啟蒙與西方話語.
相對「歷史終結」論的「西化論」,中國現代的啟蒙是否屬於全盤西化.
同樣以福柯對康得的「啟蒙是甚麼」的閱讀來理解,啟蒙是人類能夠成熟地、且有勇氣地運用自己理性,可以成為自己理性的主人,於是,其可以對歷史與現實批判性反思.
這恰是魯迅一代致力的追求,也是中國現代民族國家話語的核心組成部分.
那麼,是否可以指認為「全盤西化」我認為,「全盤西化」是一個結論性語彙,也就是說它是針對事實的結果,即福山在「歷史的終結」篇中所言,是從技術到管理經驗、乃至政治制度都全搬西方.
而對於中國民族國家話語中的啟蒙,始終沒有一個結果性事實可以論證其全搬了西方;儘管魯迅一代曾有口號要以西方為樣,那卻是個個飽讀經書之士針對中國行進艱難的事實提出的權宜之際(即欲開窗必先拆屋之說).
中國的現代歷程飽經變換與滄桑,不是甚麼模式說照搬就可以搬過來了的.
以政治制度來說,從皇勸進入現代,幾多變換,在我看來,這恰是由傳統進入現代的必經過程,而中國的現代行進狀態只是與世界他方同步而已.
而王斑在這部分思考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在危機中產生的歷史敘述,是否憑某種延綿不斷的邏輯導致了中國現代革命進程中後來的災難、暴力和政治的浩劫」倘若我換一種問法:即中國啟蒙試圖成熟而有勇氣地運用自己理性的結果是否是造成後來中國當代史中出現的災難緣由回答自然是「否」!
當然有學人認為中國的啟蒙承繼的是法國大革命的一脈,若按這樣的思路繼續下去,很容易跌進有關啟蒙論述以及圍繞此話題的闡釋爭執;為了避開如此的危險,本文欲始終立足於康得關於啟蒙的解釋,故在此將中國現代進入革命進程的話題暫且懸置,而在後文的分析裏,或許此點亦是《歷》文旨中欲發掘現代性進程中另類的蹊徑、層次與想像的一個思路(見上文).
也就是說,中國的現代進程中無論是理念還是實踐,都不是一個恒數,而是充滿了變數,所以多析少結視為策略.
即使是常被指責和貶斥的中國現代語言,儘管與古漢語相差甚遠,但若說其只是模仿之作亦是淺薄和無知的.
中國現代漢語的誕生,恰是為我手能更易更便的寫我口,是為了更好的「公共的」運用自己理性的結果.
第二個思考點是《歷》著膽大欲為的,即強調「歷史意識」的能動性,僅僅「承認歷史書寫有賴於對未來的憧憬和希望」還是不夠的,以甚麼樣的方式達求此境這事實上是對王斑第一條路徑的後半部進行剖析,分析系譜學在中國現代文化批評中的局限性之後的可能性意義.
《歷》著在此切入了一個爭議性話題「進化論」,面對四面討伐進化論的後現代語境,作者似乎欲從中國歷史語義中辟出蹊徑.
其首先聚焦的是嚴複進化論思想中的「意志論」,指出嚴複對進化論的態度是「應然性的」,重其主觀能動潛力.
並以Schwartz的論點來概括嚴氏的進化論歷史觀是:「在非人類的自然和人類社會上,對浮士德和普羅米休士的動力和強力的提升和張揚.
」(頁29)「應然性」是指一種客觀性,這是馬克思理論中常強調的「客觀規律」.
王斑在此著重這點,不只是清晰他的論述立場(因為他的立場在通本書裏處處可顯),還投射出了一個古老的民族在遭遇現代時的切身處境.
「進化」,是歷史的嚮往,如《歷》著所言:「蘊含了民族國家,尤其是殖民地國家,在相對平等的基礎上對公正、自由的社會形態包括平等的國際社會關係的想往和呼籲.
」(頁30)本文既認同此論點與分析,但同時又必須坦言,《歷》作者在進入「進化歷史觀」的論述時幾乎有一種難以掩飾的兩難,一方面,進化話語裏包含著一種普適性的價值理念,可是由於作者的立場卻是絕對不可以站錯了方向,於是,另一方面,要時刻不忘記與普遍主義的針鋒相對.
因此作者反復強調這「普遍原則」一定要建立在自主的權力上方能行得通.
其實,以西方中心論為核心的普遍主義,儘管使用的策略性話語是普世性的價值理念,否決西方中心論者並不一定必須倒洗澡水連孩子一起倒掉,也就是說,沒有甚麼理由可以拒絕承認人性中存在一種普適的東西,就是中國傳統思想裏亦有「老吾我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生死愛恨,就像進化論中的自由、民主、科技、平等一樣是不當分西方與東方的,說得再淺顯一點,就好比人之為食,不當分男女.
儘管王斑是為中國歷史話語中的「普遍原則」以還原歷史情境的方式找一個合法性,我卻認為,其本身就是天經地義.
就像科技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在遭遇現代時可以拒絕一樣.
我倒是更願意以同樣還原歷史情境的方式去體味當時遭受重創後不幸淪為「東亞病夫」的中華民族在遭遇現代科技時,是如何提升和張揚「浮士德和普羅米修士式的動力和強力.
」我願意將已經成為兩個意象符號的人名順序顛倒來釋意,普氏顯示的正是人之主體性的張揚,似乎其他萬物在發現創造之後都可以為己所有的工具.
這幾乎可以作為人類遭遇科技之初的欣喜形態之象徵;而浮氏是人之主體發展的另一個階段,人在自己的創造物前跌入了前所未有的震驚,而由這震驚帶來諸多癲狂.
《歷》亦每每引用本雅明的「視覺震驚」論來闡釋同此理.
但在此處於浮士德,不僅是視覺震驚,而是人作為主體創造歷史的有本質意味的震驚;特別在隱寓中國人遭遇現代化,真是妙筆神功.
從古人對地球儀的執迷到不幸因了他方的大炮被迫轟開國門,中華民族似乎從創造走向昏睡然後在挨打的狀態之下驟然驚醒,世界於是景象萬千、百般好奇.
浮士德的追求、甚至抗爭,更像是今人看古人,是王斑在看自己現代的先驅,他們的赤誠與執著.
因此,王斑的第一條路徑事實上是第二條路徑分析的鋪墊,作者的努力在於為中國現代歷史正名.
《歷》著第一章核心是以魯迅為分析點來討論「批判歷史意識」.
前面本文已經談到《歷》作者崇尚現代歷史意識,即「理性分析的知識形態」(27),並且還具有意識的能動效應.
這裏再次回到康得的「啟蒙」,在康得的思想裏,上帝的世界和人的世界界限非常清晰,甚至可以說「現代」恰來自于這樣的明晰分辨,是在這樣的分辨中人才真正認識了自己.
所以,康得的人之主體來自的卻是人對世界的認識方式的「有限」,將無限的超越給上帝,在「有限」的層面裏,人才可能成為能動的主體.
事實上這裏提出的現代意識是關於「知識」的話語,當人的知識不完全是上帝的統領時,(否決讓你不吃蘋果就不吃蘋果),人的世界才誕生了.
而因了人的認識的「有限」性,以及對這樣的「有限」無窮盡的突破可能,人才有了主體意識.
因此,關於現代的討論,其實是關於「知識」話語的討論.
本文是在這樣的理解前提下來讀解王斑的現代歷史意識.
為甚麼「流水帳」式的歷史,就不符合作者的現代歷史意識標準因為沒有知識的篩選,也就是他強調的「理性分析」.
在我,福柯並沒有走向康得的反面,而是康氏的繼續,福氏質疑的恰是這樣的知識篩選有可能造成的遺失,於是引出知識背後的權力話語.
《歷》著要堅持的恰是本著知識對材料的篩選,於是就必然碰到中國現代性繞不開的話題:古今中西.
首先,《歷》著要處理的是,為甚麼魯迅一代中國知識份子要選取西方知識,而棄絕中國傳統知識,這背後是不是隱含了「霸權」話語以魯迅為範例,是在甚麼樣的語境、以甚麼樣的立場、取如何的方式、欲求得甚麼樣的結果來擇取王斑使用了「批判」,這個詞在《歷》著的論述裏,蘊育空間非常大,可謂是恩愛情仇.
當我們把討論放於「知識」的建構與闡釋範圍來討論,言說者的立場、方法、情境都將是影響視角與視域的因素,擇取甚麼材料、如何論述等等都將左右言說.
《歷》著對於魯迅的歷史觀分析基本由3點論之:其一意欲駁斥直線歷史,採取的是中西相較立場.
首先,也許王斑自己並沒有主觀意識到,但讀者卻可以從曲中領悟到他困苦於自己的立場鮮明.
上文指出過,《歷》著要強調的是進化歷史觀,那麼中國在進入現代、也是融進西方知識的過程中,如何來厘析如此的對民族感情不無傷害的「進化」王斑的方式是一方面繼續前文的「國破家亡」的歷史語境,一為強調「進化歷史觀」是「尋求從衰敗的傳統向現代的、更自由的社會過渡的諸多可能性」,目的是「喚醒歷史意識」,將「進化的想像轉變成實實在在的社會活動和知識的生產」(頁31).
另一方面,在行文層次上屬於遞進性質,即為處理這「知識生產」的中西關係,欲以歷史的迴圈多樣乃至交互雜糅的形態來析魯迅之言.
在此其選取的是魯迅全集第一卷的論說文《文化偏至論》(以下簡稱《文》).
大概研究魯迅的學人基本可達共識的是,魯迅特別是他的論證文基本有「明確的論辯物件」(《歷》亦認此點頁41),但是《歷》認為魯迅論辯「目的是駁斥盛行的全盤西化論」.
這個結論於繁複的魯迅在繁複的中國現代之初的歷史時空,未免過於簡單化.
(本文由於一時苦於溯源到原始資料,無法得出魯迅此文論辯的具體物件是何許人或群體,但基本可以與《歷》著有個商榷.
)在《文》篇的開首,魯迅其實就交待了自己的言說物件,是那些「稍稍耳新學之語,則亦引以為愧」者,這裏既包含了魯迅自己,亦包含了你我(《歷》與本文作者),是針對所有在知識面前的尊嚴之較逐的勸誡;因此,魯迅首先警示:「中國既以自尊大昭聞天下,善詆諆者,或謂之頑固;且將抱守殘闕,以底於滅亡.
」於你我不同的是,在魯迅的歷史時空,警惕自我的弱點,而這個弱點當時被認為是消損一個民族力量的,所以就更加危險.
在魯迅的論述裏有多重意義,其一是不能再「抱殘守闕」,即使是思古堯舜文明,亦要清楚吾文明有幾多創傷;其二是吸收或者批駁西方知識,亦要有歷史學養,故《文》篇的上半部在追溯西方史的發展,在這裏談到「復古」,但絕對不是複如中唐韓愈「古文運動」之中國儒家之古,而是指古希臘羅馬之古.
在現代,古希臘羅馬文明對我學人初入西方知識時有一種無尚的魅力,這樣的對此魅力的素養我願意理解是如同吾民族淵源的文明,是在這樣的文化基因的溝通層面,我們才有這樣欣賞的能力.
因此在這一層面,魯迅要警示的是在吸納西方知識時,我們要警防「偏執」:「根史實而見於西方者不得已;橫取而施之中國則非也.
借曰非乎請循其本.
」是在這樣的警示下,魯迅方開始論述「夫世紀之元···」.
魯迅亦欲通過引介西方歷史演變來防治「以轎往事而生偏至」,在他的論述裏是要我國人在知識的輸入中釐析「近世文明之偽與偏」.
其三,是為他自己以及如同他思想的現代中國知識份子強調的「西學」一辯,指出吾欲宣導的西學是何方知識,這就開始了《文》篇的下半部「十九世紀末思想之為變也」.
在魯迅十九世紀末的思想乃有古風夷.
為甚麼這麼說,《文》在此處開始論述個性的伸張,也就是說在魯迅,古希臘的人之精神嵌合進十九世紀末而生的人之主體思潮,這是國之欲強盛之根本.
因此,《文》的末篇定論於:「然歐美之強,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則根柢在人,而此特現象之末,本原深而難見,榮華昭而易識也.
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
假不如是,槁喪且不俟夫一世.
夫中國在昔,本尚物質而疾天才矣,先王之澤,日以殄絕,逮蒙外力,乃退然不可自存.
而輇才小慧之徒,則又號召張惶,重殺之以物質而囿之以多數,個人之性,剝奪無餘.
」在這篇文章裏,魯迅的結尾滿懷悲情,在他,以物質泯滅個性精神是禍國殃民的罪魁,可伸張獨立之精神在中國又何其難也.
魯迅的理想是建立人國,正如《歷》著所引,「明哲之士,必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校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施之國中,翕合無間.
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
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於天下,更何有於膚淺凡庸之事物哉」是從這裏王斑很好的以「歷史中間物」來概述魯迅一代的思想形態,它們是雜糅的,在雜糅中、在深沉的情感促動裏尋求更新與突破.
《歷》著在此的突破點是從人人轉為現代意識的「群體」,由「獨善」而尋求「兼濟」.
如何將中國傳統的個人與天下之論述契合進現代的主體意識話語中,當是《歷》闡釋魯迅《文》的獨特之處.
魯迅一代強調的是「張大個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義也」(《文》),《歷》闡釋的是「從我做起」(頁48)修身乃是為濟天下.
魯迅與王斑,這裏有一個物件與闡釋間的縫隙,在魯迅伸張個性的隱話語是對儒家的扼殺人之個性的負面進行批判,而王斑話語的背後突出的卻是儒家的正面、優秀體制的建構,是「禮」之大義.
縫合空隙,《歷》著使用的是另外兩點來闡釋魯迅的歷史意識:一為「文化記憶」,二為「希望與絕望」.
我將此二點放於一起分析,是因為在《歷》著中它們交互論述,而目的只為縫合.
王斑當是採用了康得的策略,將上帝的歸於上帝,人間的還回人間;不可知的屬形而上,我們只闡釋可以認識的.
於是,在對「文化記憶」的闡釋裏,魯迅的批判就可以順然劃為「創傷」,而在「創傷」後的絕望裏,總還是有希望.
應該說《歷》最打動我的是這種對希望的堅持精神.
回到此部分的開局,現代攜帶知識話語闖入,複雜紛繁.
《歷》在處理中國知識與西方知識,傳統知識與現代知識間,分析點設置在「記憶」,整部著作力求透析的是「記憶與歷史的互動張力.
」而記憶,自然有必要區分,而且記憶本身亦有選擇的品性.
在現代意識裏,文化記憶更是現代人以主體之身份來接觸過往的客體,有必然的時空優勢.
正如王斑在析魯迅,是在啟蒙話語反思的語境裏,因此,在同樣的「個人主體」這樣的問題上,王斑的闡釋裏就會融入多重分析元素.
上面我已經指出《歷》著獨到之處在於析魯迅「批判歷史意識」時,將中國傳統的個人與天下融于現代意識的主體性來分析.
在魯迅的《文》篇,「主體」還只是停留在「大人格」的伸張,而在反思啟蒙話語裏,這樣的主體伸張在遭遇工具理性的剝蝕時,困難重重,於是當代理論者開始注意主體中的「情感因素」,而在分析情感的倫理時,直接切入的是審美要素.
是在這樣的分析語境裏,王斑涉足的傳統中的個體話語,不是「修身」而是「獨善」,前者更多在「禮」的規範中,後者才有審美意向的馳騁.
而本來在傳統語義裏,是比較句式,「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是人生處境不同的態度;而王斑卻將這兩個句式落實到遞進關係,《歷》著中,「獨善」是為了「兼濟」,而這樣的遞進正好符合了魯迅的張個人之主體,乃創人國的遞進索求;而我讀者亦無以反駁由「獨善」趨於「兼濟」的不可以,因為「獨善」在本質意義上是「兼濟」的前提,而「兼濟」本來亦是「獨善」隱話語中的目的指向.
因此,《歷》著讀出「魯迅提出的理想個體近似泰勒所說的『表意個體』.
這樣的個體有理想的個性,他、她通過審美的手段書寫歷史.
」(頁51)此點應該是《歷》著通本的研究意旨.
於是在首先已鋪墊的「歷史中間物」的現代知識份子,在以審美情感為主導的敘述歷史裏,自然是無論「文化記憶」有何等創傷,仍然是能動向上,絕望中滿是希望的.
二要真正把握住《歷》著闡述的「歷史意識」是必然從其第一章跨越進第二章、第三章.
在本文的開篇亦指出,《歷》著的特性有一種纏綿於幻想、又不乏憂鬱之作;就好比本雅明之幽靈是怎樣悱惻綿綿於整個現代史的思考裏.
在上節分析的最後,本文遭遇到幾個問題而不得不暫停,而這些問題要得以深入也就必然進入接下的二、三兩章.
在較析魯迅的《文》與《歷》的闡釋時,涉足到人之「主體」,王斑以「進化」歷史史觀,將魯迅的「個人」放於「社會重構的想像」中.
在分析中,如同前述,王斑有一個隱在的卻無時不針鋒相對的討論物件,此處是自由主義理念中的現代公民社會等概念,於是王斑假借的是泰勒的「群體和個體」之分析,那麼給我閱讀者帶出來的問題是,中國如何從「天下」轉入進魯迅之言的「國」,此「國」與「國家」以及「民族國家」之間在概念上又有著怎樣的聯繫和區別而又怎樣從原文本魯迅的「國」進入闡釋者王斑的「群體」之分析其實這些問題的跳躍本身就囊括了現代歷程的階段性.
在魯迅年代,一如王斑使用的「歷史的中間物」,「國」與「天下」的關係在概念上並沒有明顯的分歧,而是在王斑所立當下語境裏,「國」更貼近了「民族國家」,而且這個現代意識而起的概念,在後現代的視域裏是一套寓言性的話語,在這樣的話語分析裏存有多重政治價值衝突,於是王斑使用了「群體」之概念.
將中國的現代國族理念放於因了殖民遭遇、民族存亡的危機而得以成就,《歷》著認同而且強調了這個關於中國民族國家話語建構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論述,同時王斑欲繞開的是「國家」語彙本身的強暴功能,因了這樣的功能帶出的災難,《歷》將其劃為現代創傷.
在中文現代漢語詞典裏,「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是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實行專政的暴力組織,主要由軍隊、員警、法庭、監獄等組成.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它隨著階級的產生而產生,也將隨著階級的消滅而自行消亡.
」2而英文的解釋義不只有其政治的暴力面,亦有公民身份的界定,3似乎英文的更接近「Nation-State」即「民族國家」之義.
當然因了一時沒有辦法得到最新中文漢語釋義,故並非要評價兩種語言釋義的差異,而是欲通過這樣的定義來揣摩《歷》著中欲避開的「國家」之政治暴力功能,而傾向于社會公民情感關係、民族文化認同等層面,於是而選用了「群體」之概念,而且把個體與其關係視為社會的有機情感組成;以這樣的構成來貼近攜帶沉沉文化情感的「歷史中間物」般的魯迅一代.
所以,王斑對魯迅個體意識的分析落實於「表意」.
由這個概念切入進能動的審美經驗分析.
一方面強調絕望裏的希望,另一方面透析悲劇裏的審美.
對於中國知識份子來說,進入現代有許多合謀行為,借用西方及建立民族國家等等皆是合謀來反傳統伸張個人主體,這是中國現代歷史進程的第一步,這一步裏有對故有文化情感的創傷亦有嚮往,這是《歷》著的第一章;而國家政權的建立伴隨而來的卻是政治機器對個體人性的瘋狂扼殺,由此帶來的災難和創傷就更大了;於是,《歷》著承接的後來許多章討論的都是創傷的歷史亦是一個存在,在這個存在裏如何建設性地去尋求其意義.
因此第二章就是一個過渡性章節,它承接第一章對魯迅話語的探討,而又要啟承以下諸章的中國當代創傷後的歷史敘述.
而第三章是全書思考與回應的結論,即歷史非但不可能、不願意終結,而且可以他樣的形式繼往開來.
這兩章當是最顯作者功力的章節,也是我最喜歡的兩章.
《歷》著最大的長處當是論述具有時空感,雖然沒有平板的累述歷史的演變,但思考跨度與深度無不囊括了現代意識的跌宕變遷.
《歷》著第一章在論述中國歷史遭遇現代間,首先讓梁啟超、魯迅一代執著的一是進化史觀、二是個人主體.
如何以能動的主體來展現史,是我對二、三章的讀解.
一如我開篇所指,本雅明的史觀猶如思考的引線,自始慣終.
首先,我要聚焦於《歷》第三章的篇引:「歷史中的所有陰差陽錯,所有的哀傷和失敗,都可以在人的臉相上,更準確地說,在一個骷髏上表達.
雖然骷髏之為物,毫無象徵性的表意自由,毫無古典的和諧得體,脫去一切的『人文』的修飾,但在其中,人受制於自然這一事實則表現到了極致.
」(頁107)前面本文提到康得的人對世界認知的有限,而又因了對有限的不斷突破而成為能動的主體.
如《歷》中所指,本雅明受康得影響,但我卻在這段引言裏更讀出的是本雅明對康得的補充或者說更進.
康得面對的是在上帝統領知識的語境裏的對話,因此,在發現人的有限層面中人可突現出主體的能動可能性,於是在這樣的能動主體敘述裏,歷史可以被表達.
而本雅明卻是在這樣的表達中看到了其的不可能性,《歷》在前段引文後再度引述的是「表意書寫越是堂皇,人受制於死滅的因素就更加強烈.
因為死滅在物性自然和象徵表意之間挖了一道彎曲而深邃的鴻溝.
」(頁116)在本雅明的現代意識裏,已經不是停留於對知識的認知,而著重的是「表意」,但在表意構成裏,一方面,人的時限與頹敗的增長難以成比例;另一方面,表意的紛繁在人的時限裏難以窮盡.
這個視角基點具有相當的悲劇意味,但是如何在悲劇裏尋得突破是《歷》著的最大努力.
在第二章,開篇論述「悲劇視角」,似乎尋得兩種突破途徑,其一在審美中體驗,其二在現實中直面.
這兩點融會於《歷》作者對本雅明思想的讀解.
我願意在這樣的理解基礎上堅持《歷》著的能動突破途徑是透析了本雅明的意旨;儘管《歷》著本身在這裏卻有所區分,認為「濛濛如煙然」,臉上「絕不顯哀樂」(頁118)的骷髏意像裏難尋本氏常涉及的「氣息」.
這「骷髏」所指是歷史沉物,而在「凝神」過程中,會有一條彎曲而深邃的通道,在體驗和表述如此的幽邃中,能感受不到「氣息」問題是王斑將「氣息」讀解為「主體凝視物象時,物性似乎顯示人的印記和反應,有回眸一笑的意思」(頁118).
如果我把這回眸的一笑層次更加拓寬,也就是說這笑不是一般的回眸就出的,而是古希臘的司芬克斯的笑,是那種人面獅身變換莫測的笑,是不是就容易多了在骷髏的意向亦能捕捉到那歷史意識欲表的氣息這裏涉及到關於歷史研究物件的問題,在西方馬克思理論的論述裏,這個「物件」不只是「歷時」的更是「共時」的,是可以將物件復活、再現、並在當下構起作用的思維過程,在本雅明,這個過程是如此「彎曲而深邃」,以至使個體的生命在時限定數的壓迫裏滿具憂傷.
應該這麼說,馬克思理論發展到本雅明及以後,在認識論層面有極大的突破.
一如《歷》著所指關於歷史論述的「自然-歷史」概念,與馬克思的歷史與自然觀相交,指出馬克思大體承認歷史是對自然的征服,而本雅明對這種進化觀念卻提出質疑.
我願意將馬克思的思維放于承黑格爾以來的二元關係裏去理解,也就是說,在馬克思,歷史是人文性的,其自然與歷史構成是動態的人文與靜態的自然相對而成;而在歷史物件上,更多的是在二元結構裏(特別是在人類歷史的發展階段裏)探究其本質;而本雅明,自然本身是人文的構成,儘管在表面上已成為博物館的靜物,但本質上是動態的,是具有多層面空間紛繁的組合,這在傑姆遜的《馬克思主義和歷史主義》文中引用瑞士史學家巴舍芬(J.
Bachofen,1815-1887)的話來表述:「真正科學的認識論,不只是回答物件本質的問題.
認識過程的完結在於發現物件產生的原因,而且要將它和日後的發展聯繫起來.
只有當知識能包含起源、發展和最後的命運時,只有在那時,知識才能轉化為理解.
」4我願意這樣的思考,將馬克思勞動商品的「再生產」概念運用於知識的建構過程中,於是才有「寓言」的品格,而在這樣的品格中方可企望具烏托邦意味的未來.
回到《歷》著,面對中國紛繁的歷史物件,如何將中國佈滿創傷的「過去時間」或者說影像,「充滿進現在的存在時間」裏本文的理解是,因了對歷史知識的生產方式的思考,《歷》才選用了本雅明的精神.
在表述自己的歷史性研究時,立足的是記憶,而這正是當下的主體在經驗著過去的客體的表現形態;不只是《歷》作者本人與王國維、魯迅一代、以及當代諸多紛繁的歷史現象觸碰,而且那研究物件本身也是在不斷的與其過往以及其當下的文化客體的相撞,故在《歷》著中這樣讀解魯迅的史識:「不是根據敘述情節慣例,或總體概況的歷史哲學來思考,而是在經驗、創痛和情感的層次,看歷史如何作用於人的身體.
因此,魯迅考慮的是個人在歷史各種紛繁的可能和岔路中糾纏不清的存在主義狀況.
瞭解歷史,就是了解社會文化環境如何振盪、施壓、肢解人的身體,如何侵蝕、創傷人的心靈.
以現代個人身體的快樂和痛苦來觀察歷史,歷史的知識便可以作為批評歷史事實的標準.
」(頁84)這是以一種現實主義的態度來面對歷史,是「一種對歷史浩劫毫不退避、毫不眨眼的直面相對」的歷史觀(頁87),《歷》作者給了這樣的態度極美的讚賞,甚至認為像王國維的悲劇觀亦「提倡在創傷何浩劫壓頂之前巍然不動的『壯美』心態.
」(頁87)前面我說過「悲劇-現實的歷史觀」,是《歷》建構知識並尋求突破的方式.
無論是第一章魯迅的「絕望中的希望」,還是對現實主義思潮在30年代中國走向成熟後的系列文藝作品,甚至是長焦鏡頭分析等等,無不顯露在歷史話語的「再生產」過程中,《歷》在面對歷史現象的社會結構所欲尋求的「壯美」之努力.
確實,中國自問題劇開始就涉入現實的反應生活的表達方式,切入社會問題是為了尋得解救方式,這是能動積極的態度.
我願意把這「悲劇-現實」結構作為讀解《歷》在中國現代歷史知識再生產的一種獨特方式,《歷》文本要強調的仍然是歷史不會終結,寓言民族國家的話語也不會終結.
在面對悲劇的現實主義分析裏,認為本雅明的寓言是「試圖在歷史的『無物之陣』中尋找家園,(頁109)其引用美國康奈爾大學的政治學者蘇珊伯克-默斯(SusanBuck-Morss)的論點,寓言「是一種特殊的意義表達形式,但這形式『不是藝術家自由選擇作為自我表達的審美手段,而是外在世界強加於主體的一種認識律令』」.
王斑認為這「『認識的律令』,有如康得的『道德律令』,顯示了寓言表達在每日每時的日常生存中,必須面對歷史創痛的嚴峻和急迫的威壓.
」(頁110)如果將現實與過去,闡釋者與闡釋物件也賦予「寓言」結構關係中,那麼不然理解王斑在讀解中具有的使命感無不是在表達一個群體的立場,一個欲參與社會類別的論說分析.
確實「現實主義」思潮亦是在這樣的參與意識裏,脫去了藝術純為享樂欣賞的品格,而賦予了使命意識.
因此,讀解到這裏,本文幾乎將《歷》對中國現代歷史知識的探討當成了群體論說的模式;即使是論述創傷,在現實主義的理解裏,「不僅僅是個體的,而且是歷史的見證」(頁127).
可以說這是《歷》生成的「當下的時間」或者說現實語境,以過去的時刻來作為回饋當下的理論形勢.
回到上文提到的傑姆遜的《馬克思和歷史主義》的論述,其理論派別是要力求區分和論述「同一性」和「差異性」的問題,而《歷》在讀解中國現代歷史現象中,恰好地剝析了在遭遇現代的「共時」裏,中國獨特的「差異」.
即使是現代性中具有普遍理念的「個人主體」概念.
我在第一節裏已經指出,《歷》欲分析的魯迅之「表意個體」.
在這裏我將把這個概念融進對《歷》的另一「再生產」方式的讀解,即「審美構成」中.
其與「寓言」化歷史一脈相承,只是比「寓言」有更高的追求,直逼象徵體系.
《歷》指出:「審美與歷史的交接聯姻,使得歷史意識產生了新的功用和含義.
歷史的寫作不僅僅是歷史學科對過去事實的記載和解釋,而是一個廣泛的文化象徵活動.
這個活動的目的在於,怎樣對付過去遺留下來的現實,針對過去的創痛,擺脫過去的重負,繼往開來.
」(頁67)這幾乎可以說是《歷》作者的直抒胸臆了.
當然王斑很明晰直抒是一回事,理論分析是另一回事,因此承接著他以上比較,即追求古人具體的實在情境的歷史主義認識論態度,那種認為歷史話語與審美的結合,使歷史話語偏離了認識論的中心,不再孜孜探求過往的「真實」,王指出:「審美創作中的歷史,卻更訴諸現今觀眾的感覺、情感、視覺、意識形態風尚,以及心理生理的接受過程.
審美化的歷史,將過去和現在變成關照欣賞的景觀和意象,探問今人在這意象中是否有舒適、愉悅或有歸屬.
···審美的歷史觀,在一個文化視覺體驗上,在感覺、感情結構、敘述過程和對過去的態度上,起著很大作用.
它不斷地調整、創造、翻新這些體驗的結構.
審美化的歷史借古喻今,古為今用,呼喚過去的景觀是為了理解現在,憧憬未來.
」(頁67)這是一段非常浪漫的論述,而且在這樣的論述後還有一個理論支持,即《歷》引述美國歷史理論家海頓·懷特(HaydenWhite)認為:「歷史寫作中的審美和修辭因素,並不是在求實求真的歷史書寫中畫蛇添足,錦上添花,而是歷史書寫本身的天然的功能,是歷史話語內在的機制(Metahistory1-42)」應該這麼說,王斑在把創傷歷史的沉痛細節劃給了現實主義的方法,就一身輕鬆了,於是撇開歷史創傷細節而進入的是一個群體理論立場的言說範圍,有數不清的群體話語支持,審美於歷史,是本雅明的「他人的故事」裏的「寓言」,《歷》引述阿多諾(Adorno)之言:「純粹審美觀點理解的藝術,即使在審美層面也是誤解的藝術(AestheticTheory6)」(頁95)即審美本身亦無純粹,必有寓意,與「歷史話語內在機制」相吻合.
而「表意的個體」是指甚麼呢是「審美經驗塑造的主體」(頁52)是「在創造藝術和詩歌中,詩人、歷史家喚起民眾,促使他們以藝術的有機整體模式、內外一致的親緣表意關係來建立一個社會.
」(頁51)這樣的「個體」是「主體」與「客體」的合成,可以「成為審美、社會、政治改革的對象和能動者.
」(頁52)可以說無論是「表意」還是「審美」,《歷》始終訴求的是群體意識,在這樣的意識裏去把握本雅明的「藝術氣息」,這樣的「氣息」於中國現代史,獨異一方.
中國要敘述的故事,是可以表明屬於自己的過去,並與現在和將來延續:「中國人需要一個可信服、可以與其共存的過去圖景,為今天奉獻意義,他們希望通過敘述去恢復人人應有的歸屬感和根植群體生活的身份感.
」(頁131)《歷》當是面對中國現代史、特別是苦難的歷程一個非常體己的敘述.
就好比其強調的「悲劇視角」讓人「睜開眼睛看」的現實主義歷史意識,《歷》著始終沒有回避中國現代當代史的苦難,更沒有粉飾、遮掩、或者忌諱、強辯.
而是帶著一種深深地可以被稱為「沉痛」的情感來表達一份體己的沉思,因此,才強調「記憶工作興起的重要」,在解釋這份重要時,《歷》陳述道:「創傷體驗時對個人和群體的巨大打擊,衝擊了文化的表義和象徵體系.
這個體系實際上是人們賴以安身立命、瞭解感知周圍世界的生命線.
通過這個體系提供的文化資源,我們能夠敘述故事,在日常經驗中見出意義和價值,維繫文化實踐的延續.
更重要的是,能夠書寫歷史.
創傷事件和經歷不僅僅破壞了個人和群體文化間的感情聯絡,更重要的是震撼了維持集體和個人身份的公用的文化儲備.
」(頁139)我願意以《歷》在第四章的引言來讚賞,其引用的是歷史學家羅森斯通(RobertRosenstone)的問:「在何種程度上,我們要求感情成為一個歷史的範疇成為理解歷史的一部分歷史成為情景交融、將心比心的圖景,這是個成就嗎」(頁153)我要說的是,《歷》著充滿情感的筆觸正體現了這樣一個成就.
並且力圖挖掘的是「正面的價值觀和頹敗歷史現實之間的辨正互動關係」(頁60).
在此王斑非常機巧的運用了本雅明的有關現代機械技術對人的經驗造成的斷裂、萎縮修復理論于中國的現實,正如《歷》自己表白的:「本雅明觀點並不能為八十年代的問題提出滿意的回答,但他的言說,在歷史斷裂和重建的關頭提供了很多啟示.
諸如歷史敘述、記憶、經驗、靈蘊氣息,以及個體如何與群體文化記憶重新聯繫的問題.
」(頁137)正是這些問題帶出本氏對「故事」的慨歎:「講故事的人已變成與我們疏遠的事物···講故事的藝術已經消亡.
我們遇見一個有能力地地道道講好一個故事的人,機會越來越少.
(Illuminations83)」而這個慨歎《歷》直接理解為:「歷史敘述可以說是個語言的問題,是個如何言說表達意義,聯繫過去和現在的問題.
在連串的歷史浩劫後,中國人不再擁有意義自明、讓人信服的話語,不再信賴歷史的總體規劃,不再依賴原有的經典敘述來想像與現在生存相融合的過去.
在這種情況下,講故事,也就是『講古』,成了一個棘手的問題.
」從以現實態度直面悲劇到審美經驗的表達,是《歷》貢獻其「正面價值觀的途徑」,但是表達甚麼、怎樣表達,在表達中又有如何的想像關係,其又將如何對應心理危機等等,《歷》著仍然為自己為讀者提出了諸多問題,且關鍵還在於,作者王斑自己在思想意識上的群體認同,即時時「昭示了文化形態和社會意義的重建和維持、修復和協調心理和現實之間的斷裂、個人和群體的脫節、過去和現在的隔膜.
」(頁131)正是這樣的關懷,《歷》強調在文化生產中,以上的有關歷史的問題會從各個角落呈現出來,恰是「這些問題的持續性和堅韌性,對全球化歷史終結論提出了挑戰.
」(頁137)三在我的讀解裏,《歷》前三章已經將思想體系作了圓滿的表達,這是全書的重頭,占一半篇幅;而後五章屬於思考的第二部分,為實證分析,從電影到小說,各類文藝形式中去把握歷史氣韻的生生息息.
坦率地說,如果這後面五章可以以實證來環環相扣前三章的理論鋪墊,那將是一個輝煌.
因此,雖這五章皆可單篇成文,我卻願意將其統歸於一節來論.
首先,承接上文,《歷》將歷史敘述理解在了「語言」點上,即「歷史敘述可以說是個語言的問題」,而語言一方面在前現代意識裏是一個「存在」問題,卻在後現代意識裏又成為了「牢籠」問題;應該這樣說只有在前現代的意識裏才會有《歷》引據的盧卡契的《小說理論》中的觀點:「把小說看成是經歷現代性的人眾在喪失家園後,尋找精神家園的努力.
」坦率地說,在這個前現代意識裏,中國的現代敘事並沒有、或者說還沒有來得及產生史詩般的巨著,就被洪洪潮流傾臨淹沒,於是,到《歷》聚焦的後五章,面對的是經過劫難後的中國當代敘事.
一如上文所引《歷》對創傷的理解,放於中國苦難後的當代心靈上,那是「個人和文化的象徵表意體系」被嚴重摧毀、人徹底地無所歸依的流浪狀態,在這樣的狀態裏,有《歷》在第三章提及的、也是歷來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裏慣常的對尋根派的說法,即渴望尋找文化的淵脈;但是我認為,只要切入中國尋根文學的細部,無論是情節意識還是語言句式,那要尋的「根」有很大一部分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被革命突然中斷的現代意識,敘述要表的恰是盧卡契之論.
只是對中國八十年代以後的派別思潮,我們難以深入貫之,似乎中國在現代這個意識裏從來都處於狂燥中,跟隨潮流而唯恐不及,如一位批評家所言,趕得連撒泡尿的功夫都沒有,難怪評論者面對如此的研究物件,最好的方式也就只有將其泛而論之.
在此我想指出的是,中國的當代敘述就這樣在眨眼功夫中就經歷了從「存在」入「牢籠」的飛躍.
在《歷》無論是針對小說還是電影的敘述模式分析,基本面對的是牢籠中的舞蹈.
其次,或者說更進一步值得探討的是環繞「現代」這個概念的論說.
如果按理論家的言說「現代」是不同視角下的語言表述,那麼現代敘述裏,我們同樣可以獲得許多經典文本範式,許多是表達工業文明之後的異化.
在《歷》著中幾乎很謹慎地涉及這類世界文學中的敘述,僅以例證的方式涉及到卡夫卡、普魯斯特等,而且在分析中國現代敘事裏,使用了本雅明「現代無小說」之論.
倘若將「現代」只作為一個時間概念,那麼在迴圈歷史觀的看法裏,直線的時間概念當然就淪為了「空洞」.
其實,《歷》在第三章已隱含的提出了「時間對人的意義」這樣的問題.
在本雅明的視域裏,「現代」或者說這個區域的「時間」是放於「機械複製」的無聊感受中的,可以說是在這樣的感受裏,人走向了平面,沒有了情節跌宕起伏的故事,都是複製的平板一塊.
因此,本氏對現代小說的批評不是整體或者價值判斷,而是感受表達.
這個表達裏確實容透了創傷,有語言在創傷後的乏味,也就是「空洞」;也有人對「時間」感覺上的創傷;甚至可以說是本雅明的浪漫思想根基遭受到現代而產生的「震驚」創傷.
從本氏的「對卡夫卡的反省」論文來看,對「文學作為社會生活的反應」傳統,本雅明有其個人的沉思,特別是遭遇到他那麼不喜歡卻又無處可避的現代情境時,文學該如何表達現實生活真實地反應這無聊的「機械複製」似的城市居住於是他認為卡夫卡簡直就是在為這無聊的真實獻祭,而得到的是一種失敗性毀滅感.
這裏本文當指出的是,在這個時候本雅明的閱讀裏,卡夫卡語言表達屬於卡式個人的,本雅明幾乎完全否決這只凝聽「有病傳統」的卡式文風可以引證現代語言寫作.
但是今日在我們的閱讀語境裏,卡夫卡的孤獨不只屬於他個人還屬於整個現代文學,於是更有意義的反思本氏之言當放於現實主義的浪漫質數分析點上去考慮.
沒有原于生活而高於生活,還程度上破壞了文學的「寓言」品格,是本氏不能容忍的.
5正如《歷》所言:「受創的時間感覺,已經不再包裹宗教、象徵、禮儀的呵護媒介,這些媒介再傳統、前現代的文化中賦予時間以品質、價值、意義、魅力和規範,保證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周而復始、有變化又有前後聯屬.
在現代生產和生活中,時間被分裂為七零八落的單子···這個工具性的、分秒都要『有用』的時間又伴隨著空洞化、平面化、虛幻化的時間萎縮,剝奪了時間原來積累的意義···淪為百無聊賴、無所事事的沉悶,如同嘀嘀答嗒的機械鐘擺.
」應該說,在這一點上《歷》很好地把握到了本氏那敏感的波特賴爾式的「憂鬱無聊」之感受,但是當將這份引言性感受運用到中國現當代敘述裏,王斑遭遇到了困難.
中國人對時間的傷害,可以說還沒有來得及感受,中國敘述裏的時間呆滯基本給了鄉村,中國的城市從來是五光十色.
這樣的置換語境而產生的困難在「生活經驗著歷史」論述裏同樣出現了.
王斑當是非常心儀海勒的「人生中最幸運的神賜」:「兩個人,也許更多,但不是大眾,共同生活在一起,共有經驗,共同回憶書寫他們的過去,彼此毫無隱瞞,因而過去的經驗完好無損的保留下來,這時,就產生了生活經驗著的歷史.
他們並不覺的缺少時間,並不覺得時間過得太快或太慢.
他們不抱怨,甚麼事發生為時過早或過晚.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不覺得時間的流逝,不知老之將至,因為他們的生活就是經驗著的歷史.
」(頁181)王斑即使在否論這段話的貴族氣的同時找了一個很好的理由是「海勒的說法有『應然』的意義」,於是「預設了記憶和歷史,個體生命時間與歷史之間理想的、正常的關係.
」其實海勒這純粹到剔透的「經驗著的歷史」是需要充足條件的,不只是逃開了時間剝蝕,其避開了所有關於目的性的話語,更不要說是現實苦難了.
海勒是中國傳統文人的高山仰止之境.
而這對於在納粹迫害下落荒而逃、卻又無處可逃的本雅明是天上、地下;而對於苦難的中國當代史,那更是不可企及.
因此,我願意說將本氏運用于中國現代敘述分析是非常機敏的,而且《歷》在某種程度上運用的非常恰當,那就是,本氏對機械文明給生命帶來的「震驚」王斑將其運用於對殘害和苦難的不可想像之震驚.
從魯迅的視角到當代浩劫的苦難,「震驚」,這在本氏筆下閃光燈劃破死寂的剎那,人在那霎那打破呆滯的驚恐,在中國現當代歷史敘述裏,在遭遇的不是閃光燈而是血淋淋的苦難前,產生的是一個浩然民族靈魂的驚怵,只有這樣的驚怵,才實實在在夠得上前面的修飾定語「震撼」.
於是《歷》著有了其對中國現代歷史敘述的重頭分析,即有關創傷的記憶,以及對這記憶表述的歷史.
在歷史與記憶的張力空間施展開論述.
在此《歷》涉足多重敘述模式,概括地講最基本的模式是相對官方宏大敘述的帶有個體性質的書寫,其中有見證品格的口述、回憶錄、傳記、以及電影紀實;亦有如《歷》引孟悅所指的在宏大敘述退場之初出現的似烏托邦般的拯救模式;再到時代進入80年代中後期直至90年代的消費場景的散文敘述等等,本文欲有意避開這樣的敘述形態梳理,而想指出無論哪種敘述模式,在功能上其實有相通之處.
正如《歷》所指,中國80年代前的歷史書寫「往往是根據絕對的政治標準,主觀臆斷地『挖掘』過去的某些事件和事實,尋找提供現實政治合法性的前因和後續」(頁137)在此我欲補充的是,不只是當代史沒有做到「以科學的、實證的、批評的要求,對歷史的遺跡和事實進行探究.
」(頁137)就是古代史亦難以做到.
任何一個朝代在修其官方史時,所謂的古為今用就是為現實政治服務.
所謂史家的理想狀態的修史,最好是修古史,就像《歷》常引的本雅明之言「講古」,更是證古,不帶現實政治的功利目的,而完全本著精密考證.
這種對於歷史的態度是職業性的,在品格上有著高尚的職業道義追求.
我願意這樣的理解那多重的敘述模式,也就是說在我,歷史是史家之業,群體與個體皆是這職業的研究物件;而對於運用者來說,好的狀態是借古喻今;壞的狀態是假虎為猖.
《歷》在分析敘述話語時存在因「震驚」下的創傷帶出的困難,認為創傷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文化意義系統的建構,於是費了好大的勁去剝析個體與群體間的離間,當然這也因了建立群體與個體的聯繫本來就可能是《歷》作者最想強調的追求.
在此我想說的是,不是個體與群體間的離間,而是史家與物件的離間,強調記憶苦難是為了災難不再重演的目的,是史家之責,不讓創傷性情緒影響了實證是職業本身就當有的要求;而對於經歷苦難的物件來說,記憶只會重複傷痛,不會有更好的意義.
沒有任何一種東西可以真正補償得了真實經受的苦難,咀嚼只會雪上加霜、傷口摸鹽;更坦白一點說是,將創傷當成敘述的,可以建立起敘述話語的,其實並沒有真正經歷徹骨的戕害.
以「震驚」概念來形容,真實遭遇「震驚」的是千奇百怪、也許醜陋百出的那剎那間的畫面,只有職業眼光下的這些畫面才有可能產生「震驚的審美策略」(頁284).
也就是說遭遇「震驚」的個體其實亦很難真正見證得了那個剎那,就像古人言無法踏入同一條河流一樣,在本質意義上是不存在純粹見證的.
史學,與其說是真實的記載,不如說是客觀的闡釋;或者說記載與闡釋相輔相成.
而「穿透」表面,投身於「未經雕飾、意義不確定、矛盾重重的歷史現實」、甚至「憂鬱的、意義晦暗的深淵」(頁284),以「爆破」的可能來深入「歷史事物的內核」(頁285),更當是優秀史家之志.
本文在前面分析《歷》將歷史話語與審美活動結合中提到,王斑非常強調以文化視覺體驗來書寫歷史,並認同此「屬於歷史話語的內在機制」.
當《歷》在中國現當代史話語裏體會出遭遇苦難之「震驚」時,必然促使讀者深思本文亦在前面指出的中國現代漢語詞典中的「國家」之定義,也就是說怎樣才能清楚厘析「暴力工具」它直接牽涉到的是「民族國家」話語的另一面,除維護主權之外的功能,在主權建立後的語境裏,國家以及在這個建制之下的工具性結構,特別是在國民面前,其職能是甚麼是對這職能的迷惑,中國當代製造了那麼多慘絕人寰的悲劇,迫使人不得不喪失這「國家」語彙裏本應有的文化情感的依託;而本為「公僕」性服務職能的工具角色卻成了暴力的蠻橫.
在此,《歷》對歷史敘述模式的分析裏,採取文本精讀的方式,來透析「文化視覺體驗」的書寫.
最打動人的當是作者選取的《籃風箏》.
一如本文上段所指,歷史事件的真實有其模糊或者說難以呈現之品格,王斑首先讀解的是《籃》的片頭:「幹井」的意象:「似乎生命的源泉幹凅了.
這些不詳的意象突出了回憶過去的困境和迷茫,意味著過去的輪廓不清.
」(頁169)正是這困惑不解的視覺體驗,一次次發生在「震驚」的遭遇中.
而這遭遇卻是「災難和運動紛至遝來的世界裏,日常起居表達了在動亂之中尋求一方立足之處、棲身之所.
這是在讓人旋昏,使人失明的政治大潮中能有安穩的生存.
但恰恰是這個謙卑的願望日常生活則是這願望的載體在歷史的動盪中一再被擊破,瓦解,粉碎.
」(頁171)於是從「普通百姓在危機四伏的歷史現實中難以逆料的命運」中析出「故事中人物面臨的是一種無法理解、冥冥之中的勢力,似乎不停地與每一個人的正常生活作對,週期性的造成痛苦和死亡.
現實似乎是個謎.
歷史的密碼難以解破,歷史的意義無從把握.
」(頁172)而這荒誕的歷史卻又是那樣真實地戕害著每個中國人.
在王斑直面這樣的苦難是為了尋求「絕望中的希望」,可是,在對《籃》的讀解裏,《歷》這樣動情地描述到:「在突如其來的結局中,鐵頭仰臥在地上,渾身上下傷痕累累,凝神盯著樹梢上瑟索顫抖著的破風箏.
」(頁175)這樣風中的顫抖作為一個民族在絕望裏的希望是不是太悽楚了而正是這樣的悽楚,王斑「爆破」出:「這個死寂的時刻,並沒有一個經由錯誤到正確的價值時序來定位,並沒有一個目的性的未來讓人有所展望.
時間的流動嘎然而止,封凍在一個寂靜的時刻,充斥著無以名狀的震驚創傷,與其他時刻的聯繫崩裂.
」(頁175)王斑給予了這樣的歷史敘述高度評價,認為是在當代史裏「不可多得的記憶方式」(頁176).
這裏王斑是以動人的情、那心靈生髮的「氣息」來觸碰歷史的傷痛,於是群體與個體的離間之辯似乎暫且擱置,但事實上,那個傷痕累累迷茫於樹上風中殘破風箏的意像正是當代中華民族的整體在暴力下的希冀之意象,這個意象不只是那個過去了的歷史時代,而且是當下、甚至將來的多少年之後,仍然難以泯滅的創痛.
因此我曾想問,甚麼時候中國人也會有那樣一個條件來「生活經驗著歷史」幾百年幾千年之後會不會到那時會有海勒所言的純然當然,正如本文開篇所指,《歷》即使透出憂鬱,但也同樣不失欲求陽光燦爛.
在對王安憶作品的細讀裏引述:「還是唯心主義好,唯心主義慰人心,讓人走到哪一步,心裏都存個念想.
」(頁201)如果將作者與《歷》文本以及其研究的物件、再加上《歷》整部著作思考和闡述的方式,作為交互現象來讀解,我幾乎可以這樣假設,在文化象徵的活動裏,「群體記憶」、「傳統情系」其實就是一個象徵性「念想」,儘管這個「念想」在《天仙配》的讀解裏,很有可能像那個本是「村裏人共有的女兒,是人們在無可信賴、孤獨無助之時互相依賴、互相依偎和信賴的象徵」一般在「穿越時間的神話和記憶剎那」(頁200)被驟然滑落,但是《歷》的氣質當是會拒絕那個逝去許多年許多年的女兵的老去,完全拒絕某種「經久不衰的象徵意義」被剝奪的.
正是這樣一個拒絕姿態,使得《歷》的論述始終洋溢著一種激情.
本文開篇曾指出,《歷》涉足的是一個理論繁複、且強調理論與實踐結合、卻又在實踐中遭遇全球性失敗的這樣一個現實性課題,這對於史識與膽氣都是一個考量.
中國現當代歷程是一個以特殊和差異來實現或者說突破現代資本理論的另外一枝,卻又是以成千上億人的血淚和苦痛為代價最後不得不皈依滾滾資本洪流的實例,僅僅記載苦難是不夠的,只張揚差異、一葉蔽目地將血流成河高贊為不同於繁花似錦,就更不足取;像德國面對奧斯威辛,沉痛記載,深刻反思;敢於直面所有的苦痛,亦敢於拷問這歷史進程中的任何災難性錯誤,作史為後人.
但是,當不只是意識和形態上,思維方式、敘述語言,乃至純粹的語詞、語彙,都遍佈了歷史的傷痕時,以及在創痛裏以豁出去的姿態逃亡般墜進資本的洪流滾滾後,史的工程可謂難夷.
可以說《歷》欲極盡努力,在後五章的後半部,幾乎穿越了中國進入90年代後資本時代的文學敘述,面對一個商品意識膨脹到瘋狂的語境,《歷》作者似乎很想但是卻無法像讀者掩飾那樣一種其實是費很大力氣來說服自己的平常心態面對史詩消逝的時代事實.
在第六章,也用紀德波(GuyDebord)的話來作引言:「當新近獨立的藝術以鮮豔的色彩描繪它的世界時,生活的一個關鍵時刻就已經老化.
藝術的鮮豔色彩不能使生活恢復活力,只能使之呈現于心靈.
暮色籠罩生活之時,便是藝術茂盛魁偉之日.
」(頁203)但是,儘管對散文化的敘述方式《歷》沒有褒貶,但是整個《叔叔的故事》讀解下來,似乎並沒有在叔叔故事的「鮮豔」發展裏更好地尋到「心靈」;而是那「文化形式」卻成了一個與歷史相逐的「角鬥場」.
在我的理解裏,這「角鬥」與其說是那「叔叔」故事的,不如說是《歷》思想基調的旋律與中國當下時代的較逐,這個較逐其實不只在王斑,幾乎可以說是被劃為自由派對面的新左的同一基調.
較逐的結果是,《歷》引朱天文的話:「將以嗅覺和顏色的記憶存活,從這裏並予之重建.
」(頁223)這是第七章的引言,而整章意在如何將人與物的認知關係導向「化商品的腐朽為神奇」.
這神奇之後亦是《歷》駐筆之處,那是「愛在燈火闌珊處」.
全書最後重新回到本雅明的論述:「都市詩人的快樂是愛,但不是一見鍾情,而是燈火闌珊處的愛,這最後一瞥的永訣在詩章裏與神奇的時刻相融合.
」(頁243)穿透表層的面紗,深入歷史事物的內核,「爆破」出那神奇至永訣的「一瞥」,可謂是《歷》的追求.
本文就此打住,無論是本文視域裏的《歷》還是本文自身,更願意放於邏輯層面,即研究物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某個抽象結構的可能效應,是為這樣一個抽象意義上的思維結構而產生出的理解性分析.
最後還要說的是,認同《歷》緒言中劉再複之言,這是一本讓人讀了就難以釋手的書,能帶給你許多思考,為這份啟發,我深懷感激.
忙於稻糧的斷續為文月餘,初稿完於2005年12月29日臨晨波士頓森林谷陋室註釋1FredricJameson,1934-《馬克思主義和歷史主義》,見其論文集《理論中的意識形態》2《現代漢語詞典》第424頁,商務印書館19923Country:anindefiniteusu.
Extendedexpanseofland;region;residenceorcitizenship;relatingto;orcharacteristicofthecountry;apoliticalstateornationoritsterritory.
MerriamWebster"sCollegiateDictionaryp286,Merriam-Webster,Incorporated2004.
4巴舍芬《母權》,第103頁,法蘭克福,1975.
5WalterBenjamin「SomeReflectionsonKafka」,Illuminations,p141-145,EnglishtranslationCopyright1968byHarcourtBraceJovanovich,Inc.
《二十一世紀》(http://www.
cuhk.
edu.
hk/ics/21c)《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五十期2006年5月30日香港中文大學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五十期(2006年5月30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
纏綿裏不乏憂鬱,憂鬱裏更顯執著.
將一部理論著作用纏綿喻之,似乎有不妥之嫌.
但是,我卻認為找不到更好的詞來表達一個對當代歷史、特別是立足中國當代歷史的學人之筆,這思考、這努力.
當代歷史不僅與現代歷程相系,而且無法避開一種以指導實踐為旨規的理論、或者可以直接指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可這理論又以社會主義國家實踐的徹底失敗變得使闡釋極為困難.
而立足於中國當代更是難中之最.
因為在當代,中國人的記憶裏有那麼多被自己國民信任的政府強迫的傷害,這歷史的創傷、那靈魂的疼痛是可以讓幾代人驚搐的.
可作者卻要以自己的理論素養立足中國與世界對話,帶著一個理想主義的無畏和樂觀,企圖找到縫合歷史與記憶的曲徑.
也許作者難以苟同,但卻是我閱讀的感受,以作者自己對王安憶《紀實與虛構》的評述來概之:「這個歷史其實是傳奇和神話,敘述者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因而作品的基調是憂鬱哀傷的.
」但是王斑的筆有一種憂鬱般的沉重卻不哀傷,是如中提琴般的厚重,但不乏昂揚;這是因為,批判現代的立場始終立於對「幻想」的堅持,而我開篇定論取此二字亦是來自文本自身的理論引用(見頁177),其是指史詩的魅力與詩意.
《歷史與記憶》(下簡稱《歷》)似乎是由九篇可以獨立的單篇論文構成,由一線貫之凝成專著,即為作者在導言中指明的:「本雅明歷史批判的啟示是,必須發掘現代性進程中另類的蹊徑、層次與想像,質疑中國現代性歷史的程式化敘述.
」本雅明猶如智慧的精靈閃爍於整部著作中,每一篇、每一章以警句般的形式亮出作者對中國現當代歷史敘述的思考.
一《歷》的思考方式屬對話、探討、或者說辯論型,有一個先在的話語場,作者對這樣的場境發出探討,以理說之.
作者首先強調的是「歷史並沒有終結」(頁8),這是對「歷史終結論」的回駁,而且作者要強調的還有這歷史意識和觀念不僅僅是古代型的「寫作或關於過去的文字記載」(頁26)而是現代型的「既是一種寫作方式又是人們的社會行動,既是一種敘述的表達,又是重構社會秩序、理性自覺的世俗實踐.
」(頁26)作者更進一步地以梁啟超之言來明確古代歷史觀與現代之不同:「現代歷史是由某種目標所推動,而過去的歷史只是記錄.
」(頁27)其實作者要堅持的仍然是「民族-國家」歷史的建構.
因此,作者認為:「歷史的眼光不僅前無古人,更是創造來者,展望未來.
」(頁26)於是,作為閱讀,就必然需要對這樣的語境對話做些辨析.
以「歷史意識」對話與「普遍主義」對話場域裏,「普遍主義」認為:在世界真正的大問題都解決了之後,構成歷史的最基本原則和制度可能不再進步了,因為在「自由民主」的樂土裏,以現代自然科學為代表的歷史機制、以及闡釋都趨於雷同.
所以歷史走向終結.
多半針對此論,反駁者堅持「大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比如「九一一」,比如伊斯蘭等宗教紛爭問題.
對此,「終結論」始作俑者福山區分為兩點憂慮:一為經濟發展的失敗,如中東;二為東亞的經濟成功與傳統的家長專制的結合.
但是,福山在闡釋特別是第二點憂慮時並沒有很好地深入東亞的傳統文化機制,其例舉的集體意識、集團意識,個人對多數人的認同的非理性的順從和依附,是不符合其欲批判的東亞儒家意識的,因為儒家意識並不在於「多數」,多數有可能產生的暴政恰來自反思民主機制存在的負面因素.
而儒家服從和依附的是一個建制,其在東亞傳統文化裏千年來以「禮」單字概之,在「禮」之下沒有多數投票之說,其「群體」意識在於對這個建制裏的人人都有益,屬於理念品格而不是現實的人多勢眾、投票表決.
人確實在禮的建制裏上至周公下至百姓皆為工具,以現代理念審之,其削弱個人性;但這個「禮」本身是滿懷抱負的,其構建的層層等級更是將這抱負散散於各極,事實上最大的挑戰正是有可能阻止平等意識裏「沒有理想、沒有抱負」、平面的「最後的人」的出現.
也就是說福山憂慮的挑戰絕對不來自於習慣的「東亞封閉的傳統意識」,而是東亞的現代歷史進程裏,不會全盤否論西方的引借,但是也不會完全歸功於西方文化的引借,而是傳統的現代轉化,借用後殖民理論的概念是「交互與雜糅」,這可能是歷史機制闡釋的別樣性.
王斑的《歷》屬於上述對話場域裏的討論之一種,只是作者採取的立場是屬文學性的隱而不露、卻又處處針對的方式來進行表達.
首先,作者表明自己傾向「歷史的意識」有別於相對論的「歷史性的意識」,作者借用美國歷史哲學家羅斯的分辨,前者是「有能動性,希望發現過去的發展能賦予今天以意義,為現今指出方向.
」於是,顯現歷史延續性的必要,而且使某種歷史敘述合法化.
按傑姆遜所說:歷史自身不是一種文本,除非它以文本形式或敘事形式出現,否則,我們便無法接近它.
1《歷》恰是將中國現代歷程作為多個文本現象,而且採取不同文體的分段闡釋來接近歷史.
第一章作者從《魯迅的批判歷史意識》入手.
切入的是中國現代歷程的初始形態(當然中國的現代歷程具體時刻當然可以推向現代之先的近代),也就是說民族國家話語建構的最初狀態.
中國的現代民族國家意識的產生確實伴隨著西方的煙槍大炮,且是一個民族最脆弱急需現代科技給予新活力的時刻,也確實在魯迅那一代產生對中國傳統最嚴厲的批判形態,但是,若以「歷史終結」論者的極端西方中心論的對話語境為前提,來「再現」中國現代民族國家最初的歷史情景,就自然有了王斑如此篇的闡釋了.
作者明示,此篇希望勾勒出一種朦朧中的「批評的歷史意識」軌跡,其「試圖從兩個途徑來討論.
一是簡要地評論法國哲學家福柯的系譜學歷史視點在中國語境的作用,分析其對中國現代文化批評的適用性和局限性.
二是分析魯迅對於西方現代性的反省和批評.
」(頁18)首先來看其第一條途徑分析.
其中隱含了後現代思潮對啟蒙話語的質疑語境,從福柯的譜系分析法入手是相對啟蒙的宏大歷史話語有可能掩蓋或者「霸權」了其他邊緣的、歷史橫斷面間如民間、社群等敘述,《歷》著重的是將歷史返回到當時民族危機的情境中來探討.
對此,本文不予重敘.
我更有興趣的是因了當下思潮碰撞而凝成的辨析,這可以引出兩個思考點,一為,啟蒙與西方話語.
相對「歷史終結」論的「西化論」,中國現代的啟蒙是否屬於全盤西化.
同樣以福柯對康得的「啟蒙是甚麼」的閱讀來理解,啟蒙是人類能夠成熟地、且有勇氣地運用自己理性,可以成為自己理性的主人,於是,其可以對歷史與現實批判性反思.
這恰是魯迅一代致力的追求,也是中國現代民族國家話語的核心組成部分.
那麼,是否可以指認為「全盤西化」我認為,「全盤西化」是一個結論性語彙,也就是說它是針對事實的結果,即福山在「歷史的終結」篇中所言,是從技術到管理經驗、乃至政治制度都全搬西方.
而對於中國民族國家話語中的啟蒙,始終沒有一個結果性事實可以論證其全搬了西方;儘管魯迅一代曾有口號要以西方為樣,那卻是個個飽讀經書之士針對中國行進艱難的事實提出的權宜之際(即欲開窗必先拆屋之說).
中國的現代歷程飽經變換與滄桑,不是甚麼模式說照搬就可以搬過來了的.
以政治制度來說,從皇勸進入現代,幾多變換,在我看來,這恰是由傳統進入現代的必經過程,而中國的現代行進狀態只是與世界他方同步而已.
而王斑在這部分思考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在危機中產生的歷史敘述,是否憑某種延綿不斷的邏輯導致了中國現代革命進程中後來的災難、暴力和政治的浩劫」倘若我換一種問法:即中國啟蒙試圖成熟而有勇氣地運用自己理性的結果是否是造成後來中國當代史中出現的災難緣由回答自然是「否」!
當然有學人認為中國的啟蒙承繼的是法國大革命的一脈,若按這樣的思路繼續下去,很容易跌進有關啟蒙論述以及圍繞此話題的闡釋爭執;為了避開如此的危險,本文欲始終立足於康得關於啟蒙的解釋,故在此將中國現代進入革命進程的話題暫且懸置,而在後文的分析裏,或許此點亦是《歷》文旨中欲發掘現代性進程中另類的蹊徑、層次與想像的一個思路(見上文).
也就是說,中國的現代進程中無論是理念還是實踐,都不是一個恒數,而是充滿了變數,所以多析少結視為策略.
即使是常被指責和貶斥的中國現代語言,儘管與古漢語相差甚遠,但若說其只是模仿之作亦是淺薄和無知的.
中國現代漢語的誕生,恰是為我手能更易更便的寫我口,是為了更好的「公共的」運用自己理性的結果.
第二個思考點是《歷》著膽大欲為的,即強調「歷史意識」的能動性,僅僅「承認歷史書寫有賴於對未來的憧憬和希望」還是不夠的,以甚麼樣的方式達求此境這事實上是對王斑第一條路徑的後半部進行剖析,分析系譜學在中國現代文化批評中的局限性之後的可能性意義.
《歷》著在此切入了一個爭議性話題「進化論」,面對四面討伐進化論的後現代語境,作者似乎欲從中國歷史語義中辟出蹊徑.
其首先聚焦的是嚴複進化論思想中的「意志論」,指出嚴複對進化論的態度是「應然性的」,重其主觀能動潛力.
並以Schwartz的論點來概括嚴氏的進化論歷史觀是:「在非人類的自然和人類社會上,對浮士德和普羅米休士的動力和強力的提升和張揚.
」(頁29)「應然性」是指一種客觀性,這是馬克思理論中常強調的「客觀規律」.
王斑在此著重這點,不只是清晰他的論述立場(因為他的立場在通本書裏處處可顯),還投射出了一個古老的民族在遭遇現代時的切身處境.
「進化」,是歷史的嚮往,如《歷》著所言:「蘊含了民族國家,尤其是殖民地國家,在相對平等的基礎上對公正、自由的社會形態包括平等的國際社會關係的想往和呼籲.
」(頁30)本文既認同此論點與分析,但同時又必須坦言,《歷》作者在進入「進化歷史觀」的論述時幾乎有一種難以掩飾的兩難,一方面,進化話語裏包含著一種普適性的價值理念,可是由於作者的立場卻是絕對不可以站錯了方向,於是,另一方面,要時刻不忘記與普遍主義的針鋒相對.
因此作者反復強調這「普遍原則」一定要建立在自主的權力上方能行得通.
其實,以西方中心論為核心的普遍主義,儘管使用的策略性話語是普世性的價值理念,否決西方中心論者並不一定必須倒洗澡水連孩子一起倒掉,也就是說,沒有甚麼理由可以拒絕承認人性中存在一種普適的東西,就是中國傳統思想裏亦有「老吾我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生死愛恨,就像進化論中的自由、民主、科技、平等一樣是不當分西方與東方的,說得再淺顯一點,就好比人之為食,不當分男女.
儘管王斑是為中國歷史話語中的「普遍原則」以還原歷史情境的方式找一個合法性,我卻認為,其本身就是天經地義.
就像科技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在遭遇現代時可以拒絕一樣.
我倒是更願意以同樣還原歷史情境的方式去體味當時遭受重創後不幸淪為「東亞病夫」的中華民族在遭遇現代科技時,是如何提升和張揚「浮士德和普羅米修士式的動力和強力.
」我願意將已經成為兩個意象符號的人名順序顛倒來釋意,普氏顯示的正是人之主體性的張揚,似乎其他萬物在發現創造之後都可以為己所有的工具.
這幾乎可以作為人類遭遇科技之初的欣喜形態之象徵;而浮氏是人之主體發展的另一個階段,人在自己的創造物前跌入了前所未有的震驚,而由這震驚帶來諸多癲狂.
《歷》亦每每引用本雅明的「視覺震驚」論來闡釋同此理.
但在此處於浮士德,不僅是視覺震驚,而是人作為主體創造歷史的有本質意味的震驚;特別在隱寓中國人遭遇現代化,真是妙筆神功.
從古人對地球儀的執迷到不幸因了他方的大炮被迫轟開國門,中華民族似乎從創造走向昏睡然後在挨打的狀態之下驟然驚醒,世界於是景象萬千、百般好奇.
浮士德的追求、甚至抗爭,更像是今人看古人,是王斑在看自己現代的先驅,他們的赤誠與執著.
因此,王斑的第一條路徑事實上是第二條路徑分析的鋪墊,作者的努力在於為中國現代歷史正名.
《歷》著第一章核心是以魯迅為分析點來討論「批判歷史意識」.
前面本文已經談到《歷》作者崇尚現代歷史意識,即「理性分析的知識形態」(27),並且還具有意識的能動效應.
這裏再次回到康得的「啟蒙」,在康得的思想裏,上帝的世界和人的世界界限非常清晰,甚至可以說「現代」恰來自于這樣的明晰分辨,是在這樣的分辨中人才真正認識了自己.
所以,康得的人之主體來自的卻是人對世界的認識方式的「有限」,將無限的超越給上帝,在「有限」的層面裏,人才可能成為能動的主體.
事實上這裏提出的現代意識是關於「知識」的話語,當人的知識不完全是上帝的統領時,(否決讓你不吃蘋果就不吃蘋果),人的世界才誕生了.
而因了人的認識的「有限」性,以及對這樣的「有限」無窮盡的突破可能,人才有了主體意識.
因此,關於現代的討論,其實是關於「知識」話語的討論.
本文是在這樣的理解前提下來讀解王斑的現代歷史意識.
為甚麼「流水帳」式的歷史,就不符合作者的現代歷史意識標準因為沒有知識的篩選,也就是他強調的「理性分析」.
在我,福柯並沒有走向康得的反面,而是康氏的繼續,福氏質疑的恰是這樣的知識篩選有可能造成的遺失,於是引出知識背後的權力話語.
《歷》著要堅持的恰是本著知識對材料的篩選,於是就必然碰到中國現代性繞不開的話題:古今中西.
首先,《歷》著要處理的是,為甚麼魯迅一代中國知識份子要選取西方知識,而棄絕中國傳統知識,這背後是不是隱含了「霸權」話語以魯迅為範例,是在甚麼樣的語境、以甚麼樣的立場、取如何的方式、欲求得甚麼樣的結果來擇取王斑使用了「批判」,這個詞在《歷》著的論述裏,蘊育空間非常大,可謂是恩愛情仇.
當我們把討論放於「知識」的建構與闡釋範圍來討論,言說者的立場、方法、情境都將是影響視角與視域的因素,擇取甚麼材料、如何論述等等都將左右言說.
《歷》著對於魯迅的歷史觀分析基本由3點論之:其一意欲駁斥直線歷史,採取的是中西相較立場.
首先,也許王斑自己並沒有主觀意識到,但讀者卻可以從曲中領悟到他困苦於自己的立場鮮明.
上文指出過,《歷》著要強調的是進化歷史觀,那麼中國在進入現代、也是融進西方知識的過程中,如何來厘析如此的對民族感情不無傷害的「進化」王斑的方式是一方面繼續前文的「國破家亡」的歷史語境,一為強調「進化歷史觀」是「尋求從衰敗的傳統向現代的、更自由的社會過渡的諸多可能性」,目的是「喚醒歷史意識」,將「進化的想像轉變成實實在在的社會活動和知識的生產」(頁31).
另一方面,在行文層次上屬於遞進性質,即為處理這「知識生產」的中西關係,欲以歷史的迴圈多樣乃至交互雜糅的形態來析魯迅之言.
在此其選取的是魯迅全集第一卷的論說文《文化偏至論》(以下簡稱《文》).
大概研究魯迅的學人基本可達共識的是,魯迅特別是他的論證文基本有「明確的論辯物件」(《歷》亦認此點頁41),但是《歷》認為魯迅論辯「目的是駁斥盛行的全盤西化論」.
這個結論於繁複的魯迅在繁複的中國現代之初的歷史時空,未免過於簡單化.
(本文由於一時苦於溯源到原始資料,無法得出魯迅此文論辯的具體物件是何許人或群體,但基本可以與《歷》著有個商榷.
)在《文》篇的開首,魯迅其實就交待了自己的言說物件,是那些「稍稍耳新學之語,則亦引以為愧」者,這裏既包含了魯迅自己,亦包含了你我(《歷》與本文作者),是針對所有在知識面前的尊嚴之較逐的勸誡;因此,魯迅首先警示:「中國既以自尊大昭聞天下,善詆諆者,或謂之頑固;且將抱守殘闕,以底於滅亡.
」於你我不同的是,在魯迅的歷史時空,警惕自我的弱點,而這個弱點當時被認為是消損一個民族力量的,所以就更加危險.
在魯迅的論述裏有多重意義,其一是不能再「抱殘守闕」,即使是思古堯舜文明,亦要清楚吾文明有幾多創傷;其二是吸收或者批駁西方知識,亦要有歷史學養,故《文》篇的上半部在追溯西方史的發展,在這裏談到「復古」,但絕對不是複如中唐韓愈「古文運動」之中國儒家之古,而是指古希臘羅馬之古.
在現代,古希臘羅馬文明對我學人初入西方知識時有一種無尚的魅力,這樣的對此魅力的素養我願意理解是如同吾民族淵源的文明,是在這樣的文化基因的溝通層面,我們才有這樣欣賞的能力.
因此在這一層面,魯迅要警示的是在吸納西方知識時,我們要警防「偏執」:「根史實而見於西方者不得已;橫取而施之中國則非也.
借曰非乎請循其本.
」是在這樣的警示下,魯迅方開始論述「夫世紀之元···」.
魯迅亦欲通過引介西方歷史演變來防治「以轎往事而生偏至」,在他的論述裏是要我國人在知識的輸入中釐析「近世文明之偽與偏」.
其三,是為他自己以及如同他思想的現代中國知識份子強調的「西學」一辯,指出吾欲宣導的西學是何方知識,這就開始了《文》篇的下半部「十九世紀末思想之為變也」.
在魯迅十九世紀末的思想乃有古風夷.
為甚麼這麼說,《文》在此處開始論述個性的伸張,也就是說在魯迅,古希臘的人之精神嵌合進十九世紀末而生的人之主體思潮,這是國之欲強盛之根本.
因此,《文》的末篇定論於:「然歐美之強,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則根柢在人,而此特現象之末,本原深而難見,榮華昭而易識也.
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
假不如是,槁喪且不俟夫一世.
夫中國在昔,本尚物質而疾天才矣,先王之澤,日以殄絕,逮蒙外力,乃退然不可自存.
而輇才小慧之徒,則又號召張惶,重殺之以物質而囿之以多數,個人之性,剝奪無餘.
」在這篇文章裏,魯迅的結尾滿懷悲情,在他,以物質泯滅個性精神是禍國殃民的罪魁,可伸張獨立之精神在中國又何其難也.
魯迅的理想是建立人國,正如《歷》著所引,「明哲之士,必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校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施之國中,翕合無間.
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
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於天下,更何有於膚淺凡庸之事物哉」是從這裏王斑很好的以「歷史中間物」來概述魯迅一代的思想形態,它們是雜糅的,在雜糅中、在深沉的情感促動裏尋求更新與突破.
《歷》著在此的突破點是從人人轉為現代意識的「群體」,由「獨善」而尋求「兼濟」.
如何將中國傳統的個人與天下之論述契合進現代的主體意識話語中,當是《歷》闡釋魯迅《文》的獨特之處.
魯迅一代強調的是「張大個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義也」(《文》),《歷》闡釋的是「從我做起」(頁48)修身乃是為濟天下.
魯迅與王斑,這裏有一個物件與闡釋間的縫隙,在魯迅伸張個性的隱話語是對儒家的扼殺人之個性的負面進行批判,而王斑話語的背後突出的卻是儒家的正面、優秀體制的建構,是「禮」之大義.
縫合空隙,《歷》著使用的是另外兩點來闡釋魯迅的歷史意識:一為「文化記憶」,二為「希望與絕望」.
我將此二點放於一起分析,是因為在《歷》著中它們交互論述,而目的只為縫合.
王斑當是採用了康得的策略,將上帝的歸於上帝,人間的還回人間;不可知的屬形而上,我們只闡釋可以認識的.
於是,在對「文化記憶」的闡釋裏,魯迅的批判就可以順然劃為「創傷」,而在「創傷」後的絕望裏,總還是有希望.
應該說《歷》最打動我的是這種對希望的堅持精神.
回到此部分的開局,現代攜帶知識話語闖入,複雜紛繁.
《歷》在處理中國知識與西方知識,傳統知識與現代知識間,分析點設置在「記憶」,整部著作力求透析的是「記憶與歷史的互動張力.
」而記憶,自然有必要區分,而且記憶本身亦有選擇的品性.
在現代意識裏,文化記憶更是現代人以主體之身份來接觸過往的客體,有必然的時空優勢.
正如王斑在析魯迅,是在啟蒙話語反思的語境裏,因此,在同樣的「個人主體」這樣的問題上,王斑的闡釋裏就會融入多重分析元素.
上面我已經指出《歷》著獨到之處在於析魯迅「批判歷史意識」時,將中國傳統的個人與天下融于現代意識的主體性來分析.
在魯迅的《文》篇,「主體」還只是停留在「大人格」的伸張,而在反思啟蒙話語裏,這樣的主體伸張在遭遇工具理性的剝蝕時,困難重重,於是當代理論者開始注意主體中的「情感因素」,而在分析情感的倫理時,直接切入的是審美要素.
是在這樣的分析語境裏,王斑涉足的傳統中的個體話語,不是「修身」而是「獨善」,前者更多在「禮」的規範中,後者才有審美意向的馳騁.
而本來在傳統語義裏,是比較句式,「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是人生處境不同的態度;而王斑卻將這兩個句式落實到遞進關係,《歷》著中,「獨善」是為了「兼濟」,而這樣的遞進正好符合了魯迅的張個人之主體,乃創人國的遞進索求;而我讀者亦無以反駁由「獨善」趨於「兼濟」的不可以,因為「獨善」在本質意義上是「兼濟」的前提,而「兼濟」本來亦是「獨善」隱話語中的目的指向.
因此,《歷》著讀出「魯迅提出的理想個體近似泰勒所說的『表意個體』.
這樣的個體有理想的個性,他、她通過審美的手段書寫歷史.
」(頁51)此點應該是《歷》著通本的研究意旨.
於是在首先已鋪墊的「歷史中間物」的現代知識份子,在以審美情感為主導的敘述歷史裏,自然是無論「文化記憶」有何等創傷,仍然是能動向上,絕望中滿是希望的.
二要真正把握住《歷》著闡述的「歷史意識」是必然從其第一章跨越進第二章、第三章.
在本文的開篇亦指出,《歷》著的特性有一種纏綿於幻想、又不乏憂鬱之作;就好比本雅明之幽靈是怎樣悱惻綿綿於整個現代史的思考裏.
在上節分析的最後,本文遭遇到幾個問題而不得不暫停,而這些問題要得以深入也就必然進入接下的二、三兩章.
在較析魯迅的《文》與《歷》的闡釋時,涉足到人之「主體」,王斑以「進化」歷史史觀,將魯迅的「個人」放於「社會重構的想像」中.
在分析中,如同前述,王斑有一個隱在的卻無時不針鋒相對的討論物件,此處是自由主義理念中的現代公民社會等概念,於是王斑假借的是泰勒的「群體和個體」之分析,那麼給我閱讀者帶出來的問題是,中國如何從「天下」轉入進魯迅之言的「國」,此「國」與「國家」以及「民族國家」之間在概念上又有著怎樣的聯繫和區別而又怎樣從原文本魯迅的「國」進入闡釋者王斑的「群體」之分析其實這些問題的跳躍本身就囊括了現代歷程的階段性.
在魯迅年代,一如王斑使用的「歷史的中間物」,「國」與「天下」的關係在概念上並沒有明顯的分歧,而是在王斑所立當下語境裏,「國」更貼近了「民族國家」,而且這個現代意識而起的概念,在後現代的視域裏是一套寓言性的話語,在這樣的話語分析裏存有多重政治價值衝突,於是王斑使用了「群體」之概念.
將中國的現代國族理念放於因了殖民遭遇、民族存亡的危機而得以成就,《歷》著認同而且強調了這個關於中國民族國家話語建構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論述,同時王斑欲繞開的是「國家」語彙本身的強暴功能,因了這樣的功能帶出的災難,《歷》將其劃為現代創傷.
在中文現代漢語詞典裏,「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是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實行專政的暴力組織,主要由軍隊、員警、法庭、監獄等組成.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它隨著階級的產生而產生,也將隨著階級的消滅而自行消亡.
」2而英文的解釋義不只有其政治的暴力面,亦有公民身份的界定,3似乎英文的更接近「Nation-State」即「民族國家」之義.
當然因了一時沒有辦法得到最新中文漢語釋義,故並非要評價兩種語言釋義的差異,而是欲通過這樣的定義來揣摩《歷》著中欲避開的「國家」之政治暴力功能,而傾向于社會公民情感關係、民族文化認同等層面,於是而選用了「群體」之概念,而且把個體與其關係視為社會的有機情感組成;以這樣的構成來貼近攜帶沉沉文化情感的「歷史中間物」般的魯迅一代.
所以,王斑對魯迅個體意識的分析落實於「表意」.
由這個概念切入進能動的審美經驗分析.
一方面強調絕望裏的希望,另一方面透析悲劇裏的審美.
對於中國知識份子來說,進入現代有許多合謀行為,借用西方及建立民族國家等等皆是合謀來反傳統伸張個人主體,這是中國現代歷史進程的第一步,這一步裏有對故有文化情感的創傷亦有嚮往,這是《歷》著的第一章;而國家政權的建立伴隨而來的卻是政治機器對個體人性的瘋狂扼殺,由此帶來的災難和創傷就更大了;於是,《歷》著承接的後來許多章討論的都是創傷的歷史亦是一個存在,在這個存在裏如何建設性地去尋求其意義.
因此第二章就是一個過渡性章節,它承接第一章對魯迅話語的探討,而又要啟承以下諸章的中國當代創傷後的歷史敘述.
而第三章是全書思考與回應的結論,即歷史非但不可能、不願意終結,而且可以他樣的形式繼往開來.
這兩章當是最顯作者功力的章節,也是我最喜歡的兩章.
《歷》著最大的長處當是論述具有時空感,雖然沒有平板的累述歷史的演變,但思考跨度與深度無不囊括了現代意識的跌宕變遷.
《歷》著第一章在論述中國歷史遭遇現代間,首先讓梁啟超、魯迅一代執著的一是進化史觀、二是個人主體.
如何以能動的主體來展現史,是我對二、三章的讀解.
一如我開篇所指,本雅明的史觀猶如思考的引線,自始慣終.
首先,我要聚焦於《歷》第三章的篇引:「歷史中的所有陰差陽錯,所有的哀傷和失敗,都可以在人的臉相上,更準確地說,在一個骷髏上表達.
雖然骷髏之為物,毫無象徵性的表意自由,毫無古典的和諧得體,脫去一切的『人文』的修飾,但在其中,人受制於自然這一事實則表現到了極致.
」(頁107)前面本文提到康得的人對世界認知的有限,而又因了對有限的不斷突破而成為能動的主體.
如《歷》中所指,本雅明受康得影響,但我卻在這段引言裏更讀出的是本雅明對康得的補充或者說更進.
康得面對的是在上帝統領知識的語境裏的對話,因此,在發現人的有限層面中人可突現出主體的能動可能性,於是在這樣的能動主體敘述裏,歷史可以被表達.
而本雅明卻是在這樣的表達中看到了其的不可能性,《歷》在前段引文後再度引述的是「表意書寫越是堂皇,人受制於死滅的因素就更加強烈.
因為死滅在物性自然和象徵表意之間挖了一道彎曲而深邃的鴻溝.
」(頁116)在本雅明的現代意識裏,已經不是停留於對知識的認知,而著重的是「表意」,但在表意構成裏,一方面,人的時限與頹敗的增長難以成比例;另一方面,表意的紛繁在人的時限裏難以窮盡.
這個視角基點具有相當的悲劇意味,但是如何在悲劇裏尋得突破是《歷》著的最大努力.
在第二章,開篇論述「悲劇視角」,似乎尋得兩種突破途徑,其一在審美中體驗,其二在現實中直面.
這兩點融會於《歷》作者對本雅明思想的讀解.
我願意在這樣的理解基礎上堅持《歷》著的能動突破途徑是透析了本雅明的意旨;儘管《歷》著本身在這裏卻有所區分,認為「濛濛如煙然」,臉上「絕不顯哀樂」(頁118)的骷髏意像裏難尋本氏常涉及的「氣息」.
這「骷髏」所指是歷史沉物,而在「凝神」過程中,會有一條彎曲而深邃的通道,在體驗和表述如此的幽邃中,能感受不到「氣息」問題是王斑將「氣息」讀解為「主體凝視物象時,物性似乎顯示人的印記和反應,有回眸一笑的意思」(頁118).
如果我把這回眸的一笑層次更加拓寬,也就是說這笑不是一般的回眸就出的,而是古希臘的司芬克斯的笑,是那種人面獅身變換莫測的笑,是不是就容易多了在骷髏的意向亦能捕捉到那歷史意識欲表的氣息這裏涉及到關於歷史研究物件的問題,在西方馬克思理論的論述裏,這個「物件」不只是「歷時」的更是「共時」的,是可以將物件復活、再現、並在當下構起作用的思維過程,在本雅明,這個過程是如此「彎曲而深邃」,以至使個體的生命在時限定數的壓迫裏滿具憂傷.
應該這麼說,馬克思理論發展到本雅明及以後,在認識論層面有極大的突破.
一如《歷》著所指關於歷史論述的「自然-歷史」概念,與馬克思的歷史與自然觀相交,指出馬克思大體承認歷史是對自然的征服,而本雅明對這種進化觀念卻提出質疑.
我願意將馬克思的思維放于承黑格爾以來的二元關係裏去理解,也就是說,在馬克思,歷史是人文性的,其自然與歷史構成是動態的人文與靜態的自然相對而成;而在歷史物件上,更多的是在二元結構裏(特別是在人類歷史的發展階段裏)探究其本質;而本雅明,自然本身是人文的構成,儘管在表面上已成為博物館的靜物,但本質上是動態的,是具有多層面空間紛繁的組合,這在傑姆遜的《馬克思主義和歷史主義》文中引用瑞士史學家巴舍芬(J.
Bachofen,1815-1887)的話來表述:「真正科學的認識論,不只是回答物件本質的問題.
認識過程的完結在於發現物件產生的原因,而且要將它和日後的發展聯繫起來.
只有當知識能包含起源、發展和最後的命運時,只有在那時,知識才能轉化為理解.
」4我願意這樣的思考,將馬克思勞動商品的「再生產」概念運用於知識的建構過程中,於是才有「寓言」的品格,而在這樣的品格中方可企望具烏托邦意味的未來.
回到《歷》著,面對中國紛繁的歷史物件,如何將中國佈滿創傷的「過去時間」或者說影像,「充滿進現在的存在時間」裏本文的理解是,因了對歷史知識的生產方式的思考,《歷》才選用了本雅明的精神.
在表述自己的歷史性研究時,立足的是記憶,而這正是當下的主體在經驗著過去的客體的表現形態;不只是《歷》作者本人與王國維、魯迅一代、以及當代諸多紛繁的歷史現象觸碰,而且那研究物件本身也是在不斷的與其過往以及其當下的文化客體的相撞,故在《歷》著中這樣讀解魯迅的史識:「不是根據敘述情節慣例,或總體概況的歷史哲學來思考,而是在經驗、創痛和情感的層次,看歷史如何作用於人的身體.
因此,魯迅考慮的是個人在歷史各種紛繁的可能和岔路中糾纏不清的存在主義狀況.
瞭解歷史,就是了解社會文化環境如何振盪、施壓、肢解人的身體,如何侵蝕、創傷人的心靈.
以現代個人身體的快樂和痛苦來觀察歷史,歷史的知識便可以作為批評歷史事實的標準.
」(頁84)這是以一種現實主義的態度來面對歷史,是「一種對歷史浩劫毫不退避、毫不眨眼的直面相對」的歷史觀(頁87),《歷》作者給了這樣的態度極美的讚賞,甚至認為像王國維的悲劇觀亦「提倡在創傷何浩劫壓頂之前巍然不動的『壯美』心態.
」(頁87)前面我說過「悲劇-現實的歷史觀」,是《歷》建構知識並尋求突破的方式.
無論是第一章魯迅的「絕望中的希望」,還是對現實主義思潮在30年代中國走向成熟後的系列文藝作品,甚至是長焦鏡頭分析等等,無不顯露在歷史話語的「再生產」過程中,《歷》在面對歷史現象的社會結構所欲尋求的「壯美」之努力.
確實,中國自問題劇開始就涉入現實的反應生活的表達方式,切入社會問題是為了尋得解救方式,這是能動積極的態度.
我願意把這「悲劇-現實」結構作為讀解《歷》在中國現代歷史知識再生產的一種獨特方式,《歷》文本要強調的仍然是歷史不會終結,寓言民族國家的話語也不會終結.
在面對悲劇的現實主義分析裏,認為本雅明的寓言是「試圖在歷史的『無物之陣』中尋找家園,(頁109)其引用美國康奈爾大學的政治學者蘇珊伯克-默斯(SusanBuck-Morss)的論點,寓言「是一種特殊的意義表達形式,但這形式『不是藝術家自由選擇作為自我表達的審美手段,而是外在世界強加於主體的一種認識律令』」.
王斑認為這「『認識的律令』,有如康得的『道德律令』,顯示了寓言表達在每日每時的日常生存中,必須面對歷史創痛的嚴峻和急迫的威壓.
」(頁110)如果將現實與過去,闡釋者與闡釋物件也賦予「寓言」結構關係中,那麼不然理解王斑在讀解中具有的使命感無不是在表達一個群體的立場,一個欲參與社會類別的論說分析.
確實「現實主義」思潮亦是在這樣的參與意識裏,脫去了藝術純為享樂欣賞的品格,而賦予了使命意識.
因此,讀解到這裏,本文幾乎將《歷》對中國現代歷史知識的探討當成了群體論說的模式;即使是論述創傷,在現實主義的理解裏,「不僅僅是個體的,而且是歷史的見證」(頁127).
可以說這是《歷》生成的「當下的時間」或者說現實語境,以過去的時刻來作為回饋當下的理論形勢.
回到上文提到的傑姆遜的《馬克思和歷史主義》的論述,其理論派別是要力求區分和論述「同一性」和「差異性」的問題,而《歷》在讀解中國現代歷史現象中,恰好地剝析了在遭遇現代的「共時」裏,中國獨特的「差異」.
即使是現代性中具有普遍理念的「個人主體」概念.
我在第一節裏已經指出,《歷》欲分析的魯迅之「表意個體」.
在這裏我將把這個概念融進對《歷》的另一「再生產」方式的讀解,即「審美構成」中.
其與「寓言」化歷史一脈相承,只是比「寓言」有更高的追求,直逼象徵體系.
《歷》指出:「審美與歷史的交接聯姻,使得歷史意識產生了新的功用和含義.
歷史的寫作不僅僅是歷史學科對過去事實的記載和解釋,而是一個廣泛的文化象徵活動.
這個活動的目的在於,怎樣對付過去遺留下來的現實,針對過去的創痛,擺脫過去的重負,繼往開來.
」(頁67)這幾乎可以說是《歷》作者的直抒胸臆了.
當然王斑很明晰直抒是一回事,理論分析是另一回事,因此承接著他以上比較,即追求古人具體的實在情境的歷史主義認識論態度,那種認為歷史話語與審美的結合,使歷史話語偏離了認識論的中心,不再孜孜探求過往的「真實」,王指出:「審美創作中的歷史,卻更訴諸現今觀眾的感覺、情感、視覺、意識形態風尚,以及心理生理的接受過程.
審美化的歷史,將過去和現在變成關照欣賞的景觀和意象,探問今人在這意象中是否有舒適、愉悅或有歸屬.
···審美的歷史觀,在一個文化視覺體驗上,在感覺、感情結構、敘述過程和對過去的態度上,起著很大作用.
它不斷地調整、創造、翻新這些體驗的結構.
審美化的歷史借古喻今,古為今用,呼喚過去的景觀是為了理解現在,憧憬未來.
」(頁67)這是一段非常浪漫的論述,而且在這樣的論述後還有一個理論支持,即《歷》引述美國歷史理論家海頓·懷特(HaydenWhite)認為:「歷史寫作中的審美和修辭因素,並不是在求實求真的歷史書寫中畫蛇添足,錦上添花,而是歷史書寫本身的天然的功能,是歷史話語內在的機制(Metahistory1-42)」應該這麼說,王斑在把創傷歷史的沉痛細節劃給了現實主義的方法,就一身輕鬆了,於是撇開歷史創傷細節而進入的是一個群體理論立場的言說範圍,有數不清的群體話語支持,審美於歷史,是本雅明的「他人的故事」裏的「寓言」,《歷》引述阿多諾(Adorno)之言:「純粹審美觀點理解的藝術,即使在審美層面也是誤解的藝術(AestheticTheory6)」(頁95)即審美本身亦無純粹,必有寓意,與「歷史話語內在機制」相吻合.
而「表意的個體」是指甚麼呢是「審美經驗塑造的主體」(頁52)是「在創造藝術和詩歌中,詩人、歷史家喚起民眾,促使他們以藝術的有機整體模式、內外一致的親緣表意關係來建立一個社會.
」(頁51)這樣的「個體」是「主體」與「客體」的合成,可以「成為審美、社會、政治改革的對象和能動者.
」(頁52)可以說無論是「表意」還是「審美」,《歷》始終訴求的是群體意識,在這樣的意識裏去把握本雅明的「藝術氣息」,這樣的「氣息」於中國現代史,獨異一方.
中國要敘述的故事,是可以表明屬於自己的過去,並與現在和將來延續:「中國人需要一個可信服、可以與其共存的過去圖景,為今天奉獻意義,他們希望通過敘述去恢復人人應有的歸屬感和根植群體生活的身份感.
」(頁131)《歷》當是面對中國現代史、特別是苦難的歷程一個非常體己的敘述.
就好比其強調的「悲劇視角」讓人「睜開眼睛看」的現實主義歷史意識,《歷》著始終沒有回避中國現代當代史的苦難,更沒有粉飾、遮掩、或者忌諱、強辯.
而是帶著一種深深地可以被稱為「沉痛」的情感來表達一份體己的沉思,因此,才強調「記憶工作興起的重要」,在解釋這份重要時,《歷》陳述道:「創傷體驗時對個人和群體的巨大打擊,衝擊了文化的表義和象徵體系.
這個體系實際上是人們賴以安身立命、瞭解感知周圍世界的生命線.
通過這個體系提供的文化資源,我們能夠敘述故事,在日常經驗中見出意義和價值,維繫文化實踐的延續.
更重要的是,能夠書寫歷史.
創傷事件和經歷不僅僅破壞了個人和群體文化間的感情聯絡,更重要的是震撼了維持集體和個人身份的公用的文化儲備.
」(頁139)我願意以《歷》在第四章的引言來讚賞,其引用的是歷史學家羅森斯通(RobertRosenstone)的問:「在何種程度上,我們要求感情成為一個歷史的範疇成為理解歷史的一部分歷史成為情景交融、將心比心的圖景,這是個成就嗎」(頁153)我要說的是,《歷》著充滿情感的筆觸正體現了這樣一個成就.
並且力圖挖掘的是「正面的價值觀和頹敗歷史現實之間的辨正互動關係」(頁60).
在此王斑非常機巧的運用了本雅明的有關現代機械技術對人的經驗造成的斷裂、萎縮修復理論于中國的現實,正如《歷》自己表白的:「本雅明觀點並不能為八十年代的問題提出滿意的回答,但他的言說,在歷史斷裂和重建的關頭提供了很多啟示.
諸如歷史敘述、記憶、經驗、靈蘊氣息,以及個體如何與群體文化記憶重新聯繫的問題.
」(頁137)正是這些問題帶出本氏對「故事」的慨歎:「講故事的人已變成與我們疏遠的事物···講故事的藝術已經消亡.
我們遇見一個有能力地地道道講好一個故事的人,機會越來越少.
(Illuminations83)」而這個慨歎《歷》直接理解為:「歷史敘述可以說是個語言的問題,是個如何言說表達意義,聯繫過去和現在的問題.
在連串的歷史浩劫後,中國人不再擁有意義自明、讓人信服的話語,不再信賴歷史的總體規劃,不再依賴原有的經典敘述來想像與現在生存相融合的過去.
在這種情況下,講故事,也就是『講古』,成了一個棘手的問題.
」從以現實態度直面悲劇到審美經驗的表達,是《歷》貢獻其「正面價值觀的途徑」,但是表達甚麼、怎樣表達,在表達中又有如何的想像關係,其又將如何對應心理危機等等,《歷》著仍然為自己為讀者提出了諸多問題,且關鍵還在於,作者王斑自己在思想意識上的群體認同,即時時「昭示了文化形態和社會意義的重建和維持、修復和協調心理和現實之間的斷裂、個人和群體的脫節、過去和現在的隔膜.
」(頁131)正是這樣的關懷,《歷》強調在文化生產中,以上的有關歷史的問題會從各個角落呈現出來,恰是「這些問題的持續性和堅韌性,對全球化歷史終結論提出了挑戰.
」(頁137)三在我的讀解裏,《歷》前三章已經將思想體系作了圓滿的表達,這是全書的重頭,占一半篇幅;而後五章屬於思考的第二部分,為實證分析,從電影到小說,各類文藝形式中去把握歷史氣韻的生生息息.
坦率地說,如果這後面五章可以以實證來環環相扣前三章的理論鋪墊,那將是一個輝煌.
因此,雖這五章皆可單篇成文,我卻願意將其統歸於一節來論.
首先,承接上文,《歷》將歷史敘述理解在了「語言」點上,即「歷史敘述可以說是個語言的問題」,而語言一方面在前現代意識裏是一個「存在」問題,卻在後現代意識裏又成為了「牢籠」問題;應該這樣說只有在前現代的意識裏才會有《歷》引據的盧卡契的《小說理論》中的觀點:「把小說看成是經歷現代性的人眾在喪失家園後,尋找精神家園的努力.
」坦率地說,在這個前現代意識裏,中國的現代敘事並沒有、或者說還沒有來得及產生史詩般的巨著,就被洪洪潮流傾臨淹沒,於是,到《歷》聚焦的後五章,面對的是經過劫難後的中國當代敘事.
一如上文所引《歷》對創傷的理解,放於中國苦難後的當代心靈上,那是「個人和文化的象徵表意體系」被嚴重摧毀、人徹底地無所歸依的流浪狀態,在這樣的狀態裏,有《歷》在第三章提及的、也是歷來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裏慣常的對尋根派的說法,即渴望尋找文化的淵脈;但是我認為,只要切入中國尋根文學的細部,無論是情節意識還是語言句式,那要尋的「根」有很大一部分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被革命突然中斷的現代意識,敘述要表的恰是盧卡契之論.
只是對中國八十年代以後的派別思潮,我們難以深入貫之,似乎中國在現代這個意識裏從來都處於狂燥中,跟隨潮流而唯恐不及,如一位批評家所言,趕得連撒泡尿的功夫都沒有,難怪評論者面對如此的研究物件,最好的方式也就只有將其泛而論之.
在此我想指出的是,中國的當代敘述就這樣在眨眼功夫中就經歷了從「存在」入「牢籠」的飛躍.
在《歷》無論是針對小說還是電影的敘述模式分析,基本面對的是牢籠中的舞蹈.
其次,或者說更進一步值得探討的是環繞「現代」這個概念的論說.
如果按理論家的言說「現代」是不同視角下的語言表述,那麼現代敘述裏,我們同樣可以獲得許多經典文本範式,許多是表達工業文明之後的異化.
在《歷》著中幾乎很謹慎地涉及這類世界文學中的敘述,僅以例證的方式涉及到卡夫卡、普魯斯特等,而且在分析中國現代敘事裏,使用了本雅明「現代無小說」之論.
倘若將「現代」只作為一個時間概念,那麼在迴圈歷史觀的看法裏,直線的時間概念當然就淪為了「空洞」.
其實,《歷》在第三章已隱含的提出了「時間對人的意義」這樣的問題.
在本雅明的視域裏,「現代」或者說這個區域的「時間」是放於「機械複製」的無聊感受中的,可以說是在這樣的感受裏,人走向了平面,沒有了情節跌宕起伏的故事,都是複製的平板一塊.
因此,本氏對現代小說的批評不是整體或者價值判斷,而是感受表達.
這個表達裏確實容透了創傷,有語言在創傷後的乏味,也就是「空洞」;也有人對「時間」感覺上的創傷;甚至可以說是本雅明的浪漫思想根基遭受到現代而產生的「震驚」創傷.
從本氏的「對卡夫卡的反省」論文來看,對「文學作為社會生活的反應」傳統,本雅明有其個人的沉思,特別是遭遇到他那麼不喜歡卻又無處可避的現代情境時,文學該如何表達現實生活真實地反應這無聊的「機械複製」似的城市居住於是他認為卡夫卡簡直就是在為這無聊的真實獻祭,而得到的是一種失敗性毀滅感.
這裏本文當指出的是,在這個時候本雅明的閱讀裏,卡夫卡語言表達屬於卡式個人的,本雅明幾乎完全否決這只凝聽「有病傳統」的卡式文風可以引證現代語言寫作.
但是今日在我們的閱讀語境裏,卡夫卡的孤獨不只屬於他個人還屬於整個現代文學,於是更有意義的反思本氏之言當放於現實主義的浪漫質數分析點上去考慮.
沒有原于生活而高於生活,還程度上破壞了文學的「寓言」品格,是本氏不能容忍的.
5正如《歷》所言:「受創的時間感覺,已經不再包裹宗教、象徵、禮儀的呵護媒介,這些媒介再傳統、前現代的文化中賦予時間以品質、價值、意義、魅力和規範,保證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周而復始、有變化又有前後聯屬.
在現代生產和生活中,時間被分裂為七零八落的單子···這個工具性的、分秒都要『有用』的時間又伴隨著空洞化、平面化、虛幻化的時間萎縮,剝奪了時間原來積累的意義···淪為百無聊賴、無所事事的沉悶,如同嘀嘀答嗒的機械鐘擺.
」應該說,在這一點上《歷》很好地把握到了本氏那敏感的波特賴爾式的「憂鬱無聊」之感受,但是當將這份引言性感受運用到中國現當代敘述裏,王斑遭遇到了困難.
中國人對時間的傷害,可以說還沒有來得及感受,中國敘述裏的時間呆滯基本給了鄉村,中國的城市從來是五光十色.
這樣的置換語境而產生的困難在「生活經驗著歷史」論述裏同樣出現了.
王斑當是非常心儀海勒的「人生中最幸運的神賜」:「兩個人,也許更多,但不是大眾,共同生活在一起,共有經驗,共同回憶書寫他們的過去,彼此毫無隱瞞,因而過去的經驗完好無損的保留下來,這時,就產生了生活經驗著的歷史.
他們並不覺的缺少時間,並不覺得時間過得太快或太慢.
他們不抱怨,甚麼事發生為時過早或過晚.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不覺得時間的流逝,不知老之將至,因為他們的生活就是經驗著的歷史.
」(頁181)王斑即使在否論這段話的貴族氣的同時找了一個很好的理由是「海勒的說法有『應然』的意義」,於是「預設了記憶和歷史,個體生命時間與歷史之間理想的、正常的關係.
」其實海勒這純粹到剔透的「經驗著的歷史」是需要充足條件的,不只是逃開了時間剝蝕,其避開了所有關於目的性的話語,更不要說是現實苦難了.
海勒是中國傳統文人的高山仰止之境.
而這對於在納粹迫害下落荒而逃、卻又無處可逃的本雅明是天上、地下;而對於苦難的中國當代史,那更是不可企及.
因此,我願意說將本氏運用于中國現代敘述分析是非常機敏的,而且《歷》在某種程度上運用的非常恰當,那就是,本氏對機械文明給生命帶來的「震驚」王斑將其運用於對殘害和苦難的不可想像之震驚.
從魯迅的視角到當代浩劫的苦難,「震驚」,這在本氏筆下閃光燈劃破死寂的剎那,人在那霎那打破呆滯的驚恐,在中國現當代歷史敘述裏,在遭遇的不是閃光燈而是血淋淋的苦難前,產生的是一個浩然民族靈魂的驚怵,只有這樣的驚怵,才實實在在夠得上前面的修飾定語「震撼」.
於是《歷》著有了其對中國現代歷史敘述的重頭分析,即有關創傷的記憶,以及對這記憶表述的歷史.
在歷史與記憶的張力空間施展開論述.
在此《歷》涉足多重敘述模式,概括地講最基本的模式是相對官方宏大敘述的帶有個體性質的書寫,其中有見證品格的口述、回憶錄、傳記、以及電影紀實;亦有如《歷》引孟悅所指的在宏大敘述退場之初出現的似烏托邦般的拯救模式;再到時代進入80年代中後期直至90年代的消費場景的散文敘述等等,本文欲有意避開這樣的敘述形態梳理,而想指出無論哪種敘述模式,在功能上其實有相通之處.
正如《歷》所指,中國80年代前的歷史書寫「往往是根據絕對的政治標準,主觀臆斷地『挖掘』過去的某些事件和事實,尋找提供現實政治合法性的前因和後續」(頁137)在此我欲補充的是,不只是當代史沒有做到「以科學的、實證的、批評的要求,對歷史的遺跡和事實進行探究.
」(頁137)就是古代史亦難以做到.
任何一個朝代在修其官方史時,所謂的古為今用就是為現實政治服務.
所謂史家的理想狀態的修史,最好是修古史,就像《歷》常引的本雅明之言「講古」,更是證古,不帶現實政治的功利目的,而完全本著精密考證.
這種對於歷史的態度是職業性的,在品格上有著高尚的職業道義追求.
我願意這樣的理解那多重的敘述模式,也就是說在我,歷史是史家之業,群體與個體皆是這職業的研究物件;而對於運用者來說,好的狀態是借古喻今;壞的狀態是假虎為猖.
《歷》在分析敘述話語時存在因「震驚」下的創傷帶出的困難,認為創傷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文化意義系統的建構,於是費了好大的勁去剝析個體與群體間的離間,當然這也因了建立群體與個體的聯繫本來就可能是《歷》作者最想強調的追求.
在此我想說的是,不是個體與群體間的離間,而是史家與物件的離間,強調記憶苦難是為了災難不再重演的目的,是史家之責,不讓創傷性情緒影響了實證是職業本身就當有的要求;而對於經歷苦難的物件來說,記憶只會重複傷痛,不會有更好的意義.
沒有任何一種東西可以真正補償得了真實經受的苦難,咀嚼只會雪上加霜、傷口摸鹽;更坦白一點說是,將創傷當成敘述的,可以建立起敘述話語的,其實並沒有真正經歷徹骨的戕害.
以「震驚」概念來形容,真實遭遇「震驚」的是千奇百怪、也許醜陋百出的那剎那間的畫面,只有職業眼光下的這些畫面才有可能產生「震驚的審美策略」(頁284).
也就是說遭遇「震驚」的個體其實亦很難真正見證得了那個剎那,就像古人言無法踏入同一條河流一樣,在本質意義上是不存在純粹見證的.
史學,與其說是真實的記載,不如說是客觀的闡釋;或者說記載與闡釋相輔相成.
而「穿透」表面,投身於「未經雕飾、意義不確定、矛盾重重的歷史現實」、甚至「憂鬱的、意義晦暗的深淵」(頁284),以「爆破」的可能來深入「歷史事物的內核」(頁285),更當是優秀史家之志.
本文在前面分析《歷》將歷史話語與審美活動結合中提到,王斑非常強調以文化視覺體驗來書寫歷史,並認同此「屬於歷史話語的內在機制」.
當《歷》在中國現當代史話語裏體會出遭遇苦難之「震驚」時,必然促使讀者深思本文亦在前面指出的中國現代漢語詞典中的「國家」之定義,也就是說怎樣才能清楚厘析「暴力工具」它直接牽涉到的是「民族國家」話語的另一面,除維護主權之外的功能,在主權建立後的語境裏,國家以及在這個建制之下的工具性結構,特別是在國民面前,其職能是甚麼是對這職能的迷惑,中國當代製造了那麼多慘絕人寰的悲劇,迫使人不得不喪失這「國家」語彙裏本應有的文化情感的依託;而本為「公僕」性服務職能的工具角色卻成了暴力的蠻橫.
在此,《歷》對歷史敘述模式的分析裏,採取文本精讀的方式,來透析「文化視覺體驗」的書寫.
最打動人的當是作者選取的《籃風箏》.
一如本文上段所指,歷史事件的真實有其模糊或者說難以呈現之品格,王斑首先讀解的是《籃》的片頭:「幹井」的意象:「似乎生命的源泉幹凅了.
這些不詳的意象突出了回憶過去的困境和迷茫,意味著過去的輪廓不清.
」(頁169)正是這困惑不解的視覺體驗,一次次發生在「震驚」的遭遇中.
而這遭遇卻是「災難和運動紛至遝來的世界裏,日常起居表達了在動亂之中尋求一方立足之處、棲身之所.
這是在讓人旋昏,使人失明的政治大潮中能有安穩的生存.
但恰恰是這個謙卑的願望日常生活則是這願望的載體在歷史的動盪中一再被擊破,瓦解,粉碎.
」(頁171)於是從「普通百姓在危機四伏的歷史現實中難以逆料的命運」中析出「故事中人物面臨的是一種無法理解、冥冥之中的勢力,似乎不停地與每一個人的正常生活作對,週期性的造成痛苦和死亡.
現實似乎是個謎.
歷史的密碼難以解破,歷史的意義無從把握.
」(頁172)而這荒誕的歷史卻又是那樣真實地戕害著每個中國人.
在王斑直面這樣的苦難是為了尋求「絕望中的希望」,可是,在對《籃》的讀解裏,《歷》這樣動情地描述到:「在突如其來的結局中,鐵頭仰臥在地上,渾身上下傷痕累累,凝神盯著樹梢上瑟索顫抖著的破風箏.
」(頁175)這樣風中的顫抖作為一個民族在絕望裏的希望是不是太悽楚了而正是這樣的悽楚,王斑「爆破」出:「這個死寂的時刻,並沒有一個經由錯誤到正確的價值時序來定位,並沒有一個目的性的未來讓人有所展望.
時間的流動嘎然而止,封凍在一個寂靜的時刻,充斥著無以名狀的震驚創傷,與其他時刻的聯繫崩裂.
」(頁175)王斑給予了這樣的歷史敘述高度評價,認為是在當代史裏「不可多得的記憶方式」(頁176).
這裏王斑是以動人的情、那心靈生髮的「氣息」來觸碰歷史的傷痛,於是群體與個體的離間之辯似乎暫且擱置,但事實上,那個傷痕累累迷茫於樹上風中殘破風箏的意像正是當代中華民族的整體在暴力下的希冀之意象,這個意象不只是那個過去了的歷史時代,而且是當下、甚至將來的多少年之後,仍然難以泯滅的創痛.
因此我曾想問,甚麼時候中國人也會有那樣一個條件來「生活經驗著歷史」幾百年幾千年之後會不會到那時會有海勒所言的純然當然,正如本文開篇所指,《歷》即使透出憂鬱,但也同樣不失欲求陽光燦爛.
在對王安憶作品的細讀裏引述:「還是唯心主義好,唯心主義慰人心,讓人走到哪一步,心裏都存個念想.
」(頁201)如果將作者與《歷》文本以及其研究的物件、再加上《歷》整部著作思考和闡述的方式,作為交互現象來讀解,我幾乎可以這樣假設,在文化象徵的活動裏,「群體記憶」、「傳統情系」其實就是一個象徵性「念想」,儘管這個「念想」在《天仙配》的讀解裏,很有可能像那個本是「村裏人共有的女兒,是人們在無可信賴、孤獨無助之時互相依賴、互相依偎和信賴的象徵」一般在「穿越時間的神話和記憶剎那」(頁200)被驟然滑落,但是《歷》的氣質當是會拒絕那個逝去許多年許多年的女兵的老去,完全拒絕某種「經久不衰的象徵意義」被剝奪的.
正是這樣一個拒絕姿態,使得《歷》的論述始終洋溢著一種激情.
本文開篇曾指出,《歷》涉足的是一個理論繁複、且強調理論與實踐結合、卻又在實踐中遭遇全球性失敗的這樣一個現實性課題,這對於史識與膽氣都是一個考量.
中國現當代歷程是一個以特殊和差異來實現或者說突破現代資本理論的另外一枝,卻又是以成千上億人的血淚和苦痛為代價最後不得不皈依滾滾資本洪流的實例,僅僅記載苦難是不夠的,只張揚差異、一葉蔽目地將血流成河高贊為不同於繁花似錦,就更不足取;像德國面對奧斯威辛,沉痛記載,深刻反思;敢於直面所有的苦痛,亦敢於拷問這歷史進程中的任何災難性錯誤,作史為後人.
但是,當不只是意識和形態上,思維方式、敘述語言,乃至純粹的語詞、語彙,都遍佈了歷史的傷痕時,以及在創痛裏以豁出去的姿態逃亡般墜進資本的洪流滾滾後,史的工程可謂難夷.
可以說《歷》欲極盡努力,在後五章的後半部,幾乎穿越了中國進入90年代後資本時代的文學敘述,面對一個商品意識膨脹到瘋狂的語境,《歷》作者似乎很想但是卻無法像讀者掩飾那樣一種其實是費很大力氣來說服自己的平常心態面對史詩消逝的時代事實.
在第六章,也用紀德波(GuyDebord)的話來作引言:「當新近獨立的藝術以鮮豔的色彩描繪它的世界時,生活的一個關鍵時刻就已經老化.
藝術的鮮豔色彩不能使生活恢復活力,只能使之呈現于心靈.
暮色籠罩生活之時,便是藝術茂盛魁偉之日.
」(頁203)但是,儘管對散文化的敘述方式《歷》沒有褒貶,但是整個《叔叔的故事》讀解下來,似乎並沒有在叔叔故事的「鮮豔」發展裏更好地尋到「心靈」;而是那「文化形式」卻成了一個與歷史相逐的「角鬥場」.
在我的理解裏,這「角鬥」與其說是那「叔叔」故事的,不如說是《歷》思想基調的旋律與中國當下時代的較逐,這個較逐其實不只在王斑,幾乎可以說是被劃為自由派對面的新左的同一基調.
較逐的結果是,《歷》引朱天文的話:「將以嗅覺和顏色的記憶存活,從這裏並予之重建.
」(頁223)這是第七章的引言,而整章意在如何將人與物的認知關係導向「化商品的腐朽為神奇」.
這神奇之後亦是《歷》駐筆之處,那是「愛在燈火闌珊處」.
全書最後重新回到本雅明的論述:「都市詩人的快樂是愛,但不是一見鍾情,而是燈火闌珊處的愛,這最後一瞥的永訣在詩章裏與神奇的時刻相融合.
」(頁243)穿透表層的面紗,深入歷史事物的內核,「爆破」出那神奇至永訣的「一瞥」,可謂是《歷》的追求.
本文就此打住,無論是本文視域裏的《歷》還是本文自身,更願意放於邏輯層面,即研究物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某個抽象結構的可能效應,是為這樣一個抽象意義上的思維結構而產生出的理解性分析.
最後還要說的是,認同《歷》緒言中劉再複之言,這是一本讓人讀了就難以釋手的書,能帶給你許多思考,為這份啟發,我深懷感激.
忙於稻糧的斷續為文月餘,初稿完於2005年12月29日臨晨波士頓森林谷陋室註釋1FredricJameson,1934-《馬克思主義和歷史主義》,見其論文集《理論中的意識形態》2《現代漢語詞典》第424頁,商務印書館19923Country:anindefiniteusu.
Extendedexpanseofland;region;residenceorcitizenship;relatingto;orcharacteristicofthecountry;apoliticalstateornationoritsterritory.
MerriamWebster"sCollegiateDictionaryp286,Merriam-Webster,Incorporated2004.
4巴舍芬《母權》,第103頁,法蘭克福,1975.
5WalterBenjamin「SomeReflectionsonKafka」,Illuminations,p141-145,EnglishtranslationCopyright1968byHarcourtBraceJovanovich,Inc.
《二十一世紀》(http://www.
cuhk.
edu.
hk/ics/21c)《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五十期2006年5月30日香港中文大學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五十期(2006年5月30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
#推荐# cmivps:全场7折,香港不限流量VPS,支持Windows系统
cmivps香港VPS带来了3个新消息:(1)双向流量改为单向流量,相当于流量间接扩大一倍;(2)Hong Kong 2T、Hong Kong 3T、Hong Kong 无限流量,这三款VPS开始支持Windows系统,如果需要中文版Windows系统请下单付款完成之后发ticket要求官方更改即可;(3)全场7折年付、8折月付优惠,优惠码有效期一个月!官方网站:https://www.cmivp...

CloudServer:$4/月KVM-2GB/50GB/5TB/三个数据中心
CloudServer是一家新的VPS主机商,成立了差不多9个月吧,提供基于KVM架构的VPS主机,支持Linux或者Windows操作系统,数据中心在美国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机房,都是ColoCrossing的机器。目前商家在LEB提供了几款特价套餐,最低月付4美元(或者$23.88/年),购买更高级别套餐还能三个月费用使用6个月,等于前半年五折了。下面列出几款特别套餐配置信息。CPU:1c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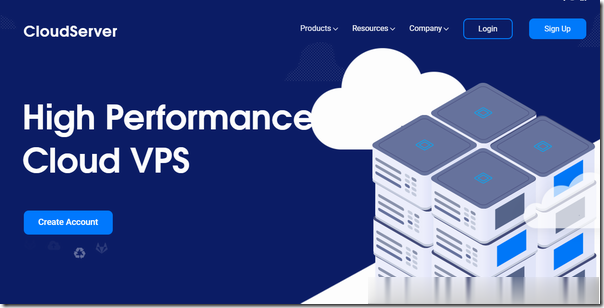
恒创新客(317元)香港云服务器 2M带宽 三网CN2线路直连
恒创科技也有暑期的活动,其中香港服务器也有一定折扣,当然是针对新用户的,如果我们还没有注册过或者可以有办法注册到新用户的,可以买他们家的香港服务器活动价格,2M带宽香港云服务器317元。对于一般用途还是够用的。 活动链接:恒创暑期活动爆款活动均是针对新用户的。1、云服务器仅限首次购买恒创科技产品的新用户。1 核 1G 实例规格,单个账户限购 1台;其他活动机型,单个账户限购 3 台(必须在一个订单...

如何建群为你推荐
-
9flash在“属性”对话框中的“Move”后面的框中输入Flash动画文件的绝对路径及文件名,这句话怎么操作?直播加速手机上什么软件可以帮助直播加速,大神们推荐推荐雅虎天盾高手进来看看我该怎么办 新装的ie8 内存使用率达到100%了ios系统iOS系统为什么那么好iphone6上市时间苹果6什么时候在中国大陆上市cisco防火墙思科防火墙策略extended什么意思263企业邮箱设置263企业邮箱如何修改密码主板温度多少正常主板温度多少算正常?qq新闻弹窗腾讯QQ的新闻弹窗关闭不了,这对腾讯有什么好处?优锁N78怎么锁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