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怎么把网页的字变大
版权信息奇特的工具:艺术与人性著者:[美]阿尔瓦·诺伊译者:窦旭霞责任编辑:吴炜孙桂均李蓓杨波书籍设计:邵年目录版权信息前言第一部分第1章得到组织第2章重组自我第3章天生的设计师第4章艺术魔圈与伊甸园第5章艺术、进化论以及谜中之谜第6章关于狂喜、运动与幽默的短笺第7章哲学之物第二部分第8章看你是否独具慧眼第9章艺术缘何如此枯燥第10章神经科学在研究艺术时的局限第11章艺术是一种哲学实践,哲学是一种美学实践第三部分第12章制作图画第13章使用模型第14章绘画策略第15章空气吉他风第16章音乐之声第四部分第17章一份极其简略却高度自以为是的美学史致谢注释译后记前言几年前的某天我正和一位艺术家聊天,他问起我关于视觉科学的问题.
我跟他讲到,视觉科学家正试图弄明白,为什么我们会看到这么多——我们看到周围的物质世界丰富多彩,而留在我们眼睛里的明明是一些渺小、扭曲且颠倒的影像.
在如此薄弱的基础之上,我们却看到了这么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艺术家的回答却大出我的意外:胡扯!
他鄙夷地一笑置之.
他们怎么能问出这等问题我们倒是该这样问:为什么我们对周围的世界如此漠视世界如此丰富,有太多的东西等待我们去发现,为什么我们却只看见这么一点点这段对话发生时我还在读研究生,艺术家的话却长留在了我的心底.
关于视觉体验,它让我清晰地看到人们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是科学家的观点:"看见"这一过程发生于大脑,因为是大脑把视网膜上获得的信息变得有意义.
另一种是艺术家的观点:"看见"并非是一种自然而然、自行发生的过程;我们太容易忽视本来存在的东西.
看见是一种收获,我们的收获,我们与存在的东西交流才会有的收获,而我们常常会视而不见.
这二十年来我一直在研究知觉和知觉意识,我试图创立一种新的方法来解读知觉,最终形成了知觉的行为生成观.
据此来看,"看见"并非是发生在我们大脑或其他任何地方的东西;它是我们要去做、去达到或获得的东西.
正如我们所能获得的其他任何东西一样,只有依赖我们的技能、知识、条件和环境,包括我们的社会环境,我们才能获得这样东西.
直到前不久我才突然意识到,近年来我的研究恰恰都是为了证明我讲到的那位艺术家的观点,他说的一直都很对.
体验离不开大脑,这点非常确定,但大脑不能解释故事全部.
科学家的理念非常贫乏,它妨碍了我们的体会:真正去感知的不是大脑,而是具有行为能力的动物和人.
我开始认识到,且在我的文章中极力主张:与其说"看见"像是在消化吃下去的东西,不如说它更像是在爬树或是阅读一本书.
但这故事还让我想到更多,艺术家说得对.
科学与哲学,要说关注艺术,它们都倾向于居高临下地俯瞰.
它们试图解释艺术,把艺术当作一种需要分析的现象来看待.
或许我们早已忽略了一种可能:艺术本可以成为我们的老师,至少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并非因为艺术是一门神秘的学科,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是自己的研究方式,也是自己真实的知识来源.
回想与艺术家的对话,我便想到了这些.
这种可能性既令人兴奋又令人迷惑.
说它令人兴奋,因为它立刻就让我们看到了艺术的重要性;但同时它也令人迷惑,因为艺术与科学不同,科学很明确地关注知识的产出和理解,而艺术所关注的知识又该是什么特点呢这里提供了部分答案:艺术给我们机会,让我们看到自己怎样达成自觉的生命,怎样把世界变成知觉(或其他形式的)意识的焦点.
因此,在艺术这个领域里,我们可以认真地思考上面艺术家所提到的问题:不是"我们怎么看到了这么多"而是"为什么我们只看到这么一点点"当然,事实是,艺术让我们从无视到看见,从看见到看见更多或看见不同.
三个观点是本书的动因.
首先,艺术不是一种技术实践,但技术实践是它的先决条件;艺术作品是奇特的工具.
技术不仅仅是我们为了达到目标而加以利用的东西,尽管这样说也差不甚远:技术组织了我们的生活;没有技术我们的生活将难以想象;技术成就了我们现在的样子.
而艺术实际上参与了实践、技巧、技术对我们的组织,最终,它将成为我们了解自己的方式,必然也会成为重组我们自己的方式.
艺术工作,它的真正作用,是富于哲学意义的,这是第二个富有生机的观点.
艺术是一种哲学实践,而哲学是一种艺术实践——这是艺术家的所爱,是否哲学家所爱我却不敢担保.
这是因为艺术与哲学——虽然表面差别很大——实属同一类型,它们孜孜以求的共同问题都是我们组织自己的方式和重组自己的可能性.
我并不是说艺术家这么认为(尽管有人这么想);我的意思是,这是他们的一直所为,而哲学家所为的恰恰也是如此.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生机勃勃的观点,这要等我们取得足够进展后它的意义才能被理解:如我所说,艺术与哲学都是倾力于创作书写的实践.
第一部分参与一件你完全不懂的事,我认为,是生活中最为引人入胜的事.
——阿加莎·克里斯蒂第1章得到组织西方艺术中关于母亲哺乳的描绘比比皆是.
展示圣母圣婴本就是基督教思想的核心,这原也不足为奇.
但是描绘给婴儿喂奶的图画对我们这么重要,其原因很可能超越了我们对耶稣生活的兴趣.
毕竟,哺乳是我们哺乳动物一个根本的生物特征,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它也是我们培养感情的最早的机会.
事实上,至少我这么认为,哺乳也是我们了解艺术本质的关键.
母亲哺乳的画面如此多见,可能表现了艺术一个由来已久的特征:艺术总是关注艺术自身的.
哺乳与艺术本质之间的联系可能并不那么明显,这表明要让大家清晰地了解艺术以及艺术在我们生物学中的根源,我们任重而道远.
谈及哺乳,有件事颇为引人注目:在所有哺乳动物之中,唯有我们人类做得最差,不仅仅是因为哺乳对我们来说很困难——许多婴儿首先要学会含住奶头.
因为对食物的需求迫切且强烈,所以这任务无论对母亲还是对孩子都变得极为艰巨.
而作为喂食者,我们的脆弱还远不止于此.
其他的哺乳动物,一旦幼崽含住奶头,它们就会完全投入地吃奶,直到吃饱,任务完成,除非有外界因素让它被迫松口(比如其他幼崽的抢食).
但人类的婴儿却不是这样.
我们的宝宝吃奶时常常左顾右盼,不是被声音吸引了注意力,就是满心喜悦地睡着了,再不就是光顾着咂着奶头玩,根本忘了吃奶才是正事.
是这样吧事实上,人类的哺乳如此低效,以至于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不由猜想,或许在人类,主要的进化意义并不在于喂食,而是别有他意.
或许我们是让它退化了.
我们哺乳不是为了喂食,只是为了触摸、爱抚和拥抱.
身体的接触会诱发神经化学反应(比如后叶催产素的分泌),这对人是有益的、必须的,于是,我们就有了这一事实:身体接触会加强母婴之间的感情,这恐怕与神经化学不无关系.
·现在,让我们来详细地探讨这一问题,首先看一下哺乳过程.
注意,它有一个明显的形态:妈妈抱住婴儿,把乳头或是奶瓶放进宝宝嘴里——为阐明我的观点,这种分别无关紧要——宝宝开始吃奶.
然后,设想一下,他扭头转开了.
妈妈对此做出的反应是轻轻晃动怀里的宝宝,把他拽回到正事上.
这是妈妈的自然反应,不是学来的,也不是别人教的.
宝宝继续吃奶;有动静惊扰了宝宝,他停止了吸奶;妈妈轻晃,宝宝再吸;很快他又把头扭开了,妈妈再晃.
这过程重复循环着.
当宝宝长大点,强壮点了,妈妈也获得了更多的自信,这过程便进行得更为顺利、更为高效.
但是,那个基本的问题——让宝宝吃饱了再入睡——仍是一件耗费精力,需要协商的事.
现在,回顾这一过程,你会发现,它表现出六个明显的特征:首先,它是原始的、根本的、生物的.
哺乳不是人类文化的产物,而是根植于我们哺乳动物本能的东西.
它是植根于自然的.
其次,尽管它根本、原始,但很显然却需要母子双方共同发挥精细、发达的认知技能.
给与受、集中精力与精力分散、感觉、倾听、对另一方的动作或不动作做出反应——哺乳活动包含了所有这些因素,更不用说矛盾冲突了——宝宝不等吃饱就睡着了!
他还在不停咂嘴,但好像根本不在吸奶了!
第三,很明显,整个活动有一个结构,它按时间顺序组织起来.
的确,这里面有一种像是轮番进行的结构.
宝宝动作,妈妈倾听;妈妈动作,宝宝倾听并作出回应.
这可能是我们生命发展中最早的交替行为;甚至可能是动物世界中最早的轮流动作的例子.
请注意,哺乳活动的这种时间动态使它看起来非常像是一种原始的对话.
令人称奇的是,只有我们,使用语言的物种,才会进行这种复杂的、交替为之、对话一样的交流.
第四,无论是母亲还是婴儿都不会编导或指挥哺乳活动.
当然,母亲相比婴儿力量要更为强大,她有更多的主动权,她要操心结果并寻求朋友和助产士的帮助.
但是活动本身似乎就是顺其自然地发生,尽管其中交织着微妙的倾听和回应、行为和感受,而且有着明显的轮流为之的瞬间动态.
活动的整体要求,掌控着参与活动的每个个体的行为,也就是说,它排斥个体的操控行为.
第五,整个活动有它的功能.
的确,如我们所见,这种活动的具体功能究竟是什么我们尚不甚明确,但它肯定与喂食或建立母子亲情有关.
哺乳似乎是一种建立感情的活动.
最后,尽管我们已经看到,哺乳几乎像工作任务一样会有矛盾冲突,需要协商洽谈,但至少潜在来讲,它对母子双方都是一种快乐的源泉.
这六个特点显示出哺乳怎样组织了我们.
任务本身塑造我们,成就我们,也约束我们;我们发现自己在这个活动场景中被组织、被塑造了起来.
我要提出"组织活动"这一术语,哺乳就是一种组织活动.
所谓组织活动,我指的是任何像哺乳一样表现了我所列举的六种特征的活动.
我宁愿选用这种通俗的表达方式,因为组织活动是原始的、自然的;它是一个竞技场,需要我们集中精力,去看,去听,去做,去经历;它表现了时间结构;它是自然发生的,不受活动中任何个体刻意的操控;它有一个功能,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社会的或是生物的;它令人愉悦(至少可能).
重要的是,组织是一个生物概念.
生物都是有机体——有组织的整体,而且生命留给科学的一个核心的概念谜题就是去解读单纯的物质以及本属物理学的秩序怎样被挑选出来,并以这样一种自我创造且创造世界的生命方式合成一个整体并被组织起来.
公司有它的组织结构,好职员会努力服务于组织(成为"组织的人");"组织"在商学院里也可以是一个技术术语.
但是,组织,从根本上来讲,是我们的生命状态,是我们的存在状态.
活着就是得到组织,既然我们不仅是有机体,我们还是人,我们发现自己还在更大程度上与我们的环境、彼此之间、我们的社会紧密相联,被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人们发现自己就是被像哺乳这样一些共同参与的活动组织了起来.
本书一个重要的观点便是:以此理解艺术以及艺术问题的本源,虽不中,亦不远矣.
·这里有另外一例组织活动:交谈.
从一个层面,意识层面来讲,当两个人谈话时,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在表达各自的观点并彼此关注.
但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交谈在一个更为根本的层面上把我们的行为联系、统一、组织起来.
谈话双方常常会不经意地采取同样的姿势,他们调整到一个适当的音量,他们看着彼此,或是看着身边的同一件东西,以高度控制的方式.
当然,这样一来,他们就参与了一种包含听、想、集中精力、做和经历的复杂活动,这种活动大多是自然发生的,没有刻意人为的操控.
显然,交谈是人类自然的活动——它是基本的,我们无法想象没有交谈的人类生活——即便很显然它同时也需要双方进行精密的认知调整.
交谈有它的功能、目的,既有对于交谈双方的——无论引起人们交流的兴趣是什么——也有对于物种层面的.
交谈是一种沟通感情、共同生活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机制.
交谈令人愉悦:它可以引人入胜,令人忘我,富有挑战,如此等等.
我讲过,哺乳可以是一种原始的对话,或者更好的表达方法是:交谈是一种更为周密的或经过精心设计的哺乳形式.
由于技能、兴趣及场合不同,可能它会有所改良、修正和放大,但无论如何,其根本的组织结构都是相同的.
顺便说一句,交谈的例子也让我们看到,为什么说在开车的同时打电话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
开车是一种组织活动,它需要你集中精力,做出行动,还要对其他人的行为作出反应,参与一系列有着自己特定时间模式的行为.
当你开车时,你不仅仅是在开车,你是被锁定在一个完整的关系空间中,并在此被组织起来.
这一关系空间包括你与周围其他人的关系,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不仅有车辆内部环境,还有整个路况环境.
而打电话的要求与之完全相同却互相冲突.
你被扯进一个完全不同的组织活动,有着不同的关注目标、不同的时间节奏.
而我们一起开车或一起走在大街上的彼此交谈就不是这样,此时,我们的对话活动在一个共同的兴趣空间里进行着共同一致的调整.
但是打电话意味着我们是在对电话另一端一个遥远的人讲话,我们参与且生成了另一个不同的空间环境,我们要使用不同的方法和提示来引导注意力.
重点是,我们严重地脱离了自己所处的环境.
开车、交谈、走路的案例表明,我们自己被卷入组织模式的方式,天生的与后天习得的之间并不矛盾.
无论是在习得技能的背景下,还是在新奇的环境中,我们开展活动并被手头活动组织的能力,甚至是在此过程中迷失自己的能力,在我们都是自然的.
我们的天性就是要获得第二天性(secondnature).
从组织活动的理论观点来看,开车、走路、交谈表现的都是与哺乳活动展露的同样的、根本的人类天性.
·组织活动还有另一重要特征:它是习惯性的,而习惯根植于生物性之中.
我的意思不是指我们有走路、交谈、开车的习惯,即把它们当作是日常活动,尽管你当然也可以真的这么做.
我的意思是,要从事这些活动并把它们做好,也就是说要熟能生巧,我们需要进入放松的、习惯成自然的状态.
注意观察有经验的母亲给大点的孩子喂奶:两个人就像是沉浸在这种熟悉的几乎是惯例性的活动中,妈妈刚刚还在打着电话,这会儿她用另一只手解开衣襟,把孩子安顿好,而孩子此时咕噜一下就含住了奶头,像从树上滚落一样,整个活动几乎是自动地毫不费力地展开.
而在某种意义上,这活动正是同心协力、亲密交流、全神贯注的一个典型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要理解这种组织活动——这种习惯成自然的活动——不能仅仅把它们看作是发生在参与者神经系统里的事情.
当然这不是说,如果你知道怎么干预参与者的神经系统,你就可以改变或打断活动的组织.
我要说的重点是,这种活动的组织根本不是在神经水平上,就如不在原子水平上一样,但它也不是有意识的刻意行为的层次.
我们是在一个中间层次被组织起来,即机器人专家达纳·巴拉德(DanaBallard)所称的"体动层次"(embodimentlevel).
这一重要层次既不属于"动物性"(subperson-al)层次——无论我们怎样构建模型,它都还没到发生在我们身体里面的水平.
毕竟,我们感兴趣的,恰恰还是这个"人"所做的,他在看什么,在关注什么,等等.
但它也不属于"属人"(personal)层次,即人在刻意状态和权威状态下做决定的层次.
司机无需刻意地决定刹车、换挡;行人走路无需决定转换重心;宝宝也不是"刻意地"再次开始咂奶.
·组织活动不必是交互的.
有时环境自身就把我们单个人组织了起来,感知就是这样一种情形.
这里我们需要特别当心,因为感知可以有很多情形.
正如对话不止有一种情形一样——我们吵架,我们交流信息,我们喁喁私语,我们洽谈商务等——观看(比方说)也不止有一种情形.
我们用眼睛来引导我们驾车、做饭、沐浴、看书.
即便是看电视这样一种看似被动的行为,虽说你只是在盯着一只盒子(或说是屏幕),但注意力还是指向了电视节目所展示的世界,那才是我们关注或思考的.
感知显然要受到行动的牵制.
(在第五章,我会详述关于知觉的不同思考方式,以及它们于我们主题——艺术的意义.
)但是,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我随巴拉德的说法称之为"体动层次"的观看.
每当你转动眼睛或手臂时,都会造成一些感官变化.
当你相对于环境移动时,事物的外观也会稳定地变化.
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意识不到这些变化.
也就是说,我们出门时身上穿的衣服颜色发生了改变,并不会给我们留下印象;但是在绝对直觉上,它们的确是变了.
(毕竟,就颜色来说,在阳光下看起来肯定是不一样的!
)而且当我们靠近一件东西时,也不会感觉它在变大.
心理学家把这称为知觉恒常性.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周围事物在我们活动时产生的这些大小、形状、颜色上的明显变化,我们肯定会非常敏感;事实上,正是我们对它们的熟练掌握,让我们太过熟悉它们,得心应手,才使得我们有可能利用这种变化模式,作为我们锁定这一稳固世界的手段.
注意,我们观察这世界可不像是看电影那样,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注视着屏幕上的影像.
我们会不停地移动,调整目光,或眯眼,或斜睨,不让世界离开视觉焦点.
如果我的观点没错,那么"观看"就是我们与周围世界有时间延展的、动态的交流,就像掌管我们开车、走路、哺乳的原则一样,也要受到时机、思索、行动、自发性、功能、愉悦等原则的指导;同时各种形式的后天认识与期望以及这样那样的任务要求(修钟表、打字、开车回家等等),也会对它起到支配作用.
只要我们不脱离恰当的描述层面,"观看"就是一种组织活动.
它根本、天然但又是很复杂的认知行为;它有时间组织,但其组织又不是我们刻意控制或决定的结果;当然,无论是对我们个人,还是对我们的工作任务和社交关系,或者是对我们人类,它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知觉中的行为》(ActioninPerception)一书中我指出,"观看"是探索世界的一种特殊活动.
尤其是,我们自身的行动怎样生成和控制感官反应,对此我们有着内隐的实际解读,而观看就是利用这些内隐的解读来探索我们周围的世界.
现在我要说的是,根据上述观点,观看(以及各种形式的感知)就是我们对周围世界获得认知的一种组织活动.
·至此,我的观点是:我们是被组织的,我们是有组织的,我们是有机体!
我们的生活由大大小小的组织活动构成,我们的生命就是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组织活动的层层套叠,庞大而复杂.
谈话、走路、吃饭、感知、开车,我们总是被组织结构所俘获.
这是我们的本性,事实上也是我们的生命状态,这是有关我们的基本事实.
重要的是,这些组织结构并非我们自己所造.
当我们走路、观看、倾听、哺乳或谈话时,我们不会指导、编排或创造这些组织我们的动态模式.
但我们也并非它们的奴隶——我们从事这些活动本身已然证明我们是活动的主体.
我们交朋友、找伴侣、从A点去往B点、在人群中认出某君,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但是我们会,至少很可能会,迷失在这些复杂的、构成了我们生活的组织模式里.
所有这些与艺术有什么关系答案很简单:我们从组织活动中创造艺术.
只有随着我们论述的推进,这其中的真正含义才会渐渐明了.
第2章重组自我上一章我介绍了一种思考组织的方法并阐明了我们是被组织的,我们被习惯性的活动组织起来.
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大部分的组织生活都已被编写好,但我们却并不遵从任何剧本;我们行动是出于习惯,但我们对自己的行为方式却常常缺乏了解.
例如,得知开车的同时打电话竟有这么危险,人们会感到无比惊讶,因为他们不知道,从道理上来讲,他们的注意力已完全被那些组织他们的活动占据,他们深陷活动之中.
现在我提出的观点是,艺术正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一基本事实——我们是由诸如哺乳、走路、谈话、感知这类活动组织、结合、联系在一起的.
现在让我们转向跳舞来对此假说做更深入的诠释.
·毋庸置疑,跳舞是一种组织活动.
我们天生就会跳舞.
跳舞是身体对节奏、音乐或动律做出的一种自然的响应,同时它要求发挥关注力和知觉辨识能力.
我们对于听到的音乐、舞伴的动作以及自己的动作都要高度敏感.
跳舞展现了一个人对自我的理解与认识,也表现了对彼此间的关系、与音乐的关系的理解与认识;跳舞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认识和感知活动;即便如此,它也是基本的、天生的和自发形成的.
不用说,跳舞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组织的,其结构可能很复杂却不容置疑.
一段舞可能有它的节奏组织;事实上,它与交谈和哺乳一样,也可以有轮流交替的组织结构.
人们有目的地跳舞,但他们并不决定怎样去跳,至少在由舞蹈带动动作并得到组织的意义上他们无需选择;跳舞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
有一个舞者可能会"领舞",但这也只是释放自己,任由舞蹈引领自己的一种特别方式.
优秀的舞者随兴而动.
当两个人共舞时,他们身体的律动、动作的变换、思维和对周围世界的感知完全受控于一种更大的组织,那就是跳舞本身.
跳舞有它的作用.
有人跳舞是为了结识男孩或女孩;有时我们跳舞是出于某种场合的需求——比如婚礼,或某些文化的赞礼;有时我们跳舞可能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感受,或者为了确立自己的身份,表明自己是该群体的成员.
记得托尼·莫雷诺(TonyManero)吗约翰·巴德姆(JohnBadham)1977年执导的电影《周末夜狂热》(SaturdayNightFever)里的主人公,由约翰·特拉沃尔塔(JohnTravolta)出演.
托尼跳舞有着最重要的原因,纯属个人的原因.
只有在舞池里他才感觉自己充满活力,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才能从自己琐碎卑微的生活中解放出来.
跳舞对他本人起着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值得强调的是,尽管托尼由跳舞找到了自我,发现自己与众不同、富有创意、备受追捧,但这在他身上所起的作用与跳舞并无本质上的联系;高超的运动技艺或者做一个成功的商人都可以发挥同样的作用.
在此是跳舞起到了这种作用,但这作用是跳舞的自然属性.
正如我们所见,跳舞是一种组织活动,它令人愉悦;虽然认知上复杂但同时也是基本的、自发的;它有明确的时间组织,也有明确的作用;它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舞者被卷入舞蹈之中.
我们被卷入舞蹈之中,正如婴儿被卷进吃奶一样.
你吃奶无需作出选择,正如你无需选择看见墙上的标语.
只要你识字,你就会不由自主地看见它.
甚至可以说,是标语撞见了我们.
我们被卷入构成我们生活的活动中——观看、阅读、走路、谈话、跳舞,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由活动构成的.
我们是有组织的,但我们不会自己组织,因此我们很容易迷失;我们没有向导.
·那么,依此背景,让我们来提一个问题:艺术舞蹈又是怎样的跳舞与艺术舞蹈之间是什么关系我希望大家明白,无论我怎样谈到艺术舞蹈,有一点必须清楚:它决不仅仅是跳舞的一种方式,一种人们称为跳舞的组织活动的参与方式.
为什么不是你可能会问.
舞蹈编创者不就是要创作舞蹈吗不,舞蹈是一种组织活动,你不能创造它们,你只能参与其中.
我们是被舞蹈俘获,舞蹈是自然发生的,是情景促成了它们.
人们舞之蹈之;他们决定舞蹈起来.
但是舞蹈的能力恰恰是释放自己的能力,甚至可以说是让自己随舞蹈动起来.
·好吧,因此说舞蹈编创者并不创作舞蹈.
那么,舞蹈编创者做什么一种合理的说法是,他们是把舞蹈呈现出来.
可是,呈现舞蹈又是什么意思呢设想一下房地产经纪人向我们展示一座公寓楼的样板间.
这是一套真实的单元房,它本身可租可卖,但却一直空着,就是为了做一个样板进行展示.
它的确是一套公寓,一个可以住人的地方,但它却有不同的用途.
它被用来展示住在这楼里会是什么感觉.
当然,从房产商的角度来说,它就是被放在舞台上用来展示的,配上家具、鲜花、装饰等,做成有人居住的样子,但却并不用来住人.
样板间与楼里其他普通公寓房的区别并不在于房子本身,其建筑、外观等并无差别,区别在于这房子的使用目的.
舞台上呈现的舞蹈也是如此.
当编舞者呈现一台舞蹈时,他是在展示舞蹈.
也就是说,他把跳舞本身呈现出来.
艺术舞蹈向我们展示舞蹈,实际上是,把我们人类作为舞者的一面展现出来;艺术舞蹈向我们展示舞蹈,同时让我们看到舞蹈在我们生命中的位置,或者说可能有的位置.
编创舞蹈呈现的是"我们由跳舞组织"这一事实.
这并不否认在舞蹈作品中时有跳舞发生,也不否认演员有时真的是在为我们跳舞,炫出舞技,展示动感.
正如样板房虽然不是家,却可以布置得与真正的住家一模一样,艺术舞蹈也可以与跳舞一模一样,虽然它并不真的仅仅是在跳舞.
艺术舞蹈就像样板间,它是展出模型,是一种展示,其目的是让观众去看并有所感触,或者去看并努力有所见,而跳舞做不到这些.
舞蹈表演绝不可能仅仅是把舞会搬到舞台上.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艺术舞蹈有时看上去会与普通的跳舞有着天壤之别.
舞蹈家如乔治·巴兰钦(GeorgeBalanchine)、威廉·弗西斯(WilliamForsythe)或杰罗姆·拜尔(JeromeBel),他们的目的和我们的目的不同,和托尼·莫雷诺的目的也不同,截然不同.
他们是要把舞蹈及其对我们的意义展现出来.
·如果说艺术舞蹈有它的意义,那它的意义绝不同于跳舞的意义.
托尼跳舞是为了实现自我;其他人跳舞要么为了庆祝订婚,要么为了吸引他人,要么就是为了自娱自乐,但编创舞蹈的意义绝不满足于此.
因为舞蹈——不是跳舞,而是舞蹈,即艺术舞蹈——它本身不仅仅是跳舞的一种方式,因此,它的目的不是要去实现我们通常跳舞所要达到的目的.
我想当然地以为,艺术舞蹈非常重要.
并非因为跳舞本身很重要,而是因为我们是舞者,而且这是关系到我们组织方式的一个深刻而重要的事实.
呈现一台舞蹈就是把这种组织活动展现出来,在此活动中,我们出于天性会沉陷其中,但又容易在其中迷失自己.
舞蹈展示了我们的一种组织方式,即我们是由跳舞组织起来的.
跳舞的价值是一回事,舞蹈的价值是另一回事.
舞蹈在我们的生活中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跳舞本身重要,而恰恰是因为我们是天生的舞者.
这一结论有着深刻的意义.
·舞蹈与我们的生物本性密切相关.
舞蹈源自于我们天性里的某种东西,它根植于我们的生物本性之中.
并不是说跳舞最好被看作是一种神经生物系统的现象,也不是因为观看演出是需要依赖神经系统的一种感知活动,尽管事实的确如此.
这不是我的意思,我要说的是,舞蹈与生物本性是另一种不同的联系,但更为直接.
舞蹈关注的是我们是怎样由跳舞组织起来的,重要的是,跳舞对于我们是天性.
沉醉于组织活动是我们的天性,而跳舞是一种组织活动,它是让我们沉醉其中的活动之一.
艺术舞蹈就是研究我们这种沉醉活动的一种实践.
我们天生是不自知的舞者,艺术舞蹈让我们邂逅自己的这一面.
如我们所见,艺术舞蹈,不是跳舞,它是把跳舞当作一种现象来参与其中.
而跳舞现象——组织活动——是天然的、根本性的、原始的,当然这并不是要否认它的文化性与习得性.
是天然的还是文化的,从人类组织的生物学立场来看,它们之间的分别已经失去了意义.
艺术舞蹈对人类组织的生物学做出了贡献.
生物学与组织的联系已经超越了组织活动的概念,这些联系表现在我们都是有机体这一事实之中.
我前面讲过,组织是生命的一个重要标志.
面对来势汹汹、试图分解我们的生命过程,生命物质总是要朝着自我维持、自我繁殖的方向组织起来.
细胞,或许是最微小的生命形式,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它要从周围环境中摄取能量,不只像小电器用电池供电来提供能源,更要利用它来制造自己、繁殖自己,创建并维护自己与外界隔开的界限(细胞壁).
借用马图拉纳(Maturana)和瓦雷拉(Varela)的一个新巧术语:自我创生(autopoiesis).
生命与自我创生密不可分.
这一观点又让我们想到了康德(Kant).
康德认识到,尽管牛顿力学给了我们描绘小到粒子、大到星球运动所需的各种原理,但这样的物理学仍不能解释生命.
生命过程——新陈代谢、生长、死亡,当然也是物理过程,然而却不只是物理过程.
生物体是一些特别的物理系统:这些系统的生命在于它们独特的组织方式.
如康德理解,它存在于它们自我组织的事实之中.
就我的目的而言,我要说的重点是:舞蹈,以及所有艺术——舞蹈只是我选的一个代表和例证——都是在努力寻求提出、展示、揭示和阐明我们的这一面,即我们发现自己怎样被组织起来.
舞蹈以及所有的艺术都是组织实践,或者,我们会发现,它们是重组实践.
它们的价值直接源自于组织的根本意义——组织在塑造人类、事实上是所有生物中的根本意义.
艺术舞蹈是哲学.
如果这一论点正确,舞蹈编创者所做的,就是要找到一种方式让我们看见,用海德格尔(Heidegger)的话来说,一种隐蔽的、含蓄的或是躲藏在背景中的东西,即跳舞在我们生命中的位置,或说是我们在这种活动中的位置,在这种称作跳舞的自我组织的复杂活动中的位置.
舞蹈编创者把所有这些展现出来,让我们看到舞蹈在我们生命中的位置.
艺术舞蹈显露的是关于我们自己的某些东西,因为它是我们所从事活动的自发性结构,所以在我们的视线中隐匿了起来.
这是一种典型的哲学活动.
回想一下我们从柏拉图文章里了解到的苏格拉底的哲学实践.
这些对话都有一个熟悉的结构:参与者试图表达他们的所知,却遭遇一个尴尬的事实:他们说不出自己知道什么,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并不具备他们自以为拥有的知识.
当然,与此同时,通过探究、对话——通过提出他们以为想说或有意要说或迫切想说的东西——他们获得,或至少能够获得某种类似感觉一样的认识,知道他们的观点怎样联系起来、组织起来.
柏拉图说,知识就是回忆.
在此,这一论断意味着,它与收集新的信息无关,而是发现你本已拥有的信息——你自己的经验、观察、信念等——怎样联系统一起来.
我们思考、质疑、辩论——这表明我们会在自己复杂的思考活动中迷失方向.
柏拉图将所有这一切展现出来,并由此给我们提供一种找到自己的方法,一种在迷失的地方找到出路的方法.
其结果不是一种确定的知识或无可争议的结论,或诸如此类的东西;相反,这种结果更像是一种领悟,大致来说,就是在此你知道路在何方.
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说道:"哲学问题有一个共同的形式,那就是,我找不到出路.
"意思就是,我迷路了.
他的哲学方法实际是,创作一张可用的地图("清晰地呈现"),让迷路者找到方向.
如果我说得没错,这正是舞蹈的目的——把我们作为舞者的自我形象表现出来,让本来隐蔽或不曾领会的变得清晰.
舞蹈作品——艺术作品——富含哲理.
或者,更明确地说,哲学和舞蹈的目的都是同一件事——一种领悟,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来讲,它要有一个清晰的呈现——只不过它们是在我们不同的存在领域里做着同一件事.
哲学是观念、概念和信仰的舞蹈,因为所有这些只存在于我们的思想和谈话这些组织活动中;而舞蹈是跳舞(或身体动作)的哲学.
哲学和舞蹈的出发点都是"我们是有组织的",但我们自己并非这种组织的作者.
舞蹈是一种哲学实践,哲学是一种舞蹈实践.
或者,还有一种更易领会的说法,即舞蹈和哲学是同属于一个范畴的两个分支,如果需要一个更好的名称,权且让我把它称作是对我们组织的研究.
哲学和舞蹈都是组织和重组织的实践.
它们是实践(不是活动)——研究方法——目的是阐明我们发现自己怎样被组织,并由此找到我们重组自我的方式.
·你可能会表示反对:肯定不是这样!
舞蹈热情奔放,大汗淋漓;它是身体的运动,音乐的诠释;它有感情,舞蹈不像哲学那么高冷和学究.
即便舞蹈也有学识上的关注,但舞蹈与哲学关注的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但是这里出现了两个误解.
首先,哲学的确需要学识,但它完全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高冷,在第11章中我们还将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
它源自于困惑,热衷于辩论,致力于说服,哲学进行得如火如荼.
相反,在这种意义上,舞蹈可以说是相当高冷的.
再者,我并不是说舞蹈和哲学性质相同,或者说是阐释哲理的冲动激发了舞蹈家,或者说跳舞的愿望触动了哲学家.
不,不是这样的,哲学不同于舞蹈就如同绘画不同于音乐,诗歌不同于雕塑.
但是,从根本上来讲,它们做的都是同一件事:我们是由自己所做的事情组织起来的;它们要把那些隐含的组织方式揭示出来.
第3章天生的设计师艺术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们总是在忙于制作.
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制作东西——绘画、雕塑、建筑、装置.
艺术似乎在从事手工艺和技术,它们总是与劳作和建构密不可分,即使是表演艺术——像音乐和舞蹈——在实践中也总是密切联系着.
音乐家使用乐器就如手艺人使用工具,舞蹈家和歌唱家的功夫、技巧常常令我们叹为观止.
难道画家和雕塑家是一种特别的手工艺人或技术工匠吗艺术与精湛的技术、手工艺、表演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与艺术作为组织实践又有什么关系很多艺术家就像叮叮当当的修补匠,或是疯狂的科学家,或许像运动员和马戏团小丑,就是一点儿也不像哲学家.
这样的描述未免有失艺术高傲的身份,但事实的确如此.
可是艺术起源于一种创作的冲动,这又该作何解释现在就让我们从这类问题入手.
这里有一个简短的并不完全的答案:艺术与组织活动之间有一种密切的联系.
大致说来,工具(比如锤子或电脑)是组织活动的核心.
技术不是简单的东西,它是我们用以实现组织活动的工具.
技术组织了我们;确切地说,它们是不断发展的组织模式.
一旦清楚地认识到这一联系——技术是组织模式——我们就可以理解,哺乳实际上是一种原始的技术;同样,跳舞也是一种技术活动.
所谓发达的技术实际就是指我们以更为复杂的方式来组织自己,但基本的组织原则都是一样的.
艺术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实践,就如舞蹈也不仅仅是一种跳舞方式,但是,艺术要以技术为前提,只有在此背景下我们才能读懂艺术.
舞蹈关注的是"跳舞组织了我们",而绘画(比方说)则是在对"图画(或者说图画制作和图画使用的技术)组织了我们"这一事实作出反应.
图画,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技术,而图画制作和图画使用是组织活动.
因此,它们都是艺术的原始素材.
画家可能会作画(尽管从是否描绘什么、是否准确、是否逼真的意义来讲,并非所有的绘画作品都是图画),但这并不代表他的职责就是要画更漂亮的图画;同样,舞蹈家的职责也不是跳舞.
有时,画家和舞蹈家的艺术恰恰是在画家不能画画、舞蹈家不能像一般舞者那样动作时得到了展现.
失败是艺术最为重要的研究渠道之一,而如果艺术家只是技师,只是工匠,那么失败就毫无意义.
要让这观点更加清晰、更有说服力,我还需要列举更多的事例.
本章我将进一步探讨技术的本质;在第4章里,我再详细论述我的根本论点;然后,在第三部分中,我会让大家看到这一论述如何帮助我们解读绘画艺术和音乐.
·关于技术,有一件事引人瞩目,即技术于我们是天性.
虽然这个观点已不再新鲜,但它值得我们再重复一遍.
就如蜜蜂要筑巢、鸟儿要搭窝一样,人类天生就会使用工具.
我们是天生的设计师,这个结论在考古记录中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在超过上百万年的时间里,我们的祖先在技术上并没有重大突破.
有证据表明,他们使用简单的石头工具凿凿砍砍,但几十万年过去了,找不到证据显示这些简单的技术有任何改进或提高.
在5万至7.
5万年前,人类使用工具的能力出现了革命性的大爆发.
此时我们发现了具有特殊功能的高度改良的工具的遗迹,甚至有制作工具的工具.
同一时期,人类开始穿上衣服并使用图形技术(著名的洞穴岩画).
也许正是此时,我们人类开始像现在这样讲话.
现代人类,在行为上和认识上的智人,大约出现于5万年前,这一事件恰好与技术发展的大爆发时间吻合.
这种创造能力的异常爆发与变革社会的创新该作何解释有一种可能是我们变聪明了.
有人说,这时出现了大脑的突变.
但至少有一个理由让我们对此持怀疑态度:我们缺乏创造力的祖先在生理上似乎与我们没有什么差别,至少我们从他们的遗骸中可以这样判断.
我们都知道,解剖结构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在这种技术大飞跃至少10万年之前就已存在了.
还有另一种解释:人口的变化可能会帮助我们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
也许我们一直都是聪明的发明者,或至少在我们的创新开始很久之前我们原本就很聪明.
但由于我们各自生活在孤立的小群落里,或许我们的发明没有一件能够传播开来或得到传承,结果,没有人能继续累加我们的成就.
或许我的子孙没能学会或者我们的群落里没有子孙能学会我会做的事.
总之,如果我们必须疲于奔命且手头只有自己生产的资源,那么我们的创造力将受到极大局限.
人口密度的小幅度增加就会改变游戏的规则.
群体变大、与其他部落的接触增多,使贸易和分工的出现成为可能.
如果你能供给我需要的东西,我就可以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改进工具上.
而如果我周围有足够多的人,其中某个人就可能成为我的学徒,学会我的技艺,并继续加以改进.
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在这一时期,相对较远的部落之间产生了贸易.
所有这些都只是推测,值得深思的是这些推测背后的几点深刻意义.
首先,不要以为我们使用技术是因为我们变聪明了,或许让我们集体变聪明的正是新的社会组织形式.
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
有人说,我们使用工具毕竟与动物有所不同,哪怕是筑巢的动物.
神经学家约翰·克拉克尔(JohnKrakauer)在一次交谈中曾对我讲到,把人的手接到大猩猩身上,它仍然不能用手完成我们能完成的事.
明白这一点,你就能理解这种观点了.
我们不单单使用工具,我们还思考问题,而其他动物能否做同样的事,我们并不了解.
然后,这些新型的社会组织,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的群居方式,形成了一个游戏场,在此,新技术得到培育和发展.
如此说来,如我早先提出的,技术可以被看作是不断发展的组织形式.
这很容易理解.
设想一件工具,如门把手.
只有以整个生活方式作背景,我们才能理解这样一种工具.
门把手只有对居住在房子里的人才有用,他们需要用门来抵御寒冷,阻挡陌生人和野兽的闯入,用门来保障夜间安全和保护财产.
再进一步说,很显然,门把手有一个先决条件:我们要有这种特别构造的身体,有能够使用门把手的手,我们的身材能够够着门把手且有足够的力量来推动门本身的质量.
要让门把手这样的发明粉墨登场,首先需要搭建一个文化和生物学舞台.
但是,门把手一旦出现,使用门把手这一事实本身就退到了我们生活的后台背景中.
我们基本不需要停下来思考有关门把手的问题.
除非我们是设计师,否则我们无需经常想起它.
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进出房间上,集中在我们要做的事和要去的地方上.
使用门把手开门关门成了第二天性.
事实上,门把手成为我们在自己建造的房子里和居住的地方来回进出这一整套小小组织活动的核心.
我们由门把手组织起来,自然而然地伸手,恰好握住它们.
·这里我们忍不住会想,人的问题及需要是有限度的,只不过用来搞定事情的工具和设置因时而变罢了.
可是这种想法错在哪儿呢设想一下,你正在飞越大西洋的半途中.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你所做的事也是早在人类历史之初人们就开始做的事: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一个地方.
从这一视角来看,飞机与火车、汽车、马车,与我们自己的脚并无区别.
它只不过是一种把我们从A点带到B点的工具.
但我们也需要知道,我们是在地球上方5英里(约8.
05千米)的高空中飞行,我们是在做一件全新的事.
没有技术,我们根本无法做到.
重点是,剔除了技术——飞机以及支撑商业飞行的复杂的信息合成数字系统——你看到的不是以不同方式飞行的人类,而是根本不会飞行的人类.
既然我们是飞行的人类,既然这种出行方式和彼此联系于我们已经必不可少,那么,鉴于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通信方式,离开了飞行所必须的技术,我们将不复是我们.
我们的生存方式——我们生活的组织方式——可以说,是由技术构成的.
将技术剔除之后,剩下的不是我们,而顶多只是我们的"远房表亲".
再设想另外一个例子,现代公司办公环境.
电话让不同地方的同事之间可以谈话,电子邮件也使得通信更为便捷.
不仅单人与单人之间,单人与多人、多人与多人之间也都能方便地交流.
如今的办公通信系统——比如户内社交网络软件——使公司能够获得一整套全新的组织形式.
脸书(Facebook)让人们建立了与他人的联系,不断更新的状态吸引着人们的关注.
而户内社交网络系统,如吱吱喳喳(Chatter)使得社交网络不仅可以以个人为主,还可以以话题为主得到组织.
话题不仅穿越了办公空间和项目团队的界限,还把公司间互不相干的群体联系起来.
现在设想你在一个有着上万员工的大公司里正努力解决一个问题,你可以查找有关此话题的历史聊天记录,基本可以获得整个公司的信息.
如果仍有问题,你可以明确地知道该与谁联系,这人可能你从未谋面,也可能他在世界的另一端.
现在,除去组织公司业务的软件技术,你再来设想一下这家公司.
你想象不出,去掉了组织技术的公司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组织.
技术不仅仅是满足我们原先已有的需求,也不仅仅靠扩大我们所能做的事来满足我们的需求;它是让我们做一些全新的事情——不仅解决旧的问题,同时也形成新的问题.
·这些思考产生了一个深刻且令人激动的观点——恕我一再重复——技术本身就是不断发展的组织形式.
技术组织了我们,也因此使我们成为我们这样的人类.
"技术"一词源于希腊语technē,意为技能和手艺.
想起技术,我们常常会想起工具、器械、建成的网络、基础设施,等等,我们会想起硅谷和生物工程.
但是,追根溯源,技术是一种技术活动,是专门技能、聪明才智、融会贯通和深思熟虑的代名词.
在哺乳这种最原始的组织活动里也存在技术.
我们已经看到那种从开始尝试去做、努力做好到后来熟练掌握、流畅进行的转换过程.
再回想一下我们学习第二语言的经历,先是痛苦的词汇记忆和语法学习,我们要花大量的精力去思考单词、语法、发音和习惯用法,但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所有这些都淡化了,我们发现自己只是在使用这种语言,不必再去思考是怎么用的.
此时,语言不再是一种协调我们与他人、与周围世界关系的中间媒介,而成了我们与他人、与周围事件取得沟通的直接方式.
这种见解让我们体会到技术是天生的,也就是说是基本的.
技术是由技能组织的活动.
哺乳、谈话、跳舞,以及第2章讲到的组织活动,以这种方式来看,都是技术实践.
·你试过在电话里跟小孩子讲话吗小孩子不会打电话.
打电话之所以对小孩有困难,是因为它与面对面交流不同:你说话必须更清楚,而且必须要敏感地知道对话的性质不同.
当然,你还必须注意要以不同的方式向对方传递信息,因为你们互相看不到对方,不像在同一空间里那样注意力指向同一件东西、同一篇文章或同一件事.
但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更令人信服的理由.
小于10岁(比方说)的孩子不会以我们成年人的方式进行交谈.
交谈是一种表现亲密和分享自我的方式,就像跳舞、拥抱或辩论;它不只是为了分享信息和解决问题.
尽管有的小孩善于拥抱,当然也会欣赏音乐并随之舞动,但他们通常不懂得怎样像大人一样与人共舞,也不懂得怎样交谈.
相比之下,青少年就不同了,他们自主与他人培养感情的需要来得非常强烈.
对他们来说——至少我年少时是这样——电话非常重要,而花一整个晚上与人漫无边际、天马行空地海聊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我想用这一例子说明,技术也就等同于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以及我们知道哪些事该怎么去做.
技术是我们做事的组织方式.
但是,这种等同有一惊人的结果,我们早先已经注意到了:技术担负着深重的认知意义.
技术使得我们能做许多离开了技术则根本无法完成的事情——飞行,现代职场里工作;它也使我们产生了许多若离开技术则根本无从想象,也无从理解的观念和思想.
无论从保守还是激进角度来看,事实都是如此.
保守地说,技术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的解决方法,同时也产生了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我们需要更先进的捕鼠装置;内燃机在不断改进;电脑操作系统的更新永无止境;甚至是一个不起眼的门把手.
技术不是静止的,它欢迎也鼓励改良和提高.
在当下做名工程师就是直接跳进发展进程的中间,接过先人留下的担子.
工程师,无论是软件工程师还是修路建桥的工程师,都无需思考他们所做事情的发展历史,但是他们思考的每一件事——引起他们兴趣的、重要的问题——都是由历史决定的.
这种思考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
技术抛出的问题实际是关于如何生存的问题——如何更高效地去做我们本来在做的事(飞行、驾驶、使用电脑,等等).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早已身处技术的海洋中,我们根本不会想到这些问题.
生活的长河不断流淌,我们总是处于河中游,总是在生活之河的半道上.
技术让我们产生新的思考,还有一层更为激进的意义.
我会进行复杂的计算——解二次方程、算出我该缴多少税、在餐馆买单时算算我们每人该付多少钱——可这都要归功于我知道怎样使用数学运算符号.
算术符号是我进行数学思考的工具,离开它们,(至少是)我根本无法计算.
最初,算术符号的产生是为了记录.
为了记住自己拥有多少只羊,我们先是在包里放等量的石子,然后学会了在木头上刻下道道,或在地上画下记号.
可是一旦我们有了算术符号,使用符号来思考新的算术问题就成为可能.
现在我们学校里教的数学就是这样.
我们先是学习怎样写数字,然后利用这些书面符号进行简单的运算,最终解决复杂的问题.
没有符号也能进行基本的数学推算,婴儿和动物在此方面都表现了良好的才能.
但是,如果没有书面符号和图形,你能想象实数、素数、超限数、群、拓扑学等这些概念吗不能.
但是,在此我们必须当心,因为这种表述往往会导致低级的误解.
数学运算需要用到符号并不意味着数学家要研究符号体系(尽管的确有专门研究它的数学分科).
我们计算的时候不再去考虑数字,就像要数清自己有多少只羊我们不会去想这是些石子一样.
我们用石子和数字来思考我们拥有多少只羊.
这一观点不只局限于符号,我们可以将其扩展至语言本身.
思考事情有一种方式是盯住它看、关注它、把它拿在手上仔细观察.
但是,如果一件事情在空间、时间上都天遥地远,你怎么去思考它你怎么去想象裘利斯·凯撒未来七天的早餐你要吃些什么太阳系的引力中心在哪里宇宙大爆炸是什么你尚未出世的后人会过怎样的生活我们需要以某种方式在思想上抵达这些问题.
我们使用语言、文字.
现在,思考这一问题:你的思想发生在哪里你会说,它不仅发生在大脑里,还发生在手上、在纸上或在键盘上.
因为即便你像许多认知科学家一样,相信我们进行算术运算的能力要依赖我们大脑思考数值、进行推理等诸如此类的能力,很显然,它同样要依赖我们使用外在符号的能力,就是我们写在纸上或黑板上的那类符号.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说技术不仅扩展了我们能做的事,还扩展了我们是怎样的人.
我们的思想流出我们的大脑,流在纸上,流进世界.
哲学家安迪·克拉克(AndyClark)(爱丁堡大学)和戴维·查莫斯(DavidChalmers)(纽约大学)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在哪止步余下的世界又从哪里开始似乎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大脑里的东西要比我们写在纸上的东西更为优越.
对于我们的思想来说,对于那些让我们感兴趣的思考和问题来说,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
思考更像是架桥或跳舞,而不像消化食物.
我们从根本上而言彻头彻尾就是技术的生物.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思想,如同跳舞、旅行、谈话一样,是一种组织活动,而技术是不断发展的组织形式.
·现在,回到我们的主要论题:我们是有组织的,但是,在纷繁复杂、天罗地网般的组织模式里,我们往往会迷失自己.
我以为,艺术,正是由此获得了它的原动力.
艺术,以及哲学,同样都是研究我们组织模式的实践,或者说是研究我们以不同方式参与不同组织模式的实践.
艺术决不只是更多的组织.
明白了这一事实,明白了技术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是根本的、生物的、不可或缺的,那么,艺术总是关注着制作东西——绘画、雕塑、建筑等——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艺术的绘画,以及雕塑、建筑等恰恰是要研究我们的生活是怎样被制作图画的技术以及其他相关的制造技术组织起来的.
艺术产生在描绘与制造的领域,并非因为艺术家对制作更好的捕鼠器或画出更逼真的图画感兴趣,而是因为描绘、制作等从深层来讲都是重要的组织活动,也因此是我们经过了文化陶冶的人类天性里非常重要的方面.
第4章艺术魔圈与伊甸园本书的基本论点是:我们的生活是由组织构成的.
艺术把我们的组织带进我们的视野,如此一来,艺术重新组织了我们.
因此,作为艺术家的画家,其真正的事业并非作画.
而正如我们一直探讨的,舞蹈编创者实际也并非在跳舞.
由此,我们可以考虑有两种层阶:第一层阶(简称"一阶")是组织活动或是技术的层次;在第二层阶(简称"二阶")上,低层阶的组织本质得到展现和审视.
在第一层阶上,我们有像谈话、运动、跳舞、绘画、唱歌等这样的活动.
一阶活动的显著特征是它们都是基本的、不由自主的组织状态,它们是我们出于天性或习惯成自然的第二天性所做的事.
但这并不否认在这一层阶上,许多活动如谈话、跳舞、绘画等都具有社会属性和文化特征.
与之相应,在第二层阶上,我们有不同种类的艺术:诗歌与小说、绘画与摄影、舞蹈、音乐,等等.
二阶的实践来源于一阶的活动,却又重塑了一阶的活动.
本书贯穿始终的主题是:哲学是一种第二层阶的重组实践,它立足于我们第一层阶的认识活动——推理、辩论、信仰的形成,更重要的还有,科学研究——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恰如舞蹈编创之立足于动作与跳舞,或者,作为艺术的绘画立足于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的绘画活动.
第11章中我将直接探讨这一主题.
我们再来考虑一下工具.
工具只有在其被使用的语境下才有意义,剥离它的语境,它不过是一个物件.
图画也是这样,第5章我将专门讨论这一话题.
去除一张图片的标题,或把照片从家庭相册中取出来,脱离了语境,那它作为图画的意义就不复存在,它不再有任何描绘价值.
艺术的兴趣就在于去除工具所使用的背景,由此使它们变得陌生、奇怪,通过让其陌生化,让人们去思考那些原本想当然的使用方式和背景.
一件艺术作品就是一件特别的工具,一种奇异的手段;我们创作奇特的工具来审视我们自己.
这种叙述只是接近主题的第一步.
比如,当我们强调编创舞蹈,确切地说,是在研究跳舞而不是参与跳舞的一种方式时,我们让人们认识到了舞蹈艺术的重要一面.
可是,这样一来,舞蹈就是高层次的跳舞,或者,艺术实践,如我所说,就是高层次的活动,这种想法未免太过简单了.
那么,就让我们再深入、再复杂一点吧.
首先,请思考,尽管艺术和哲学都是在研究我们是怎样被习惯性地组织起来的,但重要的是,这些第二层阶的活动产生于第一层阶的活动.
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就像是绘制地图,关键是,人们绘制地图并不是为了收藏,而是因为没有地图人们就容易迷路.
我们需要编制一份地图来表现大地的延展;这一任务源自于一种真实的需要,一种真切的焦虑感.
艺术以及哲学就是如此.
一阶的活动——走路、谈话、唱歌、思考以及出于各种目的制作和使用图画——组织了我们,这些活动形成了我们所处场所的地形概况,但我们对于这一地形的延展缺乏认识;我们可能会迷路.
于是,我们求助于艺术和哲学,这样,在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我们就可以找到方向.
艺术,以及哲学,是组织或重组织的实践,是某种试图弄懂我们自己组织方式的实践.
这些实践活动的存在源于真切的、事关重大的需要.
正是在这里,在这一需要扎根如此之深的事实中,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艺术总是与情感和感受有着深刻的渊源.
迷失自己,找到自己的方向,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感受深切呢.
因此,通过把事情深化,而不仅仅是一阶活动对应二阶活动,我们看到了第一个重点:二阶的重组织实践产生于一阶的组织活动之上.
它并非高高在上地俯瞰这种活动,相反,它是源自于活动内部的一种动力,要弄清我们究竟在哪里能找到自己.
因此,艺术与我们的生活领域、与组织活动有一种根本的、真实的、至关重要的联系,艺术正是来源于此.
深化的第二点:重组实践反过来改变了一阶的活动.
以跳舞为例.
跳舞是我们的天性,艺术舞蹈将这一事实展现出来,让我们去观察去解读.
但是,艺术舞蹈的存在——它们的形象、它们的力量:凝聚力以及作为样本示范活动而凸显出来、指示我们该怎么做的力量——又反过来影响并塑造了我们关于跳舞的观念,由此指导我们该怎样跳舞,哪怕是在我们独处时或身处最熟悉的环境中.
在一个有舞蹈再现的世界里,艺术舞蹈为我们跳舞做出了示范,再要脱离舞蹈形象去跳舞就几乎不可能了.
观看人们跳舞,你会发现他们是在表演,他们引用和抽取他们学会的动作、姿态、神态、舞步和风格,原本那种天然的、随心所欲的、未经雕琢的跳舞动作仿佛都来自于同一动作库(motionbank),全部盖上了文化的烙印.
我们原本灵感闪现、激情四射、自我陶醉的跳舞得到了舞蹈的组织而变得循规蹈矩.
编创舞蹈反过来影响和改变了其本源的一阶的活动.
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舞蹈编创的新素材,即我们人类作为舞者得到组织的一些新的方式.
这个过程的一个后果是,跳舞和舞蹈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因为我们跳舞时舞蹈的痕迹无所不在.
另一个结果是——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重要的论点,前面我多次提及这一观点却未曾解释和证明——我们跳舞得到了艺术舞蹈的重组.
那么,最终,这就是艺术的重组方式,它能重组是因为它被领会、被消化,然后再次作用于一阶的活动.
没有什么能比文字更完美地阐释艺术的魔圈结构及其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了.
我们普遍认为,相比口头语言,文字是新近的发明——只有几千年,最多不超过1万年——而口语则比较古老,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之初.
口语属于人类的生物传承,而文字则是约定俗成的、文化的产物.
无论这一区分正确与否(下文中我会说明这并不完全恰当),我们都可以放心大胆地说,语言的概念是由文字和书写在我们语言生活中的作用形成的.
在我们看来,文字就是语言的影像;我们以为,书写揭示了语言的样貌.
自始至终,我们都认为语言是可以书写的.
文字可能不是语言的镜子,但它却反映了语言的自我形象.
无论是普通人还是语言学家,我们首先要掌握文字作为一种表达语言的方法,然后才能形成关于语言的思考和体验.
我们能够感受语言,是因为语言出现在文字作为技术——以及意识形态——的语境中,但我们往往忘记这一事实.
文字塑造了我们的语言概念,由此形成了我们对语言学现象的体验,这一事实往往被忽略.
阅读完以下事例,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
这是节选语言学教科书的一段介绍,作者试图解释语言结构的概念.
假如发声顺序只有线性结构(即一个音紧随另一个音),那么,句子就可以写成一个连续的发声顺序.
例如:(3)thisboywillspeakveryslowlytothatgirl.
但是句子并非没有结构的发声顺序:任何一个母语为英语的人都可以告诉你(3)中的发音是以"单词"分组的,并且能告诉你怎样把单词划分开.
例如,我们都认为(3)中的单词可以划分成以下(4)的样子:(4)Tisboywillspeakveryslowlytothatgirl.
(这男孩会很慢很慢地对那女孩讲话.
)而不是像(5)这样:(5)Thisboywillspeakveryslowlytothatgirl.
Thisboywillspeakveryslowlytothatgirl.
但是,尽管英语的拼写体系提供了一个系统的表现方式,呈现了发音怎样形成单词,但总体来讲,对于单词怎样形成词组,它所提供的表现方法很不充分、不连贯也很零散.
例如,我们一致认为(4)中的very要与slowly一起,修饰slowly,而不是speak——但我们的拼写体系却不能体现这一事实.
为了表现这种次语法上的结构关系,我们把两个单词划为一组独立的单元,如下:(6)Tisboywillspeak\[veryslowly\]tothatgirl.
同样,我们也都一致认为that要与girl一起,而不是与to在一起.
于是,再一次,这种直觉只有靠把两个词划在一组才能得以体现:(7)Tisboywillspeak\[veryslowly\]to\[thatgirl\].
同样,我们有着共同的直觉,this要与boy一起,可以如下体现:(8)\[Tisboy\]willspeak\[veryslowly\]to\[thatgirl\].
语言学家所说的,关于哪个词与哪个词"在一起"构成结构单元的"直觉",我们不可能会有所不同.
但在这个介绍中,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似乎根本没意识到这种直觉恰恰就是关于"我们该怎样书写语言"的直觉,而不是关于话语的直觉,好像话语会摆脱书写的塑造作用似的.
按要求我们应把字词作为图形元素来考虑,它们可以也应该写在一起.
请注意,作者把单词、句子、词组的归类视作理所当然,这本身就已表明,关于语言是怎样构成的,我们早有一个本体论深植于文化之中.
在实际讲话中,流畅的语音和动作让你根本不会去注意单词和词组.
或者相反,你的确发现了它们,因为在我们创建文字体系来代表话语,由此来规范话语时,这恰恰是为我们讲话人设立的本体论.
在潜在的物理声音中你找不到单词和词组.
"我们一致认为",是的,我们都生活在一个语言世界里.
就像全垒打和安打虽然在棒球场外根本没有存在的余地,但棒球迷们说起它们时却再自然不过.
因此,说单词、词组、句子、哪个词跟哪个词在一起,只有在我们语言游戏的场景中才有意义.
而就表现游戏动作的方式来说,这里的语言游戏早已形成.
在语言世界里,我们用的是文字.
文字并非从外部来代表语言,形成发音和词形.
我们把"cat(猫)"写作CAT,我们认为CAT通过拼出这个字的读音(我们如何念cat),由此拼写出了这个单词.
但是,如果不是已有样本告诉我们怎样(以书写来)表现它们,我们对它们的读音一无所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会写那些本来就是单词的声音.
门实际发出的吱吱扭扭声、地板的叽叽嘎嘎声,我们是写不出的.
我们用文字表现的不是声音,而是话语或语言.
而它表现出的声音也不是像物理学家所想的那种声音.
它们是我们可以写在黑板上的字,必须是能拼写的东西.
我们的书写不会脱离语言领域;书写本身就是我们用语言所做的标准事之一.
因此,单说口头语言要早于文字,而文字是作为一种代表口语的技术被创造出来的,这种观点不足以证明书写怎样塑造了我们现在样子的口语.
我们不可能退回到过去,抹去文化的印记,从书面语中剥离出原本真正的口语.
我们可以想象语言在其天地之初的模样,在伊甸园里,那时还没有文化、阶级和文字来实施它们的控制标准和规定.
但是,事实上,一代又一代语言使用者因为意识形态的限制和文字的使用已使语言发生了很大变化,再来区分语言本来或曾经的样子与其经过陶造之后的样子已经毫无意义.
看起来口语是一阶的、文字是二阶的,但在我们生活的语言领域,语言使用者已经不可能再脱离文字的影响去思考语言;我们已经不可能回到大堕落之前伊甸园的样子.
二阶的语言——它的概念体系、它的自我诠释——已经与我们口语中、我们生活中的语言水乳交融、难解难分.
我们已经发现,语言学,一直自视为一门科学,可能你并不赞成这一观点.
语言学理论——即当我们知道这是一种语言的规则体系时所了解的理论——其证据基础就是一种语言的讲话人关于哪些发音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符合语法、哪些不合语法所作的判断.
但是,是否符合语法的判断并不能给我们信息让我们理解语言的本质,即作为一种生物天赋,语言自然的特征,也就是说,非文化的特征.
这些判断只不过是我们在进行自我理解,一种彻底被文化渗透且受到意识形态塑造的自我理解.
书写,以其约定俗成的标准——受媒体、阶级、社会权力等的影响——会篡改口语.
对此,有人表示反对.
有些传统的文体规范会统辖书写,但在街头小贩或是放学后街上玩耍的孩子口语中你却听不到.
无疑这说法没错.
权且让我们要求,书写享有特权,免除了口语规范;事实上,那些规范可能很奇怪、不准确或百般规矩.
但也要注意,文字,一方面给我们资源,让我们得以思考自己在讲话时是在干啥,另一方面,它也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思考自己的说话方式,由此以不同的方式说话.
事实是,书写,通过给我们提供一个口语的样板——尽管口语充满了规矩——反过来改变了我们的说话方式.
我们的口语总不能脱离文本和写作的左右.
就如一个孩子在舞池里会学着罗宾·西克(RobinTicke)的样子跳舞,见过西克的舞蹈之后,他就不可能再无动于衷,仍按其原本的方式随心所欲地舞动.
说话也是一样,我们会照着在书中看到的人们的讲话方式讲话,或照着(比如在影院、剧院里或在电视上)听到的人们讲书面语的方式讲话.
书写,作为一种语言技术,对于人们用口语交流多少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对表述某些意图也较为实用;它最终反过来改变我们关于说话的思考,因而也改变我们说话时关于自己的思考,以及怎样说话的思考.
这当然会进而导致我们的书写发生更多的变化.
这种循环从未停止,其结果就是一个紧凑的、有着历史痕迹的、多层次的脚本化语言结构.
那么,我的主张是,艺术与哲学(二阶的实践)与它们的原始素材(一阶的活动)之间的关系就好比书写与口语的关系:说话人发明文字用来示范该怎样讲话,或向他们自己呈现语言;这种语言形象的存在,又反过来改变和重组了我们原本的说话方式.
·实际上,哲学与其他艺术、与文字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类比.
我还要说,艺术以及哲学,其实都是热衷于创作书写的活动.
·关于哲学起源,有一个流传久远的神话,它始于交谈,始于对话,而不是书面的文字.
毕竟,柏拉图的老师,最早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从未写下过一个字,我们对于苏格拉底的认识全部来自于柏拉图的文字记录;他所重建的记忆中或假想中的对话.
事实上,无论苏格拉底是否曾书写,他的哲学作品从根本上说都算不上交谈.
苏格拉底的对话不是以交谈开始,而是以打断交谈开始;他质疑他的朋友同仁们日常进行的思想与谈话.
因此他让他们感到愤怒;可能正因如此,他被同时代人视作是一种威胁.
苏格拉底总是在告诉他们,他们的谈话不够水准.
例如,尤西弗罗(Euthyphro)告诉苏格拉底他为什么要去法庭.
苏格拉底没有顺着尤西弗罗继续与之交谈或讨论,而是挑衅他为自己的行为讲出理由.
他迫使他去讲清他以前从未费心想过要讲清,也不知道该怎样讲清的东西.
尤西弗罗,苏格拉底也一样,他们都缺少一种方法,一种工具去讲清楚统领他们思想和行为的东西.
对于他们的思想活动,他们没有一个清晰的观点,一个清晰的认识.
苏格拉底的对话远非交谈,而是一种质问(或曰反驳,希腊语里的enlenchos).
但是质问的目的是质疑对话本身,暴露它的局限,把我们原来想当然的东西——例如,我们使用词语所表达的意思——当作一个问题放到审视焦点.
苏格拉底站在对话的背后,站在我们进行的思想背后;他刺激我们尝试去审视所有这些我们想当然的东西.
一个苏式对话被展现出来,它是对话的典范,但不是对话.
它是哲学,或者,我们可以说,它是艺术.
苏格拉底也许没有写下任何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满足于口头表达,满足于只用对话.
苏格拉底占据着一个有利位置,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第一次可以认真地尝试创造一种方法来呈现我们的谈话和思考实践.
因此,苏格拉底向书写的创造迈出了第一步,至少,作为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他感受到了这种需要.
柏拉图对诗歌与艺术的著名批判是在《理想国》(Republic)中.
他认为诗歌贻害无穷,是人类灵魂和社会的毒品.
既然柏拉图视诗歌与其他艺术是对哲学宗旨的侵害,那么,我们还能认真地把哲学与艺术看作是一回事吗我们当然可以,因为我们认识到柏拉图抨击的并非真正的诗歌,而恰恰是荷马与赫西奥德的诗歌中所表达出来的那种口头的、史前无文字的文化.
荷马史诗不是用文字书写的诗歌;荷马史诗没能将文字用作它的素材,而是随意地用词,以及词汇所表达的思想与生活习惯.
在柏拉图看来,《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就像是流行的曲调,它们的创作设计纯粹是为了方便记忆,这样就使它们能够不具批判性地发挥作用,永久保存希腊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
柏拉图讨厌诗歌是因为它不过是歌咏,不过是口头吟咏.
雅典贵族讨厌苏格拉底——他们判了他死刑——是因为苏格拉底拒绝只满足于讲话.
在柏拉图看来,荷马史诗中没有艺术,恰恰是因为里面没有哲学.
而荷马史诗里之所以没有哲学,是因为它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无文字的思考模式.
舞蹈编创者知道自己,至少可能是在探索一种尚未发现的记录方法.
舞蹈编创(字面意为"跳舞+编写")这一词汇本身就能表现它的自我定义.
编舞在努力争取却总是不能充分地书写记录,这是它的标志.
如果我的想法没错,那么,这一特点也是所有艺术以及哲学的标志.
·为了更清晰地阐释这一观点,让我们再回头来看看书面语言中的文字.
棒球里的记分,这种看似边缘生僻、深奥难解的图形实践,或许能让我们获得一定的见解.
一场棒球赛大约要持续3小时,期间的活动繁琐杂陈.
运动员在场上跑来跑去,其他人在场外做着热身,主教练与场上队员、教练员彼此来来回回地交换着信息.
由于每场比赛都存在着无数可能,因此棒球比赛中所发生的动作、行动事件实际是无限的.
但是有一种特定的活动叫作记分.
每场棒球赛都有一名正式记分员,而球迷和热爱球赛的人也会记分.
最初级的记分方式是记录谁赢了,更复杂点的是要全面地记录场上发生的变化.
3人出局后半局结束,队员按照特定顺序轮流出场击球,直至3人出局后换另一方球队进攻.
击球手站在本垒前面对投球手.
如果投出的球是好球可以击打,而击球手没有挥棒,那么就是"一击/好球";而有的球不在好球区,如果他听之任之不予理会,那就是"坏球",对他有利,4个坏球保送上一垒.
有时他会把球击出场外,这有可能是好球,但也可能不是好球;还有些时候他击出的球在场内,这对他有可能意味着出局,但也有可能是跑垒的机会.
记分意味着要记录比赛中所发生的事,而一份记录清晰的记分卡让你知道,对每个击球手来说,他击球时都发生了什么,而对每一局球赛来说又发生了些什么,它使你可以"回放比赛".
这里直接产生了两件有趣的事.
首先,记分并不容易.
你需要了解场上情况并作出判断,比如跑垒员是否抢先于外野防守队员上垒,是偷垒还是别的什么.
人们对于如何记录一场比赛意见并不一致.
然后,在记录棒球比赛时,你当然不可能记录场上发生的所有事.
大多数记分员会标记每一次投球:这是好球还是坏球它能否被击进场内可我认为大多数记分员不会去记录每次投球的确切位置(是高是低是在好球范围内,还是低过中心区域)他们也不会记录每次投球的间隔时间,或投手在球出手前是否擦到了耳朵或身体的其他部位.
其结果就是,记分不能给你提供足够的信息、资源让你可以真的回放比赛.
这不是录像,而是一张清单,一份相对于场上发生事情的特定分类、相对于个人兴趣的数字记录.
记分卡上会标明跑垒员在二垒守垒员投向一垒时成功上垒,获得内场1分,但不会记录,比如说,跑垒员头部在先滑向一垒.
我们可以说,头部在先滑向一垒赢得1分,在记分时属于无关紧要的范畴.
当然,如果是针对某些特定目的,它就事关紧要了.
你可能非常关心跑垒员的健康与安全状况;几乎在任何情况下头部在先从本垒滑向一垒都是极其愚蠢的.
因此,如果我是场上教练,我可能会关注这种细节.
但是,总的来说,若不是为了特殊目的,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
它对于了解场上状况没有特别的意义.
这让我们想到了第三点:记录一场比赛没有一个单一的方式,怎样标记取决于记录员的个人兴趣.
有人标记投球位置,有人喜欢用彩色铅笔,有人使用这种表格,有人使用那种表格.
这说明我们会有一些共同的、群体的兴趣,也有约定俗成的做法,因此,只有针对一个群体的共同目标,才能说我们做的是好还是差.
现在我们来问:记分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在做些什么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有人答道:是为了记录场上发生的事.
这答案没错,但流于表面.
不如说记分是一种思考比赛的方法,也是组织我们对于比赛的理解的方法.
这是一种探寻意义的活动,是一种研究.
我们记录比赛是对比赛进行回顾、思考.
如此说来,我们还可以看到它进一步的含义.
事实上,记分不是比赛之外的活动.
怎样记录比赛当真决定着比赛的进行,因此它对选手至关重要.
重要的是,无论你是否真的费心去记分,棒球都需要你具备记分员的心态,就是说你要以记分员的方式去思考场上发生的事.
我们怎样记录比赛会影响运动员对其行为的感受和思考、他对自己状态的认识等.
运动员活在记分员的现实中.
·那么,就让我们沿着棒球记分的思路来思考书写(书面文字)及其在我们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
有关文字历史的书籍往往把文字当作是记录口语的一种编码方式.
为此原因,他们往往会以为字母体系——我们的书写方式——更为优越,因为它能够代表口语的发音(而不是概念,比如说).
但是我们的思考却提出了另外的可能.
最初的文字根本不是用来代表口语的;无论我们书写些什么,它都是一种用来思考所写内容的技术.
这是一种为了弄清意义的方法,一种(再)组织方式.
事实上,关于文字的起源,有一些较好的理论表明:它是一种标记技术;书写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计数.
起初的书写的确就是字面记录的意思.
最早的书写者是记账的人,他们书写并非为了代表他们的语言,也不是为了谈论羊或蒲式耳,而是用它们记录有多少只羊和多少蒲式耳以及完成的交易.
快进至当今的音符.
音符不是用来朗读的,无论是用法语、韩语或是英语,它是用来演奏的.
当然你可以大声朗读出来,但并不是只能用一种语言来读,而是用其中任何一种语言都能读.
我们使用音符不是为了记录说话方式,而是为了探究音乐思想和音乐问题.
数学符号情形完全相同.
假如没有数学符号,我们很难想象会有现在的高等数学.
我要说的不是我们使用符号进行计算,像用基础算术一样;我也不是要说,符号本身就是数学元素(比如在模型理论里).
我要说的是,符号可使我们构想问题并思考一些现象.
如果没有符号,我们根本无法做到.
这些文字应用都是基本的.
我的观点是,它们是最早的、基础性的、原始的文字应用.
我们书写并非为了记录语言,文字与语言本身一样,是用来思考的.
应用文字来记录音乐、记分棒球比赛,或进行数学求证,这些并不只是特殊的应用;它让我们看到文字并不完全是语言的附属品,为了记录语言而随后发展的产物.
相反,它是人们为了参与周围世界而使用的一种独立的语言技术.
它是参与世界的一种结构体系,一种方式,一种风格.
如果你认为文字是一种记录语言的方式,那么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口语首先出现,然后才出现文字.
但是如果你能领会,同语言本身一样,文字是为了认识世界而使用的图形技术,那么,哪个先出现就另当别论了.
历史事实是,出于记录语言目的而使用的文字显然是新近的发明.
是的,但是我们还知道,有些图形的使用——例如欧洲和非洲岩画中所表现出来的——至少与我们的语言能力同样古老(或曰与我们有理由相信的语言能力一样古老).
因此说,使用图形技术——即文字——来思考世界和我们的问题与语言同样古老,这一观点并非无稽之谈.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字实际上是独立的语言.
当然,我们的确是使用文字来代表语言,这正是我开始的论点.
我们使用文字来弄懂作为语言使用者的我们.
这让我们想到了更重要的、真正引人注目的一点:这种要求——弄懂语言组织我们的方式——早在为此目的使用图形手段(如绘画)之前就产生了.
思考:让人听懂自己并思考自己谈话方式的需求——要把话讲清楚,作出明确的阐释,作出裁决、解释、引导他人的需求——可能从一开始就存在.
语言带来了误解的可能,如果不需要清晰地说明和表达一个概念,也就不会有语言指导,如一个人该怎样讲话正确的、首选的、最简单明了的讲话方式是什么再想想棒球赛:无论你是否记录比赛,记分员的立场或态度都早已存在,站在这一立场上你会问:这里发生了什么这是好球,还是坏球该怎样记分这一立场本身就是比赛的一部分.
而关于语言的反思态度也是如此.
如果没有关于语言的态度、观点、规范、规定和思想,也就不会有我们所认识的语言.
从来就不曾有什么伊甸园,因此,也从来不曾有过一种我们随心所欲地自由使用的语言;我们总是需要不断地去思忖这样一些根本的问题,如怎样继续下去哪是对哪是错他这么说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他要这么说等等.
因此,无论是出于什么意图和目的,如果讲话人不具备我所谓的书写者态度,那么根本就不会有语言.
而这,我们前面已注意到了,与能否实际获得文字技术来代表语言无关.
在我们开始使用绘画(即文字)来规范口语讲话之前,我们早就在用讲话(口语)来规范讲话(语音)了.
使用文字来规范语言是对一种迫切需要作出的回应.
·关于文字的这些思考带来了微妙的结果.
首先,文字不是语言的附属品.
在棒球比赛的案例中,文字与语言本身一样,是我们用来思考棒球的工具.
如此一来,发明一种方法来记录棒球比赛,对棒球比赛起到了重组和变革的作用.
将此类图形技术应用于语言也是同样的情形,像棒球比赛一样,书写语言对语言起到了组织和改变的作用.
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像棒球比赛一样,不是我们可以把这种图形技术应用于文字中,而是我们必须这么做.
为此,我必须非常谨慎.
当然,并非如字面所说,我们必须发明某种方法来书写语言.
在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并未发明文字,而且如今也有许多语言口语表达非常完善,但却从未有过文字.
我要说的是,无论我们是否真的创造一种方法来书写我们的语言,至少从观念上来讲,我们都做了同样的事.
对于我们自己的语言活动,我们都采取了一种所谓的书者态度.
如果没有这种自我组织的作法,就不会有语言.
就如棒球比赛,如果不去思考棒球就不会有棒球.
二阶的思想反复地、不断地渗透进一阶的活动.
这可能就是意识形态该有的样子:关于一种活动的思考如此深入地渗透到这种活动中,以至于我们很难再将它们真正区分开来.
棒球比赛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语言也是一样.
那么,当我说艺术,以及哲学,都倾力于创造书写,它们的目标或意图都是文字的创造时,我的意思实际就是,它们恰恰产生在这样一种关键时刻:我们真切的、充满活力的一阶活动已成了它们自身的问题,也就是说,此时,它们已经是成熟的组织活动,但又受制于对此活动的自我认识(即一种意识形态).
有人说文字是强制性的.
毫无疑问,文字、字典与语言管理机构都会让人联想到民族、国家.
不管怎么说,很显然,没有文字,我们以为的社会文明、政府、法律,更不用说科学,都不可能产生.
因此,从我们的立场来看,既然我们生活在一个书面语言成熟的世界里,文字已然存在,那么艺术旨在创造文字或者再为它的权威作用添砖加瓦便毫无道理.
无论是艺术还是哲学,其目的都不是要以此方式来为统治思想服务.
试着把自己放回到最初创造文字的那个人的状态.
想象他的思想状态:第一次要想出一种方法来写下我们的语言,这是怎样一项自我探索、自我组织的工程啊!
显然,这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
但是请注意,今天说起跳舞,我们发现自己恰恰是处于同样一种状态,我们根本找不到一种方法来记录我们的跳舞和肢体动作.
当然,有些体态,如"她耸起双肩"、"他向我挥舞拳头",都是可以名状的元素,可是,真让我们表达那些庞大的、巨量的流水般的动作、姿势、姿态、体形、面部的表情,语言彻底失效,可以说我们是彻底的文盲(或曰是失语的状态).
毋宁说,我们与先人处于同样的状态,他们实际上已经具备了书写者的态度,却根本没有这样一种技术,也没有必需的概念工具来写下这一切.
所谓舞蹈编创就是我们为此找到的方法,正因为如此,我们所称的舞蹈就是以舞动肢体来做哲学的一种方式.
创造一种方法记录肢体的动作,与当初创造文字记录语言完全一样,是变革性的、富于想象的;如今时过境迁,文字已不复当初.
要理解曾经发生的历史变革,我们可以这样说:文字,曾经作为一种规范方式被用于语言之中,如今它反过来对语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至于我们认为文字本身就是组织语言的一种工具.
艺术、哲学如今要做的不是拒绝或远离文字,相反,我们"需要记录自己"的需求又从头开始了.
我们需要用书面语言写下我们的组织.
这就是文学艺术的工作.
文学艺术家使用了我们能找到的所有方式:我们必须表达自己,或写下我们的故事,或讲述自己的生活.
他们让这些变成他们的问题.
他们努力创造新的写作方法.
要写下我们是怎样由文字组织的,这一写作任务可能要求在技术层面上直接参与文字本身,于是,艾米莉·狄更生(EmilyDickinson)[1]把词汇用作装饰页面之物,而詹姆斯·乔伊斯(JamesJoyce)[2]则将书面语言发挥至想象的极限,最终生造了一种在常规意义上根本无法理解的语言,而其价值也正是在此处得到了体现.
文字,如此熟悉、如此霸气、无所不在,此时却变得如此陌生.
但也有艺术家别出心裁.
他们并不关注怎样书写,而是在叙事方式上做文章.
因此,他们重写、重组了讲述一个故事应有的方式.
这时我们会想到赫曼·麦尔维尔(HermanMelville)[3]和托马斯·曼(TomasMann)[4],尽管逐字逐句地来看,他们并未做新的尝试,但在他们笔下,整个叙事成了一种新鲜、奇特的东西.
·对写作者态度适用的无疑也适用于画者态度.
我们天生有一种冲动:我们会退一步观察闯入我们视线的世界,然后把注意力转向我们观看世界的方式.
这不需学习,我们都能做到.
记得小时候晚上躺在床上,单凭眼睛和外面钻进来的灯光,我就可以玩得兴致盎然.
闭上一只眼,睁开另一只眼,外面的路灯就跳跃起来;眯起眼睛,灯光就变成万道光芒;大拇指一挡,整栋大楼、甚至是月亮都被遮住不见了.
这多么神奇!
因此,在我看来,这一说法不无道理:作为视觉艺术家,从一开始我们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途径.
我们可以描绘这个世界,而且在描绘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描绘和思考来调配这个世界(例如,拜占庭艺术);或者,我们也可以调配我们的视觉体验(文艺复兴、印象派艺术).
这两种创作冲动在所有时期都有所表现,但有时两者会交替主导.
有一种熟悉的观摩绘画史的方式,据此,画家旨在揭示事物的外观,以期达到一种写实效果.
不仅是伟大的自然主义,即便是在印象派作品中,也可见到对这种关注的表达.
创造一种方法来写下我们的词语曾经是艺术创作的一项解放性成就,而找到一种方法用绘画来记录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无疑具有同样的变革和解放性意义.
同样,正如权威的传统书写体系会限制艺术创作,扼杀新思想和个性表达,绘画时若过度地追求写实,一丝不苟地描绘我们的所见或是事物的外观,同样会限制创新.
因此,狄更生或乔伊斯会背弃传统的、规定的写作方法,不依赖词汇和词组;画家塞尚、马蒂斯和毕加索则拒绝按照事物看上去的样子去描绘它们(或者去重新思考该怎样观看这世界).
恰恰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改写了我们原本描绘这个世界的想当然的方式.
当然,另有许多视觉艺术家干脆摆脱视觉感知的问题,别出心裁,另辟蹊径来发现和重组.
正如托马斯·曼从语言的创新转向叙事方法的创新,有的画家要么干脆放弃了作画,如巴内特·纽曼(BarnettNewman)、马克·罗思科(MarkRothko)、罗伯特·欧文(RobertIrwin);要么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使用自然主义(即关注有效的描绘),如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Richter),大卫·霍克尼(DavidHockney)、卢西恩·弗洛伊德(LucianFreud).
我要说的道理很简单:画家与广告画册的设计者不同,后者是为了推销;而作为艺术家的绘画者目的是要把绘画本身,或曰视觉本身置于画框中进行审视研究.
如果其结果是一幅画,那么这幅画作不只在向你展示某件东西,而且会激发你去思考:在这幅画里,或通过这幅画,或由于这幅画,你能看见些什么.
如诗歌、小说一样,作为艺术的绘画其天职是要书写我们,或是以新的方式再次书写我们.
而这一职责之所以重要,如果我说的没错,至少部分是由于利用图形技术——书写、绘画、树立绘画者和书写者的态度——实是我们的天性.
·舞蹈编创旨在用跳舞和肢体动作来写作;哲学力图要把我们平常的思想与谈话中所想当然的东西彰显出来;绘画,则是在用我们由先祖那里继承来的图形技术进行同样的探索.
但是,似乎最接近于以图形媒介把握自己的艺术形式的就是音乐.
似乎只有在这里,我们从文字与语言中所发现的记录与实践之间的完美契合才得以实现.
就像你可以大声地读出页面上书写的文字一样,有些人似乎也可以从乐谱中读出音乐.
乐谱主宰了音乐的演奏实践,它的出现标志着音乐作为艺术的诞生.
这个话题太大,在这里我无法深入地探讨,但有几个要点可以保证我们不至于偏离方向.
首先,说乐谱决定了音乐的演奏方式,这是一种错觉.
乐谱是演奏的工具,只有在诸如创作、教学、训练、应用和批评演奏过程中对乐谱的应用等特定的实践场景中,它才主导作品、主导音乐本身.
认为书面文本,作为一个普遍原则,决定了我们该怎样将它大声朗读出来,这也是一种错觉.
关于这一观点存在许多细微的歧义,容易引起混淆.
①并非所有脚本记录的都是语言.
棒球比赛的记分簿中没有任何东西规定它必须用英语或西班牙语来朗读.
②在字母文字体系中,我们的确有明确的朗读方式,但是请注意,让格拉斯哥人、纽约人和一个孩子来朗读同一文本,即使他们读的都对,但听上去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文本,即记录,会留有很大的诠释空间(声音的大小、强调的重点、个性的体现、在哪里停顿,等等).
③我们还忘记了,尽管有些文本如短篇小说、诗歌等有确定的朗读方式,其他类型却未必.
语言学家赫顿(ChristopherM.
Hutton)(在交谈中)曾问:朗读一张网页是否只有一种方式书的封底呢或者路标地铁广告而且,即便你在读小说,你会大声地朗读页面上的所有内容吗比如,你会读出页码及书眉里的信息吗④反过来也一样.
同一个中文文本,用普通话和广东话都可以朗读.
在某种意义上,文本与数学符号一样,不能决定它的读音.
的确,我们可以通过某些方式使用文本来对表演起到管理、指导或告知的作用.
当然,乐谱也一样.
但是,绝非由于乐谱如它曾经那样,全凭自身主宰或决定了音乐.
或许我们原本就可以这样说:是音乐主宰着乐谱.
这一点意义深刻.
贝多芬给他的乐谱作了很多标注.
这些指示是乐谱的一部分吗抑或它们只是告诉你该怎样读乐谱一个人写的乐谱能否解答他关于该如何演奏的所有问题不能.
没有一个文本能够自我诠释.
事实是,在历史上的某个特定时期,音乐家发明了一种方法,以书写方式——写下它们的旋律、音阶和所用乐器——来示范自己的音乐活动,而这反过来又影响了他们的实践:它使音乐家以一种新的方式来重新思考他们的音乐活动.
乐谱起到了重组织的作用.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乐谱与音乐作品的绝配,我们曾无比自信,但在发现音乐作品实际上只局限于有限的几个音乐种类之后,我们的信心大大受挫.
你无法写下布鲁斯、爵士乐或电子乐的乐谱.
20世纪之后,作曲家必须发明新的方法来写下他们的活动,他们的挣扎与舞蹈编创者的挣扎不相上下.
如果说音乐作品与乐谱密不可分,那么,音乐作品就要涉及一个问题:如何书写自己.
音乐热衷于这一问题:书写自己.
这一观点我认为并非牵强附会.
我曾问过一位作曲家朋友,一名学生,他最喜欢的作曲家是谁托马斯·阿代(TomasAdes),他说,然后解释道:"单就他将音符写在纸上的才华,无人能及.
"多么精辟的评价!
可能你会天真地认为,音乐关心的就是音乐,而音符只是音符而已.
而我这位朋友关于阿代才华的认识,直接指向阿代的写作成就,他创作一个文本,一份乐谱的成就.
因此,我想说,对所有艺术:艺术以及哲学,其目的都在于书写的创作.
有时,它的表现形式是拒绝以传统的方法绘画、写作、标注或谱曲;有时,它的表现形式是从草涂乱抹开始,编织方法来向我们自己表现自己.
第5章艺术、进化论以及谜中之谜柏拉图说,要作一幅画很简单啊,所有人都可以做到.
只要拿着镜子对准你感兴趣的东西,呵!
一幅画就有了.
柏拉图错了.
如果镜子里的影像是图画的话,那么,地上的脚印就算得上是雕塑咯人们绘画总是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而镜像却不一样,它自然天成,与我们不期而遇.
而且,出现在我汽车后视镜里的车我能真实地看到,但照片里的祖父早已谢世,我却再也见不到了.
但是,从另一种意义来说,也许柏拉图纯属无意,他也可能恰是歪打正着.
镜像或许算不上图画或照片,但有时我们使用镜像就像使用照片一样,这是因为我们以为自己或别人——我们看上去的样子——就是照片里的样子;照片就是我们的模型.
用艺术史学家安妮·霍兰德(AnneHollander)的话来说,照片是"我们评价直接观感的标准——包括对镜子里的自己的直接观感".
因此,当我们在浴室、门厅或卧室里转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时,吸引我们兴趣的实际是一副即兴创作的自画像.
霍兰德是这样说的:盯住镜子的人并不是在客观地审视,而是像在画室里专注地摆着姿势创作个人画像,甚至连抓拍都算不上.
可以这么说,镜像是短期的、过后即被删除的自拍像.
霍兰德的观点意义深远.
她的兴趣在于服饰,她说,我们对服饰的态度与反应折射的是呈现在视觉艺术中的标准和规范.
我们用图画中设立的标准来品评我们看到的人们的着装,也品评我们自己穿上这衣服后可能有的形象.
相比仅仅认为艺术影响了我们观看自己的方式——类似于意识形态可能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态度——这一观点要更为有力.
她还得出一个更为惊人更为激进的观点:我们平时对着装以及对他人的着装方式所表现的鲜活的兴趣——这种兴趣不受地域限制,不受时代限制,一直是人类始终萦怀的牵念,甚至它可能是我们作为人类的一个重要标志——实际也是对艺术与艺术史的一种参与.
别忘了,我们在第3章里曾注意到,我们穿着打扮自己至少已有3万年的历史.
当我们装扮自己时,我们也是在对别人的外表作出反应.
看到图画和摄影作品里记录的影像,我们会照着引用、模仿和玩味;同时,也会关注自己出现在照片里的可能形象.
这一想法令人兴奋.
这样一来,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街角的男孩要穿那样的球鞋,那样的牛仔裤,又为什么要戴这种首饰,选择这种图案纹身;原来这都是他们独特的、明确的风格选择.
他们在很认真地对待这些,并非随意而为.
也许这有点老生常谈:我们的文化不断地被年轻人的时尚品味影响着——20世纪50年代的火爆浪子、60年代的嬉皮士、70年代的朋克摇滚、90年代的嘻哈一族,等等.
但是,如果霍兰德的观点没错,无论这些孩子想出什么新招来装扮自己,他们实际上是在艺术领域内作探索.
通过打扮自己,他们是在用图画玩味艺术,其方式就与我们站在镜子前搔首弄姿自我欣赏不无相似.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图画让我们成了它的囚徒,它俘获了我们,我们被它统治着.
但同时,它也给我们提供了从它的掌控中解放自己所需的资源.
我们不能摆脱图画;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装扮,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创作不同的图画,这样,艺术就把我们从技术强加于我们的组织和规范中解放了出来.
可是,在这当中有一点很难令人信服.
肯定有人要说,人们穿着在先,创作人们穿着的图画在后.
我们自己关于服装和服装穿在人身上的形象的视觉经验肯定出现在标准之前,且提供真正的评判标准;我们会以此标准来衡量我们通过直接观察所认识的东西的图像呈现是否真实,是否有价值.
总而言之,文化会作用于视觉本身的观点不值得认真对待,因为视觉是生物性的,而生物特征要先于文化.
但霍兰德的观点允许我们对此提出挑战.
严格地说,我们不需图画就能看见,但是照片——至少是人们着装的照片——形成了我们对于着装形象和感受的观念,甚至包括着装后可能产生的形象与感受.
我们自己的经验——视觉的、身体的还有社会的——都来自于我们受文化影响、由图画形成的着装观念.
这并不是要否认视觉是生物现象,我们和动物一样拥有的生物现象,而且它还可以得到医疗,无需考虑人文因素.
但是,医生在给我们检查眼睛时总是要让我们分辨字母或图片.
讲到这里我们同样会感到吃惊,即便是医学意义上的感光视觉表现似乎都与图画密不可分.
我们可以也应该将霍兰德的观点引伸一下,把观看当成一种注视,或凝视,一种充满了思索的审视或视觉评判行为,可以说,这一想法本身就是从图画当中获得的.
毕竟,图画创作出来就是用来审视的;文化规范中没有任何一条会阻止我们去仔细地观察或盯住一幅画.
相反,即便得到允许,通常我们也不会像盯着画中人一样去盯着一个大活人,毕竟,盯着人看很不礼貌;如果我们真的盯着眼前的人,那我们很可能会有冒犯她的风险.
图画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件东西的样本:如果我们退后一步,带着超脱的、置身事外的眼光去观看、去审视而不是去使用,这东西又会是什么样.
图画与其说是我们应用审美意识的结果,不如说它是审美意识的前提.
相比审美意识,图画的出现在先.
我们可以对比美学的、沉思的审视与自然状态下的观看.
自然的观看是行为的、内嵌的、从属于任务的,是对自然界的敞开,而不是对世界的一种反思或审视状态.
大多数时候,大多数观看不是凝视,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审美,它不倚重刻意的观看和审视行为.
我们开车、系鞋带、准备晚餐然后吃晚餐,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用到眼睛和其他的感官.
自然状态下的观看是自然发生的、下意识的,也是直接的、不由自主的.
自然的观看是呼应周围事物而做出的行为;而审美的观看,更像是一场思想的盛宴,是对所看事物的品味与思索.
说没有图画就没法看见物品,或者说观看没有生物自主性、不能脱离创作和使用图画的文化实践,这都不对.
我要说的是,如我在第4章中所述,就像文字塑造了我们的语言概念一样,图画塑造了我们关于观看的概念.
文字会轮转回来影响和改变我们的语言生活,图画也会反过来影响和改变我们使用视觉本能的方式.
图画成了一种观看的工具,成为一种评价标准,我们以此来评价直接的认识,至少是某些认识.
图画把观看从一种在背景中运作、指导我们工作与游戏的技能,转化成一种专注的、充满思想的评价活动.
但是图画改变的不仅仅是"观看"这一过程,它改变的是"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或至少是,我们对于所见东西的观念.
因为观看是行为的、内嵌的、从属于任务的,所以我们看见的总是生活圈中的家具、仪器设备、我们用于操持事务的工具.
我们与所见东西的根本关系并非是观察、注视或出于好奇的关系,而更像是依赖或是认为理所当然的关系.
我们不会注视着变速杆沉思,但我们开车却的确要用眼睛;同样,我们走路也不会盯着脚下的路面观察,但还是要用眼睛引导自己的行动.
但是,说到赏画的审视——即行使我们的审美意识——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赏画意识让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家具或变速杆,而是静物,因此它让我们意识到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
一件静物是一个独立、中性、物质的东西,它有它的属性.
尤其是,它具有形状、颜色、大小等可见的属性.
而且,从赏画意识的立场来看,我们看到的也正是这些属性.
图画让我们以此方式来思考"观看",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图画就是一件静物应有状态的模型.
图画放在那里让人观察,以冷静、敏锐的眼光.
只有当我们退出游戏场,将自己超然物外,物才会显现出来.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物就是审视行为的结果,它是我们对世界的思考;只有当我们调动审美意识时,才会把世界带进视野.
因此,循着霍兰德的思路,我们可以说:图画是一种标准,据此标准,我们不仅形成了作为一种注视行为的视觉意识的概念,这种行为的结果——物的概念也得以形成.
现在的问题是,关于赏画意识出现了一个错误:妈妈、爸爸不是物,床也不是物,我们打篮球的场地也不是物.
至少在我们退后将自己超脱并以特定的方式思考他们之前,他们不是物,除非我们能像观看照片一样地看着他们.
但是,我们往往会拒绝赏画的审视,认为它是虚假的、不真实的,它"只属于文化".
可这里面的确有一定的道理.
图画摆在我们面前,世界却不像图画那样摆在我们面前;图画创作出来是为了让我们审视,而世界是由物质构成,却不像图画那样是为了让我们审视.
更加真实的现象学不仅会降低审视的突出性和重要性,也会降低物本身的意义.
但是,既然我们不能回到伊甸园,我们也无从知道图画出现之前人们的观看是什么样.
而且我们需要记住,首先,图画在我们的历史中很早就已出现,甚至史前就有了.
别说在简单的描画出现之前,就是在图画创作能力高度成熟之前有关现代人类的记录,我们都没能找到.
其次,物的概念是物理学所必需的,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有关世界的观点,一个独立于我们的世界观,它都是必需的.
对此,我们不能放弃.
物是真实的,我们需要用图画去发现它们.
同时,我们还要承认,图画这种凌驾于我们之上的力量的确有点让人心烦.
图画掌控着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它的囚徒.
新的证据表明,就连我们人类的近亲,尼安德特人(3万5000~7万年之前生活在欧洲)也曾专注于用尖锐的石质工具在岩壁上凿画.
而且,前面几章我们也曾注意到,我们的祖先似乎从我们作为人类出现伊始就一直在创作图画,把它们贮藏在私密的洞穴中.
如今,有了更为先进的制作、保存、复制和传播图像的数字技术,同时随着自拍像的出现,图画在我们的生活体验中甚至占据了更为活跃的位置.
图画曾以多种方式改变了我们观看的内容及方式,对这些方式我们已经做了探讨.
这里没什么好稀奇的.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看到夕阳,我们会惊叹,这太美了,简直像画一样!
或者,我们会说,这就是一幅画啊!
还有什么能比我们用画来评价直接感受更好地证明图画就是评价标准呢但是,图画的统治作用还不仅限于这些熟悉的观察之中.
我们拍照不是为了储存记忆;在这个图画意识的时代,我们照相甚至是为了体验:如果我们不留下影像,或不让自己与影像联系起来,这事就好像没发生过一样.
因此,当情侣们坐在海边的长椅上紧紧相拥,此时,女孩也不忘伸出手机来一张自拍以验证并记录这一重要的时刻.
这令人担忧;如果所有时刻都是柯达时刻,那么,这一时刻就不复存在.
我深深怀疑,我们给自己拍照的冲动——就如我们走过商店橱窗时观看镜子里的自己的冲动一样——反映的不仅仅是一种短暂的、转瞬即逝的时尚或冲动,更是图画以它的形象来塑造我们的极致表现.
·有人认为,审美意识在人类中是普遍存在的.
奥克兰大学的哲学家斯蒂芬·戴维斯(StephenDavies)曾写道:"我们当中谁人不曾对着夕阳、彩虹、顽皮的小猫咪抑或一个故事、一首歌有过深深的感动,获得审美的享受而这种愉悦的反应似乎是人类的普遍特征,它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和文化当中.
"关于这点,戴维斯可能没错.
绘画属于我们的史前技术,因此,它真正地塑造了我们人类的视觉体验.
不难理解,关于我们与周围事物的关系,一种赏画式思考已深深地渗透到人类的生活方式当中.
但是,如戴维斯所说,人类的"基因配置"(geneticallydisposed)就是要对(比如说)动物采取一种审美立场,因为这使得我们的先祖能够有效地应对动物可能带来的威胁和机会.
这种说法肯定不对.
无论是看到某些动物,还是同类或安全可持续的环境,都能感到愉悦,毫无疑问,这种倾向会赋予我们先祖繁衍优势;但是,当遇到野兽或恶劣环境时,如果能认识到它的危险和不适,那对他们同样有利.
但是这种自然状态下的感知遭遇(perceptualencounters)与美学的审视实在相去甚远.
美学的审视,如前所述,是一种超然物外的沉思的审视.
它是一种视觉评判,而绝不单单是一种直觉反应,无论感受多么强烈.
使它成为审美的恰恰是因为它源自于一种好奇心,且对自己要做反应的意向漠然置之.
审美态度要追根究底、充满思索,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能同时感受强烈、充满激情,但它却意味着我们不能期望从那些缺乏相应认知能力和共同的社会评价体系的物种中去寻找审美意识.
它还意味着审美观察不太可能让有能力行使它的人增强适应自然的能力.
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
面对攻击者,沉思默想绝对不是一种安全的反应;而对摆在自己环境中的好东西,更有效的反应也不应是审视.
如果说审美态度是天生的、普遍存在的,那么对此事实我们需要有不同的解释.
跟随戴维斯的论点,我想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推论.
认为一个动物,比如说一只孔雀,能够与世界建立审美关系不够令人信服——恰恰是因为,要从美学意义上观赏这世界,需要它心思缜密、具备超然于世的能力;或者能够审视周围世界,就好像这世界是需要审视的一幅画.
但是,出于同样的道理,有些人如果不能采取这种审美态度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人类有审美态度,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然而这样说却有至少两种不同的意义.
首先,事实上,大多数人都能够采取审美态度:他们会自然而然地谈论周围事物的模样;对于这类事物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品头论足.
正因为在统计意义上审美意识属于常态,即大多数人都具备审美意识,那么,就出现了第二种含义:在规范意义上,它也应属常态.
一个人应该能够采取审美立场,原因很简单,因为所有人都能.
如果哪个人不能,就意味着有什么事不对了,很可能这人有什么智力缺陷,或是不够聪明,或缺乏好奇心、创造力或感知能力和想象力.
审美意识就像男人的乳头,没有任何用处,但是人人都有.
这意味着它的存在对作为一个人的正常性(以及适存性)承载着非常重要的信息.
因此,当有人认为审美意识是我们人类天性的一种进化表现时,我们权且可以认同他们的观点.
但事实上,审美意识不过是一个特别现象而不是一种普遍能力,它需要对我们所感知的事情采取一整套与文化相关的反应和评判态度,而且似乎只有人类才具有这样的审美意识.
·然而,接受审美意识的进化论解释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艺术及其在我们生活中的意义.
审美意识毕竟不是艺术意识.
对于任何东西,包括猫咪、夕阳、波音747等,我们都可以采取审美态度,而且我们也的确总是在审美,因此,从审美意识这种生物常态来讲,我们无法跨越到对艺术的领悟.
审美观察挑拣不出艺术来.
事实上,我们不能以审美配置来解释艺术,还有一个难以按捺的原因.
我一直主张审美意识要依赖于图画创作技术早已事先存在.
但是,正如我在第4章中所述,艺术的工作(也是哲学的工作)恰恰是要创造这些技术,这些我们书写自己的方式.
如果这观点没错,那么,我们需要艺术来创造这些技术,它们的存在是艺术的前提——因为我们从组织活动,从技术实践中创作艺术——而且它们的存在使得我们最初采取了审美意识:无论对艺术欣赏,还是对艺术创作或技术(或科学!
)的创作,审美意识都是必需的.
沿着时间的长河我们向上追溯着,无论多远,在我们发现人类的地方,我们同时也发现了语言、服装、图画以及技术.
我们还发现了艺术.
·但是,难道我们就不可能用进化论的观点来解释艺术这一整套复杂的行为模式吗对其最初的起源,我们就不可能给它一个生物学上的解释吗有学者认为我们一定可以的.
例如,独立学者艾伦·迪萨纳亚克(EllenDissanayake)认为,既然艺术如此普遍,广受欢迎,人们热切地参与其中,又对我们如此重要,且它所带来的生理愉悦又是如此强烈,那我们一定可以在生物进化中找到它的根源.
我们热爱艺术以及艺术创作,就如同热爱食物一样.
当一种热爱或激情如此直接、无需经过文明和"高雅文化"的媒介,这一定是因为它对我们有益.
我们喜欢它是因为作为动物我们需要它.
为了阐述她的观点,她引用了沃尔特·惠特曼(WaltWhitman)《自我之歌》(SongofMyself)里的诗句,以表明我们可以从艺术之中获得像性爱一样的生理上的愉悦.
我听到曼妙的女高音,技艺高超、训练有素她令我颤栗,像立在爱的巅峰交响乐队令我晕眩,天旋地转胸中涌出不可名状的芬芳我的心在悸动,仿佛坠入恐惧的深渊它带我乘风远航……我赤裸双脚轻轻试探……顽皮的海浪舔舐着它们我彻底袒露……却被一阵无情的狂风毒雹撕裂沉醉在甜蜜的吗啡里……我的气管揪紧,挣扎在死亡边缘再度释放,感受这谜中之谜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生命的意义她说,是这种对艺术极度的、肉体的、强烈的反应需要一个解释,而只有进化论,只有真正从物种的角度,只有将进化史上的时间跨度考虑在内,才能给出一个恰当的解释.
如果本书观点正确,那么迪萨纳亚克恰恰是将事情搞反了.
艺术的作用不是直接的;它们从来就不会那么简单、毋庸置疑或直截了当,像食物和性爱带来的(或可能带来的)愉悦那般简单、毋庸置疑、直截了当.
对艺术的反应总是受到扰乱,有批评,有质疑,有语境,也有反思,它们必须是,且绝对是文化的.
若说有例外的话,那似乎就是音乐.
音乐施展的力量及其直接性似乎使它很特别.
欣赏图画,你需要盯住它看;欣赏雕塑和建筑,你需要仔细审视,而且必须冷静、超脱;但是音乐却直击你的感觉,它用一股自然的力量直接将你吞没.
你无需任何特别训练便可感受到它的作用.
毕竟,音乐能够平复狂躁的心绪,至少人们是这么说的.
据一位神经学家说,它在人身上的力量是作用于心理及神经的;音乐可以,或似乎可以,操控.
这些都不对.
是的,音乐会影响我们.
但是,一声不期而遇的大声斥骂同样也会影响我们.
我们对于辱骂的反应会瞬间自然爆发,完全不经调停,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对语言知识的熟练掌握和运用,而我们对音乐的反应也总是要以一个共同的音乐知识和文化为背景.
对于一个音乐门外汉,贝多芬毫无意义.
事实上,不了解音乐的外行根本听不出贝多芬的曲子.
参观泰姬陵时,看着它的廊柱,我根本无法分辨上面的阿拉伯文字和边缘蜿蜒曲折的波浪线装饰.
同样,不熟悉音乐的人也难以区分贝多芬与勃拉姆斯、莫扎特或亨德尔,甚至与查尔斯·明格斯(CharlesMingus)的区别也分辨不出.
当然,如果让人们坐下专心地去听,他们会发现音乐中有些东西会吸引他们的兴趣.
但是,让人坐下专心去听,这本身就已经是音乐文化里的举动,而不仅仅是运用听力器官(倾听与仅仅听到可不是同一回事).
我们大部分人都对自己同时代或是上一代的音乐有着特殊的感情,你认为这种感情只是一种巧合吗关于对当代或相对当代的偏爱倾向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作为一种文化,我们对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少数音乐家都赋予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那么,这是因为他们是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以至于现今全世界都以他们为标准来衡量音乐成就呢,还是因为我们共同的音乐文化本就是建立在他们的成就之上关于音乐听起来应该是何种感觉,他们是否早已深植于我们的音乐观念之中不管怎么说,此处我们稍稍岔开话题只不过是要说明:音乐、绘画以及所有艺术都是文化的产物;只有在文化的背景下,它们才有意义.
但重要的是,这绝非是暗示我们对艺术作品的反应不够强烈.
在我看来,迪萨纳亚克所想当然的,不仅是天性与文化的一种头脑简单的对立,还有一个更为微妙,我认为,也同样糊涂的观点:激情与感受是生理的、物质的,它们与思想、智慧和领悟相对立;似乎后者总是与语言相关,是刻意的,而且实际上形成于社会习俗之上.
迪萨纳亚克想说的是,艺术有着太强的震撼力,不可能是形成于领悟力或知识之上;它的动物性太强,不可能隶属于文化.
与此相反,我认为,人类存在的标志便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不可能将思想与感情、造化与教化分离开来.
在第3章中我们已经注意到,我们是天生的设计师.
技术塑造了我们的生活,它组织了我们,由此成就我们现在的样子,成就了我们的天性.
我极力主张,这种组织应当被看作是生物性的.
文化的发展不仅会轮转回来影响我们的思想,同时也会塑造我们的身体.
试想:现今的人们相比300年前的人体型要大得多.
参观莎翁小镇,你会惊讶地发现,这里的东西怎么都这么小呀!
这是因为,这些房子、桌椅都是为身材更小的人而造的.
体型大小当然属于生理现象,但是,若说过去几百年来我们体型的增大与基因变化有关,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
事实上,真正发生变化的是文化——农业、医疗、卫生,是这些东西改变了我们.
也有事例说明文化会改变基因.
1000年前,大多数人的肠胃都无法消化果糖,但牛奶营养丰富,家畜蓄养与随之形成的充沛的奶源生成了一种(文化)环境,在此环境中,能够消化牛奶的人具有更强的繁衍优势.
这么一来,奶制品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立刻就变成既与生物相关,又与文化相关了.
再试想,尽管普遍识字只是近期的现象,但看书似乎只有依赖神经系统中某些极为精细且高度专属的结构才成为可能.
假若大脑中负责阅读的部分受到伤害,那么我们的阅读能力就会有相应的特定的缺陷;这些神经区域当初得到进化不可能是为此目的,但现在它们却有了这样的目的,是大脑在这里限制了文化吗还是反过来说,是文化组织了大脑所以说,认为文化或技术完全游离于生物性之外,这种想法根本就是一个错误.
而说身体的欲念、感觉、渴望和愉悦与我们的知识与领悟无关,这样的观点同样不靠谱.
需要证据吗只需问问自己:你所吃的东西,如果你了解它的来源,会不会影响你品尝它的味道当你知道摆在面前搭配如此精致的肉酱竟然是狗粮时,它的口感会不会有所改变或者,再以性爱为例:你喜欢亲吻你的爱人,是因为你喜欢亲吻的感觉,还是因为你爱他(她)才喜欢吻他(她)思想实验:假设你正在与某人约会,你很高兴,很开心.
当你发现这人的性别并不是你原本期望的,这会不会影响你的感受呢[想起了尼尔·乔丹(NeilJordan)的电影《哭泣游戏》(TheCryingGame).
]重要的是,即便你单靠盲吻可能无法从一队人中挑出哪位是你的意中人,但喜欢吻你的爱人决非出于偏见.
其他所有形式的评价也是这样.
我们的喜好,我们认为有趣的、吸引人的、摄人心魄的东西都是由我们的技能、知识以及理解所形成的.
说到艺术时尤其如此,在艺术领域里,真正的审美问题不是,你喜欢吗而是,你为什么喜欢迪萨纳亚克力图以惠特曼的诗歌来证明艺术反应那种肉体的、发自肺腑的感性特征,此处我发现,迪萨纳亚克的论述令人吃惊地自我挫败.
从某一方面来说,惠特曼的诗歌刚好是19世纪的一件文学艺术作品,它有着毋庸置疑的艺术价值,但它并未像诗歌本身描绘的那样让读者产生那种身体的躁动和肉欲的兴奋.
因此,它的存在本身就证明,说感受强烈的生理反应是艺术的必然要求,或艺术的真正目的,这种观点实属妄言.
但是,惠特曼诗歌的感染力证明,文化技能及其背后的领悟能力——识字、对阅读的熟练掌握与阅读兴趣等——都是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的必备工具;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是某种"高端文化"的装饰.
诗歌本身表明了思想与感受是彼此依附、难解难分的.
惠特曼诗歌探索的相遇,不是邂逅一位女性,也不是偶遇她的声音,而恰恰是听到一位训练有素、技艺高超的女高音,也即与艺术的相遇.
诗歌让我们去思考,通过这样的相遇,我们怎样体会他在诗的最后一行称之为"谜中之谜"的东西,即我们生命的不可解性.
惠特曼的案例让我们看到,生理感受与情感反应都是艺术的前提,是它的素材,而不是它要达到的目标.
艺术的目标要更为高远.
对惠特曼来说,对我们也一样:艺术是一种哲学.
·最后,关于艺术的进化论解释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它们太空洞了.
它们没有讲明为什么人们要创作艺术,或者艺术为什么对我们这么重要.
它们根本没有抓住艺术的实质.
问题不是他们提出的艺术理论我们是否能够认同,而在于他们根本就没有触及艺术的实质.
(后面我们会看到神经生物学理论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比如,迪萨纳亚克自己就曾提出,艺术的作用就是"使与众不同",而"与众不同"对于亲密关系的形成以及最终形成个人认同感及集体归属感都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这一观点貌似很有道理,但它并不能解释我们为何要创作艺术,或艺术为何对我们如此重要,原因很简单,艺术不是唯一一种可以让我们"与众不同"的方式.
宗教会让我们与众不同;而且,我想她也会同意,游戏、仪式、爱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如运动、战争、贸易等(所有这些其源头都可追溯至史前)都能让我们有所不同.
如果艺术有什么独特的品质或独特的价值——它当然有——那迪萨纳亚克的理论并未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活动也在进化途径中具有选择价值而存留了下来.
她的解释未能够锁定她的解释对象是艺术,而不是能够"使与众不同"的更为广泛的活动.
新墨西哥大学的心理学家米勒(GeoffreyMiller)力图以性选择来解释艺术的适应性价值.
艺术就如孔雀的尾羽一样,它不属于第一级的适应.
笨拙的长尾不会增强孔雀的适存能力;实际上,它是积极的反适应.
正因为这样,拥有一条长长的尾羽反而成了一只孔雀适存能力的标志.
因为对潜在配偶来说,它表明,拥有长尾羽的孔雀要远超出生存的最低门槛,因此才可以担负这样一种无实际用途反而风险很大的炫耀.
雌孔雀愿意选择长尾羽的雄孔雀,因此才使得孔雀的长尾羽获得了适应性价值.
米勒认为,艺术也是这样.
创作艺术的能力、拥有以及买卖艺术的能力、培养自己艺术兴趣的能力,这些都属于价值高昂的成就,只有富足和智慧的人才能承受得起.
因此,从事艺术或对艺术的敏感就成了潜在配偶一项令人艳羡的特征.
艺术被选择存留是因其具有表明适存能力的作用,尽管艺术以及艺术活动本身并无直接的适应性,也就是说,并无扩大适存的能力.
这种解释的细节我们无需关注.
尤其是,这一观点的荒谬在于,好像把艺术用于择偶的语境中就能彻底解释艺术的意义了.
对此,我们可以不予评论,我们只关注与我们目的相关的内容.
对艺术的择偶解释只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某些方面,艺术和孔雀尾羽或是炫酷的跑车或奢华的首饰一样.
但是这种观点却不能解释,为何艺术还具有以上所说的这些性感炫耀所不具备的价值.
斯蒂芬·戴维斯提出了一个更有前景、更深刻的解释.
据此解释,艺术,无论其本源如何,最终都会获得一种适应性特征的名分.
首先,戴维斯注意到,艺术的起源可能与扩大适存无关,它可能是某些适应性特征比如智力、想象力、幽默感、社交能力、情绪控制、创新能力与好奇心等的附加效应.
但是他说,如果现在还以为艺术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拱肩",即把它当作是适应性认知能力的一种非适应的附带效应,那就错了.
原本作为一种拱肩的最终都可能承担了适应性意义.
戴维斯提醒我们,我们已注意到肚脐和男性乳头都没有适应性作用,但是,由于表现正常性的原因,拥有它们最终成了代表正常的标志,由此也是健康和适存性标志.
同样道理,他说道,尽管艺术行为——包括创作和欣赏图画以及唱歌、听歌等——可能并不直接具备扩大适存能力的意义,但是我们从事艺术活动的能力最终都会获得适应性意义.
因为要从事这些活动对人的认识能力有很高的要求,而且它在人群中普遍存在,如果在此方面无能就会是一种明显的缺陷,"一个对任何艺术形式都不感兴趣的人会是无比乏味的,就如一个人没有学识、缺乏幽默感、不懂社交礼仪、不会关心他人或没长肚脐一样.
"因此,艺术行为是表现适存性的强烈信号,它们的起源可能是与扩大适存无关的附带效应,但最终却成了适应性的真正标志.
用戴维斯的推理方式,我权且可以解释审美意识如何被最终选择存留,尽管它事实上并不具有扩大适存的直接价值.
但要解释艺术本身,我却不明白这一观点会如何发挥作用.
同样,这一解释的问题也在于它无法从源头阐释艺术以及艺术的独特价值.
他把艺术阐释为适应性的,只说到"艺术是一种可以传播的人类行为方式,它被看作是表明形态良好或发育正常的重要标志",正因为如此,它"不仅在统计学上属于平均水平,因它成功地普遍分布于人群中,而且,在评价意义上最终也成了一种规范,无论它开始的出现是作为一种适应还是作为一个拱肩.
"这里有个障碍:以此观点来看,任何形式的"人类行为",只要它是我们认识能力的充分表达,而且分布足够普遍并被牢固确立,那它一定是一种适应性特征.
这有点令人担忧,因为这网撒得也太开了.
以此观点,如果艺术是一种适应性特征,那么阅读、写作肯定也是.
一个人在阅读与写作中当然会显示他的智慧;而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不能阅读或写作当然是一个明显的缺陷.
那么,依照戴维斯的观点,阅读和写作就是适存性的强烈信号,因此也是适应性特征,无论其根源如何.
我们可以勉强承认,阅读、写作像其他一些变革性技术,比如火以及一系列的文化传承实践一样,实际都是适应性特征.
既然艺术是适应性的,那么出于相同的机制,它们也都获得了适应性特征的名份.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观点解释了艺术,但其恰恰是把艺术看作是另一种极具认识挑战性且被普遍牢固确立的技术实践.
如果说艺术的价值有其独特的原因——假若艺术不仅仅是技术——那么,戴维斯的观点对此似乎只能无言以对.
在某种意义上,这似乎是一个好结果.
它让我们看到了对于帮助我们理解,生物学所能做到的极限.
关于艺术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进化论的解读是有贡献的,但仅限于把艺术看作是一种技术.
艺术看起来与技术非常相似;它是无用的技术;艺术作品是奇特的工具.
因此,事实上,艺术与其技术根源从本质上来讲将永远是不可区分的.
艺术家的绘画作品从物质来讲可能与广告商的广告画没有什么分别,虽然一幅画是艺术品,而另一幅画只是一则广告,它们两者在本质上没有差别.
因此,由我在本书中形成的观点来看,上述看法与达尔文主义有些搭调:依着达尔文的进化论解释,艺术与技术看上去应该完全相同.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它们并不相同.
技术是为目的服务的,而艺术恰恰是要质疑那些目的.
艺术承担的任务是揭示、改造和重组;艺术就是要质疑那些让技术应用成为可能的价值、规则、惯例以及假设.
因此,如果说艺术的意义超越了它在我们生活中作为技术的意义——的确如此——那么,我们就需要跳出进化论,以别的方式来解读.
·一阶的组织活动对应二阶的重组实践,这种分析框架可以帮助我们弄清这一问题.
在被我引申的、社会意义上,这是一个生物学事实:我们是在一阶活动上被组织起来的.
因此,如果用达尔文进化论的框架可以解释这些一阶的活动,那倒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戴维斯的探讨对此给出的解释比我了解的其他任何解释都更为确切.
但我们不应期望这种解释也能适用于二阶的重组实践.
因为重组实践不是,至少看上去一点都不像一阶的社会、生物组织模式;相反,它们是一些探究模式,是对关于我们生存状态的、一阶活动的研究和展示.
事实上,现在进化论学者的理论处境可能还要更糟,原因可能与内在过度简化的一阶、二阶的对比有关.
在第4章与本章里我们已经充分探讨了跳舞与谈话(现在甚至还包括知觉)这些一阶的活动,由于对这些活动的二阶研究反过来改变了它们,一阶活动又得到了重新组织.
这意味着,即便是谈话、观看、画画这样的一阶活动也总是要被二阶的艺术与哲学所引导和体现,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也会活跃在二阶艺术与哲学之中.
我们可以说,艺术与哲学总是近在咫尺.
这意味着艺术与现实生活和组织活动是并生共存的,艺术与哲学一直就在人类生活的边缘.
艺术与哲学早已含蓄地存在于我们基本的、组织的、植根于生物性的生活方式之中.
而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在以另一种方式表明一件人所共知的事实:人类是动物——我们被活动模式局限着——但我们又不仅仅是动物.
我们是动物,但决不仅仅满足于从事生存活动;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我们总会有千头万绪的思想,这些千头万绪的思想又是从哪来的.
我说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当然,人类是动物却不仅仅是动物,这一命题的确也是两大阵营的分界线.
自然学者,无论哪种流派都牢牢抱持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应该能够了解我们的本性,作为一个物种的动物本性.
许多人拒绝接受这种自然主义.
首先是人文学者,他们坚持认为文化性游离于生物性之外,不受生物性的限制;人类本性中没有任何一项能够限制我们成为怎样的人、有怎样的思想、怎样的价值观.
同时,那些拒绝接受科学的人也会反对,无论是出于宗教原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我非常同情自然学者,我们的确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
而且随着本书讨论的深入,这已经初露端倪:艺术与人类的生物天性密切相关.
但关键是,没有什么逼迫我们必须要说人类属于畜类;相反,我们可以说,人类畜类都是生物类,每一类下面都涵盖芸芸众生.
坚持认为我们能够以解释畜类的方式完全透彻地解释人类,这未免过于固守教条、缺乏想象.
我们干嘛要这么认为相反,因为我们不能以解释大猩猩、玉米或细菌等的方式来同样地解释人类,就此以为人类一定是神圣天赐、是超自然的生物,这种想法也是同样地顽固不化.
·小时候,我常在华盛顿广场的公园里玩耍.
有一天——那会儿我肯定不过11岁——在公园入口处我见到一群愤怒的抗议民众.
从他们的标语牌上我得知,纽约大学邀请了一位"纳粹分子"到学校来做讲座.
这可太恐怖了!
群众被激怒了.
记得我当时非常害怕,所以至今仍记得演讲人的名字:爱德华·威尔森(E.
O.
Wilson).
如今,爱德华·威尔森是哈佛大学著名的生物学家,他不是、也从来不是什么纳粹分子.
但是,他的确敢于捍卫"社会生物学".
根据社会生物学理论,人类社会生活的某些特征,就如蚂蚁的生活一样,是可以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解释的.
而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人们的政治想象力里,生物决定论本身就带有种族理论、人种优良学和伪科学的意味.
抗议群众想要湮灭这种讨论.
几年后,我坐在上西区某家餐厅的餐桌旁听人在讨论一本重要的新书,叫做《人的误测》(TheMismeasureofMan),这本书的作者是来自哈佛大学的科学家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JayGould).
他在书中讲到,偏见与错误的价值观塑造了所谓的人类智慧科学.
其中的寓意是,当考虑价值观和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人的时候,没有科学的位置.
好吧,绕了一大圈,让我们回到正题.
不久前托马斯·内格尔(TomasNagel)在他的一本书中大胆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代生物学是否有资格声称它能解释人类本性.
该语一出,他立时广遭批判,有人说他加入到了宗教权力以及愚昧无知的反科学队伍之中.
尽管他的论点与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表的一篇论文实际并无不同——当时那篇论文让他一举成名——但现如今世事已变.
在一片谴责声中,内格尔受伤不浅.
我们力图以生物进化论来解读艺术,这是本章的话题;此时,我们需要提醒自己注意这种瞬息万变的政治大背景.
·艺术必须被还原为神经生物学或进化生物学现象,持此观点的人代表的不是科学,也不是出于理性.
他们的立场是关于科学和科学原则的幻想;他们代表的是科学主义,而非科学.
科学主义坚持认为我们可以客观地描述现实世界,不会受到我们个人的特别兴趣、需求、价值观或立场的影响.
据说,假如在某个遥远的星球上有科学家存在,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对这世界的描述会与地球上科学家的描述不谋而合.
但事实是,我们被囿于躯体,只能用自己的感官来体验这世界,且只能以秒、分、时、天、年等来认知时间尺度.
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的局限,而科学方法所做的恰恰是让我们超越这一局限.
如内格尔所述,科学的目的就是形成一种"本然的观点"(viewfromnowhere),或者用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Williamsburg)的话说,就是"绝对的实在观"(absoluteconceptionofreality).
这似乎像是笛卡尔的观点,我们的观点是出自固有意识;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丰富多彩、热闹纷呈,但这是一种虚假的表象,是我们自己杜撰与个人知觉的结果.
我们似乎看到的物质属性不会被载入绝对实在的最终描绘中,因为它们不过是经过我们大脑处理后的效果;它们本身是没有色彩、黯然无声的.
物质世界,至少在笛卡尔和牛顿及最早的科学革命者看来,是由遵循力学原理运动着的微粒组成的.
周围世界中我们认识的所有东西——从山川湖泊到冰激凌、从晚霞到玫瑰花瓣、从太阳到地球——都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都是由物理粒子构成的,粒子本身又由更小的粒子构成.
归根到底,一切的一切,去除品性,都是纯粹的物质.
照此描绘的科学主义,就与人们所谓的还原唯物主义无异.
还原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所有东西都是由以不同方式结合而成的物质构成的.
还原唯物主义有一个更深远的结果就是,最终科学会对所有东西给出一个大一统的解释.
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一切的一切都是物理的(或者是物理和化学的).
有人说,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就是坚信上帝不存在.
事情不是这样.
在这一意义上,科学没有世界观.
科学的立场就好比一个需要修车的女人所持的立场.
"检查引擎"灯亮了,她想知道原因.
灯亮了需要解释,这就好像是她身上有一痒处,要去挠它.
现在,对于"检查引擎"灯为什么亮了,有着无数种可能的解释,包括"它并没真亮,一定是我的幻觉""我的守护天使觉得今天我不宜出门""间谍在我车上做了手脚"……但这些都不是很好的解释,因为它们都不合乎常理,也就是说,它们根本挠不到痒处.
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是,在正常情况下,它们不太可能发生.
照常规来看,更大的可能应该是,发动机打不着火了.
另一个原因是,这种解释发生的可能性太小,它们引起的问题可能比解答的问题还要多,这就好像是在用羽毛挠痒.
在我看来,真正自然的、科学的态度应该就是,承认发动机坏了.
有人说,科学坚信这世上没有上帝——仿佛这事是科学的发现一样,或是它学来的或探索得来的,或是终归能发现的——事情并非如此;更为恰当的说法是,对科学来说,上帝并不相干.
如果你是虔诚的信徒,我猜这也够糟了.
但是,要做出实质性的断言——上帝不存在——是一回事,而说上帝的问题与自然科学互不相干又是另一回事.
也就是说,在自然科学里,上帝的问题并不出现.
一些宗教思想家,如著名的哲学家阿尔文·普兰丁格(AlvinPlantinga)认为,如果没有上帝,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我们自己的认知能力.
他宣称,科学态度是自相矛盾的.
为什么这么说他的持论大致如此:根据科学,我们的认知器官得到进化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增强我们的适存能力,而不是为了准确真实地反映世界.
那么,站在科学的立场来看,它所信仰的只不过是一簇带电的神经元,它们的作用不是去获得真相——真相又意味着什么——而只是让我们的身体达到它所需要的状态,以躲避猎食者、获得食物、找到配偶等,这算是什么信仰因此,科学势必会要求我们的认知能力并不可靠.
可是这样一来,我们又怎么能够认真地看待科学,把它当作是我们可以信赖的东西证明其真实性的证据都是自相矛盾的.
这种持论很机巧,但他自己也是糊涂的.
它对科学的思考就跟科学主义一样,把科学当成了一种解释万物的庞大万能理论.
重要的是,科学并非信仰科学的可靠性,或就此事来讲,信仰人类认知能力的可靠性.
科学是我们理性的一种表达,而不是对它的一种信仰.
请思考:理性不是规定我们可以怎样想、不可以怎样想的一套古板的规则和规定,而是去体会我们的兴趣、知识、证据、关注以及我们对"其他条件相等"的感觉,怎样形成我们关于哪些是可能的、哪些是恰当的、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重要的判断.
而关于女人修车的这件事,如果她足够理性,她就不会再费心去想什么守护天使、幻觉或间谍之类.
我们不需上帝就能做到理性和理智.
事实上,如果我们没有敏感的理性,连哪是合理解释,哪是不合理解释都分不清的话,那么,我们也便弄不懂上帝或别的任何东西——我们分不清什么叫"分清".
而一个科学的理论,比方说进化论,也不能给我们证据证明我们不够理性.
平心而论,理性表现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中,它不需要我们去争辩,我们也不能争辩.
我们不需上帝来保证我们的理智和理性.
普兰丁格就是在此犯了谜糊.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也无需科学来保证我们的理性.
理性不是一种生理特征——像蝴蝶翅膀的颜色一样——会置其他于不顾而自己发生改变.
理性是一种状态,我们可以称之为思想,或知觉,或意识.
因此,如果我们要研究理性的生物基础,那我们的研究必须要以理性为前提,无论它有多么的不完美、多么的问题重重.
科学主义不仅形成了我们的文化对待思想问题、意识问题以及人性问题的态度,也塑造了对于艺术本质的态度.
但是,拒绝接受一个大一统的科学和还原唯物主义的论断并不一定是要背弃科学.
而拒绝承认进化生物学(或神经生物学)具备资源作出对人性的解释,并不意味着要拥护什么不靠谱的理论,如神创论,或是去散播迷信.
就因为我们无论是以神经生物学还是以进化生物学都无法解释艺术,或理性,或更概括地说是价值观,因此就要放弃把自己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来进行解读,这种想法是非常愚蠢的.
因为它的前提是,吸引我们兴趣的所有现象,本质上都与生物进化论或是神经生物学有关.
但是,科学中没有任何东西会引导我们去接纳这样一种狭隘的观点.
无论我们还知道些什么——我在本章以及第10章的阐述就是要保障这一知识——我们都知道,关于我们对自己的解释,我们现在所做的与还原唯物主义或神经生物学或进化生物论毫无相似之处.
·我们不能将艺术还原为天生的审美意识,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
相比艺术,审美意识有着更为广阔的施展空间.
而且,如我所说,在艺术缺席的情况下,想要弄懂审美意识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因为是艺术给了我们图画,又是图画使得审美意识成为可能.
但是,我们可以说,千百年来我们一直在创作艺术,我们为了审美意识而创作艺术,更多的是因为我们要解读它,而不是因为要激发它.
并非因为如哲学家杰西·普林兹(JessePrinz)所说,艺术的目的在于愉悦或惊叹,或是任何其他的感受或情绪状态.
艺术的目的在于向我们自己揭露自己,因此它旨在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去获得对周围世界的感性自觉——包括审美自觉.
艺术研究审美,并非因为它旨在创造特殊的"审美"体验,而是因为关于我们是什么,我们与周围世界是何种关系,审美标志着一个重要的方面.
如果我们没有能力采取一种审美态度,那么,我们也便不需要艺术与哲学,或者没有能力从事艺术与哲学.
第6章关于狂喜、运动与幽默的短笺艺术的哲学性并不妨碍我们有此种体认:有时,艺术带来的只不过是一种狂喜的体验.
事实上,它反而解释了这种狂喜.
狂喜(Ecstasy),字面的意思是超脱自我或是一种浑然忘我的状态(Ek意为"超出",而stasis意为"状态").
狂喜的特征是你不由自主、不能自已、也不想自已,但是你的行为会引领你直至巅峰,然后不可避免地戛然而止.
这是一种高潮,一种满足,却也是一种解脱.
但是,我们一直在想,这种结构正是艺术的决定性特征——被困其中,不能自已,突然爆发——也恰恰是这种结构确定了艺术在我们人生体悟中的重要位置.
我们可以说,艺术释放了我们,给我们自由.
我们的活动、思想、谈话、知觉、意识被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组织起来,或被束缚着;艺术让我们突破这些束缚.
束缚是我们的天性,得到组织是我们的生物需求,可以说,束缚和组织是活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动物.
冲动、本能、反射——它们把我们与周围环境、与任务、与物品以及其他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但我们又不仅仅是动物.
我们的束缚令我们迷茫,它是我们的负担,也使我们感到困惑.
我们试图挣脱束缚,或至少对它的形式能有所了解.
或者,换种说法,一种我们时有体验、抓住我们感情的说法:我们是在寻求一种忘我的狂喜.
上一章,在讨论迪萨纳亚克对艺术的进化论解释时,我们曾探讨过惠特曼的诗歌.
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惠特曼的诗句:我听到曼妙的女高音,技艺高超、训练有素她令我颤栗,像立在爱的巅峰交响乐队令我晕眩,天旋地转胸中涌出不可名状的芬芳我的心在悸动,仿佛坠入恐惧的深渊它带我乘风远航……我赤裸双脚轻轻试探……顽皮的海浪舔舐着它们我彻底袒露……却被一阵无情的狂风毒雹撕裂沉醉在甜蜜的吗啡里……我的气管揪紧挣扎在死亡边缘再度释放,感受这谜中之谜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生命的意义惠特曼描述的是艺术带来的狂喜:他被俘获、感到颤栗、乘风远航、轻轻试探、被舔舐、沉醉其中、被揪紧、窒息,被拽下来,被深深拘住,但他最终还是被"再度释放",或者说,是获释,戛然而止;他被"再度释放"后遇见的不仅是"生命的意义",而是作为"谜中之谜"的生命意义.
在此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曼妙的女高音音乐激发了一种狂喜的反应,好像这狂喜只是一种强烈的反应,一种特殊的躁动.
不,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歌者的歌声带来了一种参与,一种被困,然后是获释后的发现,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在这种参与中我们找到了艺术的体验.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曾提出,尽管惠特曼的诗歌有其独特的魅力和艺术价值,但并未在我们身上产生他所描绘的那种强烈的肉体上的效应,作为对歌者的反应.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承认,在某种意义上,他的诗在我们身上的确产生了足可比拟的效果.
当然,那不是一种生理上的骚动,而恰恰是那种参与感;那种被俘获的感觉,那种为获释而付出的努力.
现在我们能够体会到,这是艺术的根本,因为它与人类的状态如此紧密地相联.
我在本书中的论点是,艺术是摧毁性的、颠覆性的,它也是一种探究方法,一种研究模式,旨在改造和重组.
艺术通过颠覆来探究和暴露.
我极力主张,艺术是一种哲学实践.
这一说法可能会产生一个结果,即任何东西都可以是艺术,但是,至少从其内在本质来看,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证成为艺术,艺术总是要被置于联系与语境之中.
艺术总有它的一个要点,就像笑话有一个笑点一样.
笑话是一种最基本的、随手可得的艺术形式.
讲笑话时我们需要做点什么,或是要激起一种反应,但我们永远不能避开一个事实,即我们必须要针对当时所处的交流氛围和讲述场景.
这么说吧,幽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门槛很低.
讲笑话的人把笑点、幽默、包袱抖给你,他感觉你能懂就可以讲给你听.
他的幽默是要以你所知道的内容为背景,或者说是你知我知大家共知的内容.
喜剧的乐趣——它们的乐趣真是甜蜜可人、回味无穷啊——就来自于大家共同的心领神会.
维特根斯坦说,你可以写一部哲学书,全部由笑话组成.
这里的关键不是说你可以用笑话来进行哲学创作,而是说每个笑话都会唤起一段品鉴时刻.
当进入笑话时,我们会发现自己要思考,要做出反应,要去评价、猜想、喜欢,也或许被拒之门外、被关掉,完全不知所云.
这正是哲学的洞见.
喜剧演员——专业讲笑话的人和滑稽演员——不仅仅讲笑话;也是在把讲笑话这件事展示出来给大家看,甚至同时也把自己作为表演者展示出来,以此让我们发现自己是在对别人进行观察和思考.
喜剧大师是在以讲述来创作艺术.
与其他艺术家一样,他们用艺术创造艺术,也因此——又像其他艺术家一样——他们使得艺术创作本身成为他们一个永恒的主题.
运动员就不是这样,他们可以是表演者却不是艺术家.
体育运动可以有恢宏壮观的场面,运动员的表现有时也会精彩纷呈、激动人心,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意义非凡,令人赞叹,当然配得上我们的兴趣与关注.
但是,体育运动中从没有艺术.
关于表演体育与表演艺术的这种分别是很容易理解的.
体育有着明确的、公认的目标,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获胜或获得佳绩,而且总是把什么是赢、什么算作成就视作是理所当然的事.
运动员是预设目标以及既定游戏规则的奴隶,艺术家则是在书写传奇:他们拒绝循规蹈矩,从不按规则游戏,或者,他们会邀请你同他们一起创造规则.
运动员是奴隶,而艺术家则获得彻底的解放.
这与创新无关,运动员也会创新.
想象第一位采取背越式的跳高运动员,他创造性地弯曲身体、后背向下越过横杆(著名的"福斯贝里式跳高"),还有那些创新投球方式或划水动作的运动员,那些应用新设备或新材料的运动员.
但是无论多么伟大的运动员都永远不会改写运动规则;对于怎样算"好"、怎样算是"成功",他们不会改写评价标准.
比如,拳王阿里使用倚绳战术,前屈身体、掩护自己,承受着来自对手的连连攻击,其目的就是要消耗对手.
"这哪是拳击!
"可能有人不由会这样说.
但是,当天结束,裁定它就是拳击、评估阿里成功的,还是基于规则、得分、点数等等人们熟悉的拳击标准.
体育运动与艺术分属不同的范畴,两者互不相干.
但这也留出了空间,让人们可以把体育运动当作原始素材进行艺术创作.
恰如事实上有跳舞的艺术一样,我们也可以有运动的艺术.
但是,正如舞蹈艺术家不再是简单的舞者,运动艺术也不再是体育运动.
有意思的是,就像舞蹈在一个多世纪前才开始成为一种艺术,马戏也是近些年来才把自己当作是一种艺术形式.
现在在这个艺术领域里,艺术家开始研究倒立、走钢丝.
他们的目的如在更广阔的艺术世界里一样,就是拒绝把使用技术、技巧看作理所当然,而是去探索这些马戏技术需要怎样的前提——它与表演、观众的关系,与高、低层次的文化政治的关系,与表演者现象的关系,谁是行家,由谁来培养技能,以及与观众现象的联系等等.
在这个场景中,杂耍和高空秋千成了进行研究的现场,让他们得以撇开原来的目标进行创作实践,进行教、学与对话,而这些都是像芭蕾和绘画一样的艺术创作的特征.
某些亚洲武术同样也可能在艺术中占有一席之地.
例如,尽管太极拳与美国拳击一样,搏击是其最初目的和主导思想,但太极拳师却不像拳击手.
因为在太极拳的发展过程中,其核心思想已从一阶的参与搏击和把身体用作武器,转变成了另外一种奇特的、深奥的有关哲学问题的思考.
它包含了对身体本质的认识、我们对身体的掌控、练功与体悟的关系、思想与意念在身体运动中的作用等等.
太极是一种武术,尚武的艺术,也是一种哲学艺术,是关于身体的哲学也是用身体所做的哲学.
在这里,与舞蹈和其他传统艺术一样,同时也与马戏艺术一样,主导太极的文化是围绕着太极大师的影响和权威得到组织和形成的,杨澄甫与陈王廷就与舞蹈大师乔治·巴兰钦和弗西斯一样,或与油画大师提香和马蒂斯一样,是在传承影响中进行创作并发现意义.
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排版、美食、跳舞、倒立、搏击、说话——都可以成为艺术与哲学生发的场所.
的确如此,尽管艺术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活动.
曾有人问我:艺术不就是给人以抚慰、娱乐或是让我们感受那无与伦比、震撼人心的美吗是的,它当然可以是这样.
但重要的是,艺术为何如此重要它又替我们实现了什么这样说远远不够,而这也反过来让我们领会了,为什么即便上面提到的种种艺术什么都不是,它也仍是我们的迫切需要,仍然不可或缺;它也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那些能给我们带来安慰、让我们开心或能触动我们心灵的并不都是艺术.
妈妈的摇篮曲不是艺术,因为它就是哄我们安睡的摇篮曲.
请注意,我们有时的确会转向艺术来寻求安慰,但这并不是反例.
诗人或音乐家祈求安全本身就是一种颠覆,因为它是对那些价值观所处语境的叛逆性解构.
但是,在我看来,大多数时候,人们像这样认为艺术是安全的、令人愉悦的,实际是将艺术与艺术的力量混同为熟悉带来的安全或背景杂音可能提供的逃避.
清洁厨房时听着巴赫的清唱剧,把从现代艺术博物馆买回的海报张贴在墙上,这再常见不过,但这恰恰不是欣赏艺术.
并不是说这样做有什么错,但它完全是另一回事.
第7章哲学之物开始写作本书时,我曾想过,如果以DVD文献片的形式来写倒是个蛮不错的主意.
DVD文献片有个好处,它不必操心怎样让人看见自己要谈的话题.
谈论的时候,它所讲到的东西都会适时地出现在屏幕上,你我都能看到,你需要做的就是做出点明.
但最终我发觉同样的方法无法用到书中,这倒给了我们新的启示:你不能指点艺术;艺术不是一件我们可以想当然的东西.
更为重要的是:怎样引出我们的话题——艺术及其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并形成我们的主题内容,这才真正是我们最大的挑战.
而这也是哲学的典型特征.
在哲学中,我们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怎样提出我们的任务、问题和话题,以便可以继续对它进行讨论.
不管怎么说,这是我在本章的特别关注:列举一些艺术作品,一些哲学之物,以便我们嗣后继续探讨时脑海里能有所参照.
·理查德·塞拉(RichardSerra)创作的雕塑会直击你的感官并改变你的感受,人们常常将此归因于它的庞大尺寸.
毫无疑问,面对30英尺(约9.
144米)高、大船一样的钢体整面陡然倾斜下来,你不免会感到发晕并有轻微的失衡感.
对有些人来说,他们发现自己身处其中是一种新奇和愉悦的体验.
遇到这样的作品你经历的是一种心理展示:你会发现你的所见怎样由自己身体的感觉、你在地面和空间里的位置所构成,并与它们紧密相连.
而有些人会觉得很不舒服.
我认识一位女士,她在参观塞拉的雕塑时,会感到晕眩呕吐.
因此,20世纪80年代,纽约公众会要求拆除位于市中心的塞拉庞大的雕塑《斜拱》(TiltedArc).
或许作为公众艺术,这作品的震撼力太大、冲击力太强了,至少某些人会这么看.
但是,如果我们只局限于它们令人不适的心理冲击力量,那么我们就低估了塞拉作品所能产生的作用.
它们不是特殊效应,不是心理演示.
事实上,甚至把它们称作是物品都是一个错误;它们更应当被称作是一个世界或一道城市景观.
参观这样的作品就是要面对一个现实:你不能观看它们,你无法确定它的位置,因为它不像一件物品那样有它的前面、侧面、后面和清晰的边界.
你不能够退后去审视你的所见,你只能步入其中,随着地势的延展进行探索.
因此,这对你是另一种方式的挑战.
遇见这样的作品与其说你是在看一件你看不懂的东西,不如说你是在某个地方却根本找不到出路.
但这不是心理操控,也不仅仅是对你的冲击,它是在邀请你探索这件作品,由此发现你自己身处何方.
作品就是世界,而这世界给你机会让你去探索、去发现、去学习.
这些作品非常复杂、霸道强悍,但它们的确是在邀你进去.
钢面非常光滑,极具色彩感,有时几乎像丝绒一般茂密繁盛,但表面特征几乎与这类相遇所带来的愉悦无关,这种愉悦来自于从迷途到知返的探索过程.
我要说这里实际上还有一种有意义的启示.
如今,我们总喜欢把神经科学当作万能钥匙去解释所有现象;我们把观看当作是某种发生在大脑里的事情.
事实上,观看需要你整个人(而不仅仅是大脑)的参与,用杜威的话讲,它是一件需要你去做、去经受的交易.
观看,或是其他任何意识体验,都并非发生在我们大脑那个密闭的腔体中,而是在外面,有他人的参与,且是在我们制造的环境中,而这种环境又会反过来围绕我们并推动我们.
塞拉的作品可能会引起某些人心理不适,也可能会戏剧性地夸张.
艺术评论家和艺术史学家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Fried)就觉得它令人反感.
但实际上它为我们所做的工作具有哲学意义:它们是哲学的空间,它让我们记起通过积极生活去发现世界是什么感觉,它令我们内心充满激动.
·几年前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抽象表现主义画展,巴内特·纽曼[5](BarnettNewman)展室是画展的核心.
纽曼的画作看起来很新颖,令人惊叹,异常地引人瞩目,甚至令人肃然起敬.
就连那些吵吵嚷嚷带着大包小裹购物袋、常常会让现代艺术博物馆变得像是候机大厅的游客,在面对这些精神食粮时,也不由自主地安静了下来.
也许是周围的景物让我的感觉发生了变化.
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的许多作品首次展出都是20世纪50年代,在贝蒂·帕尔森画廊,据报道,当时纽曼曾在画廊墙上贴了张告示,提醒参观者不要站得太远,应靠近点仔细观看作品.
这令我颇为吃惊,也觉神奇.
日常生活中,为了看清周围事物我们常常要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
我们会改变文本的距离,使它离我们眼睛近些,或者变换一下头部和身体的位置以看清东西在哪里或发生了什么事.
令人吃惊的是,大多数时候我们做这些事都是自动的、无意识的,为了看清这世界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做出调整:我们向前移动,对准想看的东西;我们后退,我们斜睨着、眯着眼或是再靠近些.
这些试图捕捉世界的巧妙方法悄然地表现着我们无声的动机和思考方式.
走进一间屋子,看到墙上挂着一幅大型画作,我们再自然不过的反应是后退一步寻找最佳角度来观察这幅画,就好像要试穿一个朋友的装备.
无论他的本来意图是什么,纽曼告诫我们不应受制于自然而然的倾向对周围事物做出直接反应——此处,自然的反应就是为了更好地观看眼前景观而自然地后退.
他是在邀请我们打破作为审视者和思想者本来的习惯,去惑乱那些不经思量的动机.
这里,我们不可能改变根本的感知动机和思考方式,但是我们可以让自己警觉它们的存在.
或许纽曼如我一样相信,艺术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发现自己在努力认识这个世界,从而认识自己.
若非如此我们将永远都无法做到.
·2013年威尼斯双年展,提诺·赛格尔[6](TinoSehgal)的情境作品在贾尔迪尼的一个主展厅中展示,我发现自己被深深地吸引了.
若说这一作品有题目,它却没在任何地方张贴.
我称它为"现场作品"而不是"演出",因为作品创作的目的似乎恰恰是要质疑演出的本质.
它没有始末原委,也没有中间过渡,它就是在那儿,像一幅画挂在画廊里一样在那儿.
2人、3人、4人或站或躺在地上,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即兴创作着音乐——隐隐约约地有电子乐声,甚至还有口技声,有时候更像是小声咕哝或是反复的吟唱,但总是很有节奏——他们随着这些自创的音乐匀速地、缓慢地移动,有些动作颇具舞感,另一些则不.
除了在音乐中和流畅的动作进程中展现出的节奏组织外,还有一种明显的组织结构.
演员们——毕竟他们还是演员——彼此互相关照,明确地呼应着动作、手势或声音.
我有一种感觉,他们似乎是在互相模仿,但又不是很直接地模仿,总像是要直抵一个动作或感觉的某种根本的核心品质.
当你进入艺术馆时,作品不会直接跳入你的视线.
有些人在地板上缓缓地动作,发出声音,但他们周围多的是穿梭的游客,作品起先几乎是不可见的.
即使有什么逻辑或规则在主导着演出内容,那也并不明确.
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作品很无聊,然后就想转身离开.
但慢慢地,作品开始进入视线,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当我离开的时候,我感觉若有所悟,看到了某些确定的、独特的东西,也即艺术的东西.
在这一作品中,演员都被当成了道具,当他们停下的时候,你没有鼓掌的冲动或是想去赞美他们的表演.
这是因为他们的表演——尽管随心所欲,常常是即兴发挥——似乎总是被某种任务或指示掌控着.
而且,这一艺术作品并不在乎能否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在表演艺术中吸引注意力是最基本的.
它并不试图抓住你的注意力或引导它,或组织它,作品就在那儿,就像墙上的画一样,而演员也像是电池驱动的机器人一样.
但是,他们当然不是机器,他们是人,而且个个生动可爱,独具特色.
但至少在表面上,对于要做些什么以及怎样诠释他作为一个团队或作为艺术家被指派的任务,很显然(或看起来是这样)他们在做着自己的选择.
他们对你漠不关心,全心地关注着自己,完全投入到任务中.
在我观看演出的90分钟全过程中,只有一位演员曾将目光直接投向我与艺术馆里的其他人.
因为他们在地板上或活动或歌唱,因为艺术馆里满满的到处是人,所以,实际上你能明显地感觉到该作品的空间界限.
当然同时你也有种很担忧的感觉,因为这界限是那么地脆弱.
演员们聚集在地板上形成了一个空间,不时有人——比如说某个孩子——会走进他们的群体;有时会有人站在旁边大声说话或打电话,好像并未注意他们已经侵入或进入了作品的领地.
对于周围人来讲,他们是在扰乱或打断作品,抑或反而是激活了它赛格尔禁止对他的作品进行任何形式的记录.
这意味着,现场的演出者有两个任务:他们要么在地板上"进行"他们的工作;要么在艺术馆内维持展厅的秩序.
每当有人要按下快门拍照时,就会有演员跳出来,阻止他们,像是安插了卧底警察.
这种维护作品边界的行为隶属于作品本身,是它的一部分.
我们看到的是作品里的作品,而我们自己也参与到了节目当中.
戏中戏本是一个让我们细思的内容.
但是,因为我们自己也身处戏中,这戏就是令人焦虑的;它界限不明,主题不定;它是一个争议的对象.
艺术并非如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所想的那样能够激活我们,相反,它给我们机会去激活它,去打开它的开关让它发生.
·当我看着罗伯特·拉扎里尼(RobertLazzarini)的手枪雕塑时,我首先发现的是,我无法对它聚焦.
无论我怎么移动调整位置、怎么眯起眼睛都无济于事,那枪就是拒绝我为了看清周围世界而进行的正常的调整.
拉扎里尼的手枪雕塑似乎超越了我的感官机制,技巧和知识都失去了作用,我无计可施,望而不及.
这种体验非常奇特,我发现自己在怀疑是不是我的眼睛出了什么问题,或许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神经生物功能的失常,一种视觉障碍,无法抓牢我的所见——有形的现实世界化为乌有!
正常生活中,人们变得失明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感官功能(如视网膜或大脑中主管视觉的神经结构)遭到损坏;另一种是视觉功能依然敏锐,但你却发现自己搞不懂映入眼帘的是什么东西,不是因为有别的某些生物神经功能的障碍,就是因为你缺乏弄懂它的技巧和知识.
比如,当你带上左右置换或上下颠倒的眼镜时就会发生类似状况,你无法协调你与周围事物的视觉关系,尽管它们就在那儿,尽管它们的确进入了你的视线,但是在感觉意识里它们却不见了.
当我们的感觉功能不能领会它们的意义时,它们便不复存在.
在这里就是这种情况,拉扎里尼的作品带来的就是这样一种类似失明的感觉.
他创作的手工艺品是对我们视觉的公然反抗,它拒绝我们,让我们无法看清它们.
拉扎里尼破坏了我们与周围世界的顺利沟通.
他的成就正在于此,通过这样——破坏我们与周围世界的顺利沟通——他让我们看到那些未曾注意的东西:我们能否看到这世界要取决于背景技能和场景.
这种艺术,至少是这种艺术,不仅具有指导意义,还是一种研究实践.
拉扎里尼给了我们一件无法分辨或无法聚焦的作品,因此,他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极限:为了看清这世界,我们能做什么,或者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拉扎里尼让我们看见自己在努力地认知这个世界.
这就是哲学的工作.
因此我主张,把拉扎里尼的作品——总起来说是艺术品——都看作是哲学之物,把他的艺术看作是一种哲学实践.
艺术作品是饱含哲理的.
·2012年,当我在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的双年展上看到莎拉·迈克尔逊(SarahMichelson)的作品《奉献研究1#》时,我被打动了,说实话,是被震撼了.
在纽约,她承担的是厚重的舞蹈历史,舞蹈与艺术及音乐与艺术世界的特殊融合,她担负着作为一个创作人的焦虑,她很严肃地对待当下所做的事情,而在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时代,严肃似乎荒诞可笑;演出既要迎合评论家们严苛冷酷的评判标准,同时还要满足为观众创新表演的要求,而这些观众可能自己也并不知道他们在寻找什么,即便找到了也不知道如何分辨.
一位评论家说这作品无聊透顶、令人困倦.
我想它的确很枯燥,就如宗教仪式也会很无聊枯燥,甚至爱、恨、贪婪、性幻想、矛盾情绪,这些如此熟悉、如此单调的感情都可能会很枯燥一样.
但这件作品,就与其他所有这些东西一样,也是一个契机.
作品的源动力是一个有节奏的乐谱.
场景是画在地板上的一幅画,有点像建筑图纸.
动作非常简单,沉着镇定,也很吃力,不断地重复,像是动物.
舞者辛苦地劳作,一直在动,向后旋转,手臂高举,汗流浃背.
整部作品就是关于他们流汗的传奇故事.
首先一位舞者胸部以下的服装开始洇湿,颜色变深,另一位舞者则是裸露的胸膛以及后背,然后是骨盆周围开始闪烁汗光,就像是一只奔忙的动物皮毛上泛出的点点汗珠,最后他们全都湿漉漉地变黑了.
舞者是在劳作,也是在表演.
挺直的身姿,高昂的头,他们像芭蕾舞演员那样展示着自己,镇静优雅,眼神专注.
他们不是劳作的动物,但也不是芭蕾舞演员,他们更像是辛劳的天使在从事着人间的种种创作.
这是些充满矛盾、犹疑的天使,也许是爱、贪婪、仇恨和欲望的天使,他们被奉献给我们,而我们发现自己也被奉献给他们.
这些演员没有给观众鞠躬,对此,我丝毫不感到惊讶.
我们不会在艺术展览馆里给艺术家掌声,演出结束后鼓掌总是一项奇怪的习俗,但这也可以理解.
在那90分钟的时间里,莎拉·迈克尔逊让某些事情发生在那个表演空间中.
发生了什么呢从有控制的动作变成了工作的汗流浃背,从冷酷变成了火热.
作为一名舞者的焦虑挣扎倒变成了一个机会;艺术创作让我们看到天使在扫视着我们.
·罗伯特·欧文(RobertIrwin)在惠特尼博物馆里展出的作品正是其作品名称所表现的元素:薄纱幕黑色矩形自然光.
没有什么神秘之处,没有什么魔幻成分.
一个庞大的矩形房间被一块悬垂下来绷紧的薄纱幕布纵向隔开,薄幕悬挂至大约头顶的高度,半透明材质,从某些角度看若隐若现,另有些角度则根本无法穿透;幕布上有一条粗重的黑色边线,墙上也画了一条黑色粗线,将墙上下隔断,阳光穿过走廊尽头唯一的大窗照射进来.
当人们进入惠特尼博物馆4层的展室时,你总能听到他们发出的惊叹声.
(顺便说一句,迈克尔逊的作品曾在这同一间展室里上演.
)这些元素结合在一起的效果不仅华丽惊艳,而且令人震撼.
是的,这里面的确利用了人们的视觉偏差,你并不总能看见薄幕,而且因为薄幕边缘的黑线,以及背后墙上类似的黑线,让你感觉这两条线就好像是一条,因此,你搞不清它们在空间里的位置.
但是作品的神奇之处并不在于仅仅是在玩视觉游戏,我希望我能弄懂它的真实含义.
这件作品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它没有焦点.
首先,你身处其中,因此你无法看清它;其次,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件东西可以让你观看或注视,或者说,所有的东西——窗户、薄纱幕、边线、地板、墙壁、展室里的其他人——都同样地吸引注意力.
与市区古根海姆博物馆里詹姆斯·特瑞尔(JamesTurrell)主题相似的展出相比,看特瑞尔的作品你知道该看哪里,它有东西让你去审视.
(我记起一件作品:一个昏暗的房间,对面墙上是一个蓝色的矩形.
在那一刻你会突然想到,这矩形就是一扇窗户,外面就是沐浴在蓝天下的广阔天地.
)或者再对比理查德·塞拉.
塞拉的作品让你迷失方向,逼迫你去探索.
你不能站在原地不动,你必须做点什么.
但欧文的作品不是这样.
在这里,你什么都不能做;或者,我们猜,是你需要做的事情太多.
作品只是一个地方,一个存在的地方,一个纯粹的地方.
空间和光,难道这就是我们喜欢待在里面的原因吗·有时候艺术就是让事情随其自然,给你机会让你去发现,比如惠特尼艺术博物馆里罗伯特·欧文的作品;而有时艺术又像是当头一棒、醍醐灌顶,让你有新的体验,比如理查德·塞拉的作品.
但也有时,这两者会同时发生,比如安利·萨拉(AnriSala)2013年威尼斯双年展上法国展厅里的作品,强悍、喧闹,同时却也冷静、低调.
在第一展室里,你看到的是一个女人的影片,镜头离得很近,你只能看见她的脸.
她似乎是在制作音乐,我们能听到乐声;或者她只是在倾听音乐从她的脸上,以及头部状态,你能够看出她是把整个身体都投入在音乐中,那是拉威尔(Ravel)的左手钢琴协奏曲.
不可能是她在演奏,感觉不像有交响乐队在场的样子,但从她的上半身来看,她有可能是在弹奏钢琴.
然后音乐时而会加速,时而会慢下来,似乎有一位DJ在操控着混音台.
第一展室的展出令人困惑.
第二展室声音洪大,振奋人心.
墙上有两部投影,每部影片里映出的都是一位钢琴师演奏的左手(骨节粗大、汗毛粗重的男人的大手).
他在与交响乐队演奏拉威尔的协奏曲.
但是两部影片中演出的是两位不同的独奏者,即便他们用的是同一份乐谱——事实上,两份录音录的是同一支乐队,同一位指挥——但钢琴独奏有着不同的选择,不同的时间节奏,结果就是多个层次的甜美的不和谐音,时而会有两个版本的会合,令人愉快.
艺术评论家布莱克·高普尼克(BlakeGopnik)说道,想不到拉威尔协奏曲以不同的方式被同时弹奏两遍竟有这么好听.
但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我们在第一展室看到一个女人的面部特写,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两只在弹奏钢琴的左手的特写.
这令我想起了小时候在《芝麻街》里看过的老把戏:一只手被当作一个木偶,这只手有时看上去很忧伤,但同时它也会看起来很开心很满足,我喜欢那种老把戏.
这里也是一样:看见两只手在键盘上翻飞,你感觉就像是看着两个完整的人,两个聪颖的人完整地出现在你面前.
这让我们想起这首乐曲的创作历史.
拉威尔为保罗·维特根斯坦(PaulWittgenstein)写了这首曲子.
维特根斯坦是著名的钢琴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右手.
此曲是为一名身体不健全的人量身打造,专门创作的.
但此时,左手出现在这里,与第一展室的那张女人的脸一样的完整、健全,它表现的就是一个完整的、健全的人.
这又让我们想起它的哲学含义.
保罗·维特根斯坦恰巧是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兄弟,路德维希是20世纪最有创意、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
维特根斯坦写作里的一个中心主题就是我们的"内在"生命(感情与思想)与"外在"生命(运动与身体)的联系.
维特根斯坦认为,它们不是两个分隔的领域.
一个人不仅仅是困在身体里的思想,而是一个活动着的活生生的人.
第一、第二展室是关于解读拉威尔——展出的题目就叫作拉威尔谜题之解(RavelUnravel).
第三展室把这些元素都复原到了一起,在这里的影片里,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第一展室里见过的女人,她坐在由两台唱机转盘组成的混音台前,正在将两张独立的唱片进行混音,尽可能地把它们合成一个录音.
她让一个转盘慢下来,把另一转盘加速,她在操控,在创作.
阳光从她背后直射进洁净的白色房间——在威尼斯展出的影片正是拍摄于这家艺术馆——乐声飞扬,她的身上也闪烁着创造的光芒.
艺术创作、歌曲制作的力量,或者说是关于歌曲制作的艺术创作的力量.
但在此发生的还不仅仅是这些.
萨拉的创意是让两位男钢琴手分别演绎浪漫的法国作曲家为一位哲学家的单手兄弟创作的乐曲,然后让一个有两只手的女人来合成这两只男性大手演绎的不同版本的音乐,使它们形成一曲全新的音乐作品.
技术,或曰由手至钢琴键盘、至笔记本电脑、至混音台的旅程,是最终存在于本件作品里永恒的主题.
技术延伸了我们,也延伸了我们所能做的事,由此也延伸了我们会成为何样的人.
技术把混音台前的女人,两位钢琴手,一支交响乐队,拉威尔,以及我们所有这些人都带到了威尼斯,全神贯注地坐在这里,让我们进入一种全新的体验.
·那天晚上,我再次观看了罗曼·波兰斯基(RomanPolanski)的电影《罗丝玛丽的婴儿》(又译《魔鬼圣婴》)(Rosemary'sBaby).
这是一部鬼怪影片,与同类题材最佳电影一样,你也可以称它为悬疑影片.
它富有哲理,更重要的是,它之所以恐怖正是因为它富有哲理.
对年轻的罗丝玛丽来说,事情有点不太对劲.
她的丈夫疏远、冷漠、只关注自己,甚至凶暴残忍;他大部分闲暇时间都与隔壁的新邻居,一对奇怪的老夫妇厮混在一起.
罗丝玛丽怀孕非常艰难,她总是不断疼痛并一天天消瘦,无论是医生还是她丈夫似乎都不想帮她.
罗丝玛丽开始感到昏昏沉沉,好像是药物的作用.
为了让心情轻松起来,她请人重新粉刷了他们的新公寓,但这对驱散大厅和房间里的阴暗丝毫没有帮助.
在这样一种阴郁的剧情下,唯一的亮点是她的丈夫盖伊工作上有了转机.
他是一名演员,由于竞争对手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双目失明,他获得了主演的机会,事业发达似乎近在咫尺.
《罗丝玛丽的婴儿》讲述的是她怎么渐渐地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
开始时罗丝玛丽拒绝承认这一结论.
怎么会有什么不对呢怀孕有时会让人感到痛苦,丈夫们工作忙压力大也时有发生,生活并不总是像童话故事般美好.
她安慰自己,并下定决心要做一个好妻子.
她要与盖伊坦诚相待,并帮助他能更坦诚地对待他们的关系.
现在,电影的悬疑特征转化成为哲学中一个永恒的关注:我们是否有可能了解别人以及别人的想法与感受.
哲学家们早就注意到,在这一领域有着很大的质疑空间:当事关别人时,我们所真正了解的,只是他们的言行,我们不可能进到他们脑子里去直接了解他们真正的想法和感受;我们与别人总隔着一定距离.
很显然,对哲学来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也一样,这种心理忧虑在我们正常的生活中大可放心地置之不理.
关于周围的人到底怎样想、怎样做、怎样感受的问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会真的让我们忧心,更不用说关于他们是否会有内在生命的问题.
这就提出了一个哲学问题:如果我们的知识基础如此薄弱,我们对他人心思的信心凭什么如此强大有时候,在遭遇神经创伤的情况下,比如,当面临一个人处于持久的植物状态时,我们必须做出决定,就要知道这个严重受伤的人心里究竟想了些什么,此时,这种忧虑便有了现实的突出的意义.
但电影《罗丝玛丽的婴儿》以一种更为惊悚的方式探讨了这些问题.
对罗丝玛丽来说,对我们、对观众来说也是一样,事情慢慢变得清晰:我们不能再相信盖伊,也不能再相信她的邻居,以及医生,甚至是罗丝玛丽生活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对于罗丝玛丽身边所有人思想和感受的怀疑现在成了一个必须被严肃对待的命题.
她的生命,她孩子的生命都取决于它,似乎她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的受害者,而且(几乎)所有人,即便是她最亲近的人也都参与了这一阴谋.
但这是不是太疯狂当然会有这样的感觉.
怎么可能所有人都参与其中呢此时,电影的悬疑主题被推到了一个极点:有没有可能这是她的幻觉,或者整件事都是她自己的凭空想象有没有可能这是某种产前忧郁症她、我们,能知道真实的情况吗《罗丝玛丽的婴儿》不仅仅是一部心理恐怖片,它还是一部鬼怪电影.
罗丝玛丽的境况之所以变得如此艰难,是因为电影中真正发生的事,真正驱动的事件是如此地不可能发生、如此的不可思议,以至于想直截了当地去"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的可能性都被排除净尽了.
魔鬼撒旦来到世上强暴了罗丝玛丽,在她丈夫的帮助之下.
这也太离谱了,不可能是真的,离谱得甚至不可想象.
恐怖电影的独特魅力正是出现在这种关键时刻,著名艺术哲学家诺埃尔·卡洛尔(NoelCarroll)说.
所有的叙述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志,那就是他们能让我们获得认知享受.
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我们感到好奇;好奇心刺激我们紧追故事的发展,去想象后面会发生什么,去体会某种情境下的力量怎样推动着事件势不可挡地向前发展.
情节需要认知,故事的乐趣就在于你能读懂它,获得对它的认识.
我认为卡洛尔的这番话颇有道理,亚里士多德在谈及悲剧时早已预见了这一基本观念.
亚里士多德说,剧情是悲剧的生命和灵魂.
而剧情关注的不仅仅是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是这事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它更多的是关注人的行为.
因此,要讲好一个故事,或者是作为一名观众要好好欣赏一个故事,你必须敏感地知道在一个人的生活场景中是什么让自己的行为有意义.
你需要当一名学生,学习人类的本性与经验.
正是因为戏剧作品,如此处展现的悲剧,有内容、有意义,是对人类体验的思想探索,我们才有可能仅靠阅读就能体会到戏剧的乐趣.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打动我们的并非壮观场面,而是领会,是理解.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同时享受故事所带来的感受或情绪反应.
悲剧,亚里士多德认为,其目的总是为了唤起恐惧或同情;但它的目的不是让你像坐过山车那样产生一种危险感觉.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恐惧不只是在我们身上或心里所产生的一种效应;它是我们对故事情节保持敏感的表现,因此,恐惧本身就证明我们已经对其达到了理解和洞悉.
现在来看卡洛尔的论点:恐怖片与其他题材影片的区别在于,恐怖题材的核心是一个无法真正弄明白的鬼怪现象.
鬼怪不可测、不可知;他们介于中间,既非生亦非死,既非人又非兽,既非自然又非真的超自然.
如卡洛尔所说,他们是处于夹缝间的.
重点是,我们根本无法理解鬼怪,我们的好奇心得不到真正的满足.
那么我要说,一部优秀的恐怖电影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悖论:它把我们带入一个谜题之中,但其内在的固有特征却从根本上排除了谜底.
而正是恐怖艺术的这一独特特征让我们能够进行这种独特的无解的哲学思考.
由此观点来看,鬼怪片的恐怖还是次要的.
我们喜欢恐怖电影并非因为我们喜欢负面情绪,而是因为恐怖电影在我们身上激发的负面情绪已经被其带来的哲学享受所超越.
我不确信这种解释对于电影《罗丝玛丽的婴儿》是否公正;或许它真正的恐怖来自于哲学家也未必能解答的悬疑:疑惑与知识的局限实际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即彻底的、绝对的、凄惨的、恐怖的孤独.
但这是我们想去发现的吗即便得到解答我们能感到愉悦吗第二部分艺术的目的就是要把被答案掩盖的问题曝露出来.
——致敬詹姆斯·鲍德温第8章看你是否独具慧眼什么是艺术为什么它对我们如此重要关于我们自己它又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停,停,停!
你可能会说,即便你知道答案,也请别告诉我们!
我们不想知道,请别毁了我们的期望.
这让我想起人们关于笑话的言论:笑话是不能解释的;试图解释就会毁了它.
这颇有几分道理:需要解释,就已经太晚了,你根本没听懂,而解释也不会让你笑出来.
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也不完全对.
说到笑话,有些东西需要你去领会,也因此有些东西需要解释.
它为什么好笑即使你很难给出恰当的答案,但这问题总提得没错,而且即便理解了别人的解释也不能替代你自行体会到段子的妙处所获得的满足.
解释、谈论或讲出段子里的笑点无法与会意而笑相提并论;你不可能凭解释让人捧腹大笑,因此,你也不可能因为谈论一个笑话就毁了它.
对艺术也是这样,解读艺术及其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并不会有损于它.
你不可能仅仅因为思考艺术就破坏了艺术的魅力.
可实际上,如今的确有一种倾向:有人想要,至少是试图要解释艺术——以及幽默及所有其他东西——这真的有可能毁掉它.
什么是艺术我们为何看重它关于我们自己它能告诉我们些什么许多人认为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都能在神经科学里找到解答:我们认为我们身上所有重要的东西都是由大脑掌控的,只要把研究重点内转我们就能发现我们的真实天性.
因此,当我们面临弄懂艺术的任务时,转向神经科学似乎成了正确的选择.
我的态度有所不同.
并非因为把艺术与我们的生物状态联系起来去解读有何不妥,事实上,这是一个令人兴奋也颇有意义的想法;而是因为关于我们的生命状态,神经科学尚有待形成一个充分的理论框架.
我们不能想当然地把神经科学当作是一件现成的知识装备.
伦敦大学的神经科学家泽米尔·泽基(SemirZeki)总喜欢说,艺术是由我们的大脑活动规律掌管的.
他说,让我们发现艺术的是大脑,让我们创作艺术的也是大脑.
一个人就是他的脑细胞与相关分子的功能集合,这一观点不是神经科学的探索发现,甚至不是它的主张;这是他们想当然的看法.
脑即我,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Crick)把这称作是"惊人的假说",他说因为这实在是超出了多数人关于自己的想象.
但是,关于这本该是惊世骇俗的假说,真正令人惊诧的地方竟在于,正如我们前面曾讲到过的,它实际毫无新奇之处.
我们身体里有一个东西在思考、在感觉,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这观点古已有之.
笛卡尔认为在我们身体里面思想的东西一定是非物质的,他想不通肉体怎么会进行这项工作;如今的科学家猜想,大脑就是我们身体里主管思想和感觉的东西.
这两者基本的想法是一致的,而且这不是一个毫无根据的观点.
虽然看上去这有点令人吃惊,但事实上,关于大脑怎样生成意识,我们的理解并不比笛卡尔的理解更为透彻;他认为是非物质的灵魂完成了这一壮举.
毕竟,目前关于意识的神经学理论我们甚至连一个基本的雏形都还没有.
我们所知道的是,一个健康的大脑是正常的心理活动所必须的;事实上,也是所有活动所必须的.
当然,心理活动所必须的东西还有很多:我们需要大致正常的身体,大致正常的环境,如果我们想要那种我们认识且珍惜的生活,那还需要有他人,且能与他人取得沟通.
因此实际我们应该说,真正在思想、在感觉、做决定、有意识的是那个身体正常、处于环境和社会中的人.
但是,既然我们这么说,那么更为简单、更为准确的说法是,是人在思想、在感觉和做决定,而不是他们的大脑.
是人,而不是他们的大脑在创作艺术和欣赏艺术.
你不是你的大脑,你是一个活动着、生活着的人.
我们需要最终打破这个教条——你是你里面的某种东西,无论我们认为它是大脑还是一个非物质的灵魂;我们需要最终认真地对待这种可能性:有意识的思想是人和其他动物通过与其周围世界的动态交流所获得的(动态交流当然要依赖大脑,还有其他东西).
重要的是,打破当代神经科学的这种笛卡尔式的教条并不是要固步自封,放弃我们的信念,把自己作为自然的产物来进行解读;而是要重新思考,关于我们的本性,一个恰当的生物学概念究竟该是怎样.
妨碍我们进程的还有第二个障碍,即人们所称的神经美学.
神经科学试图解释艺术,却还未能找到在实验室里研究艺术的方法.
前面曾提过,该领域的理论学家总爱说艺术要受到大脑活动规律的限制,但在现实中,这常被简单地理解为:大脑会限制艺术体验,毕竟,它会限制所有的体验.
比如,泽基提醒我们,视觉艺术家不会利用紫外线作画,因为我们看不见紫外线;但他们利用形状、线条和颜色,因为我们能看到这些.
现在,毫无疑问,视觉艺术家被局限于可见的物质和效果上.
同样正确的是,我们对艺术作品的认识,与我们对所有东西的认识一样,都要依赖于我们天然的感知能力,而感知能力当然也受到大脑的限制.
但是,大脑怎样限制了我们的感知能力这类事实并不能解释我们怎样感知艺术;这不会比用它来解释我们怎样感知体育运动,或者怎样感知地铁里坐在对面的那个人更有说服力.
有人可能会问,难道这里的问题不是我们怎样感知艺术作品吗实际上我们应该问的是:我们为什么要把某些作品看作是艺术为什么它们会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吸引我们、触动我们或对我们说话又一次,关于这种美学评价,神经学家或心理学家给出的最接近的解释是,这是一种个人喜好.
但是,我们喜欢的东西或偏爱的东西,各种品级都有,初不限于我们看作是艺术的那些"高大上".
而且,我们之所以认为这件艺术品比另外一件更为重要,与我们之所以喜欢这栋房子、这种香味而不喜欢另一种,原因是不一样的.
在这里,靠美来解释无济于事:美既太过宽泛又太过狭义.
并非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美的(或令人愉悦,虽说大多数是这样),而且并非所有我们认为美的东西都是艺术作品(比如一个人,或一抹夕阳).
不管怎么说,美的本质也不是我们可以想当然的东西;我们对美的理解也不太可能离得开对艺术及其问题的事先参与.
我们再次发现,并非是神经美学瞄准了靶心却打偏了,而是它根本未能把我们的目标,艺术,放进靶心.
或许还是为时尚早.
神经美学,以及关于意识的神经科学本身,都还处在它们的发展初期.
等超越了第一代先锋的开创工作,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神经科学对艺术的解释会取得进步呢利用神经科学的方法和工具也许会产生有价值的艺术研究,对此,又有什么原则性的理由要持怀疑态度呢表示否定是件可怕的事,我不想停止探讨或关闭对话.
但是,我们的确有理由怀疑神经科学对艺术的实证研究前景.
原因之一,把我们对艺术作品的反应只看作是一种反应本就是个错误.
它们更像是一种评判,而与所有评判一样,它们需要经过深思熟虑.
而且,它们的形成要依赖于我们的知识、背景、经验、文化环境、共同的态度,以及艺术家、专家和我们其他所有人之间持续进行的对话.
据说,有种审美反应其神经基础可以得到有效的发掘,这一观点让我想到,恐怕只有远离艺术及其影响的人才能严肃地去完成这件事.
一件艺术作品不仅仅是一个触发器,去激发你的感觉或知觉反应,或别的任何东西.
在这一意义上,它不只是一件东西,更是一件工作品.
艺术是一个话题.
实际上,根据激发体验概念去理解一般的观看(或感知),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好像事物是在我们大脑内部点亮,体验似的.
这可能是一种传统的思考与讲话方式,是英国方式,却也太简单划一;世界会作用于我们,改变我们的思想;但我们也会反过来影响世界,由此改变那些正在改变我们的东西.
我们仅靠活动一下就能做到这样,更何况我们还会制作、做和掌控.
相对激发论,约翰·杜威(JohnDewey)提出了另一选择:感知是一种需要去进行、去从事的活动,是我们与周围世界的互动.
或者,如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JamesJ.
Gibson)所称,观看不是发生在眼睛大脑系统里,而是发生在眼睛大脑头身体场景环境系统里.
它是一件需要我们去做的事,而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体里的事.
就像需要我们去做的所有事情一样,它所依赖的绝不仅仅是一时间发生在我们脑袋瓜里的反应.
一件艺术作品不是一块石头、一件睡衣或一支铅笔,它更像一个笑话.
而笑话不仅仅是一件东西或一个触发器;笑话是一种交流活动,它是一种回应,一种互动,一种触动.
领会一个笑话也不仅仅是做出反应或受到感染;我们曾经说过,它是一种造诣.
因此,比如:两位爱尔兰人走出酒吧.
是的,这有可能.
想想要看懂这笑话你需要了解多少东西,它不仅仅涉及民族与文化,饮酒与成见;还有笑话本身,它的体裁、预期效果以及语言节奏等.
但是,如果说艺术作品就类似于我们的交际活动,在一个群体里的互动,在一个有着共同观念和理解的环境中的活动——希望我已让你相信它们的确如此——那么,再认为通过研究我们欣赏艺术时身体内部,即大脑内部,都发生了些什么就可以弄懂艺术,或为什么它对我们重要,那就是误导.
这是在错误的地方寻找艺术,就像是在印刷纸币的纸上寻找金钱的价值.
或者,再用一个更贴切的比喻,这就像是在某个棒球运动员甚至是观看棒球比赛的某个观众的脑海里去寻找棒球及其棒球的意义.
你可以研究在这些大脑里发生了些什么,但这对你了解棒球毫无帮助,充其量你可以了解神经系统里伴随发生了什么.
对艺术的研究也是这样.
神经美学两头都错了:艺术作品不仅仅是一件东西;而艺术作品的价值也不仅源于它对神经系统产生的作用.
这并非要否认艺术品或笑话亦或是石头会在神经系统产生作用,它们当然会.
所有东西都会对神经系统产生作用.
但是,如果你想解读艺术品与岩石、与夕阳有何分别,那你就需要到别处寻找答案了.
神经科学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钻进了牛角尖;它不足以成为一门恰当的研究艺术的学科.
事实上,如果我说的没错,甚至是对于研究体验本身来说,它都太钻牛角尖、太过只见木不见林了.
体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不是在我们身体里发生的东西,而是需要我们去获取的东西,与他人一起.
体验更像是打棒球,而不像是消化食物.
·这是一本探讨艺术的书.
我再重述一遍问题:艺术是什么为何它对我们如此重要关于我们自己它能告诉我们些什么我提议,为了解读艺术,我们需要把它放在技术的背景下进行探讨.
毕竟,艺术家会创作各种东西:绘画、雕塑、表演、歌曲等等,而且艺术总是与制作、手艺、修补、技巧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但是,艺术本身并不是我们的一种技术.
艺术要以技术为前提,就好像反讽要以坦率交谈为前提.
技术——制作实践,为此目的而对知识的驾驭——不是对艺术的贡献,而是艺术的先决条件.
艺术作品是一件奇特的工具,一件剔除了实用功能的工具.
艺术是功能的天敌,是歪曲的技术.
因此建筑在艺术中的地位才一直存有疑问,而伟大的建筑师造出漏雨的屋顶也并非偶然.
也因此,尽管有许多艺术会涉及爱情与情欲,但却没有色情艺术.
色情作品有它的功能,而艺术总是对功能的颠覆.
这并非要否认有些艺术作品其实也会同时具有这样那样的功能.
就好比一件东西可以是一把锤子,同时也可以用作镇纸;同理,一件东西既可以是小便池同时又是一件艺术品;或者,一只门把手同时也可以具有雕刻意趣.
说艺术是一回事,技术是另一回事,并不是说同一件物品不可以同时归属两个类型.
实际上,一件物品很可能同属两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因为它表明,无论是图画、小便池、门把手或其他任何东西,这中间的差别并非是其内部构成有何不同,而是我们怎么使用它们.
在第3章中我们曾探讨过,艺术作品是奇特的工具.
为了能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我的这一主张,有关技术及其在我们生活与文化中的地位,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这4个事实.
首先,技术对我们来说是天赋秉性,我们是技术动物,是天生的设计师.
就像(但不完全像)筑巢是鸟儿的存在方式一样,刀、工具、住处——这些都属于我们的存在方式.
有近百万年的时间,我们的祖先使用粗钝的石器勉强生活;技术进步或改善在旧石器时代的记录中彻底缺席.
然后,5万至8万年前,出现了技术革新的大爆发.
缝制的衣服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使用种群遗传学的新方法),同时非常精细的、有专门用途的石质工具大量出现.
正是这种革命性的改变标志着现代人类(以及此后的人类大脑)的出现,或许解释这种改变的最佳理由是人口的变化比如人口密度增大、贸易机会增多等,而不是出现"大脑"突变.
技术是我们的天赋秉性,这一观点有个重要的后果,就是我们需要架构一个关于我们生物状态的新理论,充分地解释技术及其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
这样一个新构建的生物学说应该能够凸显我们的群居本性.
其次,技术的范围不只限于衣服、器具及住处,语言与图画创作也是技术(或技术实践).
欧非岩画恰好与标志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出现的革命性技术创新出现在同一时期,而且似乎语言在这一时期也已经登场.
由此看来,语言本身就是标志人类出现的技术革命的表达.
第三,工具帮我们解决问题,同时也使我们形成新的问题.
耙子、锤子等工具延伸了我们的身体,而其他工具——如语言和图画——则延伸了我们的大脑,使得我们能够产生离开这些工具就根本无法实现的新体验和新想法.
有些技术——如文字(一个相对较新的发明)——既延伸了我们的身体又延伸了我们的大脑;文字使得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思想传递给声音达不到的那个人.
第四,工具只有在我们的需要和能力的背景下才有用.
我们来看门把手.
是的,它是一件简单的技术,但它的前提却是一个庞大的令人瞩目的社会背景;门把手存在的场景是一整套生活方式、整个生物学状态——门、房子、通道的存在,以及人的身体、手的存在等等.
门把手的设计者制作的是一件简单的小器具,但他要着眼于使之与整个大的认知体系和人类学体系相契合.
当你走向一扇门的时候,你不会停下来去关注门把手;你会自然地转动它,直接走进门.
门把手不会让我们迷惑.
我们从不感到迷惑以至于它所有的先决条件——整个背景现实——都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假设我们对那种文化现实感到很陌生,假设我们不能理解人的身体构造或人类要住在房子里的这一事实,假设我们来自别的星球,那么门把手实际上会是一种非常奇特且令人迷惑的东西.
关于图画我们完全也可以这么说.
报纸上每天出现的图片或家庭相册里的照片在我们看来都是不言自明的、自然的存在,它们就好像是透明的,我们透过它们看世界.
事实上,图画,像我们母语里的词汇一样,都是熟悉的交际游戏中的动作和手势.
因为我们对这样的游戏得心应手,所以游戏才看起来自然.
但是,图画的自然,就与门把手的自然一样,只是因为所有的好设计都是自然的.
设计隐蔽在自然的伪装之下.
这让我们想到了艺术.
当我们不再能把熟悉的技术背景看作是理所当然时,像门把手和照片这样一些看似自然的智慧,当我们不再能把它们的前提条件看作是理所当然时,设计停止,艺术登场了.
艺术始于事物变得陌生之时.
设计组织和成就我们,艺术颠覆我们.
它消除背景——工具要体现作用所必须具备的背景,以此达到颠覆.
面对一只门把手的时候,你永远不会问,这是什么问出这样的问题已经证明门把手的实际功能被破坏了.
甚至当你注意到门把手时,都说明它可能是一件蹩脚的设计.
但艺术是有意为之的蹩脚设计.
它是要唤起人们对它自身的注意,它的产生恰恰始于这种无根基、无用途、这种放任自流.
站在一件艺术品前,你必然会问:这是什么而且,重要的是,当我们面对艺术的时候,尽管对于这问题我们可以给出多种答案,但是没有一个答案我们可以从一开始就觉得理所当然.
当我们说这是一只门把手时,我们同时也说明了门把手是什么.
但如果比方我们说这是一幅画,我们却不能说明一件艺术品是什么.
面对一件艺术品,假设我们问:这是什么它是干什么用的我们需要自己来想出答案.
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立场,重要的是,这立场要与背景联系起来,与我们通常想当然的东西联系起来.
艺术家制造奇特的工具,因为工具,指我所说的广义的工具,对人类是至关重要的.
它们组织了我们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是它们成就了我们现在的样子.
艺术作品把我们的制作实践和我们要依赖我们所制作东西的倾向展示出来,也因此把我们的思想、谈话和图画创作的实践都展示出来.
艺术把我们展示出来,艺术让我们看见自己.
·在《逻辑哲学论》(TraotatusLogico-Philosophicus)中,维特根斯坦宣称,所有命题都有一个一般的形式:事实如此;事情如此;事态如此.
当你在谈论什么的时候——无论是关于爱情、经济或是玫瑰花的颜色——你所做的实际上都是在作出断言:事情是如此这般的.
一个命题代表的是事物的一种可能的状态.
我们的思想和谈话,尽管种类明显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基本命题形式.
在后期的作品中,维特根斯坦自己也坦承这一观点值得怀疑.
但是,暂且让我们把谨慎抛诸脑后,现在我要以年轻维特根斯坦的精神来提出自己的断言:艺术作品都有一个一般的形式.
艺术作品的一般形式就是:看你是否独具慧眼!
艺术作品激发你去尝试、去努力地观察以使你能够有所发现.
请让我解释一下所有的艺术作品无论它是舞蹈歌曲诗歌、电影或任何东西)都是在向你提出挑战,让你去看见它,去看懂它.
艺术作品(不是艺术家,也不是演员)在说:看你能不能把焦点对准我问题是通常我们不能至少不是立即就能设想一下,你走进画廊,眼前是一排排你并不熟悉的作品.
起初,它们只是海量的一无特征的东西,但你在费力地辨识,你看出了这些作品的相似点和不同点.
慢慢地,事情发生了变化:设想一下,你走进画廊,眼前是一排排你并不熟悉的作品.
起初,它们只是海量的一无特征的东西,但你在费力地辨识,你看出了这些作品的相似点和不同点.
慢慢地,事情发生了变化:有些作品开始进入你的关注范围,就像是在舞会上某些面孔开始引起了你的注意.
起初是一群人,然后你看见了某个人,带着他独特的个性.
艺术的天职就是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完成这种从看不见到看见的转变.
以这种方式,艺术重申了我们感知体验的一个基本特征,即:我们对周围世界的意识、知觉、领悟并非自然而然地产生,而是需要通过有思想的、积极主动的观察去获得它们.
从这一角度来看,《周末夜狂热》里的托尼不是艺术家,无论他的舞蹈有多么精彩炫目,那都不是艺术.
托尼是在炫耀,他的画外音是:来看我!
我已和盘托出!
我多性感!
我多男人!
我多强大!
我多霸气!
他跳舞是为了自我实现;他的舞蹈是力量与诱惑的舞蹈.
他跳舞是为了证实自己,让他知道自己不只是一间小五金店的员工,而是一个舞蹈着的、傲娇的、充满活力的、精力旺盛的男子汉.
舞蹈,无论对托尼来说有多么灵感迸发,多么激情四射,多么个性闪现,实际上都只是一种技巧,一种为了实现个人需求的技巧.
对他来说,无论是作为一个舞者还是作为一个拳击手(就如电影里他的朋友一样的拳击手)实际并无本质区别.
艺术作品的画外音从来都不会是:我要和盘托出!
(后面我会写到,流行乐似乎是一个反例,但事实并非如此.
)相反,艺术家会让你看到一些你看不见的东西,或说出一些你不会言说的东西.
艺术家会提供机会让你发现自己正在努力寻找的方向.
艺术家在说:来认识我,看懂我,把我放到你的焦点.
看你是否独具慧眼!
这是他或她的格言.
因此艺术家给你机会让你改变自己,并发现你或者我们如何把世界放到自己的焦点.
托尼还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事实:艺术舞蹈绝不仅仅是把舞跳得更好(像我们在舞会、夜总会、婚礼上看到的那样).
在某种意义上,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但它确实与跳舞无关.
充其量,舞蹈艺术是在利用一些与跳舞作为一种社交活动相关的熟悉的规范、目的、兴趣、风格、态度及感觉;舞蹈艺术操纵它们并使它们变得模糊;它由此中创作出艺术来.
舞蹈编创,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跳舞的变乱(或颠覆);而后面我们也会看到,绘画艺术实际是对图画制作的变乱.
·此时你可能会表示反对.
你可能会想,当然,说到现当代艺术时,这都非常有道理.
艺术作品是奇特的工具,它们总是充满讥讽,它们在挑战我们,让我们看见它们,这种观点似乎是为马塞尔·杜尚[7](MarcelDuchamp)之后或是保(MarcelDuchamp)之后或是保罗·塞尚[8](PaulCezanne)之后的艺术量身定做的.
但是,对于更为广泛的任何时期、任何地域的所有艺术,我们是否可以严肃地认为它仍普遍适用有人认为,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艺术是一种新近的发明,不早于18世纪.
在此之前,艺术,作为一个独立的分类,有别于其他形式的精巧加工及作品;这一想法本身似乎就是不自然的.
一面是艺术品与工艺,另一面是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我们这种划分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
但这是否意味着艺术理论难免会有一些错误的判断在里面比如我在此所提出的理论,把艺术与非艺术品的划分看作理所当然,似乎它们的差别是本性使然.
艺术,如今对我们似乎是如此地突出,无可回避.
在这一意义上,它是我们这一独特的文化时代所留下的印记.
我的个人观点是,艺术与制作的区别实实在在、不容混淆.
制作的产品,其优秀的标准事先给定且能明确表述,它的最终目的是实用性.
而艺术指向的产品若说有任何优秀标准,那也总是要经过再三商榷、再三考虑,它的目的是研究和转变.
我们能够体会这种差别或许是现代生活的巧合,因为它对我们很重要.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区别是我们的发明,它也不是随意规定或毫无意义的.
有效的立论是一码事,巧言善辩是另一码事.
很久之前亚里士多德就曾努力形成方法来阐明它们的不同.
因此,艺术与制作的差别,就如立论与巧言善辩的差别,或真理与嘲讽的差别一样,不容置疑.
顺便说一句,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曾有过此种情况:艺术品事实上可能会同时属于两种范畴.
即便如此,这种区别仍不容否认.
我不是历史学家,也没有能力提供一份普适的调查报告.
但是我敢说,这样一份调查完全可以被完成,而且事实证明我所提出的奇特工具理论会帮助我们理解所有地域、所有时代的艺术.
对我来说,似乎这有些风险,因为一些非常远古的艺术——或是来自某种偏远文化的艺术有时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来不再具有挑战、不那么难懂了.
这可能是由于它们已被归于"艺术瑰宝"的行列,而且是在艺术殿堂的玻璃罩下被呈现在我们面前.
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作品我们不熟悉,我们不懂它在做什么.
在这两种情况下,作品都不会迫使我们投入关注,或是挑战或是影响我们,也就是说,它们不是作为艺术呈现在我们眼前.
比如,我们常常发现自己在仰慕古代大师的杰作,单单是因为它们的装饰成分,或因为它们的历史意义,或高昂的货币价值,也或许是因为它们展现的无与伦比的高超工艺.
因此,若说我们景仰这类艺术作品是因为它们颠覆或破坏或抛除我们想当然的权威,这似乎有点不合情理.
毕竟,这些作品为我们所做的不是这些,至少大多数时候并非如此.
它们已经过气儿了,或者作为艺术作品已经失效了.
但是,直到我们学会再次观看它们,直到我们学会去把它们的开关打开,或让它们亲自现身,如它曾经的样子,而不是,这么说吧,以复制品的海报出现.
一旦这么做了,我们就会发现,只要在那些我们称为艺术品的东西里有艺术存在,它总是要包含那种从看不见到看见的转变,也即我一直在引导大家注意的东西.
我们来看一些文艺复兴时期的例子.
它们会让你感到我的观点在这些绝非当代的作品中仍然适用.
我们从达·芬奇的两幅油画开始.
一幅是他的资助人米兰摄政王卢德维科公爵夫人的画像,另一幅是公爵情人的画像.
在一种意义上看,这两幅画作都是可爱的美人画像,达·芬奇按照约定应该交付的也正是这些——把这些美人展示出来,在当时也是她们的荣耀——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们远不止这些.
公爵夫人画像(美人费隆妮叶)(LaBelleFerronniere)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主人公直视着我们,她把自己呈现给我们.
看着她画像的眼神,我们也便看到了她.
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我们看不见她的手,她的手放在腿上,被隐藏在一段矮墙后面.
相反,在达·芬奇为公爵年轻的情人切奇利娅所画的肖像(抱银鼠的女子)(TheLadywithAnErmine)中,切奇利娅看着别处,她本人却无所掩藏.
我们看不见她的眼神,却能看见她的手,她抱着银鼠的右手异常引人注目.
手很大,骨感分明,强壮有力,颇具男性气概,而且在画中非常突出.
这既不是对一个年轻女性手的写实描绘,也不是对她的美或对她人格的完美表达;这几乎是一种漫画式的夸张.
这两幅画像让我们看到一种构思上的鲜明对比.
我们看到两位美人:一个是她的眼睛,另一个是手,它们在向我们揭示画中人的存在.
将眼睛与手以这种方式联系在一起使这些画像不仅仅是人物肖像,对那些心里带着恰当问题的人来说,它们成了对于画像本质特征的探询——在一幅画里要展现一个人的什么人们通常以为,只有眼睛才是心灵的窗户,在此,达·芬奇也同时证实了传统智慧的真实并非牢不可破.
心灵,在手上也可以得到表现.
因此,最终,我们可以说这些画作达到了通过眼睛来看、来知晓与用手来抓住、来制造和创作的完美融合.
我亲眼见过的达·芬奇油画中,只有一幅人物的眼睛和手同时打开,展现在我们面前供我们审视,这就是救世主耶稣基督的画像《救世主》(SalvatorMundi).
在这幅画像中,耶稣看着我们,并做出赐福的手势.
就像他在卢德维科公爵夫人以及女友画像中所作的一样,达·芬奇通过对手和眼神的运用,把人类与艺术与上帝并列放进一幅画里让我们审视反思.
(实际上还有另一幅画我们可以同时看见眼和手:蒙娜丽莎.
或许正因为如此,这幅画作才具有独特的魅力与影响.
)现在,我不想说这些评论仅仅是个开始,我还没有谈到材料、尺度、色彩等,但他们已足够证明这些画作展现的绝不仅仅是画里的美人.
事实上,无论合约要求是什么,它们展现出来的都远远超越了达·芬奇按约定所应达到的.
这些油画在用思想说话.
这样一幅油画既可以是为赚取报酬而完成的产品或对一个人的记录(即商业画),同时也可以是一次探索,对于从事这样一种商业的绘画交易究竟意味着什么的探索.
这些作品有挑战、有质疑、有颠覆,正因如此,它们才成为艺术而不仅仅是描摹.
因此,我以为,纵观我们的历史,普天之下,无论我们在何处发现艺术,我们都会发现有一些制成品或是舞台事件,在以此种方式提出问题,也许还提出了解决方案.
再看另外一例,也是来自文艺复兴时期,安德利亚·利奇奥(AndreaRiccio)的摩西小雕像,原本坐在帕多瓦教堂的喷泉顶上,面对圣坛.
我猜人们在参观教堂的时候,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很少有人会去特别留意这雕像.
这可以原谅.
人们一般会想,它不过是一件宗教饰品,仅此而已,别无他意.
但是,艺术史学家亚历山大·纳格尔(AlexanderNagel)说过,仔细审查会让你发现一些出人意料的问题和困惑,要想让这些问题浮出水面必须经过某种深思熟虑地参与.
恰恰是这些困惑和问题使得这件作品变得有趣有意义,而绝不仅仅是装饰.
设想一下,此处的摩西与通常一样,头上有角.
传统中通常把象征一神论创立者神圣的头顶光环诠释为头上长角.
但这些角有所不同,它们是公羊角.
或许是艺术家搞错了,但这种可能性不大.
公羊角有着独特的螺旋,绝对不是摩西头上常见的角,而在异教徒的神宙斯阿蒙头上却很常见.
那么,你很难不感到震惊,至少在赋予足够的关注之后,这尊雕像里的人形是一神论的创立者,而在此,对全世界来说,他却显得像是一个异教偶像.
但还不止这些,当他从岩石中取水的时候,雕像中的摩西被描述为手举魔杖.
上帝指示摩西要单凭言语吩咐磐石发出水来,但他却使用了异教徒的舞台道具.
那么,此处描绘的是宗教堕落的一个情景.
摩西在迎合人群,一群由崇拜偶像者组成的观众,至少部分人是.
在此摩西表现的正是对上帝的悖逆.
利奇奥本身是一位公认的青铜器大师,但这里的雕像没有那个时代青铜器常见的富有光泽的铜绿,倒像是从非常远古的时代出土,历经时间的侵蚀.
利奇奥的青铜雕像事实上充满了神学歧义.
我们再次在这件艺术中看到艺术,但却不是在我们想像的地方.
它不在我们能看见的地方,却恰恰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或是在此作品给我们提供的探索机会里.
这是一个陌生的摩西,至少,这个摩西必然要迫使细心的审视者去思考那些未说的、未遇见或未实现的东西.
正是在这里,在这种被呈现出来的质询中,艺术作品诞生了.
我们再来看另一类例子,还是来自文艺复兴时期.
关于西方传统艺术有一条共识,用安妮·霍兰德的话来说就是,西方传统艺术的目的就是坚定地再现可见世界.
只是这有什么要求却并不明确:怎么算是再现事物怎样在油画或雕塑中真实地再现可见事物有一种倾向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其本身可能就是文艺复兴的产物,那就是以心理方式来理解这种写实性再现.
人们通常以为,画家的目的就是要制造错觉.
因此,比如说,艺术史学家贡布里希(E.
H.
Gombrich)在写到马萨乔[9]的《圣三位一体》(1425~1428)(HolyTrinity,withtheVirginandSt.
JohnandDonors)时这样说:"我们可以料想当这幅壁画揭开时佛罗伦萨人会有多么惊诧;它就好像是在墙上开了个洞,透过这洞可以看到一个新的墓室,是布鲁内列斯基的现代风格.
"文艺复兴时期人工透视画法的创立与应用正是在与这种"纵深错觉"的关系中得到了普遍的理解.
通常以为,透视法给出了视觉原理,根据这些原理制作的绘画能够欺骗眼睛,让人产生错觉.
这是些优秀的画作,因为它们是有效的错觉.
但是,哲学家约翰·海曼(JohnHyman)注意到,透视法描绘的并非视觉的原理.
其原理并不告诉你当一幅画呈现在你面前时你会看见什么.
相反,它们给出的原理是让你去搞清楚在通常条件下,从一个视点来看,你能看见哪些东西.
人工透视法提供了一种工具或计算方法,一种技术手段,让你确定哪些是可见的,因此它给所有关注怎样画出事物外观,即真实呈现现实的人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工具.
我们自然都认可贡布里希的描述,说马萨乔的画给出的是一种纵深错觉.
但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没有人会因为这种错觉而真的被误导或迷惑或感到惊讶.
当我们看到这幅祭坛画时,我们不会真的以为是在透过教堂墙上的洞观看,就像我们不会把建筑师的白桦木模型错当成真正的房子.
值得关注的是,再现性绘画——我并不是说艺术品,只是图画——力图把不在眼前的东西展现给我们.
重要的是你要领会到,他们把这种张力,这一几乎自相矛盾的目标,直接袒露出来.
因此,图画给我们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在画中,显然不在眼前的东西有了存在如见的感觉.
重要的是要记住,当我们思考图画及其描绘力量时,我们对于图画的视觉意识绕过了它们是图画的事实,它包括画框、大小、在墙上的位置等等,当然同时也包括它所描绘的东西.
图画提出问题,至少可能提出问题.
设想在一幅再现性图画里的整个时间问题.
在一幅画里你可能看见动作在进行,事件在发生——一个人在跑,一匹马在跳,水在流,云在聚集(在此我想到的是尼古拉斯·普桑[10](NicolasPoussin))——但是画面本身并没有动,画里没有时间,或者说画里的时间是停滞的,动作是静止的.
但是当时间和动作都静止的时候你又怎么会亲历事件,看到动作的进行绘画提出的就是这类问题,我们如何看见不在眼前的东西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言明这些问题.
事实上,正是这一事实——我们留下了如此多的不言而喻——才使得图画(如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的照片)能够作为图画毫无矛盾地发挥作用.
大多数图画都有一个标题,或者直言其意,或者给出语境.
你怎么知道十字架上有胡子的那个人是耶稣是你认识他的外貌吗我们怎么辨别哪幅画像是公爵夫人,哪幅是他的情人在此,语境和交际意图就是一切(后面我还会详述这些).
关于艺术绘画——指做着艺术工作的再现性画作,可能是绘画,也可能是摄影、雕塑、或数码作品(注意:并非所有的图画都是艺术作品,也并非所有的艺术作品甚至不是所有的绘画都旨在成为一幅画)——有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它们激活了某些谜题,而通常其谜底早已被视为理所当然.
据说詹姆斯·鲍德温曾说,艺术品会彰显问题,而我们已知的答案掩盖了这些问题.
因此,谈及艺术作品时,关于常规的语境,我们不可以将任何东西想当然.
但是,正因为我们通常可以把照片的语境(或标题)看作理所当然,图片才可以在描绘事物上发挥如此有效、毫无争议的作用.
因此,当我们应对艺术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考虑语境本身,或是考虑绘画,或在宗教背景下考虑绘画.
这就是艺术让我们做的,这是艺术要求我们做的.
而且我们也看到,如果我说的没错,利奇奥的雕塑、达·芬奇的画像、马萨乔的祭坛画,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做着这些;它们是艺术品,因为它们所做的工作正是艺术的特殊兴趣使然,尽管事实上它们同时也在发挥直接的图画作用(描绘的、商业的、教育的、宗教的、装饰的作用等).
·我记得年少时曾与朋友一起去大都会艺术馆参观杰克逊·波洛克[11](JacksonPollock)的画展.
莎拉喊道:我一点都看不懂!
这都是些什么呀!
这样的画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画出来!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至少是正常的第一反应.
多年以后我从纽约飞往加州,随身携带了一件艺术家罗伯特·古德诺夫(RobertGoodnough)的金属小雕塑.
作品由一些尖锐的钢条扭结而成,颜料星星点点地散落其上.
负责安检的工作人员把我拉到边上询问——那还是"9·11"事件之前——"这是什么"年轻女子问道.
我答,"一件雕塑,是件艺术品.
""啊,"她笑了,然后又开始看它.
她很镇静、很随意,不慌不忙地盯着它看了好半天之后,她最终宣布:这件艺术品里可没什么艺术!
然后挥挥手让我通过了.
的确,这件作品在安检人员眼里是一件令人迷惑的东西,价值可疑.
对一件奇特的工具来讲,这是一种正确的反应.
对于艺术作品,这些是恰当的、合理的、真实的反应,而妨碍我们体会此种反应的原因,往往是我们最常体验艺术都是在艺术档案馆里(比如说,博物馆).
我们被告知它们是具有艺术价值的东西;正因如此,它们才会出现在这博物馆;正因如此,它们才会立在这底座上.
因此我们去参观、去欣赏它们,努力去理解是什么让它们如此特别.
我们猜想这肯定与是谁创作了它有关,与创作它所需要的高超技艺有关,或是与它的美轮美奂、它的主题、它的稀缺有关,或是因为它们(被认为)本就是要给我们带来乐趣.
我们看啊看啊,等待着,期望会有灵光闪现,会有魔力击中我们.
我们从挂在墙上的文字介绍里寻找庇护,从语音讲解里寻找答案,但我们不会投入地去看、去欣赏,与作品对话,因为我们不会,这样做让我们缺乏安全感.
但是,这是在错误的地方寻找艺术.
让我们回到与笑话的对比.
笑话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创作有多难,要记住它有多费力或它听起来有多好笑;笑话的价值——我们可以称其为美学价值——在于它给了我们一个去领会它的机会.
但是,你不会就因为有人告诉你这笑话多好笑,把它放进笑话博物馆里就领会了它的妙处.
无论你听懂了还是没听懂,领会它都是需要你去收获的东西,它取决于你的知识、你的预期以及你以为与讲笑话的人在做什么.
笑话总是在且只有在交际场景下才发挥作用.
要听懂一个笑话与讲一个笑话几乎需要同样的机智.
这是一种造诣.
艺术也恰是如此.
艺术与讲笑话事实上不仅形式类似;讲笑话——或总的来说是讽刺的使用——在某种意义上是最基本的艺术现象.
它是对预期或直截了当或毫无疑问的颠覆.
我们说的话出人意料;我们说的并非我们的本意;我们让听话人大吃一惊,且迫使他去思考、去弄懂不单是那些说出来的,还有那些未曾言说的、那些不能言说的,以及让对话发生的整个场合和背景.
该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论断:艺术要以技术为前提,但它自己却不是一种技术实践.
艺术的先决条件是操作和制作实践,它本身却不是惯常的制作或事务.
舞蹈编创者以跳舞进行创作是因为我们(托尼、布鲁克林的孩子、纽约人、人类)碰巧都是舞者.
但舞蹈编创者不是舞者,他们要做的与托尼要做的不同.
他们研究舞蹈,由此研究我们!
而像古德诺夫这样的雕塑家们不只是在制作这样那样的东西,他们是在用激情、材料和那些组织我们熟悉的、有目的的制作实践(以及体验)的传统方式进行工作.
艺术正是产生于此;这是艺术的源泉,也是艺术所要探索和暴露的.
这些观点还有另一结果:艺术,的的确确,是一个进行探究的领域.
在这方面,它就如哲学,是一种研究实践.
因此,之所以认为会出一个艺术神经学是个错误,这是又一重原因了.
就如不会有数学或哲学神经学一样,也不会有艺术神经学;或者说,任何声称自己为研究数学或哲学的神经科学只可能与数学或哲学有着最偏远的联系,充其量它只表明我们要进行数学或哲学思考有一个必要条件(即我们需要有个大脑!
).
最后,这是新的一点:这些思想也表明了艺术为什么需要批评.
批评不是报刊杂志的八卦副刊;批评是艺术的氧气.
艺术总是给我们话题去思考、去讨论,可以说,它产生在批评的空间里.
这一见解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再想一下笑话,我们不会通过解释一个笑话让它变得好笑,但是,我们已经注意到,笑话的本质是它有东西让你去领会.
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总有些东西需要解释.
艺术也是这样,只是说你喜欢这件或那件艺术品永远都不是结局,可能你只能做到这样,但是如果你喜欢一件艺术作品,"为什么"总是一个恰当的问题.
如果像逻辑学家所说,假说催生的是关于真理的问题,那么,艺术作品则会催生这样一些问题:它为什么有价值(或有趣)——或者干脆,这到底是什么贡布里希说道,根本没有艺术这样一种东西,有的只是艺术家而已.
如果所有这些千态百样的我们称之为艺术的东西果有某种同一性,那就是它的故事.
艺术,若说它是种什么东西,那它就是一个历史大故事.
贡布里希是在对"艺术回避定义"这一事实作出回答.
它拒绝被还原为一些基本属性.
另一方面,艺术提出的这一挑战——不仅包括这件或那件作品到底有何好处,还包括这幅或那幅画、这行为、这物品、这装置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到底算不算得上是艺术的问题——是艺术最基本的关注和问题之一.
艺术自身就是它的问题.
艺术,无论它还与别的什么相关,它总是要与其他艺术、与艺术家、与观众、与教师与学生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艺术自身实际上就是一种批评实践.
第9章艺术缘何如此枯燥还记得小时候感到无聊透顶的日子吗我记得有一年的夏天,放暑假,现在回忆起来,仍然觉得它是那么的漫长,长得不可思议,长得漫无尽头.
闷热,没完没了,自由散漫,没有组织,烦躁不安.
苍蝇嗡嗡地叫着.
我成天与弟弟打架,无所事事.
父母遥不可及.
一般说来,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空间让你感受这种极度的无聊.
随着人慢慢长大,生活围绕着项目、计划、需求、目标被组织起来,这些活动纠合在一起,其结果就是时间飞速地逝去.
或许我们会偶尔驻足关注一下节奏,但很快又会被更为重要的意义和组织所俘获.
甚至有人会说,我们的日子还不等开始就结束了,因为我们现处的时刻早已被定义为与尚未发生事情的联系,与目的、意义和计划的联系("昨天你干什么了""上班了.
").
这当然是好事,这是必须的,这是我们的成就.
我们的生活不是一种匆匆忙忙的机械状态,不是碌碌无为、一件接一件的事情.
它是我们成长的标志,用约翰·杜威(JohnDewey)的话说,是我们完整的标志.
我们的生活不只有一系列的感觉;它们包含了丰富的、需要名状的经历——威尼斯的晚宴,购物,垒球比赛,我在柏林的那一年——时间流逝,这些经历整合在一起.
成年人不会感到无聊,成年人不可能感到无聊,因为那种独特的、隐隐有些痛苦的情绪状态,那种没完没了、毫无意义的被困感觉,只有在没有组织、没有计划、没有任务、没有责任的状况下才会出现.
在成年人的生活里,无聊出现的前提条件是不存在的.
这与艺术有什么关系我的猜测是:所有这些都与艺术息息相关.
成年后,只有站在艺术面前,我才有那种最为近似的感受,再次重温童年那种丰满绚丽的无聊.
不要误会!
我热爱艺术,艺术是我的工作;我研究艺术,我在一个艺术家庭里长大,艺术对我非常重要.
但是,我很难想出还有什么比看演出更无聊,比走进美术馆——又是美术馆——更令人恹恹欲睡的事了!
墙上挂满了画,它们近在咫尺,却默默无闻,了无表情,拒人千里,至少乍看上去是这样.
不只是那些糟糕的艺术才可能像这样引发你的焦虑感受,漫无尽头,被困其中,一无所获.
站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或是弗里克美术馆,或柏林老国家画廊里——这些在我看来近乎艺术圣殿的地方——在熟知和喜爱的作品面前,我同样会发现自己彻头彻尾地冷漠如霜,像是一个人打不开开关,作品(或者是我)处于关闭状态.
以这种"待机"状态在艺术上浪费时间实在是一种折磨.
艺术是什么它为何对我们重要我猜想,艺术的枯燥可以给我们提供一定的线索.
无论是谁,想要充分地解释艺术及其在我们生命中的位置,都不能躲过一个令人惊诧的事实:艺术有令我们厌倦的力量.
我们生活中的其他所有东西都在缓解无聊,而它却仍然坚持着这种力量.
艺术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无聊至哭,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具有这种力量.
但是艺术令我们无聊的潜能与它会令我们感动、令我们颤栗、令我们蜕变、令我们兴奋的事实并不矛盾.
事实上,它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正如害怕伤心你就不能遭遇爱情,如果不能忍受寂寞和无聊得要死、恹恹欲睡,那你便无法面对艺术.
艺术之所以可贵,只是因为其价值直接与它可能令我们无聊的程度成正比.
为什么会是这样对此问题我们手头有现成的答案.
毕竟,艺术作品是奇特的工具.
也就是说,它们是不能使用的工具,一无所用.
它们是一些没有实用价值的文本,或是不能展示任何特别东西的绘画.
因此,它们要求我们停止做事,停止行动,停止对实用性甚至是相关性的要求.
再一次,我们可将之恰当地比作哲学.
哲学不会像物理学、数学或经济学那样产生积极有用的信息,让你可以拿来用于生活中这样那样的领域.
在这一意义上,艺术如哲学一样毫无实用价值.
邮购目录里的衣服图片告诉你可以买到哪些东西;建筑模型让你看见你可以建成什么样的房子.
但是,舞台上的舞蹈墙上的油画它们从跳舞、展示或学习中抽离出来.
它们令你突有感悟.
就是说,如果你让它们这样.
如果你肯暂停和变乱俗务,如果你进入那种特殊的空间,那种艺术所带来、所允许的转换状态.
在此,艺术场合就如宗教场所教堂一样,在这里可以发生那么多的事,但只是因为什么都不曾真的发生:它们是让你完成自我蜕变的场所.
艺术作品是脱俗的,它们要求你与自己热衷的生活切断开来.
在现实意义上这的确如此.
在剧院时你当然不能像平常一样讲话、收发电子邮件,如果这样,那你就是心不在焉,你根本没有投入、欣赏、关注正在上演的内容.
艺术场景与哲学场景一样,要求你抛弃俗念和执着的习惯,以枯燥为帆,乘风起航.
面对艺术就要像一个孩子,你变得无助.
艺术让人回归童真;艺术摧毁一切.
这是现代思想里关于艺术的一个老主题.
托尼奥·克罗格[12](TonioKroger),斯蒂芬·迪达勒斯[13](StephenDedalus),文学作品里的这些年轻的艺术英雄,都与生养他们的资产阶级社会为敌.
艺术变乱,陌生化,于是颠覆.
因此,如我曾说过的一样,色情艺术在用词上几乎自相矛盾.
色情有着明确的功用,它的目的是打开你的开关,让你兴奋;要做到这样,它需要给你提供影像、念头、幻想和机会,以达到你想要的样子——比如性唤起.
但色情不会令你或任何事情有所改变.
也因此,建筑——文艺复兴时期被奉为艺术之后——许多方面在艺术里感到最为尴尬,总是挣扎在纯设计的边缘,纠结于要不要顾及人类对于功能的需要、习惯和现实生活.
这么想,伟大建筑师的作品里会有漏雨的屋顶和关不严的门就不足为奇了.
完美的屋顶和严丝合缝的门都是品质卓越的工具,优秀的工具要求完全符合使用者事先明确的要求.
但是艺术家关心的总是破坏这些,去变乱那些作为习惯和背景早已存在的东西.
一个真正的艺术大师造出的建筑不会适合居住;如果说真有色情艺术存在的话,不管它有什么益处,它肯定不适合用来进行自慰.
假设你不懂棒球却被带去看棒球比赛,这会是一次无聊透顶的经历.
但这无聊顶多是表面的;你无聊是因为你看不懂比赛,你不懂比赛规则,不懂它的故事、它的意义,你遭遇的是别人的语言,或是别人的工作.
但是,谈及艺术——我不管是哪种艺术——并不是因为你不懂它的规则,因为根本没有什么规则.
没有一种代码可以让你学会了就能坐享其成、一劳永逸地观看比赛.
艺术总是把规则的地位,把游戏——故事、描绘——就该有个道理的观念揪出示众,让人去重新思考.
艺术刻意地令人无聊;或者说,它让你遭遇一种情形,这情形让无聊成为一种顺理成章的自然而然的反应.
有的艺术家将这明确地表达出来.
前卫作曲家约翰·凯奇[14](JohnCage)就是一个著名的例证.
在垂暮之年他在哈佛大学做了一系列讲座.
讲座是对几个著名音乐教本的仔细研读.
这些教本被搅乱在一起,成了一些没有意义的合成文字.
到了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原本几百人的观众锐减至十几人.
他劝人们要去聆听,在空洞与寂静中发现音乐.
这并不容易理解,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大多数理智的、思维正常的人;甚至对大多数成熟的艺术观众来说——这就像一粒太大的药丸,难以下咽.
但是,这只是一个极端的案例:只要存在艺术,它总会发挥作用.
灯光暗了下来,你被困在座位上,现在那里有些什么,你必须得有所认识,如果你能做到.
大多数的艺术家,但可能不包括凯奇,都愿意更直接地去考虑你的愿望和好奇心,照顾你先是聚精会神、然后迷失焦点的自然倾向,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让你得到娱乐.
但是要投入地欣赏艺术,总是,必然是,你可以想见的最为脆弱的事.
孩子们已经感到无聊了;对于年轻人这再自然不过.
他们还不需要艺术;要让孩子参与艺术游戏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作为习惯的生物,被束缚于这样一种生活中,其组织机制与基本原理之复杂,远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理解;我们真正需要它.
或者,我们可以学会需要它,我们可以通过学习知道它的意义.
艺术品,虽然乍看上去总是高冷孤僻、隐晦难懂,但它确是与我们的对话,与我们已知的或自以为已知的,与我们期待的或自以为期待的,与我们关心的或自以为关心的东西的对话.
舞蹈家乔纳森·布罗斯(JonathanBurrows)说道,艺术家与观众之间有着一种隐而不露的契约关系:观众一路玩下去,艺术家提供完成转换所需要的线索和材料.
给观众讲一些他们无法领会其妙处的段子毫无乐趣可言,因此,必须要有对话,要有你予我取.
这一构想完全正确,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正如我们不能把评价、理解或聚焦艺术作品的规范、规则或方法看作理所当然一样,我们也不能想当然地去论定艺术的成败.
枯燥是一个陷阱,但它是一个必要的陷阱,恰如你可能会输掉比赛一样.
但比赛不会失败,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是输家.
一个评论家有理由宣布一件艺术品枯燥无聊,但这顶多只是解释这件作品有何不足的一个开始.
·实际上,我们的文化里还有一个地方枯燥盛行:教育.
被困在讲堂或教室里,被迫跟随或迫使自己努力去跟随老师的步调与节奏,学生们常常发现自己被置于一种痛苦的无聊状态.
我认为,老师与艺术家都在冒同样的风险,这并非偶然.
老师毕竟也是演员,如果他们认真对待自己的职责,他们实是在从事与艺术一样的活动.
教师不仅仅是要汇报已知的内容,不只是知识的传播者;他们更像是助产师,要帮助生产知识.
为把知识带到世界,他们要使尽浑身解数,想尽一切可能的方法.
枯燥在课堂上可不受欢迎.
对此,谁敢提出挑战但认为枯燥是有效教学的天敌那就错了;认为教师就应当作为娱乐者寓教于乐更是非常错误的(就如把艺术家当作娱乐者一样大错特错)!
让学生享受教学过程不是衡量教师业绩的标准.
学生需要按下"打开"开关,学生需要忍受寂寞和艰涩的过渡,由此使他们激活自己,承担获得领悟的本分.
顺着这一思路继续实是超出了我的预期.
教师毕竟不是艺术家,即便在此方面教师展现了与艺术工作非常重要的亲缘关系.
但我想就此话题充分表达我的观点,以使大家看到我们的文化在面对枯燥时表现出的焦虑.
我们期望学习、领悟、成长都应当是直截了当、一帆风顺的,这一期望高度可疑.
学无定法,评价一个老师的绩效也没有一种事先认定的衡量标准.
因此,回到艺术,对于艺术与娱乐有何关系,根本没有什么硬性要求.
艺术家不是娱乐者,恰如舞蹈家不是舞者,画家不只是要给你画些什么一样.
乍看上去,这给流行音乐和电影提出了一个大问题.
毕竟,这些都是市场的产物,在此,它们的成功或失败确如色情一样,要与取悦或迎合受众的程度密切相关.
现在还抱着柏拉图的观点,或是赞成现代学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Greenberg)或泰奥德·阿多诺(TheodorW.
Ardorno)的观点——认为有一种东西叫作纯艺术,艺术与娱乐是分裂的;艺术若是取悦大众,迎合世俗的口味就算不上是艺术——实在是不合时宜的,可以说是太过时了.
第10章中我将再回头探讨流行艺术——重点讨论流行音乐.
我认同纽约画廊主杰弗里·戴奇(JefferyDeitch)的观点:时尚、摇滚、涂鸦、街头艺术,现在这些都与艺术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有至关重要的联系.
但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它们怎样做到了这样,对我们、对艺术这都是一个问题.
因为一种不够艰涩深奥的艺术,一种不穿隐形衣的艺术,一种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领会的艺术,一种对抗枯燥与不快的艺术似乎根本不能算作艺术.
因为,如果艺术只是把我们的开关打开,让我们感觉良好,然后任凭我们随波逐流,无所改变,那么它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10章神经科学在研究艺术时的局限艺术是什么为何它对我们如此重要关于我们自己它能告诉我们些什么这是我们的问题.
在第8章里我表示过对神经科学的怀疑,他们试图用神经科学的方法和工具来阐释艺术问题.
本章里我将再次回到这一主题.
之所以这样做,有两个重要原因:首先是因为,通过更好地解读神经艺术论之所以不可行,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艺术及其对我们的重要意义;第二个原因是,尽管神经科学对艺术的还原论研究方法有着明显的缺陷,且不见任何可谓有意义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但它却备受尊崇且颇为流行,这本身就揭示出在我们的文化和价值观里有些东西着实令人不安.
问题在于神经科学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并非是被科学方法所限,这点可以肯定,而是被一些并未获公认的哲学假想束缚住了.
这些假想与其说是一个关于我们是什么的理论,不如说只是一个观念.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大脑,盛在血肉之躯的大缸里.
或者,换一个比喻,我们就像是潜艇船员,待在一艘没有窗户的潜水艇里(身体),在暗无天日的能量海洋中(世界)沉浮,除了舱内显示屏上呈现的东西,我们对于周围世界一无所知.
重要的是,这一模型——脑即我,身体是大脑的容器;世界,包括其他人,都是无从知晓的刺激因素,神经系统的反射来源——并非神经科学的一个发现,而是神经科学从一开始就想当然的一系列假设.
它是笛卡尔的理念,只不过披上了唯物主义的外衣.
当然,并非所有的神经科学家都赞成脑即我的说法.
事实上,有些学者如弗朗西斯科·瓦雷拉(FranciscoVarela)、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Damasio)等都曾努力构建一种可行的理论.
我本人在认知哲学的研究,包括与伊凡·汤普森(EvanTompson)、苏珊·赫尔利(SusanHurley)、凯文·欧瑞根(KevinO'Regan)的合作研究,绝非要批判神经科学,而是想通过消除其内在默认的笛卡尔式假设来对它进行改善.
事实上,自20世纪后半叶这一学科诞生之日起,怎样将大脑研究的问题安置到更广泛的心学研究中,一直被看作是认知科学的一个核心挑战.
在此,1982年戴维·马尔(DavidMarr)《视觉》(Vision)的出版非常关键.
马尔的书出版当年,正值大卫·休伯尔(DavidHubel)与托斯坦·韦塞尔(TorstenWiesel)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他们的获奖原因是在人类视觉系统方面所做的研究,其基础是发明了从单细胞进行记录的技术.
这一研究令人们看到了希望:我们有可能从根本上,也就是说,从细胞的层面来解释我们的视觉成因.
他们认为,我们的所见由细胞的激活而生成,每个细胞各司其责.
比如说,有的专门负责形状,有的则专管颜色、运动、方向等.
但对此的乐观态度马尔却不能接受.
他说,想从单细胞的基础上去解读视觉,就好比想通过单根羽毛来了解鸟儿的飞行.
问题不应是问每个细胞都在做什么,相反,我们应该问的是,视觉系统本身要解决什么问题或者,以马尔喜欢的方式来问:视觉发挥了怎样的计算功能马尔推论,一旦搞清了这些,你就可以提出进一步的问题:像人脑这样的机制——比如说相对于一台数字化计算机——是怎样执行构成视觉的信息处理法则或运算程序的我们往往以为马尔是在说,我们无需把精力放在硬件上;要了解思维,最主要的是研究大脑的软件.
这并不完全正确.
我认为,马尔的深层意思并非是我们不应集中精力研究大脑;他的重点是,既然我们专注于大脑,我们需要做的就不是把它当作是一块肉或一个电化系统,而应把它看作是一台计算机.
没有人比丹尼尔·丹尼特(DanielDennett)做得更多,使这观点成为认知科学的利器.
他说,大脑只是一台协作引擎(asynacticengine)(也就是说,这引擎用的只是符号的一些纯形式的、表面的、毫无意义的属性),但它却发挥了语义引擎(asemanticengine)的作用(即,它似乎对意义和重要性非常敏感).
问题是,它是怎么做到的在身体组织里展开的简单的因果程序怎么形成了它们最终拥有的代指世界、分析计算的认知意义丹尼特极力主张,我们从单纯的神经生理学转到把大脑作为辅助和成就心智生活的东西来解读,需要通过构建一些问题,如相对于某个动物的整体生活,大脑都做了什么从这个动物做了什么、获得了什么,到在大脑里又发生了什么,我们要在这之间来来回回地转换,然后才能讲出一个故事;大脑里发生的事属于这个故事,也是这个动物生活故事的一部分.
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把这种生活还原为大脑.
丹尼特的阐释产生了一个新奇的结果.
设想一个女人在法国读法文报纸,读到一个俄罗斯人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犯下了一起凶杀案.
我们在我们的报纸上,俄罗斯人在他们的国家也都读到了同一事件的报道.
我们所有这些人都相信,一个俄罗斯人在特拉法加广场犯下了凶杀案.
但是,请注意,没有理由认为我们有着共同的心理状态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产生了共同一致的大脑状态.
我们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大脑,经历着不同的历史,在不同的地方,通过看不同语言的报纸了解到所发生的事件.
我们之所以对同一事件有着相同的认识,并非因为我们的大脑在任何具体方面处于相同的神经生理状态.
我们的认识相同并非是有关大脑的事实.
在丹尼特看来,即便大脑对于我们所有认知的获得至关重要,这仍不可改变.
在丹尼特看来,认识更像是整个人的功能状态,这些状态不只与身体内发生的事并行发生,还要取决于人或动物与环境的关系.
在丹尼特看来,意义并非产生在头脑里面.
因此,任何脑袋里面的东西——包括大脑或别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是意义的来源.
尽管丹尼特、马尔以及其他神经学家为认知神经科学的理论基础做了大量工作,但如今的情况依然是,大多数的神经学家(不包括上面提到的几位)——甚至是那些从未对意识的本质、艺术、爱等这些重大问题作过研究的人——还在执着于那个单一的命题,其实它与笛卡尔的观念并无二致,对此,恐怕他们都羞于公开承认.
这个重大命题即是:所有的思想、感受、体验、印象、价值、争论、情感、态度、秉性、信念、欲望、野心等都在你的大脑里面.
可能你并不知道大脑如何掌管这一伟业,但据说,我们已开始有所理解.
而且,你脑袋里的这些物质片段怎样组织起来形成你的性格、思想、理解、困惑以及对宗教、物质或性的欲求,在此领域得到的新认识一定是所有学科中最令人振奋、意义最为重大的知识.
或说他们如此断言.
那么,这里永恒不变的观点就是:我们的生活体验,我们的日常世界,我们每天的行动、反应、感受和关注都是神经系统里的事情.
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我们所知非然的领域,它作用于我们的神经系统,又被其自身的作用进行了屏蔽.
这作用是世界与心智中间隔开的一堵墙,我们发现自己就在墙的这一边.
我们所认识的事物并非如它本身的样子,我们认识的只是大脑对它们进行的内部构建.
很少有科学家会公开宣称这样的事情——或即便有,通常也无章可循,或只出现在缺乏实验证据的通俗读物里——但既然它的出发点是神经还原论、内在论,这也就是必不可免的.
某些科学家试图从两条路径逃离这个笛卡尔眩晕症.
他们承认,要理解金钱之爱或亲子之爱,除非一方面采取经济学和历史的立场,另一方面呢,自然也离不开个人的立场如亲情和关爱等.
然而搞来搞去,却左右不外乎一个关于我们自己的事实:我们是一种什么动物,由于我们的认知局限,何种解释令我们满意.
情爱只是种神经状态.
金钱之爱也不过是一个神经学事实.
哪怕我们发现,要描述母子关系,不用"情爱"这一通俗心理学范畴还真是难办,但至少原则上是可以不用的.
假如你不满意,那只是你的事情,谁让你头脑不够科学来着我承认这世界作用于我们,在神经系统激发出相应的反应.
当然是这样!
但事实是我们也会反过来作用于世界,眼睛、头部、身体的每一次动作都会改变我们与周围世界感觉交合的特点.
事物不是在神经系统里激发内部反应的触发器,它们提供机会让我们与之进行持续的互动.
出现在我们体验里的世界,可不像是呈现在我们脑海里的一幅画;它更像是我们从事活动的游戏场或竞技场.
不是大脑的活动,是我们的活动;不是在我们脑袋瓜里的活动,而是我们在这世界上与周围万物的活动.
我们关注的是整个动物的活动,一个有躯体的、处于环境和社会中的动物的积极主动的生活.
大脑是人类生活和意识所必须的,但这绝非全部.
我们的生活不会在大脑中展开.
不要去想:大脑是创造者,我们生活在大脑构筑的虚拟世界里;而要这样想:大脑的工作就是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这里有我们,有世间万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单靠神经激活模式我们还不能解释意识,这是公认的事实,至少目前还是这样.
事实上,说到要弄清我们为什么会有意识,意识又是怎样形成的,相对于笛卡尔,我们并未有太大超越.
这我在第1章中就曾讲过.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这是因为我们是在错误的地方寻找意识.
意识不是我们身体里面的神经反应,尽管它的形成要依赖这些反应;事物也不是激发神经反应的触发器,尽管它们当然会造成很多这样的效应.
而体验不是效应,不是由外界对神经系统狂轰乱炸所产生的结果;相反,体验是有时间延续的活动模式,是整个生物与世界(包括他们的群体世界)积极互动的结果.
弗朗西斯科·瓦雷拉与伊凡·汤普森写道:大脑、身体与世界使得意识产生.
究竟意识是单纯的依赖神经过程,还是在构成上同时要依赖身体与世界,包括群居世界,以及它们的动态交流模式,这最终可能会成为一个需要实验验证的问题.
或许我们最终需要走出大脑来解释或弄清人的体验,这种可能性甚至未被当作是时下的选择.
我们只是以为,隔开大脑与环境的膜莫名其妙就成了自我与世界之间的重要分界.
我认为,借用丹尼特的话来说,这就是"笛卡尔唯物主义残留的过气赠品",而神经科学却仍不能挣脱它的束缚.
正因为如此,在第8章里我坚持认为,我们不能想当然地把神经科学看作是一件现成的知识装备,并将之应用于我们关心的艺术问题;也因此我坚持认为,关于我们的生命本质,神经科学还需要构建一个完备的理论.
事实上,如果我的观点正确,我们非但远不该从神经科学的立场来解释艺术,这种解释还有可能顺序是搞反了方向.
就是说,对艺术的更好解读很有可能会让我们拓展思路来构建一个关于我们自己的更为可信、更为合理的设想,最终为一个更完善的神经科学铺垫基础.
事实上,更进一步说,艺术——本书中我在努力证明——根本不是一种现象,一种像消化或是视觉一样的现象,静静地等在那里需要人来作出解释;它本身就是一种研究工具,一种探究方式,它研究的是吸引我们兴趣的关键问题,比如人的本性.
艺术本身就是我们研究自己的场景,这一观点为我们打开了一种可能:艺术与神经科学会有一种全然不同的合作方式.
·如果你完全同意我在此提出的对神经科学的质疑,那么你可能会发现,所谓的神经美学只不过是神经科学知识帝国里的另一范例,只是神经科学试图构筑一个所有东西都基于大脑理论的另一篇章.
但实际上,神经科学最新的对于艺术的特别关注,揭示了关于神经科学研究的一些更深层和更根本的问题.
当我们转向视觉神经学及其被放在首位的"神经再现"(neuralrepresentations)时,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视觉意识——据说是我们的真正所见——是由大脑里的图画所产生的.
马尔将大脑里的这些图画称作是2.
5D的素描,它不是3D世界羽翼丰满、栩栩如生的完整模型,实际上是它的图片.
从技术上来说,它是一系列光点强度在视网膜上的排列组合,但是结果被转化成一张线形图,在这个图上,物体之间的界限被标注出来.
视觉使得我们形成了一个三维世界的认识.
但是,据视觉文献中的广泛记载,尽管如此,它给我们的体验却是一个二维或二点五维的世界.
从这一立场来看,看见一个立方体是在你的大脑里(或是在你的心里)有一张立方体的图片——实际上是一张线形图;而这反过来又解释了为什么当我们看见一张立方体的图画时就能体会到这是一个立方体.
对于负责观看的大脑来说,一张线形图就相当于这个立方体.
其间的逻辑不可撼动:立方体本身,虽然有其三维立体性,但被光学投影进行了屏蔽.
我们眼睛里看到的就是事物在这里的模样,也就是说,在眼睛里我们充其量只能看到立方体的2D(或2.
5D)投影.
神经美学——或至少是关于图画、绘画、描绘的理论——从一开始玩的就是视觉神经学的游戏.
那么,现在来想一下哈佛大学视觉科学家帕特里克·卡瓦纳(PatrickCavanagh)提出的论断:既然艺术家的目的是要创作有效的图画,那么他们做的就是神经研究学者的事;他们的绘画是大脑实验.
这里强调的是:艺术就是一种神经科学,或艺术家所做的与神经学家所做的是一样的事情.
如果我的理解没错,这实际上只是第一原理的陈述,没有任何新发现.
毕竟,看到立方体的线形图就能看见一个立方体,这一事实表明,至少对大脑里的视觉来说,立方体的线形图就等同于立方体.
这是视觉科学的公理.
因此,看到画家在画中利用的阴影我们不会立即发现错误,这一事实表明大脑在构建视觉世界时并不受物理知识的管辖.
卡瓦纳断言,如果我们看到世界以三维方式出现,那么当我们活动时,图画就会看起来不和谐、不准确.
对此断言,卡瓦纳甚至无需引证支持,因为图画并未以此方式让我们吃惊,这证明我们的确是没看到三维世界.
再重复一遍,艺术家在绘画时实际上是在进行神经科学实验,这一自以为是的发现根本就不是什么发现.
它来自于那个熟悉的初始论点,即在我们的体验中我们并非被事物本身所局限,而是被它们的神经图像局限了.
卡瓦纳是从他的哲学起点去宣读他的神经美学.
事物在视觉神经上的再现就等同于其再现的事物,这一等同论产生的结果值得注意:尽管事物本身有其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物质属性,但在神经科学里却几乎不发挥任何作用.
如果你想研究对事物的知觉,那么只要用目标事物的图片就足够了.
根据等同原理,一幅画的力量完全可以被它所描绘的东西所代替;反过来也一样,一件物品的意义(至少对视觉来说)完全可以由它一幅恰当的图画来实现.
因此,无怪乎,对于女神帕瓦蒂的一尊11世纪的青铜雕像为什么备受青睐,心理学家、实证神经学家拉马钱德兰(VilayanurS.
Ramachandran)会提出这样的解释:出于神经进化心理学原因,这应当是"我们"对身材丰满的女人做出的反应.
话虽如此,但无论这雕像如何传神,显然它不是一个身材丰满的女人.
但等同论使得人们完全有理由把一尊雕像、一幅画当作是一个透镜,透过它遇见它所描绘的东西;或者说在这一具体案例里,以神经学语言来讲,雕像就等同于一个身材丰满的女人.
但是,一幅画就等同于它所描绘的东西,这实在是太不靠谱了.
后面我会讲到,看见一件东西是一回事,看到它的图画是另一回事.
也就是说,无论图画具有多么强大的表现力,最好还是不要让我们相信这样的观点:图画会给我们与身临其境完全相同的感受,无论它描绘的是什么.
当你观赏一幅画时,尽管你明知画里的东西根本不存在,但可能你会感觉它就在眼前;在这雕像里可能你会看见一个身材丰满的女人;但如果真的面对一个身材丰满的女人,显然你会是完全不同的状态.
机智的神经学家会对此提出反对.
如果看到一件东西与看到它的图画有区别,当然是这样;尽管你知道这件东西并不在眼前,但如果这幅画让你看到它,那么,图画体验的独特结构在神经系统里已经得到实现.
神经科学不是要忽略这种感受上的重要差别;它只是相信这一观点:如果它本身在神经系统最终没有差别,那就不算什么重要差别.
好吧,我们已经发现,任何类型的心理状态——爱、对金钱的看重、有意识的体验等——都等同于大脑里的反应,这种自以为是的论调还没被完全阐释清楚呢,可不管结果如何,神经等效论——看见事物与看见其图画是同样的神经状态——就被卡瓦纳和拉姆查德兰与威廉·赫斯坦(WilliamHirstein)扯进了对艺术再现(representations)的分析中.
如果你不想接受,那就要放弃卡瓦纳"画家即神经学家"的论断;以及拉姆查德兰与赫斯坦的论断,即雕像是一件超级刺激源,就如一个丰乳肥臀的女人一样,被完美地设计来刺激大脑神经.
这两个案例都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拉姆查德兰与赫斯坦的故事把艺术品撇在了故事之外,不顾它特别的价值与品质.
关于一件艺术品,在拉姆查德兰与赫斯坦看来,一旦我们做了我们的真正工作,即他们认为,解释了让我们兴奋的来源,那么我们需要了解的所有一切就都清楚了.
但是,真正引起我们兴奋的不是图画,而是这个世界(在此例中是女人);或者说,图画(或雕像)能让我们兴奋只不过是因为它等同于这个世界.
拉姆查德兰与赫斯坦并未能对此具体的艺术品做出解释,它独特的外形、铜绿、大小、重量、宗教意义等.
这并不奇怪,既然物品不在神经科学的考虑范围内,艺术品也一样,在艺术神经学(神经美学)里,作品本身毫无作用,从不会成为研究的重点.
事实上,我们还不清楚艺术品是以怎样的面貌出现在神经美学里.
毕竟,对神经科学来说,物品本身只是一些触发因素,在作用上就等同于它们的神经再现.
那么艺术品也是一样,充其量它们只是在神经系统中激发反应的东西;由于它们在神经系统产生的效果,物品自身就对自己进行了屏蔽.
因此,无怪乎神经学者会在没有雕塑的情况下,只用雕像的照片来研究我们对雕塑的审美反应;或者还有人会把在磁共振成像仪(MRI)里观察油画的数码照片而激发的反应当作是审美体验.
如果等效论是对的——倘若一幅画在神经系统上等同于它所描绘的东西——那么艺术研究无需艺术作品出席也可以大书一笔,这可算作是超级的科学方法了.
但是,如果我们都同意:首先,看见一幅画是一回事,而亲身经历是另一回事;其次,说到艺术,我们感兴趣的是能够直接抓住我们注意力的作品本身以及那些实实在在的物质,这么说吧,而不是作为透镜的东西,不管我们透过它们能看见它所表现的什么.
那么,我们的问题就出现了:神经美学似乎不能把它自己的主题——艺术——作为一个研究主题放进靶心.
从根本上讲,不能把艺术作品置于焦点源于这样一个教条:艺术品的意义就是它在我们感觉系统(或情感)上的作用.
实验学者依赖艺术品照片而不是作品本身,这意味着他们一定是忽略了实际作品会在人身上激发更为强烈的反应.
这种反应不仅仅对绘画再现内容敏感,对规模、装置等其他一些因素也极为敏感.
但还有更深层的、技术性不太强的一点,这一点更为重要:艺术作品不是反应触发器,审美体验也不是大脑里激发的反应事件.
没有任何刺激物能够代替艺术作品,哪怕是艺术品本身,因为艺术品不是刺激物.
在第8章里我们已注意到,实际上,神经美学无法把艺术品本身放进研究核心这一问题早已在泽米尔·泽基的课题论断中显露端倪.
他提出,看见艺术的是大脑,大脑的律条会限制艺术.
为了证明他的观点,泽基引用的事实是,蒙德里安(Mondrian)的绘画利用了人类对色彩极为细致详尽的感觉表现;而没有艺术家会利用紫外线创作艺术,因为这种光线毕竟是不可见的.
这里的问题是,大脑限制了我们的艺术体验,并非因为艺术或艺术的神经再现或艺术体验有何特别之处,而是因为大脑限制了我们对所见任何东西的视觉体验.
既然艺术作品要被研究、被视觉察验,那么我们能够从事的只能是我们看得见的东西.
这里我们看到的,与其说是关于艺术鉴赏的神经学基础的一个错误论断,还不如说这论断把艺术及其独特的神经基础都摒除在严肃的考虑之外.
它远未做到给出任何解释.
·或许,将注意力转向审美体验——当我们看到美的或令人敬畏的(或崇高的)事物时所感受到的强烈愉悦——以此研究它的神经关联,这一方法可能会更有前景.
这是神经学者加布里埃尔·斯塔尔(GabrielleStarr)与她的同事维瑟尔(EdwardA.
Vessel)与纳瓦·鲁宾(NavaRubin)所采取的方法.
但这里也存在问题.
我们假设审美体验存在神经关联,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关联有任何解释意义.
下面的例子来自另一领域:据称男女大脑有别,这种区别被当作性别是硬性关联(genderishardwired)的证据.
但问题是,如果说男人和女人在行为上、认识上、体验上有差别——这并非是我的假设,只是说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差别在神经生理上也会存在.
怎么会没有呢但这并不排除可能是社会、文化、环境因素驱使、导致也因此解释了这些差别.
审美体验也一样,如果有审美体验,那么这些体验必然有它们的神经关联.
所有东西都会在大脑里留下踪迹(而不是,大脑能够追踪到所有东西),这一点非常明确,所有东西都有它们的神经关联.
但是关于我们感兴趣的体验,这些关联能教给我们什么尚有待发掘.
我还没发现任何证据证明它们做了这些.
另一问题在于,关于审美体验,要列出有意义的、稳定的或必然的(更别提充分的)标志十分困难.
有些美学遭遇(aestheticencounters)打动人心,有些则不;有些能打动我却未必能打动你;有些在这一场合能打动我,换种场合又不了.
它们大多数根本不能打动人,直到,这么说吧,我们学会被打动.
假如有一个四星分级表,你能挑出那种你标为最震撼人心的审美体验吗这是斯塔尔的方法.
她与她的同事让受试者判断经典艺术作品的照片是否具有震撼力,按程度强弱分为1~4级.
我怀疑我们能否以此方式来操作审美体验.
而且,它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审美体验的一个根本特征.
对此我也深表怀疑.
下面我会回到这个话题.
实验中,斯塔尔和她的同事让受试者在磁共振成像扫描仪(MRI)里观察艺术品的数码照片并记录他们的体验.
他们把标为4级震撼的体验当作是"极致的审美体验".
然后他们论证道,事实上,在所有不同的艺术领域里(音乐、绘画及诗歌),这种体验都有强烈的神经关联.
具体说来,他们论证,"极致的审美体验"会在被称为"大脑默认网络"(defaultmodenetwork)里激活,而那些不太强烈的体验(观看图片并在"震撼"级别中被标为1~3级)则不会.
据说,与这一网络相关的脑区被认为,相对于静息状态,在从事任务或面向世界的活动时会受到抑制;但当注意力从世界转移开时,在静息、白日梦、心猿意马、思想驰骋期间,它会重新获得基本速率.
他们还表示,默认网络是明确自我的神经系统,这一论断几乎本能地呼应了一个观点:当我们受到强烈的美学震撼时,这一系统就被激活了.
这就好像是在说,受到审美感染会让我们欣然忘我,让我们内省,让我们脱离简单的观看,脱离面向物质的审视而转向更似冥想的什么东西.
这一观点颇有启示意义,但可能缺乏有力支撑.
首先,我要质疑仅靠脱离世界的做法自我是否可以被明确、被代表或被激活.
自我不仅仅是以自我反思的"me"出现——受到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观点的启发,包括克里斯托弗(KalinaChristoff)、考斯迈利(DiegoCosmelli)、莱格兰德(DorothéeLegrand)、伊凡·汤普森在内的研究团队如此提醒我们——还有大写的"I",作为行动者的"我".
有证据表明,在注释里我有引用,事实上所谓的大脑默认网络在从事任务和参与环境期间也时常被激活.
这么说,默认模式的激活意味着什么,我们并不明确.
因此,在这种激活与为了研究目的而被贴标的审美体验之间,我们该作出何种推定关联也尚不明确.
·至此我已经申明,我认为你不应当把所有的知觉体验都当作是在脑袋里发生的事件.
因此,你也不必奇怪我会拒绝接受审美体验是发生在脑袋里的特种事件这种说法.
但是,在此我的担忧并非源于我自己的"外在主义"(externalist)观点.
审美反应有一个显著特征——这我在第8章里也曾讲过——即它们是一种认知造诣,类似于领会一个笑话.
"领会"需要机智、见解、悟性.
关键是,领会的范围涉及你要交流些什么和期待些什么,尤其是对交流方式的预期.
审美反应与此类似.
审美反应还有另一个特点.
我们体验审美时,不仅仅是孤立地观看艺术作品(像我们在大脑扫描仪里所做的那样);我们常常要去学习进行审美体验,而且我们的反应需要受到启发,受到别人的看法和说法的影响,包括:老师、评论家、朋友、家人对作品作何评价有何想法还有,我们以前所见作品有何参考关于这作品我们能做些什么我想做什么审美反应不是固定的数值,而更像是我们在持续进行的对话中所采取的立场,这对话在我们的寻常日子里、在我们的生活中以及在我们文化的历史性时刻中不断地进行着.
审美反应是可以培养,可以教化的;同时也受到挑战.
审美反应本身就是艺术抛给我们的问题,而不是我们为了弄懂艺术本身可以想当然的东西.
这让我想到最后一个特征(第8章里曾提过):审美反应是种评判.
面对艺术作品我们要有立场,我们不能只是"喜欢"它;我们喜欢它,如康德所说,是"普遍的声音"(universalvoice),就是说,我们期望别人也喜欢它.
如果别人不喜欢,那么我们希望他们说出不同意见.
这里要说的话有太多太多.
哲学家亚历山大·奈哈马(AlexanderNehamas)提出:美学评价只是对话的开始,而不是结论.
艺术被体验,在争论、批评和说服的场景中.
康德的见解让他意识到所有这些都包容一个事实:在这领域无法裁决纠纷,没有决策程序,没有规则,没有办法证明谁对谁错.
这可能是艺术遭遇的根本.
但艺术还是提出了这个问题:到底谁是对的那么,审美体验不是表征、不是反应、不是固定的数值,它们是行动、是参与模式、是对话时刻.
我们甚至没有任何理由去问:它的神经关联是什么而且,寻找神经关联已经偏离了配得上称作审美体验的东西,而是转向了我们头脑里的事件亦或是感觉.
约翰·杜威有一个悖论式宣言——被用于本书题词——正是艺术品的存在妨碍了我们构建一个合理的美学理论.
的确,它不是关乎物品,也不是关乎物品在我们身上激发的反应.
杜威说:艺术是体验.
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它是关乎我们要用艺术品做什么.
在这一意义上,它关乎艺术的使命.
总而言之,神经科学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太钻牛角尖、太具象、太理想化、太违背现实,不适合成为研究艺术的恰当工具.
但是,还有一点需做出更深入的解释.
如我们所见,神经科学把艺术当作是一种现象,因此它像研究所有现象一样研究艺术.
艺术品引发的体验具有独特的"美学"特征,正因为如此,它才被当作是触发器.
我曾讲过,艺术的激发理论和审美体验论实际上不能把任何一个实体(entities)带进研究视野.
艺术没有得到解释,反倒被解释偏了.
现在我们回到核心问题:艺术不是一种可以被解释的现象;相反,它是一种试图去做出解释的模式或活动.
这是本书的核心论题,我将在第11章中开始转向此论题.
但是,只有在后面的几章里我才能够充分地阐述这一论断的意义.
艺术与哲学属于同一种类型:如前文所说,它们都是重新组织的实践.
有关艺术以及哲学与生物学的关系,这一论断最终会显出重要且令人惊喜的含义.
它还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把审美还原到神经系统是极其错误的想法,其荒谬程度丝毫不亚于我们把哲学本身也还原为大脑里的事情.
第11章艺术是一种哲学实践,哲学是一种美学实践"实践"是被哲学家、人类学家和形形色色的理论家挥霍过度的一个词汇.
与任何术语一样,"实践"有它的用途,却也标志了一个灰色地段,在这里,理论的车轮往往会失去牵引,开始自由运转.
我父亲是建筑师,他在纽约开了间酒吧.
他常说他接手酒吧的时候并不认为自己离开了建筑行业.
对他来说,经营酒吧就是一种建筑实践.
我猜他的意思大概是,酒吧嘛,是为人们准备的空间,而建筑呢,则是室内空间的艺术.
我母亲是陶艺师.
从20世纪50年代末,她就开始从事制陶工作,就是那种传统的英式美式陶器.
但她是在生产陶瓷,并不做陶瓷雕塑,她抟土造瓷——饮水杯、盛食物的餐盘餐碟以及各种家用的瓷器.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她只是一个工匠,一个手工艺人,但我坚持认为,她所做的是一种艺术实践.
因此,经营酒吧可以是建筑实践,而制作陶瓷碗碟也可以说是一种艺术实践.
本章,我想唤请大家注意:无论是作为实践还是作为领域,在艺术与哲学之间,都存在着更为深刻的渊源.
艺术与哲学共同具备的第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们都没有题材的限制.
的确,一些传统的话题吸引了哲学家的关注——例如,身心问题、公正的本质——而艺术家也有一些特别倾心的关注,尤其是在媒体(油画、印刷、水彩等)和主题(依然是生活、肖像等)方面.
但当然,这些界限与归类并不能表明艺术与哲学作为学科的真正疆界.
事实上,哲学家的哲学表现在各个领域及环境中:物理学、神经科学、化学、语言学、经济学,还有谈话、决策、爱慕、知悉、忧虑、宗教——所有这些地方都可能成为哲学的生发之处.
艺术也是这样.
没有人可以因为这不是艺术的恰当主题或这不属于艺术创作的范围就说"这不是艺术".
爱、神、政治、幽默、领悟、视觉、美食,你大可继续列举下去,艺术家可以在所有这些领域找到灵感.
因此,这是哲学和艺术的一个显著特征.
这种实践不像历史要受到史实的限制,不像物理学要局限于物理现象;它们没有主题的限制.
如果艺术与哲学有什么同一性,那恰恰是因为它们都是实践.
它们有着共同的传统,对于方法、价值和进行方式有着共同的关注.
艺术与哲学就像是一次漫长的谈话,参与的人进进出出.
有的人在即将结束时加入进来,有的人从一开始就加入了,有人来晚了却坚持要了解先前说过的话,还有人半路插进来却并不完全清楚现场状况.
或者,艺术和哲学也可以被比作武术:一个门派的同一性就是师承的同一性;它是真正的人的关系——徒弟与师父、与师父的师父、与师父的师祖,如此等等.
那么,哲学究竟是什么每一代哲学家都要面对这一问题,而且是非常迫切地面对.
学习哲学的时候,我们似乎不可想当然地以为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知道自己在学什么,因此哲学家在书写哲学史时不仅仅是在报告事实或讲述故事,同时也是他阐释哲学的一种方法.
因此,哲学家,无论是现在还是2000年前,总是要质疑哲学并质疑哲学的价值.
哲学在不断地更新,不断地修正,不断地发展演变,不断地重新思考自己.
哲学对其自身就是一个问题.
艺术恰恰也是如此.
艺术心心念念的一个核心话题便是:什么是艺术杜尚的《泉》(Fountain)是艺术吗是,为什么或者,它怎样成了艺术他到纽约的一家五金店买了一件现成的小便器,这小便器成为艺术是因为艺术家的购买还是因为艺术家在上面的签名还是因为这是一个杜撰的签名或者是因为他把它送去展示,使得一件卫浴用具变成了一件艺术品或者可以说,一件卫浴用具根本不是艺术品,让其成为艺术品的是对小便器的改装.
的确,这作品是一种展现.
杜尚的作品提出的正是这样的问题,他的作品在问:艺术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重要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典型特例,独具现代特色.
但是所有的艺术,总是在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令其他艺术家孜孜以求、苦思冥想,也令艺术的本质扑朔迷离.
如此,与哲学一样,艺术也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地更新、修正、复原和再造自己.
还有一个事实令人瞩目:在哲学与艺术中,我们可以谈论沿革、历史甚至发展,但我们不可以论及进步.
这是因为,在这些领域中不会有突破、发现、结果或成果之类,当然也就不会有任何发现会抵消或废弃以前的发现,或为未来的发现做出铺垫.
我们阅读哲学典籍或论文不会去找它的基准线(bottomline).
"哲学家X认为怎样怎样""笛卡尔认为我思故我在""康德认为空间和时间都是直觉的形式".
首先,这些不是让所有同行都感到满意的、公认的、确立不移的命题,相反,它们是一次重要谈话中的动议(moves),但它们都不能结束对话;其次,这种哲学论题没有能够自立(self-standing)的内容,若不是追随哲学家的思辨旅程,你不会懂得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
简而言之,哲学没有基准线,而且没有任何独立的哲理箴言可以与数学、物理学和生理学的发现一样骄傲地并立在科学的圣殿之中.
一篇哲学文章更像是一个总谱(score),而不像是对事实或发现的记录.
当实证科学家公布一个发现时,他们会报告之前为之所做的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写作摘要只是一件微末小事.
一份哲学摘要却总是闪烁其辞、含糊暧昧.
一篇哲学文章本身就是哲学,而不是一份实验报告.
像总谱一样,哲学文章是作者以自己的风格或见地从事哲学思考的工具;阅读哲学文章就是追随作者的思想、感受和迷惑,参与它们的表演.
就算一个外星人来到地球并发现解码哲学典籍的方法,他仍然读不懂它们.
因为他们不会有共同的迷惑与好奇、共同的困境与纠结,而这些正是哲学的前提.
对于没有哲学忧虑并不会为之所困的人来说,哲学文本毫无意义.
而只要恰当地稍作改动,所有这些也同样适用于艺术.
诚然,有些艺术家制作物件,所有艺术家都会创作或鼓捣点什么.
这些作品并非现成的就能放在博物馆档案中收藏的天生自足的成就,虽然说起来这有点不太体面,但作为一种文化我们的确是这么想的.
只能说,它们是一些契机,对于那些心怀意念要用它们做些什么的人们,它们提供了积极参与的契机;艺术作品又没有物质上的同一性,对此,我们还能怎样解释一个小便器与画布上的作品,或是一首歌、一座建筑、一件祭坛装饰有何共同之处艺术作品本身死气沉沉,就像是单纯的声音或无用之物.
是我们赋予了它们生命,让它们在参与思考、对话和鉴赏中焕发活力.
它们要表现力量,就如笑话要表现力量一样,是作为棋步参与到交流与反思的棋局中.
创作者与公众要共同承担起这一任务,才使得艺术成为可能.
我们可以说,艺术与哲学都是实践.
它们的价值并不在于它们的结果;方法和结果同等重要.
因此,重述一遍:我们可以谈论历史、发展和影响,以及重大的成长与变革——就如我们在探讨一次交谈、一个人的感悟或一种文化实践时用到这些概念一样——却永远无法更为肯定地谈论进步.
因为艺术家所做的不是发现;而且他们的所为,离不开自己的自然场景:好奇、困惑、陶醉与渴望.
在某种意义上,杜威说的完全正确:博物馆是与艺术对立的.
就好像只要盯住它看或者通过记下录音或讲解员的话,你就能看到艺术一样!
好像艺术的价值就这么轻轻松松地被传达出来了!
艺术品不会只是静静地待在博物馆里,闪耀光芒等待世界来发现它.
观众与创作者需要通过艺术家创造的机会彼此交融、共同参与;我们在感知艺术的同时更要去践行艺术.
正是这些关于艺术与哲学的事实使得艺术和哲学成为文化问题.
艺术品与艺术家都是质疑的对象,哲学家亦如是.
是的,的确有一个艺术市场,但它疯狂、缺乏理性,与艺术缘何重要并无必然联系.
因此,无怪乎,在这样一个还有太多迫切需要、太多高昂花费的世界里,政府和基金机构要千方百计地寻找理由来证明他们资助艺术或哲学的合理性.
那么,既然哲学研究永远也不会产生什么公认的定理或确定的理论,那它又怎能成为一件有价值的事它又凭什么让人们投入大量的资源,结果生产的产品,却因其本性使然,完全不可付诸应用或服务于这样那样的领域这一切值得吗对此,柏拉图的解答是,哲学的价值并非源自于辩论的结果,它的价值在于转变我们的理念:看我们原本持有的不同的观念、信念和价值观,如何在突然之间互相关联得到了统一.
在哲学讨论的过程中,你得到转变.
开始你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个人身份,而最终,面对你与你的对话者可能想出的观点的明显缺陷,你意识到你并不知晓.
但是,你的不知正是因为你已有所领悟.
可能你并未学到任何新东西,但你会发现你原本知道的东西展露出一种全新的光彩.
哲学不会改变任何事物,它听任事物保持其固有的状态;但它重新组织我们思考和推理的方式,哲学改变的是我们.
哲学的目的不在发现,而在领悟.
现在看来,一次审美体验,与苏格拉底或柏拉图式的哲学对话有着完全相似的结构:它也是有感而发、有为而作的;有思索,有机辩,有交锋,有交流.
起初,我们对存在的东西视若无睹,但是通过观察、探询和质疑,我们开始有所发现.
作品激发我们去重新组织我们的发现、我们的期待与我们的思想.
艺术的工作,与哲学的工作一样,是对我们自己的重新组织.
而这种重组,这种工作,其目的也在于领悟.
我听到有反对声:艺术不像哲学一样充满学识,它不是思想的游戏.
我们怎么可以将阅读哲学典籍与观看舞蹈表演相提并论或者,跳舞又怎能与写作哲学书籍相比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过的,在这一反对中有一个不言而喻的错误,即哲学被错误地描述为冷漠的.
哲学充满智慧,是的,但这并不意味它冷漠;哲学是由情感驱动的,有困惑、有迷茫、有好奇,它热情洋溢.
同时,如果你认为舞蹈艺术家不能解决问题,不进行研究或提出问题,那他们的工作就完全被低估了.
关键是,正因为哲学与艺术事业所涉及的问题无比重要——我们已然发现,这两项事业没有边界——我们的参与才有重大意义.
·艺术是一种哲学实践(反之亦然),由这一观点来看,我们可以解释艺术的3个特征,这是以别的方式(尤其是神经心理学理论)很难解释的.
首先,如第10章中提到的一样,艺术有个显著且永恒的特点:它总是让我们争论;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
我们要讨论,作为艺术,这个或那个好在哪里;首先要讨论它是不是艺术,然后讨论艺术究竟是什么;假设我们认为我们知道艺术是什么,我们又要讨论它是否具有真正的价值.
如果你真正关心艺术,那么这些问题的确炙手可热.
对于艺术问题的态度会划出人们之间的界限,这一界限标志着我们能否彼此理解,能否彼此相处;它也标志着人们在更大尺度上的文化和历史的差异.
我的主张是,审美分歧是一种哲学上的分歧(或者说哲学实际上是美学争议的领域).
与数学或物理学不同,哲学中没有求证程序,但这并不是因为问题不真实存在,而是因为这些问题并不生成新的事实或产生的只是逻辑上的因果.
哲学困惑关注的是,我们身处何地,以及我们所知的有哪些可以居之不疑.
哲学辩论有说服性也有教育性,同时它们又很现实.
它们关注的问题是,(在这个或那个知识或实践领域)我们该怎样继续进行下去.
如果说艺术是哲学的一个亚种,或者——如我所述——两者同属一个更大的属种,那么,当我们发现艺术如哲学一样,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领域,我们便不再感到惊奇.
艺术与哲学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自我转变,实现领悟.
其次,艺术家制作东西.
他们敲敲打打,他们舞台呈现,他们建造房屋,制作模型,塑造、浇铸、描画、构筑,无所不能.
但我们都知道,他们绝不仅仅是制作者,他们制作东西绝不仅仅是为了画一张更好的图画或让人们得到更多娱乐.
绘画艺术家,从我的观点来看——对此,后面我还有更多的话要说——是在利用绘画技术把图画以及图画在我们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展现出来,其目的是唤起人们对它们的注意.
这并不是说对艺术家来讲有时创作一幅逼真或漂亮的图画无关紧要,但这远非故事全部.
刚刚探讨的观点帮助我们渐渐领会到:艺术作品是哲学之物,如果说我们值得用图画去阐释哲理,那也是因为,图画对我们很重要.
我们的生活中的确离不开图画,它们的确组织了我们的生活.
事实上,它们是如何做到的,我们却并无真正地领会与掌握.
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图画,我们却认为理所当然.
画家——也就是说,那些以绘画为职业的人,关键是,并非所有的画家都以绘画为职业,比如巴内特·纽曼、阿德·莱因哈特(AdReinhardt)、埃尔·赫尔德(AlHeld)——是在相关形式的困惑与需要发生的地方做哲学,并将之付诸于描绘行为.
最后,正如我们之前一直所探讨的,艺术可能会非常枯燥;它常常让人无聊到想哭.
如果艺术作品是奇特的工具,如果艺术的发生一贯以破坏为己任,总是要求我们以不同的方式观看且努力发现我们并不确切知道该怎样去看的东西,那么无怪乎我们往往会一无所获,只是发现自己被困,眼前的作品遥不可及,甚至我们的生活都远离了我们.
这种枯燥的常态,这一独特的陷阱,恰恰也是哲学的标志.
哲学结出的果子不会帮你实现你在做哲学之前为之奋斗的目标;它不会生产治愈要命疾病的良药,也不能帮你终结全球变暖;但它会帮你以不同的方式看世界,使你能够再创自我,重塑自我.
并非所有的艺术都枯燥,哲学也是如此.
但是,枯燥是活生生的可能,它就在那儿,以完全相同的方式,等待着艺术与哲学.
第三部分鲜活的知觉,也即我们实际感知到的东西,既不是几何图案也不是影像画面.
——毛里斯·梅洛-庞蒂第12章制作图画场景:儿子所在的一年级教室里,独奏音乐会正在进行中.
我环顾四周,看了看其他的家长,令我惊讶的是,没有一个家长在盯着看场上的小演员表演.
他们的目光无一例外地专注于各自手中的摄像或照相器材的显示屏.
有人带了三脚架和昂贵的摄像机,也有人满足于用手头的智能手机拍摄.
让我对此情形无比感慨的,并非是在父母眼中影像足以替代演出本身;也不是因为这是一个表现电视录像强大力量的特例,即便在现场演出面前,它仍抢占了我们的注意力.
不,不是这些,令人瞩目的是,所有这些家长都在密切地关注着表演;他们在看,却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以制作图像的方式.
如果你曾尝试过实物写生,要用画笔画出现实生活,那么你就知道这其实有多难.
该先从哪里入手该怎样引导人们的关注点哪些是重要的想要画出有效的图画,你需要学会重新思考你所看到的——这世界应该怎样被表达和呈现出来该如何将它构建起来要想画好某样东西,你需要非常用心地去研究它.
如今,有了数码摄影,制作图画变得简单易行,成本低廉.
制作一张数码快照其艰难程度根本无法与用画笔描画现实相比.
但是,绘画与业余摄影有一个共同特点:制作图画——即便是在小学教室里以手持设备拍摄数码录像——对所描绘的事物予以高度关注.
因此,它是一种观看的方式;一种对自己所见给予特别关注的方式,恰如跳舞是对所听音乐的特别关注一样.
与图画紧密相联的是观看,但与之紧密相联的又不仅仅是观看;它还关系着我们对自己所见的思考,对我们所见表现出的兴趣.
此外还有两种兴趣:别人怎样看我我希望别人怎样看待我这个观察者请注意,在独奏音乐会上给孩子们拍摄录像时,我们关心的并非是孩子们完全视觉意义上的外表样貌(无论它确切是怎样).
我们认识他们的模样.
我们关心的是他们是谁,他们在做什么,以及他们在怎样表现.
我们想把他们展示出来,而不是他们的外貌.
图画,在其主要类型中至少有一种,是独具一格,特重视觉的;它瞄准的是这个世界,并把它的视觉样态呈现在我们眼前(关于非视觉图像我们稍后讨论).
但图画不仅仅关乎外表形象,它还在展现我们的所见,也即我们所关注的事物(无论出于何种原因).
儿子教室独奏音乐会的一幕给我一个重要启示,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启示——我们需要制作图像.
这是一个简单的、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我们并没有发现它们.
它们不是自然产生的现象,像池塘里的倒影或自行车电镀车把上的影像那样;也不像墙上的影子一样是自然形成的现象;图像不是我们俯身可拾得的;我们要制成它们.
它们是人工制品;是制作的产物.
许多制作图像的设备——包括数码相机或传统相机——都是对自然成像、反射等诸如此类现象的利用.
圣菲研究院(SantaFeInstitute)的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W.
BrianArthur)说道:关于技术有一个普遍的事实,即它们驾驭自然,并把我们对自然现象的理解付诸应用.
这里的重点是,图像是人工产品,而图像制作是一种技术实践.
简而言之,图画是一件工具.
我们制作图画并不是为了好玩,至少通常不是这样.
工具的设计有一定的目的,且以需求、期望和问题为背景.
为什么所有的家长都在专注地制作图像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但这很重要也很能说明问题.
这与图像无关,因为这里面的动机很复杂,或许如同我们的生活本身一样复杂.
为什么我们觉得需要用图像来记录下孩子们的生活假设不记录我们会失去什么我们这样做又能成就什么回答这类问题不是图像理论的任务,但是图像理论的任务应注意到,每当我们制作图像,我们都有类似的理由,这些理由早已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复杂机制中.
在这一意义上,图像就像文字、语言一样.
我们为什么要说话让我们数算一下:达成交易、表达歉意、想法要回开瓶押金、恭维老板……我们为什么要制作图像这一问题的答案恐怕同样地丰富多彩、语境各异.
图画用途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对它进行有效的概括.
图画是显示事物的工具,用以把事物展现出来.
这种概括抓住了图画制作的基本功能,对于激发图画制作的多种多样的背景、条件和语境既不会有失偏颇也不会有所忽略.
毕竟,我们为什么想要展现事物当我们试图回答这一问题时,我们就会得到各种各样想要的具体原因.
图画是用以展示的工具,这一定义还有另一种意义.
它将图画妥善地安置在它本来归属的地方,在我们与他人进行互动交流的场景中.
要观看一幅画——对此我们很少有所意识——你必须去领会它要向你展示什么,而通常要做到这样,你需要对微妙的背景有敏锐的感知.
报纸广告版上的这张图片在告诉我,超市里的鸡肉在优惠促销.
要看懂这张图,要领会它所传达的信息,你必须对商业广告或诸如此类的复杂背景极其敏感.
关于工具和技术,这是一个普遍的事实:门把手(又来了!
)简单直观、使用方便,但却离不开其自然场景(也即文化背景).
门把手的前提条件是首先要有门,我们生活在房子里,我们需要从这一房间走到另一房间;我们的身体,尤其是手,要长成这种特定的样子且能发挥正常的功能.
门把手对孩子或对残疾人或对来自其他偏远文化的人来说,可能构成障碍.
但是,只要背景安然存在,只要我们想当然的所有事情可以被安全地视作理所当然,门把手就是一件毫无悬念、毫不起眼的东西,简单到基本可以从意识中消失.
我们不必去看它,不必去想它;我们无需费力去使用它;它变得如同我们立足的地面一样自然,我们在这世界的行动只是为了与之相协调.
而大多数情况下,图画也是这样.
出了艺术馆,我们很少会去审视图画.
就是说,如果我想在网上订购一件外套,我会仔细研究中意的外套图片,但我实际研究的是那件外套,而不是照片;当我对着爱人的照片遐想时,令我着迷的是她美丽的脸庞,不是照片.
如果背景安然妥当,让我们把图片当作图片来使用,能够显示或展示事物,那么图画本身,就像门把手一样,或是像我们立足的地面一样,就会隐没到背景之中.
·图画是一种人工产物,它们更像是情书而不像化石.
我们不是发现它们;我们需要制作它们.
前面我就讲过,这几乎是明确的事实,无需赘言.
比如说这只鸡的照片,报纸上宣传当地市场促销的照片,就是复杂的广告社会实践所做的一个行为.
还有比这更显而易见的吗柏拉图会表示反对,这我们早已注意到了(在第5章中).
他说,要作一幅画很容易啊,你只要举起一面镜子!
镜子里的影像是一种反射,但在柏拉图看来,图画就是这个样子.
柏拉图还认为,图画一无所用.
毕竟,我们对反射的影像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世界本身.
我要了解周围这世界的实在本性干嘛要通过观察那些在安全带搭扣上、眼镜片上、或池塘表面上自然产生的影像柏拉图对图画的鄙视也是对视觉世界的鄙视.
观看,在柏拉图看来,其本身只是对我们周围事物的一种反映方式;观看,就如镜子一样,只停留在表面.
实际上,这一观点——观看是与表面形象的交流——也是有关视觉的现代实证思想的组织观念之一.
它早在柏拉图的思想里开始萌发,而在后期的科学革命者那里得到了成熟的发展——开普勒、达·芬奇、笛卡尔、伽利略、牛顿——他们为视觉科学夯实了基础.
开普勒把对光线物理几何的成熟理解与对眼睛结构的正确描述结合起来,从而准确地描述了光线在进入眼睛时的折射.
开普勒是第一个证明眼睛是一种复杂的成像设备的人.
眼睛就像一面复杂的镜子,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照相暗盒.
开普勒与其同时代人还认识到,视觉的故事不可能终结在视网膜上的影像.
毕竟,我们看到的世界是直立的,而视网膜上的影像却是颠倒的.
视网膜上的影像一定是经过了某种处理后才让我们感知到它所呈现的样子.
它需要在"心眼"前再来一次倒置.
后来,19世纪、20世纪研究视觉的学者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
我们不是用眼睛在看,我们是用大脑在看.
他们认识到,视网膜上的影像与我们视觉意识中所见到的影像大不相同.
除了眼中的影像是颠倒的,而且有两个之外,还有太多不同:首先,我们的眼睛几乎在不断地运动,但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稳定的世界;我们的两只眼睛里都有一个盲点,这里根本没有感光体,但我们的视野中感觉不到任何空白;视网膜的分辨能力并非处处一致,我们体验到的世界在其边缘却没有模糊不清;在视网膜的边缘,色敏感接受细胞消失,但我们看到的整个视觉世界同样的色彩斑斓;视网膜前面毛细血管及其他组织纵横交错,不时会导致光线受阻并发生折弯,但我们的清晰视觉并未受到干扰;视网膜上的影像极其微小,我们看到的却是正常尺度的世界;最后,视网膜影像不过是数学意义上的影像,是在一个二维平面上的投影(视网膜表面大致呈凹形),但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却是实在的立体构成,呈现完整的三维空间关系.
我们看到的不是视网膜影像;它们充其量不过是影像加工过程中的输入信息,只有经过这一加工过程,我们所认识的视觉才成为可能.
视觉科学就这样传承下来,在当今大学中占绝对主导地位.
视觉科学与柏拉图的根本观点相同:观看就是在心里形成影像.
因此,观看,与摄影非常相似,是要对我们所看见的进行加工的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
当然,这一认识随后形成了认知科学家对于我们体验真实图画的解释.
由此,比如说,斯蒂芬·平克(StevenPinker)就曾说道,似乎这无需证明:"无论是何种假设,只要它促使我们的大脑看到这世界是作为一个世界而不是一些涂抹的颜料,那么它就会促使大脑把绘画看作是世界而不是涂抹的颜料.
"这里面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我们去看这世界时就能看到它,同样的原因,我们看一幅画时就能看到它描绘的世界.
那么,这其中的推理是什么呢当你看这世界时,你实际看到的,实际被呈现给你的,是一幅视网膜(或神经)上的图画.
所有观看都是一次与图画的相遇.
因此,当你面对视网膜上的图像时,无论是什么促使你的大脑看见这世界,当你面对一幅外界图画时,它都会促使你的大脑看见这世界.
图画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呢根据这一观点,当你看见一幅画时,比如祖母的照片,你遇到的正是与直接遇见祖母本人在你身上产生同等效果——影像、感受——的事物.
当你看见祖母的照片时,你就能感觉到祖母,因为照片会在你眼中生成祖母的内在图像.
照片就像一个外化的视网膜影像;它是一个感觉触发器(重述第10章里讨论过的话题).
至此,关于对图画的体验,我们看出这种解释有多么地不完善、多么地荒唐可笑.
如果平克和他同事的观点正确,那么看到祖母的照片就会与亲眼见到祖母本人产生同样的感受.
但问题是,观看图画与看见其所描绘的实物并不相同.
任何把我们在照片里看到祖母时的所见归结为照片与祖母本人在我们身上会产生相同作用的解释都是站不住脚的.
如果心理学家所说正确,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观看图画有什么特别之处,即图画能给我们呈现显然不在我们眼前的东西.
我们也无法理解观看还有什么特别之处.
重要的是,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在我们的感觉中可不是简单的事物表面的投影图像.
我们视觉体验到的要远远超出眼睛里的投影.
例如,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你的身体、体形、表情、肤色的投影特征,我看见的是你.
你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人,有个性的人.
我能感受到你的人格,你的男子气或女人味,还有更多.
再设想一下我对一个西红柿的视觉体验.
我能看见它的表面,这是肯定的,但我也能感觉到它隐藏的那部分,是一种丰盈的3D感觉.
再设想我对你来信含义的体验:信的意义并未从纸上投射到我的视网膜,然后在我的视觉系统处理中心得到重建,但是看到信我还是能在视觉上感受到它.
最后一例,我对我所在的这房间的体验并不像它会出现在照片中那样,从中心向四周事无巨细地蔓延开来.
我看见什么完全取决于我在看什么,我在想什么.
很可能我和你交谈了1小时却根本没注意到、根本没"看见"你穿的是什么衣服.
仅仅冲击到我的眼睛并在大脑中产生反应不足以让这东西在我的体验中显现出来.
关于所有这些现象——包括我在别处所探讨的——有一件事值得关注:你作为一个人,或比如说,作为一个男人的特质,我看到的不透明固体的隐匿部分,词汇的含义,它们出现在我面前并非由于它们在我眼睛里的投影,而要归因于我知道些什么以及我能做些什么.
我能看到房间里的细节,看到西红柿的另一面,感受到你的人格,体会你信里的含义.
我之所以能做到这些,其基础是我的知识,我的技能,我的阅读能力(比如说),以及我对相关概念的掌握.
如平克所说,视觉是一种光学过程,它的形成源于对一个意象的接收.
这一观点本身就是一个我们在不断地传来讲去的传说,尽管它几乎毫无道理.
与触摸一样,观看也不过是要在心里留下意象.
看见你是与你相识相遇的另一种方式;看见不是自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而是需要我们去做的事.
与我们要做的所有事情一样,它取决于我们在哪儿,我们和谁在一起,我们知道些什么,以及我们想要什么,又有些什么.
因此,我们该怎样使用和解读图画我们又该怎样利用它们来观看第13章使用模型把图画看作是刺激反应的影像或是头脑里的图像,以这种方式来解读图画我们不会有太大建树.
这些主张不能解释图画里的事物如何以奇特、微妙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
现在我们该认真地探讨这一观点里的意义了:观看不是欣赏大脑里的图像,观赏图画也不是与大脑里图画的交流.
相反,我们应该这样问:当我们观看的时候,我们在做些什么尤其是,利用图画我们怎样观看它所描绘的东西我的建议是,图画是一种特殊的模型(model);模型是我们用来代替别的东西的东西,模型是一个替代品.
我并非是从专业角度来使用"模型"这个词.
建筑模型(比如巴沙轻木模型)、(塑料)飞机模型、时装模特、公寓样板间,对于这些我们都不陌生,更不用说科学模型和生物学里的动物标本.
所有这些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我们要用它们来思考和研究别的东西.
房产中介公司用样板房来展示你可能购买或租用的房子的特征;科学家的模型给我们展示一种结构,对这种结构的研究会揭示,比如说,某种条件下分子的活动;时装模特让你看到衣服穿在身上的最佳效果;生物学里的动物样本是真实的动物,它们对药物的反应(比如说)能让我们推测得出近似的物种(人类)会对药物产生怎样的反应.
我们不会以为模型起到的作用是心理上的,也不会以为模型给我们呈现的景象就等同于直接遇见我们模拟的东西.
衣服穿在模特身上比穿在我身上好看,而房子的轻木模型在很多方面与房子一点儿都不像.
说到模型,显然它们的有效性、它们给我们展示什么的能力,与我们怎样制作它们,尤其是怎样使用它们密切相关.
我们观察它们,研究它们,思考它们.
正因为对它们的观察和使用,我们可以获知一些别的事情,一些真正引起我们兴趣的事情: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我们使用房子模型来代替实际的房子,因此,我们真正需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要用它来替代而且,是什么让我们有理由这样做,或是什么允许我们使用这种替代关于模型,有两件重要的事情值得注意.
首先,没有东西可以单凭其内在构成成为一个模型.
轻木房子模拟的是建筑师的设计规划,但建筑师造这建筑完全可以用来纪念几年前建造的房子;而同样是这所建筑,事实上完全可以不必用作模型,而用作玩具,像玩偶房子一样.
然后,任何东西作为模型只有相对于我们独特的兴趣或目的才有用.
沃森(Watson)和克里克(Crick)的模型使得科学家能够直观地看见DNA的分子结构在生物成长过程中怎样使某些信息得以储存和交换;而一件轻木房子,比如说,在显示房子的规模及其各种比例方面非常有用,却不能传递任何有关材质的信息,对于周围风景、布局之类也无太大参照意义.
这里的重点是,模型是探索世界或实现特定目标的方式.
我们使用模型来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
模型之所以有用、成功和准确,是因为它能达到一定的目的.
出于临时需求,模型也可以即兴拼凑而成.
为了向你演示我们以后在哪儿会面,我会用餐桌上的几只刀叉和盐罐、胡椒罐临时搭建那个城市的小小模型.
我会说,"这是华盛顿广场的拱门""这里是第五大道的施工现场",然后用这个即兴凑成的临时模型,我就能向你演示我所提议的确切碰头地点.
模型选择的依据,是最初触动我们的、特定的需求和兴趣.
地图是一种模型,我们对地图比例的选择取决于我们想干什么.
出于模拟和研究目的,各种因素都可能会影响我们对模型的组合.
比如说,我可能会觉得这样更为合理:用一枚硬币来代指建筑工地,用餐刀来模拟第五大道,而用盐罐来代替帝国大厦.
之所以这样来构建模型,是因为,出于某种含糊且并无原则的感觉,我觉得大道是细长的,建筑工地是低矮敦实的,而帝国大厦应是高大耸立的.
但原则上讲,没有任何理由会妨碍我把这些元素进行置换.
请记住,我最初选择这种元素而不是另一种用于地图中,完全是因场合随机而定的.
假设我们俩都知道帝国大厦在哪儿,而且我清楚你知道怎样从那儿到达华盛顿广场的拱门,在这种情形下,我就可以向你演示我想展示的东西;通过把这两个地标性建筑用在地图中,我就可以指引你到一个你以前从未到过的地方.
这样我们就能体会到模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无论是科学模型,还是餐桌交谈中的临时模型,只有在共同知晓的语境中,它们才会发挥作用.
由此,我们看到,在某种意义上,模型完全是随意构建的;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们又完全不可以随意而为,因为它们反映的可能恰恰是我们称之为认识或交际困境的东西.
但模型无论如何不能随意构建,还有另一层更深远、更重要的意义.
一旦我们规定了在模型里帝国大厦和华盛顿广场的拱门在哪儿,建筑工地的位置就随之确定.
我们可以随意选择某种比例,但一旦选定,其他所有东西也都随之确定.
现在,我们就可以从模型中获得或传达新知识了.
一旦我们确立了模型与其模拟领域的映射关系,那么事情就不再受我们的掌控——重要的是,我们确立了它,出于我们的需求和兴趣.
因此,一个好的模型的确会抓住各元素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我们被迫去接受模型的推导结果.
在自然科学中,如果模型预测的事情在相关场合下没有实际发生,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模型在某个方面出了问题.
但即使是在这里,出于研究目的,修改模型是我们的本分,我们仍然要遵从模型逻辑力量的引导.
一旦我们确立了模型与世界间的同质联系,我们就要由模型来自行自为,由它来确定我们下一步该做什么.
总结:模型是我们要模拟的东西的替代,模型是我们用以思考的符号象征.
我们可以用一个好模型来作代表,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是吸引我们关注的那个事物.
·现在,回到我关于图画的主张:一幅画是一种特殊的模型,我们可以称之为视觉模型.
我们制作这种模型的唯一目的是显示一个场景的可见特征,事物的外观面貌.
一幅画能否如建筑模型一样,实际发挥模型的作用,模拟某个人或某件东西的外观,要取决于我们的兴趣和我们的关注.
例如,大多数照片非常小,若遇见真人,我们会觉得它所传达的关于这个人外表形象的信息在大小方面与其本人有着非常大的差距,而且,我们生活中零散杂陈的大多数照片其分辨率要远远低于我们的亲眼所见,它们遗漏了太多信息.
但是,通常我们不会错误地以为图画要在这些方面抓住它所描绘的事物特征.
就像我们不会以为建筑师要主张用轻木来建房子一样,我们也不会以为希拉里·克林顿就是那么小,皮肤那么完美.
我们要记住,正是因为照片有其特别的属性,我们才发觉它非常有用.
如果它有太高的分辨率,我们就不能廉价地买到刊登这图片的报纸.
而且就因为照片很小,假如我们想,我们就可以近距离地仔细观察研究它;而如果面对真人就无法做到,因为这是社会礼仪和习俗所不允许的.
我说这番话的意思是,我们需要杜绝一个错误的观点:图画起到描绘作用是通过影响我们,恰如我们会被它所描绘的东西影响一样.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所有的图画都可能成为一个我们所见东西的全规模的错觉,而实际并没有这样.
我并不是要说图画与其描绘的东西相似度必然任性随意,其相似程度不会比餐桌上的模型与它代指的城市之间的相似性更为随意.
这是有区别的.
餐桌模型所重建、复制的是一座城市里几个特定地标间的位置关系;而照片所复制、重建的,(比如说)是希拉里·克林顿的外表形象.
这里往往有人会说,模型可以显示事物的外观,是因为它代表的是与它所描绘事物的一种特殊的映射关系.
这说法可能对.
但重要的是,我们只是在想这种映射,我们看不到它.
它不是一种自然的投影,是我们创建了它.
还是如餐桌模型一样,这是因为在盐罐与帝国大厦之间、在硬币与建筑工地之间有一种映射关系,它是由模型的作用表现出来的.
·我们需要关照一下那酝酿已久的反对意见了,现在正好迎面相遇.
有人抗议道,图画的显著特征是,我们就是看见它们,看懂它们,认出它们;我们看到图画无需经过特殊训练,无需参与交际活动,更不用说参与制作和使用模型的活动.
你知道妈妈的模样,因此你能在照片中认出妈妈,至少是在照片够好的情况下;在照片里看见妈妈实际上只是你在行使看见妈妈的能力,就是如果妈妈站在你面前你也会行使的能力.
这解释了照片作为证据的特殊地位.
最著名的是,奥巴马总统曾拒绝公开海豹突击队拍摄的枪杀本·拉登的照片.
最初为什么要拍这张照片可能是为了确认被杀者的真实身份.
在此我们关心的是这个人这件事,而不是关注照片或模型或视觉表现.
因此,反对是这样的:你能看见照片里的东西就是因为你能看见,图画非常直观地传达它们的内容,既然如此,模型替代理论似乎是夸大了图画的智能性,让它们看上去像是在科学理论里的构建,弄懂它们还需要特别的成熟经验.
表述这一反驳还有一种方式:理解一个人所说的话你需要懂得这种语言,语言是理解的钥匙;而懂得一门语言需要学习、训练和背景等等;但图画不是这样,你不需学习观看照片就能看懂照片;没有一种隐含的语言你必须去学.
反对者会接着说,这一论断的证据是,即使孩子和某些动物也能认出照片上显示的东西.
猴子、鸽子和其他一些动物都被证明能对照片里呈现的内容表现敏感.
事实上,根据某些研究,当看见发情的雌性猴子的照片时,雄性猴子会表现出性欲唤起.
更有甚者,即便一个孩子在生命里的头几年从未见到过照片,他也能够自发地认出照片上的动物.
这么说,图画就是自然天成的了如果图画对于动物管用,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一直拒绝接受的关于绘画和视觉本身的光学理论闹了半天原来是正确的了毕竟,如果要看到图画里的东西,你只需给他呈现一幅画.
那么,图画在人身上产生的效果(神经上的,心理上的,视觉上的)正是图画里呈现的事物状态可能产生的效果,还有什么能比这一事实更好地解释这个结果呢·为了辩论起见,我们权且先接受经验主义的断言:孩子与动物能够自发地认出图画展示的东西.
(事实上,一会儿我们就会发现,这里也有辩论空间.
)请注意,首先,这一断言不足以确定孩子与动物对图画表现的敏感是以成人欣赏图画的独特方式,我要说,它是成人欣赏图画的独特方式也是决定性的方式.
我们已注意到,关于图画呈现有一件重要的事,用哲学家沃尔海姆(RichardWollheim)的观点来说,它是双重含义的.
要领会这一卓见,设想一下,图画通常不会骗过我们,这我们已论及过.
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我们看图画时,会真的以为呈现的事物就在面前.
重点是,我们清楚地知道画里见到的事物并不真的在眼前,且并不妨碍我们看画时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图画观赏的一个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可以让我们在视觉上欣赏到某些显然不在眼前的事.
看懂图画要求你懂得,它只是在视觉上让你看到某些不在场的东西.
被图画蒙骗意味着你是被双重蒙骗:首先你以为你在看一些你没看见的东西(无论它描绘的是什么),然后你不知道你看到的是一幅画,而实际你是在看一幅画.
动物和孩子不会像我们通常看图画一样:看见相册里祖母的照片,我们会无比赞叹;而中学毕业纪念册里的照片又让我们感慨万千.
动物和婴儿不可能有这种丰富的感觉,除非他们能够敏锐地感觉到照片这种特别的缺席情境再现的结构.
没有证据表明动物或孩子会以这种方式对照片表现敏感,能够看懂照片.
有些幼儿可能会被照片所骗,但这只能表明他们没有把照片当作照片.
要敏锐地感知这一结构的双重内容要求我们记住,一幅画/一张照片(我们眼前的这件人工制品)是我们用来展示或呈现的东西,其目的是为了展示某些事物的特征;这事物在画里,却不在(至少是不必在)我们眼前.
这就好比讽刺小品,要领会一个人的讽刺不仅仅要懂得他或她所说的话、话的含义.
在这一意义上,不仅仅要去领会说出来的话,更要去领会这人在用这些特别的话干什么(建议,暗示,隐喻,表达等);图画也是如此,要看懂一幅画需要领会呈现在你面前的是并不在场的东西.
有的幼儿在看见图画的时候会伸手去抓,就像要去抓里面的冰激凌,或是要去摸毛茸茸的小绵羊.
尽管这种行为承载了一定的理解和认知成熟度,但依然达不到生活中我们所熟悉的要看懂图画所需的那种理解,认识到这点非常重要.
实际上这是一种准图画的、幼儿式参与图画的方式.
我承认这是一种众所周知的由幼儿与动物展现出的理解.
我们可以将此概括为,对幼儿和猴子来说,唤起是对图画的唯一可能反应.
·但我的反对者并不气馁.
他们接着说,就算对于图画的成熟理解要求,以我所描述的这种方式,参与一种认识实践,利用图画来代替它们要描绘的东西.
但我们仍有权认为应该把对图画更原始的反应作为最根本的反应分离出来.
这里的重点是,在画里看见某件东西,就是与一种视觉表象的简单的视觉遭遇,这事似乎无需学习,无需依赖我极力主张的方式.
别着急.
是的,但是,简单起见,让我们设想一下雕像.
我们能认出杜莎夫人蜡像馆里的真人蜡像模型,是因为它们能在我们身上产生与其原型产生的同样的效果吗或许是这样,但是对这一结论的更好解释,是一个早已存在的、更为根本的事实:模型展现了与其原型相同的特征(他们非常相像).
之所以这样,并非因为它们会在我们身上产生感觉反应,而是因为他们被塑造、被描画、被仿制成它们原型的复本(就外表特征而言).
我们能认出蜡像是因为我们认识它的原型.
我们熟悉的二维图片也是一样.
与数学模型不同,千百年来图像模型的创建恰恰是利用了我们的技能——视觉的、认知的以及其他技能.
正如一台电脑的操作系统即便是大量技术革新的结果仍可以是方便用户的,图画也可以看上去直观易认,即便它是一种发达的模型工具.
图画是方便用户的,但这并不会使它比一个先进的操作系统更像是自然产物.
因此,如果我们发现它们方便用户,那么其他有着相似视觉系统的生物会有同样的感觉也就不足为奇了.
图画,像稻草人一样,会跨越物种产生效果,但这怎么都不会削弱它是技术产物的事实.
图画是为我们而作的,也是为像我们的生灵而作的.
重要的是,认出图画显示的东西是一回事,而能够体会画中事物的独特存在方式又是另一回事.
现在让我们回到先前的公式,努力把这些理顺:图画是用以显示的工具;那么,要理解一幅画,带着理解去看一幅画,就是要去理解它被用来传达什么.
我们再一次被迫回到这一观点:只有敏锐感知交流语境的人,这种理解才有可能.
验证我的提议的最后一道测试:如果我的观点正确,那么,通过模糊其自然背景,图画就可能被剥夺内容,可能会空洞无物,一无所现.
我们发现事实果然如此.
图画有它的修辞,就是说,它要讲述一个故事,而如果你不懂图画的修辞,你就看不懂图画所显示的东西.
我知道的最好例子来自于我的个人经验:我儿子——当时他大约只有6岁——认不出照片上的我,并非因为我被挡住了或是模糊了,恰恰是因为他大概看不懂这张照片要做什么.
照片里拍摄的是我的镜像,他看不懂当时是种什么情形,为什么要拍这样一张照片,照片的标题可能会是什么.
而这也解释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当照片被倒置,或一般来说,当视点出乎意料或不常见的时候,你很难认出照片上的人.
总结一下,图画/照片作为模型的概念可以解释为什么动物与幼儿可能认出照片里描绘的东西,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要清醒地认识图画所显示的东西——而不是把图画里的东西当作真实存在——要求对修辞和背景的敏感.
图画有它的修辞,但这从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我认为至少部分是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它被认为理所当然.
(就像我们把门把手的使用背景看作理所当然一样.
)在朋友家里的墙上看到一排排朋友家人的照片你不会感到困惑,就像在比如说宗教圣地看到一些神像的独特安排,你也会觉得顺理成章.
大致说来,我们懂得为什么要用这些照片来装饰墙面,它们是在表达骄傲与挚爱,展示家庭亲情,也是在对敬爱的人表达认可和纪念.
报纸、书籍和网站上密布的照片也是一样.
对于大多数照片,大多时候,我们自己就能毫不费力地给出说明.
当然,多数时候照片都带有说明文字,它们提供了找到照片焦点所需的语境.
·道格拉斯·戈登(DouglasGordon)与菲利浦·佩雷诺(PhilippeParreno)执导的电影《齐达内》(Zidane)中有一幕场景,这位足球明星在比赛中的行为让人不可能看懂.
并非因为它们很模糊或没对准焦点,而是因为电影制作人在努力地消除足球场上的运动的叙事流,而通常正是这种叙述,才让我们能够跟上场上形势的发展.
电视足球转播要精心策划画面,通常包括多达25台至30台摄像机位.
但戈登与佩雷诺,他们是艺术家,而不只是记录片导演,采取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方式.
他们用17台摄像机只对准齐达内个人,自始至终.
结果,尽管我们能看到这个人,却永远无法看清他在做什么.
我们看到他在场上的奔跑,却又因此被抽离了语境,这感觉就如同在看一张模糊的照片.
电影的副标题是《一幅21世纪的肖像》(A21stCenturyPortrait),这部电影所做的恰恰是在研究、质疑和重新思考,一幅肖像该是什么样子,会是什么样子,或者说,曾经是什么样子.
为实现这一目的,它剔除了修辞背景和语境,而只有依靠这些,传统的肖像才成为可能.
这一例证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为什么有些画,在某些场景下,根本不是真正的图画(或肖像),而是艺术作品.
第14章绘画策略图画呈现不是自行在我们大脑或心里发生的事情.
它需要我们积极地去获得,通过图画制作与图画使用.
图画是以此方式呈现的技术,这一观点有着重要的含义.
如果说图画是我们出于不同目的而使用的东西,那么,可以想见,对应我们使用它们的多种不同方式,就会有很多种性质不同的图画.
我们看到的确是这样.
我说过图画是一种特殊的模型,但我可能也同样说过模型是一种图画.
在某些语言中,用于图画的语汇不仅适用于2D图画,同样也适用于雕塑;建筑师设计的3D房子模型不必像希拉里的照片那样是一种视觉模型,那不是我们制作它的原因,也不是我们使用它的目的;建筑师的设计蓝图也是图画(我们称其为图纸),它们是该建筑的模型,但并不是为了展示它的外观.
这些都是图画,但不是视觉图画.
令人称奇的是中世纪的基督圣像画.
拜占庭基督徒崇拜圣像,但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相信,在圣像与它们所代表的神之间有一种奇妙的联系;而且他们也不太可能会认为,耶稣与玛利亚会真的像圣像所刻画的模样.
首先,圣像画并不写实,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很卡通,尽管他们无比虔诚;再者,不同的圣像画塑造的同一位神或圣徒会以全然不同的方式来呈现,至少在某些方面.
从视觉模型的意义上来看,拜占庭圣像画算不上是一幅画.
也就是说,它不能通过展示其视觉形象来起到代替真神的作用.
圣像不够相像,它不像法警画家的素描那样旨在表现相似;但在另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我猜17世纪的基督教徒也会这么说,圣像的确有一种神似.
我们可以确切地说明这种神似表现在什么地方:通常一眼看去,你就能认出这幅圣像代表的是谁.
圣像画中呈现的人物完全遵循一些可视标准,我们可以利用视觉辨认他们,因为我们知道传统中符合他们身份的视觉特征.
同样的方式,你能认出哪个人物是君王,即便国王并无一个统一的模样;而且同样,在国际象棋中,仅凭外观,你就能辨认哪颗棋子是骑士.
拜占庭圣像画便是以此方式来表现相像.
在这一意义上,它是一幅画,并非是一个人的视觉模型,而是一个人基本概念特征的体现.
如果愿意,你可以称之为一个概念人的可视表达.
用概念符号来代表一个人,这在我们的现代感性中也并不陌生,至少不完全陌生.
比如,唐·璜与其侍从莱波雷诺外表毫无相像之处,但在莫扎特的歌剧中,单凭调换服装就足以让唐璜的敌人——曾经的爱人——转而去追踪莱波雷诺.
从某种角度看,这在心理学上是极其荒谬的;但反过来,我们可以说,在歌剧的叙事体系内,与其说人们被当作是人不如说是被当作符号,他们体现的是一些基本的特征,服装就是其中的特征之一.
再回到基督圣像画.
以此方式并不足以完全体现圣像的意义.
对圣像画来说,重要的是图画要能够替代原型,由此,在现实和传统中,它才能被允许发挥这样的作用.
那么,在这一方面,圣像就像我称为视觉图画的东西一样:它们是一种特殊的替代.
但所不同的恰恰是掌管替代或使替代合理化的相关规则.
对视觉图画来说,我们之所以使用图画是因为我们相信它模拟了外表特征.
对圣像崇拜者来说,似乎有一种双重要求.
首先,图画应该遵循约定俗成的方式恰当地来表现耶稣或圣耶利米或其他任何人的品质特征;然后,圣像应是一个已然存在的合乎法度的圣像的复本,而照此方式,有长长一列许多的复本,其中每一个在宗教敬拜中都有作用.
而且,似乎这一系列的复本按要求都应该是来源于对圣徒本人的刻画.
但我们需要记住的是,最初这个画像的刻画重点不可能是像快照一样要去捕捉外貌形象,而是要像语言描述那样抓住其本质特征.
圣像受到敬拜是因为它们有效地参与到实践中代表了我们所敬拜的人,尽管事实上它可能长得与那个人并不"很像",它们仍然会受到敬拜.
拜占庭理论是有关图画的一个深奥理论.
在某种意义上,它比在光学和透视基础上进行再现的现代观念更加接近于展示本质特征的图画——它们是我们为了自己目的而制作的替代,正是因为在实际应用中的地位才获得了其重要意义.
它超越了现代观点恰恰是因为它能避开我们的根本错误:将图画心理化,只是把它当作在观看者心里(或视觉系统或大脑中)引发反应的刺激因素.
在拜占庭理论里,重要的不是图画对我们做了些什么,而是我们要用图画做什么.
(或者说,关于图画对我们的作用意味着什么,拜占庭理论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更清晰的解释.
)在现代肖像的基本绘画风格中,我们也能看到一种类似的差别.
例如,早期的现代肖像,如老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CranachtheElder)所画的著名的马丁·路德画像,因其木头面具一样的特征而令人瞩目.
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完美地抓住了外表特征,刻画了这人的面容,但似乎完全是以一种外在的方式.
他们就像模具,或者说,就像是面具画.
这个人得到了呈现,但这么说吧,不是内在的那个人,不是那个人自己.
在一幅马丁·路德的著名画像里,这位宗教领袖手持一本书对观众打开,仿佛是要让你看清书上的词语,由此让你对他的思想,以至他是怎样一种人获得某种认识.
这大概是一种巨大创新,一种新型的表现手法!
是因为克拉纳赫缺乏技能,不足以仅仅通过呈现这个人,以他的外表来展示他的感情与态度吗或许是吧.
但这里形成的观点会让我们得到一种完全不同的答案.
克拉纳赫画的不是这个人(theman),事实上,在这种意义上,这些根本不是这个人的画像.
相反,他们呈现的是这个人物(theperson).
而这个人物,根据悠久的思想传统,不是这个人;一个人物是这个人所扮演的角色,就如演员所扮演的角色(好比唐·璜被看作是穿斗篷的那个人).
神父、教士、神学家、新教创始人——这些是一个人可能扮演的角色.
在这一意义上,克拉纳赫的目的是这样一个人物,而不是这个人.
因此,这就好像是,他的目的是要刻画那个骑士,而不是某个站在棋盘上以这样那样的方式雕刻的木头棋子.
后来的画家表现了不同的兴趣:他们的兴趣不在一个个的人物,而在于芸芸众生;不在我们扮演的角色,而在于角色的扮演者.
无论伦勃朗[15](Rembrandt)相比克拉纳赫有多么伟大,使他的画像与众不同的并非是在写实程度上的差异;而是,从根本上来讲,使命的差异.
伦勃朗与克拉纳赫完成的是不同的使命,他们创作了不同种类的图画.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更概括地说说作为艺术的图画了,同时也来面对一个重要的对我整个研究项目的反对.
图画有许多不同种类.
本章我们已探讨了不同类型的肖像画,对比了作为视觉模型的图画与作为圣像的图画,还有图纸、素描、卡通、漫画,所有这些种类都是作为技术用于展示的图画.
而所有这些技术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拜了替代原则之赐.
我们把图画用作是它所描绘事物的代表——作为替身或代言.
图画之所以有这许多不同的种类,是因为许可或掌管替代的规则、实践、传统、兴趣各不相同.
我们出于不同的目的,在不同的场合(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以不同的方式来使用替身.
掌管把圣徒的圣像画当作圣徒的标准与掌管利用法警画家的素描来发现未知凶手模样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
是什么允许我们利用一幅画来代替其原型要取决于许多因素,这可能与我们的生活和文化一样的复杂和多元化.
这是人类学的东西.
我们都是图画经济中的行动者(agent);要理解我们生活中的图画,我们需要对这种经济进行深入研究.
作为艺术的绘画目的恰恰在此.
艺术家作画不仅仅是为了参与业已存在的图画经济,这种经济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产品目录的设计者旨在向你展示他要销售的大衣;圣像画作者从事的是一种例行的复制活动,目的是保证你能获得一件合乎法度的崇拜对象;摄像师记录运动场上的赛事.
而艺术家要做的决不是这些事情,那里面没有艺术.
艺术作品的出现恰恰是在这些遭到破坏之时;这种经济、这种作用、这种修辞、这种无形的习惯作法被颠覆之时.
这可能会有多种不同的方式.
或许,如当代艺术家拉扎里尼,其目的是要把你知觉和情绪上的习惯与价值展示出来;或许,如安迪·沃霍尔[16](AndyWarhol),展示的是肖像是什么,或名人是什么,或原创是什么这一观念;也可能,如约翰内斯·维米尔[17](JohannesVermeer),想要表现的是在一幅画中,可以展示出一个家庭的内部生活,也或许,虽说在记录,却是要掩饰这种生活;又或许,如大卫·霍克尼[18](DavidHockney),展示的正是艺术家喷涌而出的想要描画、涂抹的疯狂的冲动.
说到同时也是艺术作品的图画,只有一件事是明确的:一眼看去,你根本无法看懂.
艺术作品对于初次审视是隐形、不可见的.
它需要探询.
再次回到我们的口号:看你是否独具慧眼!
你若尝试,它会给你提供需要的资源.
我们来比较一下观看艺术家的画作与观看一则广告.
在后者,当你无需去问它要展示什么时,那它就是一幅成功的广告;而前者的成功则在于,你必须去问它要展示什么,或是疑惑它到底是否真的要向你展示什么.
当然,这种分界也会坍塌.
精明的广告人也可能会制作一张你根本看不懂的图画来抓住你的兴趣,以此让你对它展示的产品予以关注.
在第4章我们曾说过,艺术(二阶实践)的特点就是,它会轮转回来对它试图解读的(一阶)活动施展影响.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图画就是在组织我们的生活,它为我们构筑了一个交际的场景,在这里我们都是漫无目的的旅人;而绘画艺术家则是在给我们提供一种方法,让我们来发现这一根本的事实,有关我们本性的事实.
而这正是专属于哲学与艺术的研究形式.
重要提示: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我关心的是艺术本身要完成的使命,我不关心艺术家的自我解读.
或许19世纪伟大的德国画家阿道夫·门采尔[19](AdolphMenzel)想做的就是把他的主题好好地展示出来;或许他就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在制作图画的工作中,像一个优秀的广告人一样.
但毫无疑问的是,无论他还取得了其他什么成就,他的画作的确是起到了展示作用,比如工厂车间里的活动,战争场面等.
重点是,如果他的油画是艺术作品,它们就不仅仅是给你展示关于这个那个的简单图画.
而事实上,的确如此,在谈及他许多最有趣的画时,你几乎不可能明确地陈述他们到底给你展示了什么.
这是因为,真的,不等它们向你展示什么,或者还在向你展示的时候,你已不由得肃然起敬,在他还有什么是不可展示的呢.
历史学家、理论家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Fried)的评论令人折服,他说,门采尔,在其19世纪40年代的油画中,给我们的作品表面来看是在做一件事——向我们展示一个场景——但实际上却是在呈现别的东西——亲临现场会是什么感觉,栩栩如生,身临其境,充满探索.
它们给你呈现的不是在画里哪些东西可以被发现,而是,你若亲眼去看会是什么感觉.
在这一意义上,它们是对视野本身的描绘.
这些"图画"是对内在意识的研究,而不是对这个那个的记录.
它们是艺术作品.
第15章空气吉他风关于汉克·威廉姆斯(HankWilliams),批评家戴夫·希基(DaveHickey)写过一篇漂亮的文章"粉红凯迪拉克",书信体,是这位乡村乐传奇本人写给死后自己的信.
希基让我们对这位艺术家及其艺术有了鲜活的认识.
令人称奇的是他根本不讨论他的音乐——旋律、和音、音品、音色、歌词、音乐思想表达上的创新——所有这些统统不曾提及.
他关注的是汉克·威廉姆斯的生活,或者说是对那种生活的想象:毒品、性、消沉、一直在路途的生活.
流行音乐,我用这个词涵盖了诸多的音乐形式:摇滚、节奏布鲁斯、灵魂乐、嘻哈、热播榜前40、瑞格,但重要的是,爵士、乡村乐或百老汇音乐剧不包含在内.
关于流行音乐,有一个重要的事实:你可以很严肃地参与其中,同时又不能像欣赏音乐一样把它当作音乐来欣赏.
事实上,像欣赏音乐一样来欣赏流行乐几乎总是无法真正融入其中.
人们挤在爆满的体育场里决不是为了凝神谛听,像坐在音乐大厅里倾听传统音乐会那样.
问一下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Springsteen)、图帕克·夏库尔(TupacShakur)、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Presley)、珍珠果酱乐队(PearlJam)、滚石乐队(RollingStones)或是碧昂斯(Beyonce)的粉丝们,他们去看演唱会最难忘的体会是什么.
他们决不会谈及音乐,他们难忘的是那种兴奋、那种激动,舞台上的人,他或她的性感魅力,在现场亲眼目睹男神、女神的感受,人群的狂热,偶像与观众间的互动;他们还会兴致盎然地讲自己怎样舞动与尖叫,也可能会讲震耳欲聋的喧闹与缤纷炫目的灯光秀.
我差一点就摸到她了!
我听到了他拨吉他弦的声音!
他们历数都唱了哪些歌,唤起他们怎样的感觉,重要的是演唱会这件事.
它之所以难忘并非因为这是一次凝神谛听的机会,而是一种全然不同的体验.
正因如此,有人可能会贬低摇滚乐或流行乐,毕竟,它不是"严肃"的音乐.
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RogerScruton)经过对这些问题的充分思考,就曾有此番评论.
他注意到,粉丝将柯特·科本(KurtCobain)当作偶像,但在某种意义上,却根本不听他的音乐.
他还说,事实上,他的音乐中根本没多少东西值得仔细去听.
从斯克鲁顿的观点来看,涅乐队(Nirvana)是一种个人崇拜,而涅音乐会只不过是纵情狂欢与离世避尘的一个借口.
没有节奏,只有冲动;没有歌声,只有科本的嘶吼与重金属乐队单调的撞击.
在涅乐队以及摇滚乐的风靡中,斯克鲁顿看到的不仅是音乐的崩溃,还有更广泛的文化的坍缩.
你本期待听众会凝神谛听,音乐创作人会清晰地表达态度,结果看到的却是毫无节制地对当下满足的追求,降服于原始粗野的冲动.
我要说,斯克鲁顿错了,并非因为他低估了涅乐队的音乐意义,对此他的评价基本正确.
之所以说他正确,是因为涅乐队的确与音乐无关,它的核心是科本,或是科本通过他的歌表现出的个性.
涅乐队的音乐,至少在某种意义上,并不邀请,甚至说根本不值得去仔细聆听.
关于这点他是对的,要听懂它你无需专注于音乐,它的魅力乃在别处.
但斯克鲁顿没想到的是,这恰恰正是关键所在.
要批评涅乐队或任何其他流行乐在此方面的失败,就如同批判印象派画家不能以更清晰、更逼真的笔触来描画他们的主题.
这些画家的兴趣不在于此,涅——或者说娄·里德(LouReed)、大卫·鲍威(DavidBowie)、大卫·拜恩(DavidByrne)、杰斯(Jay-Z)、滚石、查克·贝里(ChuckBerry)等——也是如此,这些艺术家的魅力不在让你去凝神谛听.
要在流行音乐界留下印记,有一共同的特点:你无需具备一副"好嗓子",或精湛的技艺,或经过专业训练.
但因此以为流行乐易于演奏或要求不高那你就错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你一定会以为,经过"严格"训练或有"曼妙歌喉"的歌手会做得更好,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世上几乎任何一个歌手的声音都比鲍勃·迪伦(BobDylan)要好听,但有谁比鲍勃·迪伦更会唱歌演播室里随便找出一位乐手可能都比摇滚乐队的明星更会演奏,但我们对演播室乐手不感兴趣.
而当受过经典传统训练的乐手转而关注流行音乐时——比如,歌剧演员演唱西蒙和加芬克尔(SimonandGarfunkel)或披头士的歌,钢琴家弹奏尼尔·杨(NeilYoung)的乐曲——结果你知道的:往好处说,那不再是流行乐.
也就是说,它们失去了流行音乐的活力与味道,当你把流行乐的音乐提取出来,你也便失去了它的价值.
往坏里说,这种向流行乐界的贸然进军实际上是曲意逢迎,令人尴尬.
这些天才的音乐家们——如斯克鲁顿是一位经过传统训练的音乐家、作曲家,同时还是哲学家——他们不懂,这与音乐无关,它的魅力在别处.
那是什么呢·传说毕达哥拉斯曾在一块幕布后授课,这样,他的学生,人称幻听者,被迫只能关注他所讲的话而不去关注他.
这种"幻听原则"(只听不看)在近几个世纪形成了对音乐的态度,根据这一原则,音乐提供的是一个脱离了其创作者的音乐景象.
音乐家只被看作是一个遥远的起因,其音乐产物,即音乐及其形式、含义,才是真正的关注焦点.
正因为如此,交响乐队总是要坐在乐池中,远离观众视线.
录音技术更加助长了这种幻听热情.
当今时代,大多数人了解音乐并非通过观看现场演出,而是通过网上下载,现场直播,或打开收音机,或播放一张CD,听音乐就是去关注演奏者这一观念听起来似乎离奇且不真实.
人们通常认为录制音乐传达了音乐的本质,因为它剥离了要实现音乐所需的乐器.
这一观念在高保真音响发烧友那里得到最真实的反映,他们舒适地坐在自己起居室的沙发里,操控着各式音响设备,让它传出最佳的环绕立体声效果,闭上眼睛,音乐就在自己的脑海里鼓荡起来.
从这一观点来看,电声音乐——在电脑里生成的音乐,而不是弹拉、敲击、吹奏乐器或呼号歌唱出来的音乐——才是最真正的音乐表达.
音乐是听觉的,或说是幻听的;也就是说,这才是我在此使用的这一词汇的含义,这是音乐.
音乐创作就是在声音领域里的建筑创作,音乐欣赏就是在这些非人格化的建筑里畅游.
但是,还有一种不同的音乐原则,事实上,它在我们的文化中具有很大影响力.
尽管这从未被明确地表达出来,但它充满活力,非常重要.
它没有名字.
根据这一不同的音乐原则,艺术家不是音乐的载体;相反,音乐是艺术家的载体:由此一来,音乐,成了艺术家展示自己的一种工具.
这正是流行音乐的精髓.
你无需具备精湛的技艺也能成为一名流行音乐手,你需要的是个性.
如果你热爱流行乐,你真正热爱的实际并非它的音乐;你爱的是那个人,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个歌星.
娄·里德、鲍勃·迪伦、大卫·鲍威、约翰·列侬——当你喜欢他们的音乐时,他们才是你着迷的对象.
因为他们的音乐,他们的艺术就是要把他们,或者说是他们自己的思想呈现出来.
流行乐就是表演,就是展示.
当然,它是音乐,但实际上它是一道景观,是让你用眼睛观看才能获得的东西.
与其说你想听流行音乐,不如说想亲眼目睹.
你并非是在欣赏表演,而是自己参与其中,与之共舞;你是团队的一部分,是粉丝团的一员.
我们已经注意到,从幻听原则的立场来看,流行乐看似很垃圾;从音乐角度来说,它主题简单,不够成熟,陈词滥调,过于简化.
以鲍勃·迪伦为例,他的歌很传统,唱的全是民谣、布鲁斯的老调调;他嗓音沙哑.
再看滚石乐队,即便是在他们表现最好的时候,他们还是拖沓懒散,杂乱无章,隐隐约约好像总不在调上,也不同步.
但是,无可否认,鲍勃·迪伦与滚石都是艺术家,他们的成就熠熠生辉.
他们魅力四射,令人着迷,风格独特,难以模仿.
但从音乐的角度——和音、节奏、旋律、结构——来看,他们的作品却非常简单.
这是怎么回事在此,音乐无足轻重.
因为在相关意义上,这不是音乐艺术.
对比一下近当代艺术史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这一观点.
视觉艺术,其根源在于工艺实践——设想一下塞尚、马蒂斯、毕加索——从这一角度来看,许多当代艺术家如索尔·勒维特(SolLeWitt)、布鲁斯·瑙曼(BruceNauman)、珍妮·霍尔泽(JennyHolzer)、芭芭拉·克鲁格(BarbaraKruger)、克里斯·伯顿(ChrisBurden)的作品看上去似乎根本没有艺术可言.
不仅看不出高超的技法,精湛的画艺,而且缺乏抒情的诗意或清晰的表达与美感.
如果他们是艺术家——我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是艺术家——那么他们一定有着不同的方式.
他们似乎与居斯塔夫·库尔贝[20](CustavCourbet)与伦勃朗一样是视觉艺术家,但他们实际却不是.
流行音乐也是这样,它看上去像是音乐,但它不是.
谈到艺术,我们需要问的问题是:这件艺术作品有何含义或问:它的成就在哪说起像勒维特这样的艺术家,他的艺术并不在某个具体的手势,或手,或表情,或某个物品中,它最终是在某种类似概念的东西中.
而说到流行音乐艺术家如米克·贾格尔(MickJagger)、基思·理查兹(KeithRichards)、杰斯或大卫·拜恩,他们的成就不在音乐,而是在别的什么方面.
流行音乐的目标不在音乐.
艺术家本人形象突出,要求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转向他,音乐充其量不过是他把注意力引向他的一种方式,是他抓住了你的注意力,是他抢占了你的迷恋.
他的音乐就像他的语言,你透过音乐看到这个人,或看到这个人的艺术形象.
当我们欣赏流行音乐时,吸引我们兴趣的并非声音,而是表演与个性.
或者,换种说法:当涉及流行音乐时,艺术家站在我们与音乐之间,而他是有意为之.
这一基本事实——流行音乐关乎的是某个人或某个乐队,而非关乎音乐——具有启示意义.
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就能明白,流行音乐成为粉丝音乐和个人崇拜绝非偶然;而且,现在难以想象流行音乐怎能离得开音乐录像.
流行音乐的艺术恰恰在于它对风格、态度、姿态与政治的关注.
流行歌星是性感的象征,我们热爱他们,想在某种程度上像他们一样,或至少能够与他们在一起,拥有他们,跟他们物以类聚.
流行音乐总是分为各个流派,也正因如此,它总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各个时代不同.
流行音乐直接关乎识别与认同,关乎我们为什么想要认同一些新事物或不同的事物,或认同一些再次焕发生机的旧事物,或是一些历久弥新的新事物.
空气吉他是流行音乐鉴赏最真实的表达.
当我们演奏空气吉他时,我们模仿的不是音乐,我们模仿的是乐手.
我们把自己当作那个乐手,模仿他的演奏——我们认同的是表演而不是创作.
流行乐的核心总是关乎演奏者.
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流行音乐总是与时代密切相联,而且往往让我们产生怀旧情绪,这是音乐(另一种幻听意义上的音乐)所不具备的特征.
听到一首流行歌的曲调可以把你带回到某个夏天、某个夜晚或某种情绪,而听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或即便会,那也与音乐本身的意义无关.
这是因为,一首流行歌,而非音乐作品,恰恰是在风格空间的定位,这种风格要反映当时明显的时代与文化特征.
要领会一首歌,就意味着要领会它在那一空间的位置,能够识别它或在想象中唱起它.
即使是最好、最持久的流行音乐也终有它的时效性.
这不仅意味着你能看出它的时代,还表示流行音乐会直接表达那个时代和地域所特有的声音、风貌和态度.
而这些都是以极其微妙的方式进行着.
当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犹太小子罗伯特·齐默尔曼(RobertZimmerman)将名字改为鲍勃·迪伦并吸纳了传统美国民谣的音乐特征时,他做出的绝不仅仅是几个挤眉弄眼和点头肯定,对自己、对音乐、对文化,他的文化的肯定,也许还有更多.
把传统形式当作他个人的、当代的、非传统的叙事方式的载体,迪伦把你的注意力从纯音乐上引开,而迫使你去思考他究竟是在做什么.
这是一个典型的艺术时刻.
但此刻,音乐退居幕后,他的态度、姿态、身份与公众形象被凸现出来.
滚石乐队从事的是一种非常相似的文化与个人表演,因为他们完全采纳布鲁斯的声音与风格,同时吸收灵魂乐、节奏布鲁斯、后期的迪斯科以及美国黑人创造的其他音乐形式.
和鲍勃·迪伦一样,滚石乐队并非不正统,"正统"一词在此根本不适用.
怎么才算正统,这个问题成了他们的主题,这主题既包括音乐问题,也包括性及诸如饮酒、毒品等其他问题.
但这并不新鲜.
这种身份表演,带着叛逆、矛盾、欲望与拒绝的层层包装,已经在一些黑人艺术家身上有所表现,是他们给了滚石灵感.
罗伯特·约翰逊(RobertJohnson),著名的"三角洲布鲁斯之王",去世时年仅27岁.
他绝不仅仅是三角洲布鲁斯之王,尽管他来自密西西比河三角洲.
如果你听过罗伯特·约翰逊仅存的录音,你会听到一个人在用无瑕的技艺演奏一整套风格完全不同的布鲁斯.
在《魔鬼带走了我的女人》(DevilGotMyWoman)中,是密西西比本托尼亚在哀诉;而其他的歌曲有直率的克拉克斯代尔密西西比风,也有佛罗里达风,德克萨斯风,弗吉尼亚风,各种各样的布鲁斯风格,还有更为城镇化的音乐.
约翰逊出现在点唱机时代,因此他的音乐经验不会只局限于一种单一的当地风格.
他玩的就是风格,将所有种类融会贯通,然后又将它们通通表现出来.
更为重要的是,位于核心的正是他自己,或是关于他自己的传说——在十字路口与魔鬼交易,卖掉自己的灵魂以换取天赋.
听约翰逊的音乐,就是在听他自己.
听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Hendrix)与柯特·科本的音乐也是这样的感觉,另外这两位天才艺术家也是27岁英年早逝.
或许只有黑人才具备天赋的才能演奏布鲁斯.
更荒诞的是,关于罗伯特·约翰逊的十字路口传奇还真有那么点道理.
尽管一些专业音乐家对此说法不屑一顾,但在这领域,要说一点都感觉不到种族主义的意味还真不容易.
这些音乐家想要维护约翰逊的名誉,且是在音乐基础上,但这种顾虑似乎有点走偏.
并非是要否认他在音乐上的独特贡献,约翰逊给人的感觉好像不只有一只吉他在演奏.
但即便是对他精湛技艺的赞颂,听起来也像是对他个人的颂扬,而非对音乐的肯定.
"他简直出神入化!
三角洲布鲁斯之王!
"我要说的是,约翰逊是一个创作大师,他创作的是他自己,也是一个天才的操控师,先存的民谣风格于他可谓驾轻就熟.
约翰逊是一个流行音乐家,你不能演奏他的音乐,或者说,即便你能,也只不过是对他演奏方式的历史纪念.
同样的话你无法用来评说贝多芬,一场精彩的贝多芬演出绝不仅仅是历史纪念.
罗伯特·约翰逊的演出则是现场报道,是绝唱,个性突出、与众不同、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与无可替代的个人风格.
这一特征能帮我们更好地理解流行音乐界的独特现象,即翻唱(cover).
交响乐团演奏贝多芬音乐时不是翻唱翻奏,它演奏的总是音乐,与人无关.
布鲁斯和民谣也是这样,当杰克·欧文斯(JackOwens)演奏斯基普·詹姆斯(SkipJames)时,他在演奏他们共同的音乐,他在进行传承,主导的是音乐,而非个性.
因此,当滚石乐队演奏《成熟男孩》(MannishBoy)时,他们并非在翻唱穆迪·沃特斯(MuddyWaters),尽管他们向他的歌曲创作致敬.
但是,当帕蒂·史密斯(PattiSmith)演奏鲍勃·迪伦《信仰的转变》(ChangingoftheGuards),或心跳乐队(Heart)演奏《通向天国的台阶》(StairwaytoHeaven),或大卫·鲍威演唱妖精乐队(Pixies)的《仙人掌》(Cactus)时,他们分别是在向迪伦、齐柏林飞船(LedZeppelin)与妖精乐队致敬,是帕蒂·史密斯、心跳乐队、大卫·鲍威对另外这些明星,这些共同的文化里程碑的理解与诠释.
但是,当爵士钢琴家布拉德·梅尔道(BradMeildau)演奏电台司令(Radiohead)的乐曲时绝对不是这样.
梅尔道针对的是音乐,电台司令是透明的.
事实上,这是电台司令乐队一个令人瞩目的事实,他们占据了一种介于中间的位置:它属于流行乐界,但同时又将自己一直隐藏在音乐后面,创作出的作品犹如经典音乐一样吸引人关注与赞叹,令人着迷.
介于两者之间的还有另外几例情形:当辛妮·欧康纳(SineadO'Conner)演唱《无人可以取代你》(NothingComparestoU)时,往往让人忘记她是在翻唱王子乐队(Prince);X一代(GenerationX)演唱约翰·列侬(JohnLennon)时也是这样.
但这些的确是翻唱,也就是说,他们抽取模仿的并非是原来的歌曲,而是抽取了原作艺术家的态度、理解、无拘无束和朋克精神.
·在此,我提出的观点是,流行乐从根本上来讲不是音乐,它是一种展示艺术.
尤其是,我们已经开始体会到,流行音乐是个人风格的艺术.
让我来解释一下.
每个人所做的事情都带有他或她独特风格的印记.
从作品上你就能辨认一位艺术家,通过签名你就能认出一个人.
一个人如此,一个族群、甚至是一个时代也是如此.
一个人稍具知识就能在看到一幅画时说出它是什么时候、在哪里画的,即便对是谁画的他并不确定,或并无直接或具体的知识.
风格使得模仿成为可能——它给你可以模仿的东西——但也让伪作成为可能.
因为,我们制作的所有东西都会折射出我们的制作方式,这是我们学来的方式,像学着穿衣打扮,学着走路、说话一样学来的方式;同样,我们观察事物的方式也会体现我们对风格的敏感.
几乎所有东西都会体现在服饰和时尚领域.
正因为如此,若一个人穿着另一时代的服装,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来.
但正如风格可以被直接感知,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它同时也会限制我们,限制我们所能看到的东西.
要辨别赝品很难,并非因为赝品与原作没有区别,而是因为赝品伪造出来就是要对应当下对原作的认识,它与时代密不可分.
结果就是,赝品的寿命短暂.
艺术评论家彼得·施杰尔达(PeterSchjeldahl)说,它们是最好的限时趁热供应.
它们为我们而造,为现在而造.
通常赝品造出来后20年左右就能被明显地辨认出这是赝品.
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再把我们与伪造者都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看作是理所当然,因此伪造者自己时代的明显的风尚标志就跃然而出,一目了然了.
看一下《虎豹小霸王》(ButchCassidyandtheSundanceKid).
1969年当它上映的时候,还是西部片时代,如今再看你不可能注意不到具有20世纪60年代风格的服饰、发型甚至语言.
有趣的是,当你看约翰·福特(JohnFord)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西部片(如《关山飞渡》)时,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这并非因为它们拍得更好,我猜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区别,是因为当我们想到大西部时,福特的西部片是我们眼里的原创.
在我们眼里,这才是正宗的、原汁原味的西部片,好像带我们穿越回到那个年代.
再远点,回到巴斯特·基顿(BusterKeaton),同样伟大的电影,又一次,你立马就能惊讶地发现发型不对.
再看另一类例子,重温雷德利·斯科特(RidleyScott)的代表作《银翼杀手》(BladeRunner).
故事设定在一个不确定的遥远的未来,电影明显的科幻特征令人惊叹.
但现在再看,我们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注意到20世纪70年代的发式与服装样式.
这在电影拍摄时是根本注意不到的(假使当时不是这个样子,那感觉就会异常突兀,所有的注意力都会被吸引到它们身上).
离开风格,你将一无所见.
风格成就了我们的观看点,但也妨碍我们观看.
这种效应在很多层面发挥作用.
因为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能折射出风格,而这种风格又总是与其他风格形成对比,这就让人感觉,我们的生活可以一代代地对比,由此形成历史,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我并不是说只有风格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才有历史,我的意思是,更深入地讲,我们的历史值得我们关注,值得我们质疑.
每一种新的风格都是对以往风格的明显的补充,或抽样,或引用.
你对最新潮的穿衣风格感兴趣,意味着你能敏感地发觉它与上一季有何变化.
但有时,我们对风格的这种顺利认识往往也会中断.
也许你能认出20世纪80年代的风尚,或是20世纪70年代、60年代甚至50年代的风尚,但有时,除非你是专家,所有这些统统模糊为"老派过时的".
对一个孩子来说,他无法辨认莎士比亚时期的服饰与18世纪有何差别,它们看上去都很古老.
但有时我们对近在手边的时尚敏感度也会失灵.
你能分出21世纪最初10年与20世纪90年代的风尚有何差别吗或者与我们当下这10年的风尚差别之所以岔开话题聊了这么久的风格,是因为首先我想指出,艺术总是关注风格.
画家(比如说)会彼此借用、复制、抽样或彼此促进创新,因此,在这一意义上,风格——一条线的画法,在我们了解一条线以前所有画法的背景下,怎样去理解它——正是艺术家研究的主题.
但我还想提出,流行音乐是一种更直接的风格的艺术.
画家研究风格,我们可以说,是以绘画语言表达出的风格;音乐家——幻听音乐家——也研究风格,是在歌曲与旋律以及此类领域内的风格;相比而言,流行音乐家,关注的并非音乐的独特风格,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时尚,作为个人标志,同时也作为一个群体和时代标志的风格.
我们可以说,流行音乐是时尚的艺术,而如果时尚——我指服装设计等——本身就是艺术,那么我想我们可以说,流行音乐就是时尚艺术的一种形式.
因此,如果你想理解汉克·威廉姆斯的音乐,如果你想歌颂赞美它,你不应当关注他的音乐,而应当把注意力转向他本人,以及他通过音乐传递给这世界的个性.
流行音乐是纯粹个人风格的艺术.
当然每一种艺术形式都要面对风格的问题.
绘画、雕塑、装饰艺术、表演艺术,它们都有自己在风格空间里的定位:其他人做了什么,人们的期待是什么,哪些是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有品位的东西,它们要对所有这些做出回应.
艺术玩的就是风格.
但流行音乐以更直接的方式关注个人风格.
这就是为什么当谈及流行音乐的时候,音乐是有政治倾向的.
我们根据音乐把他们分为不同的派别:嬉皮,朋克,乔克,摩登派,摇滚派,黑人音乐,白人音乐等等.
这些划分非常重要.
·位于本书论点核心的是两个层阶,围绕这两个层阶会帮助我们厘清现在的话题.
流行音乐把我们习惯性的生活组织方式当作一阶素材,这些习惯有着独特的风格表现:你选择什么发型,你怎样走路,你使用哪些俚语,你选用什么样的音乐跳舞,哪些东西让你觉得很酷(或很烂或管它是什么感觉).
因为风格是我们感知和认识生活一个永久性和决定性的因素,所以,流行音乐对风格的关注不应当被看作是肤浅的或陈腐的.
事实上,在人(person)的概念与风格(style)的概念之间有一种紧密的联系,如果注意到这点,流行音乐的独特意义就凸现出来了.
在其最初的语源学意义上,一个人物就是一张面具或脸谱,由此"人"这一词获得了"角色"的含义,犹如一个演员在戏剧中画上脸谱或戴上面具饰演一个角色,一个人物的脸就是一张脸谱,而这个人物,实际上就是一个角色,而不是扮演这个角色的人.
这一概念还牵涉了其他一些重要的概念.
首先,约翰·洛克(JohnLocke)说,人是一个"法庭"概念.
他的意思是,一个人在其基本概念上,是责任的承担者,是演员,是当得赞扬与责备的人.
洛克的基本含义是,一个人物不是生物意义上的动物——男人或女人——而是一个行动者.
正如人物是作为角色而不是扮演者的概念一样,由此,我们得到了关于人格(personhood)的概念:它是社会的,被表现的,被承担的;重要的是,他是被定义的,要与赞美、责备、评价联系在一起.
因此,人是公民,是父亲和母亲,是老板与员工,是棒球手和哲学家.
他们属于这类东西.
也就是说,好也罢,赖也罢;成功也罢,失败也罢;这都是我们在社会生活中要扮演的角色.
我们是人,总是要且不言而喻地要服从我们群体的标准.
上面我说了,人格是表现出来的.
这让我想到第二个相关概念:表现(performance).
在一种意义上,"表现(perform)"只是一个最普通的行为动词.
在我们的生活历程中,我们要进行各种动作,表现各种行为.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分出哪些事我们只是在做,而哪些行为我们在做却是在表现.
很难讲清这种分别有什么原则,但它与一个事实有关:当我们表现的时候,与单纯的行为不同,我们总是要考虑别人的评价、标准、规则或规范.
我们会说到床上表现,工作表现,运动表现,在学校里的表现,当然也有舞台上的表现.
无论你是否是其他人的评价目标——可能你是在自己的房间里练倒立或只是作画给自己看——你仍然是在表现,因为你所做的很可能会受到别人的评价,即便并未真的被评价.
重要的是,这也正是我们的实际体验.
当你独自一人的时候,很少意味着你是真正地独自一人,因为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几乎都是由我们扮演的角色以及我们要遵从的标准构成的.
你能想出任何例外吗转向艺术,现在我们能够领会,为什么所有艺术最为根本的恰恰是这种表现(或表演).
表演艺术家把关于我们生活的这些事实当作他自己要表现的原始素材.
从本质上讲,我们都是表演者.
这不是我们的选择,也不是生物本性,而是一种无可逃避的作为人的状态.
表演艺术家把自己置于舞台上,他在说,"请看我在做我所做的.
"与此同时,他一直都知道你在看着他的表现.
如果我的观点正确,那么流行音乐就是表演艺术的一个属种.
我已经说过,它孜孜以求的核心表现就是独特的个人风格.
这也解释了流行音乐的持久魅力,尽管它看似关注的都是些琐碎小事,而且相对来说,在音乐思想上缺乏创意与高超的技艺,但其魅力依然经久不衰.
·现在,我提出的这一观点——流行音乐是个人风格的艺术;在流行音乐里,音乐只是一个载体,使它以一种不同的媒介,风格的媒介来实现自己的意图——面临着一个严肃的,甚至令人生畏的异议.
当然,无论我们怎么说流行音乐,说它是风格也好,时尚也好,或个性或展示也好,问题的实质是,流行音乐,简单地说,就是一种音乐.
若说我们在欣赏鲍威的《太空怪人》(SpaceOddity),乔治·哈里森(GeorgeHarrison)的《当我的吉他轻柔地哭泣》(WhileMyGuitarGentlyWeeps),以及奥蒂斯·雷丁(OtisReddings)的《试着温柔一点》(TryaLittleTenderness)时,我们爱听这些歌,却说我们热爱的并非它的音乐品质,这是多么的荒谬可笑.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面对的异议.
我从两个方面做出解释.
首先,我不想否认流行音乐是一种音乐,就像我不想否认巴内特·纽曼、艾尔·赫尔德(AlHeld)、艾德·莱因哈特(AdReinhardt)以及安迪·沃霍尔是视觉艺术家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传统的视觉艺术,即绘画主要关注的是描绘——这种说法并不矛盾,但好在它只用来代表从15世纪初至19世纪末所有绘画的主要关注——那么,显然,后期这些画家与他们的先人所做的完全不同.
流行音乐就有点类似这个,它使用音乐的语言与观念,就如纽曼与伦勃朗一样,都是使用油彩在画布上作画,但纽曼画出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效果.
纽曼的油画不是画,或者说,它们只是微弱意义上的绘画.
披头士乐队的歌,那些大师的歌,都是优秀的作品,但是他们的伟大之处在于别的方面,现在我可以这样说,他们的伟大在于他们的社会意义.
然后,我们早先注意到,流行乐研究的是我所说的一阶的素材,不仅包括广义的风格,还包括在歌舞中表现出来的风格.
这恰恰将我们安置于这个生机勃勃的魔圈之中,而这正是解读艺术在我们生活中地位的关键.
流行音乐艺术家把歌舞组织我们生活的方式——风格——放在了第一位.
我们唱歌庆祝,我们唱歌交际,我们唱歌摇动孩子睡觉.
流行音乐家将这些展示出来.
对我们歌舞的这种呈现改变了我们唱歌与跳舞的方式,因此也为艺术表演提供了新的素材.
这种创生循环从未停止,如此,历经时日,就形成了一种高度成熟、充满智慧的音乐实践.
但关键是,我坚持认为,流行音乐上升为,或有时能够上升为艺术,并非因为它是对独特的音乐思想或问题的探索;而是因为,正如我一直坚称的,流行音乐把我们自己,风格化的自己呈现了出来.
第16章音乐之声第15章我讲到,当我们在听拉威尔、普罗科菲耶夫(SergeiProkofiev)、巴赫(JohannSebastianBach)、查理·帕克(CharlieParker)、比尔·伊文思(BillEvans)或是查尔斯·明格斯这些艺术家的音乐时,我们的兴趣不在个人.
我们不会去关注他们,或他们的思想、感受或愿望,就像我们在阅读数学家或物理学家的著作时,我们也不会去关心他们的个性一样.
我们的核心关注是这些人的作品,而不是这些人.
表演是音乐作品的工具.
研究巴赫的私生活或关心他是否吸毒对于了解巴赫的音乐没有任何帮助.
但我们在谈论流行音乐时,情况却有所不同,这在前面我们就已讲过.
在这里,恰当的理解是,音乐实际只是别的东西的载体.
音乐是对一个人物的呈现或塑造.
正因如此,摇滚明星才会有粉丝,也正是如此,粉丝不仅仅崇拜音乐家的艺术魅力,还渴望能像他们一样;想与他们一起狂欢,甚至想与他们交欢.
鲍勃·迪伦、滚石乐队、披头士乐队、尼尔·杨、性手枪乐队、杰斯、大卫·鲍威、图帕克·夏库尔、坎耶·维斯特(KanyeWest)、艾瑞莎·弗兰克林(ArethaFranklin)、麦当娜、碧昂斯,等等,我们对这些艺术家的兴趣是对他们的兴趣,音乐是他们为我们表演的直接方式.
古典音乐家是用表演来呈现自己的音乐,而流行音乐家呈现的则是他们自己.
谈及"严肃"音乐,我们关注的是音乐,而非艺术家.
关于幻听概念的音乐,如果这就是全部,那么至此我们就可完事大吉了.
但是,我们已经注意到,幻听概念远不止于此.
在音乐里,重要的是声音领域里的构造,正是这一观念与生成音乐的人类活动具有最多的因果依赖关系.
音乐,如斯克鲁顿所说,是纯声音的艺术.
事实上,单纯的声音——相对于有意义的声音,比如语言——为什么会令人着迷、引人入胜而且对人们有着重要的意义,怎样去理解这一现象是哲学家彼得·基维(PeterKivy)所称的音乐哲学的主要问题.
神经学家奥利弗·萨克斯(OliverSacks)表达的也正是这一问题,他说:"看到整个物种——千千万万的人们在演奏、谛听一些毫无意义的声调模式,大把的时间都在投入地如痴如醉地欣赏他们称之为'音乐'的东西,这是多么奇怪的一件事情!
"音乐只是缺乏意义的声音,对许多人来说,这一观点让他们理直气壮地把音乐当作,从根本上来讲,大脑里的"构建".
萨克斯说道:"我们人类……感知到声调、音色、音高、音程、婉转的旋律、和音以及节奏(或许是最为基本的),在脑海中我们利用大脑的许多不同区域将这些合成并'构筑'为音乐.
"由此观点来看,音乐是主观的、内心的、神经学的东西,原因很简单,因为声音就是这样.
这是他们的共识,比如,神经科学家丹尼尔·列维廷(DanielLevitin)在引导我们阅读下面这段言辞时,根本没有提供任何论据支持.
"音高"这一词语指的是我们大脑机制对一个基本声音频率的心理呈现.
也就是说,音高是一种纯粹的心理现象,它与空气分子的振动频率相关.
所谓心理现象,我的意思是说,它完全在我们的头脑中,而不是在外面的客观世界里;它是一系列大脑活动的终极产物,这些大脑活动生成的是一个完全主观的、内在的、有关品质的心理呈现.
声波——不同频率的空气分子的振动——自身没有音高.
我们可以测到它的运动与振幅,但是我们称之为音高的这种内在品质需要由我们人脑(或动物大脑)来构建.
但是,我们应该像这样把声音当作是主观的、内在的吗而且,音乐与声音究竟有何关系可能你会说,答案显而易见啊.
音乐就是声音,或者说,它是有组织的声音,组合在一起值得我们去听的声音;音乐家就是艺术家,声音是音乐家工作的基本素材.
在这种场景下,我们自然地会把音乐与语言相比较.
语言也是用于听的有组织的声音.
与音乐一样,说话就是发出声音,由此来交流我们的思想、感受、观点和意图.
但也有区别.
若有来自太空的外星人,他们很快会发现语言是有代码的信息.
只要时间足够,运气够好,他们就能够破解这些代码.
但是音乐,他们不得不承认,却不受这些代码的管辖.
可以说它们也是有组织的声音,但组织方式有所不同,而且结果也与语言不同.
外星人最终会把语言归结为智慧的产物,而音乐却似乎没有内容,它只是单纯的声音.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很难接受音乐只是声音这一结论.
音乐可能不会指代问题、不会描写,但它的短句和手势,是的,它们确如短句与手势一样,让人看起来它们是有结构、有意义、有内在联系的.
旋律与我们迎面相遇,它的确定性、它的给定性、它的坚实存在都是可感知的,至少在我们的体验中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我们很难挑战这一论题:音乐是声音.
而且,既然它没有信息代码,既然它的元素并不指代世界本身,那么音乐,就只是声音.
如此,我们又被抛回了原来的问题:这种奇特的声音,我们人类称之为音乐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进入神经科学.
我们早已注意到,某些神经科学家说道,在音乐里,我们认为很突出的一些品质——音高、旋律、和声、节奏、共鸣——在客观上并不真实存在,它们是主观的,它们只在大脑中.
它们不会对任何确定的物理刺激做出反应.
他们认为,要理解这些品质,你需要研究物理刺激给神经系统带来的反应,由此在我们的大脑产生这些品质.
从这一观点来看,音乐就是内在的、心理的;它与我们的神经及生理有关.
我们能够感受到音乐之声里的统一或连贯并不稀奇.
因为我们就是被如此构造的.
而且,实际上,外星人类学家无法听懂音乐的意义、组织结构也不稀奇.
因为他们不能像我们一样制作音乐.
若要像我们一样欣赏音乐,就必须得有跟我们一样的构造.
但在此,让我们暂停一下.
且放下音乐与声音密不可分的独特关系,我们先来看另一个观点.
显然,我们需要音乐.
当我们创作音乐时,我们要随时关注着音乐的效果.
即便我们不喜欢一首乐曲,根本不想费心去听它,但当它被演奏时,我们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听到它.
作为声音,音乐可以捕捉到我们,让我们成为俘虏.
但是,我们能听且要去听音乐,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音乐只是声音.
设想一下:我们用眼睛研究绘画.
绘画,从其本质上来讲,似乎与视觉有关.
但要说一幅画只是一种视觉刺激就是错误的;这么说吧,视觉艺术决不仅仅是视觉现象.
你可能会有异议,认为这正是音乐与绘画最重要的区别.
画家制作东西,我们表现出对它们的关注——我们观赏它,我们将它挂着,甚至买卖它们.
当我们思考它们的样子时,我们关注的总是它们独特的、物质的、来自真实物质的构成.
绘画作品是物质材料,它们的物质性历历在目,而音乐不是.
事实上我们恰恰可以以此来比喻音乐.
当我们听音乐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演员的演奏,他们不是在发出声音,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场景中一起演奏乐器,或者我们欣赏的是音乐录音是由真人,由艺术家和工程师创作的音乐录音.
说一首乐曲只是一堆声音,就如同说绘画只是视觉印象一样荒谬.
音乐,与绘画一样,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声音或者是画的外观,我们还要看、要听、要关注作品的内容.
绘画作品不仅仅是色彩或形状,音乐作品也不仅仅是声音.
有人把音乐还原为声音,而把声音说成是主观的.
对此,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
正如我们在前面(第8章和第10章)讨论过的,神经科学坚持体验的激发观念,神经科学对于艺术的研究往往是把艺术作品当作是对某些体验的明确激发.
无论一幅油画是什么,绘画所激发的审美体验都绝对是,实际上从根本上来讲,是视觉的.
音乐和声音也是这样,无论它会引发什么,音乐都只活在我们的心里.
因为声音在我们心里,而非在我们周围的世界里;又或者,假设它们是在我们的周围世界中——如果我们说声音是对媒介的干扰——那么,它绝对不是吸引我们兴趣的东西.
我们关心的是在我们脑海里的歌声,而绝对不是空气中的声波样式.
声音、色彩以及其他一些性质,比如热量给人的感觉,哲学家称之为"第二特性"(secondaryqualities),其本质在感觉哲学里是最有争议、最有趣的问题.
尽管自伽利略以后的思想家都倾向于宣称,你所见到的色彩效果实际是在你的心里,并不真的在你以为看到它们的地方,但对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质疑.
我的个人观点是,色彩与声音都是生态属性(ecologicalproperties).
它们以复杂的方式依赖物质和事件的本性以及它们与环境条件的互相作用.
人类对这种互动的敏感要取决于我们的构造,肯定地说要取决于我们的神经系统.
但是承认"假设不是如此构造,我们就无法感知这些动态属性",并不意味着这些属性不真实存在,更不是说它们只是内在认知.
但就我们的目的来说,有一个理由更为切题:呼啸而过的救火车鸣笛声吓了我一跳,此时,引起我注意的是救火车,那个红色的尖叫着的大家伙;而当我去听且成功听到的,正是那汽车疾驰而过.
我们可以转向语言来探讨这一观点.
有人说语言就如音乐一样,只是声音而已.
区别在于语言是有显著语义的声音.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没有语义的声音也会令我们如此着迷当我听你讲话时,我并不是在听你发出的声音.
我关注的是你,你说的话,即你讲话的意思,你的意图.
如果我被你说话的声音抓住了注意力,那很有可能我就听不懂你所说的话的意思.
的确,我要通过听你所说的话来领会你话语的意义,而且这要取决于你所做事情的性质,即声音.
但由此以为你所做的只不过是发出声音,或我接收到的只是声音,那真的有点像是空想,而且,它完全歪曲了我们的体验.
有的语言学家说,当一个孩子学习语言时,他面临的任务是找到声音与意义的映射关系.
但这很傻.
这看上去很傻,不仅仅因为我们继承了智性思考(intellectualreflection)的习惯,据此,我们会认为这种想法很有道理:比如说,当你看见一个西红柿,实际上你看见的是一堆品性,即便西红柿不在眼前,这些品性仍然会出现在你的意识里;还因为事实上你对西红柿有印象是因为你与西红柿有过接触与互动.
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可能出错——甚至是彻底被骗.
或许我们是像黑客帝国一样剧情的牺牲品,在此剧情中,我们由一个邪恶的霸主控制着.
但即便是这样,我们所错误地经历着的,也是一个西红柿,而不仅仅是感觉印象.
你不可能把西红柿排除在故事之外.
这恰恰是传统哲学所持有的观点.
如果你想忠实地描绘你所看见的东西,拒绝输入在你脆弱的意识范围之外的任何假设,那么,你的描绘将只局限于那些能立即证明它们存在的意识特征上.
如此一来,关于超出意识之外的世界观点,就是我们由感觉信息(dataofsense)所构建或形成的.
世界是一个由感觉信息建立起来的虚构.
笛卡尔式哲学家与当今神经科学家常常以此种方式来描述我们的困境.
但是,再重复一遍,关于事物看起来的样子——关于我们的意识体验本身——没有一个准确的、忠实的描述,(比如说)它已经不是对此类事物的描述:如一个西红柿,放在一堆西红柿上面,由蔬菜店的灯光照亮着,摆在那里等待出售.
如果我们想把关注限制在我们真正知道的东西上,那么我们所真正知道的就是,事物看上去似乎就是那样.
哲学家斯特劳森(P.
F.
Strawson)曾有一个著名的论述:我们并非由感觉信息出发进而构建一个世界的概念;我们是通过思想,从世界后退到一个感觉信息的观念.
再回到语言.
词汇,有意义的声音,就如西红柿和所有其他东西一样.
作为孩子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空白的声音,我们要赋予它意义,或要想出它的意思,这种猜想完全是对我们生活本来面目的幻想.
我能分辨哪些声音是词汇,就好比詹姆斯·乔伊斯的斯蒂芬·迪达勒斯能够觉察到湿床单是凉的,妈妈的气息比爸爸的气息好闻.
我们生活在语言之中,就如我们生活在人群之中一样,有床单、有爸爸呼吸里的啤酒味,也有从他烟斗里冒出的烟草味.
再回到音乐.
音乐是人类活动的东西,在此,它就如语言一样.
我们对音乐的敏感最终说来就是对我们的行事方式与我们制作的东西的好奇.
尤其是,它是对我们唱歌方式或乐器演奏方式的关注,而不是对我们嗓音的关注;而这种演奏真的就是那种表演:我们奏乐是为了舞者或观众;我们的演奏是通过敲击、弹拨、击打、吹奏乐器或呼号歌唱.
有声音,这是肯定的,就像我们说话会有声音一样;有节奏,这也是肯定的,正如我们说话、走路或做任何事都会有节奏一样.
这是音乐的东西.
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将这些构造包括音调、节拍、意图和旋律等呈现出来.
说音乐只是声音,脱离它的创作活动,脱离它的表演,就与感觉信息哲学家对人类意识的幻想一样,无异是一种空想.
音乐为何有意义它为什么令人着迷因为我们在节奏上、旋律上、音调上被组织起来,这是我们现实生存的一个基本特征.
音乐研究的就是这些组织方式.
而且它要做到这样,往往是要通过创造一些新的方式来传达我们自己,这些新方式建立在旧方式之上,参照旧方式并与旧方式(既有音乐的也有非音乐的)互相交融、相辅相成.
因为所有的音乐家都会对他/她之前的音乐家的方式做出反应,所以,音乐指的就是大家对所有这些方式的集体解读、集体智慧、集体幽默与见解.
在一项著名的研究中,一个古典音乐大赛的决赛录音被播放给普通听众听,他们的任务是:通过听录音来判断谁是比赛的最终胜出者.
结果证明,当他们听到的只是录音——没有录像时,他们都很难判断谁表现最佳,谁可能最终赢得比赛.
它们都在凭运气猜测最终的获胜者,也就是说,他们的准确率不到一半.
如果伴随录音还能看到录像,他们的分数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但当他们只看视频没有声音时,他们的表现就和专家一样.
结论:听众,作为一个群组,很容易判断哪个音乐节目表现最好,但条件是他们只能单纯凭眼睛看而不能同时被听觉所干扰!
当然,如果你问评委,他们在评价一场音乐表演时看重的是什么,他们会坚持认为重要的是声音.
怎样理解这一奇异的结果你可能会以为,这只不过说明我们普通人对听觉音乐的鉴别能力有多差,之所以让音乐专家来当评委更可靠,恰恰是因为专家懂得怎样去听,而不会受视觉、噪声的干扰.
然而伦敦大学的心理学家蔡嘉戎(Chia-JungTsay)的研究结果表明,专家的表现并不比音乐新手更为优秀.
专家组成员无法就哪一录音片段是最终的获胜节目取得一致意见,但当他们忽略音乐,而只关注静音的视频录像时,很快且准确地达成了一致.
现在,你可能将这一令人惊讶的结果归因于"视觉占领"(visualcapture),心理学家所共知的现象.
腹语演员的声音看上去像是从他的动物道具嘴里发出的,而不是出自它真正的发声来源.
这就是视觉占领.
我们听到的似乎是我们以为自己看到的.
我还担心,这些发现可能会诱使我们去想,它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我们热爱音乐的真相,并削弱了我们对音乐的热爱.
我的一位音乐家朋友说,这是所有音乐家的噩梦:打动人们的不是音乐,而是他们看到的现象!
但这有点杞人忧天.
这些实验结果挑战的不是音乐的价值,也不是音乐比赛结果的合法性.
音乐是人的表演,录制音乐是对这些表演的记录;音乐是人做的,而人所做的——人怎样表达自己,怎样发声,怎样强调,怎样吟咏和歌唱——不仅由他们所发出的声音表现出来,同时也表现在他们可见的表演中.
在理解和评估我们所听到的内容时,反而是我们的所见分出了轩轾.
对此,我们不应当感到诧异.
毕竟,我们感兴趣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声音.
但是,这里仍有东西令我们惊讶.
就算从录像判断谁是比赛的胜者要比从录音判断更容易,但我们大多数人会以为,录像+录音才是最佳的组合.
毕竟,关于舞台上的表现,它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
这个发现至今令人困惑不解.
或许解释在于任务的奇特性质:在这个实验中,我们被要求判断的,不是音乐——它的品质——而仅仅是谁赢了比赛.
谁表现得更像获胜者——获得这一信息最简单的方式当然要以我们的所见为依据.
这看似有一定的道理,但它并不表示聆听在真正的音乐评价中无关紧要.
·我对幻听音乐概念的批评,即对此观点——音乐是纯声音的现象,与制作和场景无关——的批评,并不妨碍我给它提出一个更接地气、更合理的版本.
即,就音乐来说——与流行音乐不同——吸引我们的恰恰是音乐,而不是表演者的独特个性.
但重要的是,以此来看,音乐决非无意义的声音.
即使是严肃的交响乐,也是由人在演绎,带着他们的思想,带着他们的姿态,只是这对他们太过熟稔、太过重要,早已被他们看作理所当然.
第四部分要成为一个艺术家根本与作画或制作物件无关.
实际上我们处理的是我们的意识状态和我们感知的样貌.
——罗伯特·欧文第17章一份极其简略却高度自以为是的美学史依柏拉图之见,艺术是一件糟糕透顶的事.
他认为,在一个公正的社会里没有艺术的位置;艺术家应当禁止存在.
你无需具备战争、运动或爱情的特别知识就能编出引人入胜的关于士兵、运动员或恋人的故事.
尽管艺术家们讲述的故事扣人心弦、动人心魄,但它们并不会教人任何东西,因为他们没有东西可教.
艺术并不传授知识,甚至还要更糟.
因为尽管它不传播知识,但艺术给人的印象是它在传播,它看起来似乎是在展示或呈现或告知什么.
艺术让我们堕落,因为它让我们脱离现实进入虚幻;虽然它做了这些,却又对我们隐瞒这一事实.
在柏拉图看来,艺术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色情挑逗.
它撩人心弦,而且总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绕过真相、信息、实在及价值.
艺术给人以错误的信息.
所有艺术都等同于色情描写,这一观点令当今许多人无法接受,觉得它道貌岸然、难以理喻;我们应当拒绝艺术,把艺术家清除出去,这样的建议在我们多数人看来颇不受待见;但柏拉图的观点其实与我们现代人的想法并不像乍看上去那么遥远.
人们普遍认为有些艺术作品不宜少儿观看,并不是因为它们不讨小孩子喜欢,而是我们担心它们对孩子有害.
人们普遍觉得暴力场面或性描写不利于孩子成长.
要读懂我们的心态还真不容易.
但我敢保证,在此我们的动机与其说是想保护孩子远离令人不悦的现实,不如说是我们认为或者怀疑,艺术在其涉及的令人忧心和复杂的问题上并不是一个可靠的导向.
关于性是什么、性欲是什么、性愉悦是什么,你愿意让孩子在只看色情描写的基础上形成他的认识吗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得出两种论断.
第一,色情描写是危险的——它传达的是一种歪曲的描述且有损于我们对现实的感受.
第二,所有的艺术都是色情描述.
第一种论断要比第二种更为可信.
但即使是第二种论断也比我们起初愿意承认的要更有分量.
大学校园里的生活是我再熟悉不过的领域.
每次看到影视剧里描述的校园生活总让我无比惊讶,它是那么地脱离现实,那么地不切实际.
无论是作为警方调查、爱情故事的背景,还是别的什么的背景,电影里出现的校园总是无一例外地表现为几个人所共知的、万变不离其宗的固定场景.
饶有趣味的是,即使不是全部,大多数发表小说或写电影故事的作家都上过大学.
他们在讲故事时往往并不按照他们所知道的进行描述,而总是把描述建立在一些头脑简单或不太可能的意象上.
或许这里再次让我们想起与色情的对比.
拍色情电影的人不会将他或她真实生活的性经验当作"素材"(天啊!
这不可能),而是提供一种关于性爱是什么或会是什么样子的幻想.
因此,这就可以解释,电影里大量出现的爬满常青藤的建筑物,戴着珐琅边眼镜、身穿软呢西服、英俊潇洒的年轻教授,英雄般地站在教室前,身边围满了一脸崇拜的求知者.
只能说,这种描写表达的是一种幻想.
当然,用幻想来替代现实,让一个人对现实的体验由一系列自上而下的幻想来构成,至少有些东西可能是危险的.
这是我童年时期的一个例证:曾经有一个电视节目叫作《欢迎回来,考特》(WelcomeBack,Kotter),它描述的是布鲁克林一所中学里的课堂生活.
剧中展示的一种男子气概令人着迷,富有魅力;该剧自始至终热热闹闹,令人捧腹不止.
当时我正上三年级,它真的给我提供了一个高中生活的蓝图与典范.
当然,我知道这是喜剧,是虚构,这是在演戏,但是有些东西已经定格.
情景喜剧给了我们一种指引,一个模本,让我据此构建我自己对高中生活的憧憬.
《欢迎回来,考特》可能没什么害处,但它的机制至少有可能是危险的.
正是如此,对于媒体上有关人种、性别、种族的画像,人们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它们往往会使偏见固化.
从柏拉图的观点来看,艺术除了固化偏见还能做什么呢艺术家不是科学家或理论家,他们是意象制造者.
而所有的意象都是假象.
无论是导演,还是演员、观众都不可能获得他们所涉及问题的第一手知识.
娱乐要求的不是知识,而是知识的表象.
艺术是超级模仿.
不久前,看到公众强烈抗议一部反映捕杀本·拉登的电影,这让我想起了柏拉图的观点.
电影中包含刑讯场面,而且似乎表明刑讯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美国得以获悉本·拉登的行踪.
一些评论家认为电影是在传达错误的信息——事实上,作为信息收集的一种方式,刑讯是无效的.
另有人认为,即便刑讯有效,它在道义上也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该电影应当受到谴责,因为它从正面描述了这种做法.
如此大动干戈地责难是否荒唐、可笑并非问题本身不值得严肃对待.
它们当然应该受到关注.
但认为这部电影与这问题有什么联系就实在愚蠢.
毕竟,它只不过是在讲故事,是用来赚钱的.
由一些并不了解事实真相也无需承担责任的人制作出来,卖给同样不知情、不相干的人们来观看.
作为一种文化,我们以为看部电影就能处理当今重大问题,这种想法是多么的无聊且虚荣.
在柏拉图看来,问题很简单.
艺术家绘画、讲故事、演戏剧,意象就是他们的素材;他们靠摆弄表象和映射让人相信.
但是表象——更不用说是一些经过挑选的表象,因为它们要挑逗人——对于让人看到事物的真实本质没有任何指导意义.
如果你对战争感兴趣,你应当去咨询一个士兵或者政治家,而不是去找一个小说家海聊;如果你对太阳系感兴趣,你应该去找科学家而不是去找《星球大战》的导演.
在柏拉图看来,艺术作品双重脱离了事物的本身.
艺术家再现的充其量不过是事物或事件的表象,只是表面现象而已.
艺术训练我们脱离现实去看向一个经过双重篡改的意象境界.
艺术天生是危险的,值得怀疑的,这是一个严肃的观点.
即使柏拉图吹毛求疵的苛刻态度让我们难以苟同,但至少柏拉图对这问题重要意义的执着令我崇拜:如果艺术并非立足于知识,且并不传授知识,只是局限于表面现象,那么艺术又怎么会有价值如果艺术只是模仿,它又怎么会有意义这里存在着一个美丽的讽刺:至少在本书中,从我主张的立场来看,柏拉图自己的工作在两个方面削弱了他对艺术的批判.
首先,柏拉图在他的文章中讲故事、演戏剧,他恰恰像艺术家一样在摆弄他的素材.
他给我们提供的不是事实上人们怎么说,怎么表现或怎么证明,而是一些虚构的呈现,呈现了一些虚构的谈话人可能会怎么说、怎么想或怎么承认.
再者,柏拉图是一个哲学家,而哲学,如我所说,从其本质来讲是一项艺术工程.
因为哲学与艺术一样,其任务就是要让我们认识我们的组织并重新组织我们自己.
艺术有可能会瓦解灵魂,柏拉图的这一见解完全正确.
但是我们现在能够体会,他的错误在于以为瓦解和重组总是有害的.
他正确的地方是他认识到,艺术(以及哲学)可能潜在是有害的.
这是艺术(与哲学)的本质.
艺术与哲学都是严肃的事业.
事实是,柏拉图本身富有创意的榜样应当让我们认识到,艺术可以是一种学习资源.
柏拉图的作品让我们明白,比如,一出悲剧或一首史诗,实际上可能构成一种研究,并形成一种独特的知识.
当然不是关于战争的知识,也不是关于性的知识,或关于校园生活真实状况和感觉的知识,更不是星球运动的知识,而是有关我们体会自己的观念、价值、承诺是怎样互相搭调或不搭调的知识——是一种自我认识.
从这一观点来看,《猎杀本·拉登》歪曲事实,或其作者误解误导,这些都不会妨碍电影给我们提供一个学习和重组的机会.
在这样一部电影中被激活的是我们的反应和思考,关于可能事件而不是对真实事件的反应和思考,或者说是我们对可能事件的反应而做出的回应,对于事情可能会怎样或可能揭示什么的反应.
当然,在此也允许错误出现.
但不是关于事实的错误.
对事实的无知不妨碍我们有效地研究战争、刑讯等对我们的意义.
亚里士多德看准了这一点.
在他看来,艺术比历史更为深奥恰恰是因为它关注的不仅仅是发生了什么,真相是什么;它关注的是可能性是什么,可能会发生什么;因此,它关注的是一个更为根本的现实;它让我们思考事物的本质,那些限制和规定会发生什么的事物本质.
艺术看待事物,不是看它们的真实、实在,或实际发生的那一面,而是看它们可能会有的各种不同的意义.
每部剧作、每首诗、每幅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都是一种思想实验;因此,从根本上来讲,它们都是具有哲学意义的.
正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我们首次发现一种明确的解读:文学和艺术可以是富有哲学含义的;事实上,即便是作为娱乐、描绘甚或是挑逗,如果要成功地融入思想与意义,它们就必须富有哲理;艺术必须建立在一种类似现实研究的基础上.
一篇小说必须是耐人寻味的,它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它必须要有开端,有发展,有结局.
它要表现的不能仅仅是以老套的顺序发生的任何事情,而必须是围绕着一种非常特殊的事件,即人类活动而展开的一种有意义的情节安排.
亚里士多德承认柏拉图的说法没错,艺术所做的事情就是模仿.
但他坚持认为我们对模仿的兴趣——对造像、虚构、表象的兴趣——是富有创造性成果的,是一件好事.
因为它要关注的是最深层的、涵盖最广的本质特征.
它是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兴趣,这世界由价值、关注、传记、引言、结论等组织起来;而不是对一些顺序发生的随机事件的兴趣.
亚里士多德认为文学是一种独特的哲学研究,因此文艺批评——关于艺术的评价,一件作品作为戏剧、诗歌或无论什么能否算作艺术的评价——是一项合法的哲学工程.
这一观点反过来也解释了某些可能令人迷惑的事情:如果我们认为艺术所起到的作用就是挑逗或娱乐,为什么一出戏剧我们可以看了一遍又一遍还是乐此不疲为什么一首史诗我们不仅读一次,而且可以反反复复地去品味它为什么我们阅读一篇剧本与看它在舞台上呈现表演能够获得同样多的感悟这表明,如果有某些东西在起作用,那么在艺术作品中发挥作用的一定不只是表面景象(spectacle)——舞台技艺、悬疑或是出其不意.
这清楚地表明,当我们欣赏艺术时,我们的感受和情绪——恐惧、同情、遗憾、共鸣、愤怒——不仅仅是在我们身上产生的反应,由一些不真实的事件激发的反应.
我们的参与,我们的感受都是对生命问题本身的参与.
坏结局降临在坏人身上,与坏结局降临在好人身上同样具有感染力.
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在美学上更容易打动我们的,往往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场景:一个好人由于自身的弱点,虽然出于可以理解且很自然,甚至是良好的动机,却遭遇不好的结局.
我们觉得,悲剧,以其独特的方式,尤其震撼人心且有深意.
因为戏剧是在把我们自己,我们的弱点,以及作为一个行动者的真正含义呈现出来:作为一个行动者他的生命既可以被赋予一个完美的结局,也可能遭遇一个悲惨的结局.
同一部戏剧你可以不厌其烦地重复看很多遍,因为你对戏剧中问题的思考不会立即就产生你所寻求的领悟或重组;而且阅读一部剧作同样也会让我们受益,这是因为,戏剧真的是哲学作品,它给我们机会去投入地思考.
我们再次惊异于哲学的相似.
哲学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它所提出的问题.
哲学永无止境.
只有当我们对自己、对我们的生命没有了困惑、没有了迷茫,才有可能是哲学的终结.
但是我们生命的本性就是它不仅复杂难懂,而且我们的组织方式也是无法由人身体内部来进行解读的.
人类是自身永恒的问题,因此哲学永远不会过时,文学也永不过时.
也许柏拉图是对的,他认为一个理性的社会不需要艺术,也不需要哲学,恰如一个理想的世界将不再需要医学.
如果我们接受事物本来的样子,各安其命,行事都能按照自然、良好的意愿,性情温和、判断准确,那我们就不再需要艺术和哲学.
但是,我们照此假想的是一个分明的非人类社会,或许实际上是一种动物存在.
这是一种我们不可能获得的存在形式.
海德格尔(Heidegger)说,我们是我们自身的问题,这是我们的存在标志.
与为数不多的几位思想家一样,海德格尔很清楚,艺术所起的作用是具有哲学意义的.
它的作用就是要公开展示和呈现,同时构建并创立那些,如我所说的,组织我们的结构和价值.
它揭示组织,同时也重组织我们.
海德格尔的出发点是世界以多种不同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有时我们会极目四顾并对我们所看见、所摸到或闻到的东西进行思考.
但是这种对周围事物有意识的、了然于胸的感知有个前提,如海德格尔所说,就是我们已经融入这个世界且在其中优游自在.
因此大多数已在那里为我们存在的东西并非是作为思考的对象而存在,而是作为我们的立足之地,或是作为我们从事重要事情的装备或设备而存在.
我们可以研究鞋子并思考它们,但是因为我们穿着鞋子就是为了工作或四处走动,我们不会去思考鞋子或去体会它们;我们顺从鞋子,我们依赖它们,我们使用它们.
鞋子可以成为思考的对象,但前提是它们作为生活的设施已经是"信手可得",而信手可得的东西就已经不是一件值得考虑的事.
既然鞋子被使用,被看作理所当然,鞋子这种独特的存在方式,理所当然的存在方式,恰恰要求我们不去研究或思考它们.
鞋子,以此方式为我们存在,需要从前景中退隐出去.
但这就提出了一个难题.
如果鞋子作为生活设施为我们存在要以它退隐到背景之中为前提,我们又怎么可能将这一事实本身——如海德格尔所说,器具的器具性——展现出来一旦你把注意力转向鞋子并思考它在你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你已经改变了格局,打破了魔法.
你面对的不再是一件你寻求的设施,而是一个物件.
我们将它看作理所当然,以至于不会注意它们,如果这恰恰是鞋子呈现给我们的独特特性,我们又怎么可能让鞋子作为设施成为我们的关注焦点,把我们要依赖鞋子的事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呢依海德格尔之见,这就是艺术的工作,而且是一件富有哲学意义的工作.
它是独特的哲学工作.
比如,一幅鞋子的油画,梵高的著名画作之一,就具有力量让我们看清鞋子怎样与整个生活方式(维特根斯坦会称之为生存模式)协调起来.
解读这鞋子就是要去解读依靠这鞋子艰难度日的人是什么生存状态.
这是一幅画可以展示的东西.
一幅画让我们去发现自己在这世界里的不经思量的参与方式.
但海德格尔对这一作用作出了一个更有力的论断:只有存在艺术,鞋子才可以以此方式为我们存在,才可以成为工具.
并非只是因为艺术揭示了我们这世界的构造,而是因为它创生了那个世界.
没有艺术,也便没有世界.
这里有一种方法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令人困惑的观点.
我曾说,我们需要艺术与哲学作为我们迷失时找到出路的方式.
海德格尔所指正是这个.
我们人类是自己的问题.
如果我们能够依照一阶的组织模式规定的方式随波逐流,无暇思索地忙碌着,愉快地度过一生,那也会是一件美妙的事.
但是这样一种放任自流的生活不属于人类,或许它可以是动物性存在.
关于我们的忙碌,我们对组织活动的参与,有一件事令人瞩目:它们总是成为我们的问题.
我们迷失在组织机制里,我们不是这些机制的作者,我们对它们没有清楚的认识.
文字与语言就是这样一种情形.
文字作为我们为自己示范语言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但结果我们发现,如果我们没有示范它、评判它以及试图更好地理解它的需要,事实上也就不会有语言.
恰恰是因为我们想当然地从事一些活动,才允许我们可以继续地想当然下去.
你不可能取消哲学与艺术,因为哲学与艺术恰恰是我们创生世界的方式,在某些时刻,正由于这种规范作用,我们可以让这世界退出关注视野,安然地停驻在背景之中.
艺术的工作就是这样建立起我们的世界,恰如书写的作用是让语言成为可能一样.
怎样理解艺术,它既不是科学又不受控于我们对事物是什么的认识,却可以成为一件有价值的东西柏拉图提出了这一问题,亚里士多德试图做出解答,海德格尔接过了这个挑战.
但海德格尔的解释非常抽象,而且脱离了我们关于艺术的实际思想、谈论和体验.
历史上另有两位思想家对这一主题的思考提供了更为详尽的阐述,填补了其中的细节.
首先是康德.
康德认为,也是我一直在说的,艺术产生在批评的空间里.
让我们来解释一下.
关于我们对艺术的反应,有两个令人瞩目且不可否认,却明显互不相容的特点.
康德就是让我们关注这两个特点:首先,审美反应是一种感觉.
有些艺术作品会打动我们,我们发现我们喜欢它们,我们深受触动,我们心有戚戚.
重要的是,我们的反应不受争论的影响.
没有规则会规定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反应;你无法说服我,让我发现某件艺术品很美、很激动人心或很重要——或反过来,也不能说服我相信它不美、不激动人心或不重要.
如康德所说,在这里,我们不受观念或规则的左右;我们完全沉浸在感觉的领域里.
但是,第二点,当我们把自己对一件艺术作品的反应当作是成就或见解时,情况也是这样.
当我认为一件艺术品很重要,很美,很有价值时,我的意思并不只是说我喜欢它,或它对我来说很有价值;我的意思是,它是一件有价值的东西.
我期望或我相信别人会,或至少应当会,同意我的看法.
要弄明白这一观点有一种方法,就是得去接受:当我们谈及对艺术作品的审美反应,说到真正的分歧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我喜欢一种葡萄酒的口味,而你不喜欢,我们并不是真的意见相左.
毕竟,我喜欢适合我的口味没错,你喜欢适合你的也没错.
它的口味适合我却未必适合你.
但当我们谈到美感或其他形式的审美价值时,我们绝不仅仅意味着某件东西对我来说很美.
在康德看来这甚至根本说不通.
如果我觉得某件东西美,那是因为它的确美.
如此一来,我们就有了明显的分歧.
审美判断是主观的,它们关乎感觉和反应.
同时,因其本性使然,我们可以这样说,它们似乎具有主观共通性(intersubjective)的意义.
康德说,审美评价的做出是来自"普遍的声音"(theuniversalvoice).
它们可能是主观的,但它们反映的不是我自己随意、偶然、主观的品味或态度.
当我评价一件艺术作品时,我是作为一个人,从我个人的立场来评价它;但我在评价的时候,却相信自己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
康德对此的解决方案是:他坚持认为,关于艺术作品价值的争议总是对话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一个人只是说,我喜欢德国艺术家阿道夫·门采尔,这永远不够.
你需要就这一声明进一步阐述,你要说出你为什么喜欢门采尔,或你喜欢门采尔的什么.
由此,关于艺术的评价而发起了讨论、对话或更概括地说,是批评.
而批评,就其本质来讲,是一种交流活动,一种在人们之间展开的活动,它要求人们互相尊重,彼此坦诚.
而关于此种批评交流,值得关注的是,事实上,它可以改变我们的想法,改变我们的欣赏方式与欣赏内容.
优秀的批评家不仅仅是描述一幅作品,他们还会让我们注意到那些我们遗漏的品质,或说服我们去体味那些我们忽略或不曾注意的特征.
批评的进展不是靠逻辑论理,在这一领域没有什么一锤定音的观点;批评的进展靠的是说服.
批评家都是教育者,他们教会你去发现.
既然我们是艺术热爱者,我们就都是批评家.
当然,批评崩盘的状况也时有发生.
我对一件作品的反应可能你会不以为然,也就是说,追根究底可能是因为你不把我当回事.
而这正是美学批评中决定成败的东西:是我们相互理解,甚至可以说,是我们彼此相爱的能力.
康德有句名言:美学评价必须要置身事外.
这应该显而易见.
对我儿子的音乐演奏我必然会赞赏有加,这无可厚非.
但是,如果我喜欢它只是因为它是我儿子的作品,那么我对它的喜爱就不是出于什么审美的缘故.
我儿子演奏音乐并不构成理由,让一个对我儿子并无私心的人对他的演出感兴趣.
一种美学评价要真正地表现审美,它必须是一种公正无私的反应,对谁拥有这件作品或是谁创作这件作品等要漠然视之.
但在康德看来,重要的是,我们已注意到,对一件东西是否当得我们的审美赞扬,可能无法进行客观的验证.
审美价值不是一件东西的特征,如重量或颜色一样,是我们能够探测、感知或发觉的东西.
但这意味着美学争议永远不是真的关乎艺术本身,而是关乎我们对一件事的反应.
正是如此,康德把审美反应描述为"想象力的自由游戏".
这件事不像我们看见一辆车一样一瞥而知.
它并不明示我们要如何去体验.
最终,在美学评价中,真正决定成败的是,你是怎样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当审美分歧不可调和的时候,甚至可能导致亲密关系的破裂.
也正因为如此,艺术会要求我们专注于对话与批评的意义.
这又把我们带回到哲学.
哲学分歧恰恰以此方式表现为审美.
就像你无法证明一幅画是否是一件有价值的艺术作品一样,你也无法证明你的哲学立场.
因为最终决定成败的是你,你的思想,你的专注,你的造诣,和你的妙悟.
哲学不是一门科学,它不承认实证方法或其他形式的决策程序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分歧并非实在.
它们实实在在,它们客观存在.
但是,决定成败的并非事实,而是我们怎样理解,怎样弄懂并最终评价这些事实.
那么,艺术有它的价值,恰如哲学有其价值一样.
并非由于它会像科学一样产出知识,而恰恰是因为在这个领域里我们可以与我们已知(或我们以为已知)的东西进行一番较量.
在这个领域里,我们可以努力地去弄清楚我们是怎样思考、怎样做出反应,以及怎样衡量价值的.
正如舞蹈编创不是跳舞,哲学研究和美学批评也不是要让我们收集更多的事实.
它们是我们展现自己的领域.
在这些领域里,我们是信息收集者,是感知者,而事实上作为感知者,我们的评价往往会掺杂自己的兴趣与喜好.
我们努力把自己的这一切呈现在自己面前.
作为这个简短但纯属个人见解的美学史的结束,也作为本书的结束,我要讲到的最后一位作者是约翰·杜威.
以上对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和海德格尔的解读让我们看到他们各自的观点,但我认为,正是在杜威的思想中我们发现这些观点的融合.
相比其他思想家,杜威让我更清楚地看到艺术的本质,我所理解的那种本质.
通过对杜威的解读,如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海德格尔的认识一样,我们可以形成一种艺术的概念,它显示出艺术是多么的不可或缺,无可回避,与生俱来,富有哲理.
与海德格尔一样,杜威对审美体验不感兴趣.
他关注的是艺术的作用,或者说,是艺术的意义与价值.
但在杜威看来,所有这些都与体验的本质密不可分.
亚里士多德早已认识到,体验决不只是一系列的强烈感受.
而后来的哲学家,如大卫·休谟(DavidHume)和约翰·洛克(JohnLocke)却似乎浑然忘记.
的确,有一种感觉,不定在哪一时刻,会让我们面对它强悍的轰动,威廉·詹姆斯称之为愤然怒放的、闹哄哄的混乱感受(theblooming,buzzingconfusionofsensation).
但是杜威认为,体验本身指的不是这种感觉.
我们绝非生活在一系列毫无意义的感觉之中,在一些杂乱无章的偶然感受或意象之中.
构成我们生活状态的体验,我们清楚地知道并乐在其中的体验,远比这要结构清晰.
如杜威所说,它们是浑然一体的,完整的,可以名状的:在威尼斯共进晚餐的体验,在大学里学习的经历,买房子的体验,昨晚努力入睡的体验,有孩子的体验……此种主题明确、结构完整的体验,其中有一义谛,那就是,它们是收获.
我们在制造它们.
我们不只是经历它们,我们需要设计谋划.
如果你认为生活是一条潺潺的河流,有作为,有担当,那么,获得意义与完整就是一件有价值的事,因为意义与完整是我们现实生活体验的重要特征.
每一种体验,既然它是一次经历,它就是完整的.
它有形式、有意义,它是被制造的,它是被收获的.
用杜威的话说,它是审美的(aesthetic).
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制造意义的活动.
所有体验,只要它是体验,就发生在美学空间里.
因为要完整,要浑然一体,要有所组织、井然有序,就是要有美感.
与跳舞、唱歌一样,感知本身,包括思考、疑惑都是审美,都有美感.
在杜威看来,如果不具美感也就不成其为艺术,也就根本不成其为体验.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杜威的观点就是,我们都是艺术家.
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倾力于制造体验,在做事和感觉的循环里,在做出行动并承担行动后果的循环里,去体会它们的形式与意义,它们在最基本的生物水平上组织了我们的生活.
生活本身就是制造体验的活动.
这恰恰就是艺术的含义.
在杜威看来,艺术就是体验;艺术家不是在制造东西,他们是在制造体验.
但是,现在我们遭遇了一个循环:艺术是体验,艺术家制造体验;可我们所有人都制造体验,因此我们都是艺术家.
但杜威并没有听任我们被困在这个循环中.
真正的艺术家并不仅仅制造体验,他们还制造作品(绘画、表演或无论是别的什么东西),而这恰恰为我们进行完整的体验提供了机会,因为它们的完整性一览无余.
画家用眼睛评判着画布上的效果,然后根据他对自己行为结果的感觉做出进一步修改.
通过绘画,他提炼总结了制造体验和生活本身的这一循环过程.
当你看画的时候,你遇见的是制作出来让你遇见的东西;你遇见的恰恰是一个去体会体验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机会.
而你自身现在必须去制造你自己对艺术作品的体验.
要有所体验,你不能仅凭观看;你需要激活自己,从而激活它.
艺术作品给你的是一个机会,让你去体会我们的生活如何展现在我们面前,体验如何发生,我们如何实现积极的生活.
艺术,站在你的面前——海德格尔说,它闪耀着光芒——为你做出示范.
它是一种体验,它给你提供一种体验.
艺术的作用就是把我们作为制造者,也就是说,作为体验者的根本天性呈现出来.
艺术把我们的组织方式展现给我们自己,且是以一种可以理解、可以辨认的方式.
本书开篇引用了杜威的观点,他是这样表达的:正是因为艺术作品的存在妨碍了我们对于艺术本质的解读.
我们只顾着去看那些作品,但艺术是体验.
重要的不是作品,而是对作品的体验.
但这些体验不会自然而然地呼之即来,我们需要制造它们.
艺术是一种机会,它让我们制造体验,制造自己,从而生活.
如此说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所有人都是艺术家,我们都在生活.
而生活就是一个制造体验的过程,在已经发生的事情面前,对我们的所为做出创造性回应的过程.
但艺术远不止这些.
归根结底,艺术是哲学.
它要把有关我们状态和本性的所有东西展示出来.
我们都是艺术家,以至于,正如杜威所说,而我也一直在阐释,无论我们出现在哪里,只要有人类出现的地方,对于艺术的需要,对于哲学的需要,对于理解的需要也都会齐齐地出现.
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创作无所不在.
艺术的存在不会比书写更为普更多书籍访问:www.
j9p.
com为我们需要这样.
艺术是在书写我们自己.
艺术是哲学.
艺术是在把我们的真实天性展示在我们自己面前,因美,艺术不是愉悦,艺术不是加入艺术界,艺术也绝对不是商业.
艺术不是加工制造,艺术不是表演,艺术不是娱乐,艺术不是唯原因,我们可以说,艺术真的是无所不在.
勃,方兴未艾.
我想说明的是,这些思考让人想到,恰恰是出于同样的但即使是在并无书面语言的文化里,书写语言的态度依然生机勃遍;有些文化还没有书面语言.
致谢我生长在一个艺术家庭.
我的身边到处都是艺术,以及把艺术的价值看作至高无上的人们;事实上,艺术就是衡量其他所有价值的标准,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理解艺术的能力,观赏、鉴别以及领悟艺术的能力受到高度重视,但仍不及创作艺术的能力.
这是一种暗能力吗我父亲的朋友、艺术家托尼·史密斯(TonySmith)在与他交谈中曾这样问.
我猜,当时我父亲在讨论艺术家的伟大时所使用的那种谦恭、崇拜的语气,与别人家里在谈论圣徒及其困苦劳顿却鼓舞人心的生活时所用的语气一般无异.
但这不只是在我家里,整个格林威治村都是这样,我就在这样一种环境里长大.
这是不同生命和不同作风的交织,艺术就是那条贯穿的经线.
我和我的朋友曾经把隔壁画家扰得不胜其烦.
我还记得因为我们在他和NancySpero共有的阁楼外的过道里上窜下跳,跑来跑去,惹得LeonGolub对我们大为恼火.
另一个朋友的父亲制作电影——是色情电影.
(我曾带着期盼与不安参观过他的阁楼.
)楼下就是我母亲的陶艺室,每天都有陶艺师们进进出出,不分昼夜;我家后门的邻居原本在通用电气公司工作,后来辞职专为滚石乐队负责灯光;于是就有了米克·贾格尔(MickJagger)顺便到这里来吃草莓派.
DoveBradshaw曾让我8岁的弟弟领路到一家雕塑工作室.
10岁或11岁的时候,我就参与KikuoSaito制作作品,在东四大街拉玛玛的附属实验剧场里参与演出了.
(上小学时,我还在学校编创的剧目《俄克拉荷马》中扮演柯利.
在BrianKahn制作的ArthurKopit剧作《印第安人》中,我还曾演过野牛比尔,这是一部我们在百老汇演出周期很短的先锋剧.
)根据网上格林威治村的一个旅游指南,鲍勃·迪伦、格拉汉姆·纳什(GrahamNash)、大卫·克罗斯比(DavidCrosby)都曾在小红砖公寓居住,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
我父母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就买下了它,之前曾作为租户租住在那里,因此我才知道,事实上,迪伦和克罗斯比从未在那住过.
但画家老RobertDeNiro的确住过那儿,还有他的小儿子演员罗伯特,他们都是我家的常客(我父母这么跟我说的).
迪伦的确也曾来过,至少有一次,到我妈妈的工作室里看了看陶艺课.
尽管因为我太小,无缘结识巴内特·纽曼、托尼·史密斯、杰克逊·波洛克还有马克·罗斯科,但这些人,尤其是纽曼和史密斯,在我出生之前的那些年都是我父亲过往甚密的朋友.
我之所以讲到这些名字并非为了自抬身价,而是因为,现在回头来看,我必须承认,能够在这样一个艺术社群中长大是多么地值得夸耀.
而且,之所以写下这些个人记忆,也是因为它们会帮助我阐明本书研究的动机.
对我来说,艺术不只是可以将理论付诸应用的又一现象,这是私事儿.
而艺术的问题,艺术为何重要的问题,艺术是什么,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处于何种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这才是我在哲学上的首要问题.
前言中我所提到的艺术家,就是激起我重新思考观看的本质的那位艺术家,就是我的父亲,汉斯·诺伊.
我承认,本书的中心论题——艺术是哲学实践,哲学是艺术实践——对我非常有用.
我的家人都在积极地投入艺术,在这样的背景下,它可以被最终理解为,是我为哲学及其价值的辩护,为我自己工作的一个辩护.
如果说艺术是最重要的事情,而哲学又是艺术,那么,说来说去,原来我也是一名艺术家.
看哪,老爸!
但是,促使我写作本书的,还有一些看似偶然的事件.
我的第一本书《知觉中的行为》(ActioninPerception)出版于2004年,在当代舞蹈社群中读者甚众,而在视觉艺术圈里也有不少的读者.
这可超出了我的预期.
我写作本书原是为了哲学家和认知科学家——缘于我与哲学家伊凡·汤普森(还有他的导师及朋友瓦雷拉)以及实证和理论心理学家凯文·奥瑞根的合作——就没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舞蹈家、舞蹈编创人丽贝卡·托德(RebeccaTodd),现在已是认知科学家,也是伊凡·汤普森的妻子,和我,还有丽萨·奈尔森(LisaNelson)(以及其他多位舞者,包括KarenNelson、SusannaHood、MargitGalanter、HeikeLangsdorf、AlexanderBaervoets以及比利时PaulDeschanel团队的成员,还有剧作家JeroenPeeters),我们共同组织了一个专题研讨会.
正是这次研讨会让我第一次认识了这一观点:舞蹈,或者说是舞蹈编创,原来可以成为一种研究实践,一种研究交流、知觉和意识的工具,丽萨·奈尔森的作法就是一个完美的例证.
几年后,威廉·弗西斯(WilliamForsythe)和他的合作者FreyaVass-Rhee、LizWaterhouse、RebeccaGroves、NorahZunigaShaw就联系到我,然后再晚些是NicolePeisl,FabriceMazliah,DavidStern,RobertaMosca与弗西斯舞团的其他成员,包括舞蹈学者ScottdeLahunta也与我取得联络.
我碰巧闯进了这个世界,于是开始学习该怎样去观赏舞蹈,去思考当我们观看舞蹈时我们看到了些什么,由此,关于舞蹈编创能做到怎样,也开始了一个学习过程.
我和ScottdeLahunta花了几个小时畅谈舞蹈、哲学、科学融合在一起会是什么状况[部分是在后来被称作动作库(MotionBank)的场景下].
NicolePeisl现在和我一起编舞、一起演出,同时还共同在研讨班授课.
她是灵感之源,我们的合作仍在继续(不仅在专业上,我们住在一起且有了一个孩子).
至于弗西斯和我,在过去的5年里,一直在进行着一个充满激情的、持续的交流,讨论舞蹈编创里的哲学和哲学里的舞蹈艺术.
本书就是由这些对话构成,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这些对话的记录.
最近,我又与舞蹈艺术家黛博拉·海开始了新的合作——联手开展一个表演讲座活动.
以此方式我被邀进入舞蹈世界,无论这是多么的偶然,但一切感觉就像是回到从前重新开始一样.
我爸爸的女朋友,也是我妹妹Adi的妈妈,曾经也是一名舞者;20世纪80年代,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她常常带我们一起去舞剧院的排练厅.
而且,我已经说明,我父亲从一开始就在我的故事和这一研究项目中画上了重重的一笔.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还有几件重要的事,我必须提一下.
1997年,我受LarryRinder和MarinaMacDougall之邀到加州艺术学院就知觉意识做了一个演讲.
会议的宗旨是要集中大家对于艺术与意识问题的看法,这是一个我还从未认真思考过的课题.
对我来说,这次会议是一个转折点.
首先,我开始关注这一课题;然后,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我遇见了著名的艺术理论家理查德·沃尔海姆(RichardWollheim);现在,我就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他的"美学课程;而且,我想一定是因为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以及后来与拉姆查德兰(VilayanurS.
Ramachandran)、BillViola等参加的一个论坛,1999年,我被MichaelS.
Roth邀请去圣莫尼卡盖提研究所参加艺术与神经科学研讨会.
本次会议名单上的人物也令人难忘——ElaineScarry,DavidFreedberg,BarbaraMariaStafford,PietroPerona,ClaudeImbert,TomCrow,JohnMazziotta,PatriciaChurchland等等.
记忆中,Crow不喜欢我关于艺术的观点;Freedberg和Churchland不喜欢我关于神经科学的言论.
Scarry替我辩护,在我的印象里,与其说她是出于真心的赞同,倒不如说是因为慈悲为怀.
我有点伤感,但我坚信在这个领域里一定有些工作需要做却还没有做,而我就想承担下来.
快进至近10年后:2007~2008年,我在德国柏林度过两年,与当时的妻子、艺术家MiriamDym以及两个儿子一起.
在这里,我写了《跳出脑海》(OutofOurHeads)一书,正是在这一年,我开始认真地思考关于艺术的问题.
我从霍斯特·布雷德坎普(HorstBredekamp)和LucaGiuliani那里获得灵感,他们两人都是德国成人教育学校Kolleg的永久会员,也有来自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Fried)和亚历山大·纳格尔(AlexanderNagel)的灵感,他们都是我的同事研究员.
我们关于艺术的谈话大都以柏林及其艺术宝藏为背景.
还要特别感谢洪堡大学的哲学家JohnMichaelKrois,他研究艺术与体验的具体方法也是我灵感的来源.
我还应该再补充一句,MiriamDym一直是我在艺术方面的老师,她的影响,或者说是她的行为影响,一直贯穿于本书中.
那年她在柏林有一场个人秀,每次想到奇特的工具,总免不了想起那场她的个人秀.
写作《奇特的工具》一书面临很大的挑战,部分是由于当我写作的时候,心里有这么多不同的人和观众.
我写这书既是为了上述提到过的人,也是为了其他一些我认识的人,有的是当面结识,有的是从阅读他们的书中认识,有的非常熟悉,有的并不熟悉.
本书也是为他们而作:WhitneyDavis,HubertDreyfus,MoriahEvans,LizaFior,MichaelFried,P.
M.
S.
Hacker,EdwardHarcourt,DeborahHay,ChristopherM.
Hutton,JohnHyman,RobertLazzarini,SinaNajafi,WarrenNeidich,JonathanT.
D.
Neil,RichardSacks,LeoTreitler,ChristopherWood,andAlexiWorth.
我还要向我的朋友BlakeGopnik和LawrenceWeschler特别致谢,他们总是欢欣鼓舞、精力充沛,并富有深刻的见解,给我方方面面的陪伴与指教.
向洪堡大学Bildakt符号表达课题组的全体成员致谢:HorstBredekamp,Mark-OliverCasper,MariaLuisaCatoni,KatharinaLeeChichester,FranzEngel,HannaFiegenbaum,JoergFingerhut,SaschaFreyberg,YannisHadjinicolaou,EinavKatan,MarionLauschke,SabineMarienberg,AnjaPawel,PhilippRuch,JohannaSchiffler,PabloSchneider,JürgenTrabant,JorgTrempler,StefanTrinks,PatriziaUnger,TullioViola以及FrederikWellmann.
2014年9月在柏林的一个研讨会上,他们对《奇特的工具》书稿的仔细阅读和不吝指正,促使我对本书结构做了极大的调整.
对他们我无比感激.
同时感谢我的研究生CaitlinDolan和CharlesOliverO-Donnell,他们不远万里赶到柏林参加研讨会并表达了富有见地的无私意见.
特别感谢Caitlin,他还是我在本项目上的助理研究生.
感谢我的经纪人Brockman公司的RussellWeinberger,以及Farrar,StrausandGiroux出版社和我的编辑JoeWisnovsky,还有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WrightBryan和13.
7宇宙与文化栏目组.
也感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我的同事们以及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的前同事们等的支持.
无比感激古根海姆基金会,在2012年把奖金颁发给我,支持我完成本项目的研究.
但还有两个人我想多说几句.
一个是多米尼克(DominicKahn),十一二岁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
他是我的铁哥们.
他住在柏林,这些年常常在我的文章中客串出场.
他是我的评论家,尽管有时很苛刻,但总是发自肺腑.
我要说,多米尼克的问题是,说到艺术,他总是高度怀疑.
他只管喜欢他喜欢的,却拒绝接受在我看来如此艺术,而我猜他会说是垃圾的东西.
在他看来,在巴内特·纽曼平白无奇的画布或是约翰·凯奇的音乐架构里,怎么可能会有什么意义更不用说是魔力了.
而一幅耶稣受难的十字架油画,无论是出自鲁本斯之手还是提香之手,对他必须要说些什么前段时间我曾看到过一篇报道,伦敦艺术博物馆里的一位看门人在一场深夜开幕展后被解雇,因为他清扫了遗留在地板上的烟蒂和啤酒罐.
他怎么可能知道,他清理掉的正是艺术本身.
而几个月前,在法兰克福的施泰德博物馆,我自己就曾叫来保安,告诉他似乎哪儿漏水了——在一尊独立的雕像周围,水流满地——而他却跟我解释道,这正是作品的一部分.
对多米尼克来说,我猜他的观点会是,这可正中他的下怀.
如果说什么是艺术,什么不是艺术,这之间的界限不能被明确指出,甚至不能被看到的话,那么,当然,我们称作艺术的东西只能说是"我们""人群"中某个人的说法而已.
也就是说,我们都和那个小男孩站在同样的位置,迷惑地看看四周,然后有勇气喊出:皇帝没穿衣服!
关于哲学本身,人们往往表达的是一种类似的态度.
哲学里有进步吗哲学有结果吗尤其是科学家,有时会不无轻蔑地提出这样的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很显然,他们的答案是否定的,至少与物理学、数学甚至是历史学的研究成果相比.
不仅哲学发现值得争议;而且,看起来哲学似乎无非就是个争议的场所.
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自己就明白这一点.
苏格拉底的对话从来都不是以一个明确的结论或者是一个类似发现的东西作为结局.
它们总是以困惑告终,没有肯定的发现.
但是,困惑会是一件有价值的事吗别忘了,苏格拉底被处死,就是因为他败坏年轻人的思想,惑乱他们,动摇他们对传统观念的信念.
因此,这种忧虑并非没有道理.
但是,柏拉图知道,这个问题应当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
他的想法非常正确.
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研究哲学的价值这一问题时,选择了用苏格拉底和一个童奴的对话来表明哲学方法.
对话的继续,在某种程度上要通过能让这孩子画出一幅画,或者干脆,通过表明一幅画怎样给人一个方法,让人想通一些事.
哲学与艺术并立在一起并非偶然,弄懂了一个,我相信,也就弄懂了另一个.
这是我在本书中不断重复的主题.
无论怎么说,我写作本书是为了多米尼克.
我不知道能否最终说服他,对此我还是很怀疑.
但我想,他的挑战,或说,至少是我认为他所提出的挑战,都是一个真正的挑战,我必须要去面对它.
我还想提到的另一个人是我的朋友——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纳格尔.
1989~1990年间,我们在哈佛大学的宿舍里住同一层楼,从那时起,关于艺术及其历史和意义,我们就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我们一起沿街散步,一起去参观纽约、华盛顿特区、巴黎、柏林、德累斯顿、威尼斯、锡拉丘兹、多伦多的艺术博物馆.
我们同时在柏林的Wissenschafskolleg学院做研究员.
2011年秋,我们在纽约联合举办研讨会,与会人员跨越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当时我的母校)和纽约大学美术学院(他的母校),主题是风格及其极端重要性,不仅是对艺术、时尚的意义,还有总的来说对人类的意义.
要不是他的合作与友情,要不是他自己写书为我树立了榜样,很难想象我会写作本书.
最后,向我的孩子们August,Ulysses,以及AnaRosa诺伊以及我的终生伴侣NicolePeisl表示衷心地感谢!
注释本注释是对正文的补充.
这里有每章的总结,正文中所涉及问题的更多讨论和参考.
希望这些注释能够加深读者对本书的理解,就像是观看棒球比赛一样,若有个朋友能与你一起讨论,必会加深你对棒球赛的感受.
前言我们只需睁开双眼,眼前就会呈现出一场色彩、形状、光影与质感的视觉盛宴:这是由我们的眼睛奇迹般地捕捉到的、一场回报丰厚却也危机四伏的物的盛会.
所有这些,都来自于我们眼睛里两个小小的、歪曲的、倒置的光影图案.
RichardL.
Gregory在《眼睛与大脑》(EyeandBrain)里的这番话表达了一个公认的观点:视觉的问题就是要弄明白,在如此薄弱的基础之上,我们怎么能看见这么多,我们怎样从"内里"——眼睛或大脑里的影像——到达"外在",我们的外部世界.
在我的书《跳出脑海:为什么不能说"脑即我"以及从意识生物学中获得的其他教训》(OutofOurHeads:WhyYouAreNotYourBrainandOtherLessonsfromtheBiologyofConsciousness)第6章中,我更为详细地分析批评了这一观点,这样一种观点的局限也是我的第一部书《知觉中的行为》的贯穿主题和基本的信念.
在《知觉中的行为》中,我提出了我称之为知觉的"行为生成观"(theenactiveapproach).
这一观点实际与我和法裔美国心理学家凯文·欧瑞根合作发表在"行为与大脑科学"上的论文中提出的"视觉和视觉意识的感觉运动"观点相同.
之所以选择用"行为生成"来重新命名我们的感觉运动观,首先是因为,这个观点的基本想法是,体验是需要我们付诸行动或要去作为的东西;它不会自行发生在我们身上.
而且,我要以此纪念2001年5月故去的神经生物学家弗朗西斯科·瓦雷拉的工作,他对"行为生成"这一词汇的使用,在我看来非常重要,且联系更为紧密.
"行为生成观"现在指的是这样一类观点:它们大致都认为,人的心思是积极主动的,它的运作机理只有与活动的肌体相联系才能得到理解,而且像计算或陈述这样一些特别知识技能的发挥并非它的基本模式.
第1章得到组织本章我引出了组织活动的概念,并认为这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普遍现象.
我们生性是有组织的,任何人类生物学的解释都必须要包含这一事实.
·欲更多了解哺乳及其在我们生活与发育中的重要位置,请参看Kaye《婴儿的心理与社会生活:父母怎样造就了人》.
在此我所说的哺乳,就我个人来讲,绝不是要把母乳喂养区别于奶瓶喂养.
尽管我在文中也用到了"母亲"或"妈妈",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排除那些非女性或是母亲之外的养育者.
文章中我把人类称作是使用语言的物种.
当然,无论就人类语言是否独一无二,还是动物交流是否也是一种语言来讲,这都尚有争议.
我不想就此表达立场.
就我的目的来讲,只要注意到语言在我们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如我所说,可能与哺乳有关,这就足够了.
·对话是一种组织活动,这一观点早已得到广泛认可,而且已成为一些令人兴奋的研究的主题.
人们谈话的时候:·有一种方言上的趋同性,也就是说,在相关方面——词汇、俚语、发音等等——他们倾向于使用同样的方式.
(见,如Giles,"口音的变换性".
)·他们往往以同样的语速讲话.
(见Street,"事实调查访谈中的话语趋同与话语评估".
)·他们往往采取同样的声音强度或音量.
(见Natale,"发挥社会期许性作用的动态交流中声音强度的趋同性".
)·他们停顿的频率几乎相同.
(见CappellaandPlanalp:"非正式交谈中的讲话与静默结果三:讲话人的相互影响".
)而且,讲话人往往会:·彼此借鉴对方的体态与手势(见CondonandOgston,"正常与病态行为模式的有声电影分析".
Kendon,"社会交往中的行为调节:案例描述":LaFrance,"体态借鉴与融洽";Shockley,Santana,andFowler,"合作性对话中会涉及一些人际间共同的姿势限制".
)·协调语言与动作的节奏(见Condon,"行为组织分析".
)·同步他们的动作方式("体态摆动")(Shockley,Santana,andFowler,"人际间共同的姿势限制".
)对此广泛现象的普遍讨论,见Shockley,Richardson,andDale,"对话与协调结构",以上引用均出自该书.
据一个前景可观的调查,对于人们谈话时这种趋同性和一致性的解释是,讲话人,连同他们的环境,在无论他们从事何种任务的场景里,都会形成一个单一的"动态体系",这一体系可以得到(非线性)数学模型和分析的检验.
关于这种动态体系模型,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它排除了人们一度以为的由讲话人掌管谈话的观点.
这并不是说,在这里我们不能谈到理智.
但这种理智是任由事情发生,任由情势来进行组织的理智,而不是慎重考虑和实施理性.
想看对此话题的开创性贡献,见Kelso,"动态模式:大脑和行为的自组织"(DynamicPatterns:TheSelf-OrganizationofBrainandBehavior).
·关于使用手机会分散驾驶注意力的文献有很多.
BrianScholl与他的团队在罗格斯大学进行的一项研究值得称道,它证明,在开车时或在做任何要求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工作时,打电话会导致明显的视觉意识受损.
(BrianJ.
Scholl,NicholausS.
Noles,VanyaPa-sheva,andRachelSussman,"打电话大大增加'持续无意性盲视'",JournalofVision3no.
9(2003):156.
)众所周知,打电话所引起的注意力分散要远远大于与同车人的交谈.
(见,如S.
G.
Charlton,"开车时的交谈:分散注意力的手机与会做反应的乘客",事故分析与预防4,no.
1[2009]:163-173.
)文章中我对此提供了解释:打电话和开车引起两个组织活动的互相冲突,结果就是组织的瓦解,由此导致盲视.
·我们的天性就是要获得第二天性(secondnature),这是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NicomacheanEthics)中提出的观点.
比如,他解释道,德性的获得"不是通过一种自然的过程,而是通过习惯……因此,德性在我们身上的出现既非出自天性,也非依靠天性,但是我们的天性就是要去获得它们,通过习惯来达到我们彻底的完美.
"在匹兹堡大学哲学家JohnMcDowell的作品中,尤其是在《心智与世界》(MindandWorld)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在《跳出脑海》第5章,我讨论了习惯这一话题.
我们已注意到,许多思想家都不曾忽视这一话题,亚里士多德是最主要的一个.
还有一个是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ThePrinciplesofPsychology)第一部中有一章他专门讨论习惯:"当我们从一个向外的视点来看有生之物时,其中令我们吃惊的第一件事就是,它们都是无数习惯的组合.
"关于习惯,有一件事情非常有趣:它一方面把我们封闭起来,另一方面却又让我们敞开.
试试去打破一种取决于任务的必须履行的职责,它既让你可以同时谈话、走路、交流、吃饭,可又一如既往地阻止你随心所欲的行动.
只要你是一个熟练的驾驶员,你就能凭习惯来开车,在这种身体惯性的组织层面上,你无需刻意引导和指挥自己的行动.
这使得你能够一路开车,一路观看风景,发现新的目标,但同时又能关注着周围路况或是听着广播.
习惯(或者说,是技巧)一方面扩大你的能力,一方面又限制你随心所欲.
洪堡大学的艺术史学家布雷德坎普(HorstBredekamp)向我指明了这一观点.
·文章中我引进了"体动层次(theembodimentlevel)"的概念.
关于这一层次有一件事非常重要,它不是完全的"属人"(personal)行动(有意识的、有控制的、由思想和计划所掌控),但要说是出自"动物性"(subpersonal)(自动的、反射的、不依赖思想和理解)又不完全恰当.
动物性层次的活动在毫秒的时间范围内展开.
与之相对,属人层次的活动发生在分钟、小时、天、周和终生等更大的时间尺度上.
而体动层次的活动,据达纳·巴拉德理解(他是首次提出这一观点的人),是在一个中间层次上展开,在秒的尺度上.
这是一个我们协调观看与看到的时间尺度,也是我们用一个眼神或是一个点头就能完成交流的时间尺度.
发展心理学家LindaSmith证实,儿童与他们的看护人进行有组织的交流、教与学的活动,恰恰是在这种看、看到、处理、点头和指点的层次上.
有关体动层次,想要了解更多,见达纳·巴拉德,MaryM.
Hayahoe,PollyK.
Pook,andRajeshP.
Rao,"DeicticCodesfortheEmbodimentofCognition(惯性认知的指示码)",BehavioralandBrainSciences20,no.
4(1997):723-742.
·"属人"(thepersonal)与"动物性"(thesubpersonal)的区别,由心理学家丹尼尔·丹尼特在《内容与意识》(ContentandConscious-ness)当中提出:当我们说到,一个人感到疼痛,并说出疼痛的位置,受到刺激做出何种反应,我们所说的都是在语言范围内能够述说的感觉.
我们可以就一个人怎样从火炉上迅速把手抽开要求进一步解释,但我们不能就"心理过程"要求更多的解释.
因为引入不可分析的心理特征会导致解释的过早终结,我们会就此以为这种引进是错误的,转而寻找另外的解释方法.
如果这样,我们就必然会放弃在可解释层次上来解释人和他们的感觉和活动,而转向大脑里的动物性层次和神经系统里的反应.
但是,当我们真的放弃了属人的层次时,我们同时也放弃了疼痛的主题.
后来,在《意向立场》(TheIntentionalStance)中,丹尼特坚持认为,实证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的任务就是要解释属人层次怎样产生于动物性层次之上并依赖于这一层次.
重要的是,他坚持认为,任何一个真正科学的认知心理学都必须是一个在动物性层次上的心理学.
因此,这也引出了许多故事和重重争议.
正是为此原因,丹尼特独创性地认识到:当我们转向动物性层次时,我们就放弃了一个人主动思想、生活和体验的主题,因为这些在细胞层次上和它们的因果网络里根本不可能实现.
第2章重组自我本章的基本论断是:艺术是一种重组织的实践;我们发现自己以不同的方式(天然的、生物的、也有文化的)被组织起来,艺术将这些组织方式用作它的原始素材.
我选取的例证是艺术舞蹈,它的职责并不是跳舞;它是要把跳舞,或者说,实际上是把我们都是舞者(因为天性使然)这一事实展现出来.
舞蹈艺术如此,其他艺术也是如此.
比如,就像舞蹈编创研究跳舞活动一样,作为艺术的绘画,就是要研究图画制作与图画应用活动(技术).
·人们有目的地参与跳舞,但他们并不决定怎样去跳.
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过会儿我再继续讨论.
这里的重点是,跳舞,与对话一样,是一种有着自己动态的活动;要想做好,你就必须任由自己被卷进这种活动中,让任务的要求为你做出决定.
但是请注意,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个具有思想和自我意识的舞者.
我们一边进行着流畅、自发的对话,一边还能注意自己的口误,或是其他类型的语言不当;就如我们可以一边谈话一边思考自己所说的一样,我们也可以带着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参与跳舞这样的组织活动.
同时请注意,此处我的评论并不适用于专业舞者.
专业舞者在跳舞时当然能够有思想地控制自己的动作.
当然,从我的意义来说,专业舞者并不是真正的舞者.
他们是在用跳舞工作.
关于专业技巧和自我监控的整个问题,以及这些主题与组织活动的联系,我希望在别处能够重拾这一话题.
相关讨论可见BarbaraGailMontero,"TheMythof'JustDoIt,'""TheStone",TheNewYorkTimes,June9,2013.
·舞蹈编创不是跳舞,但它直接参与跳舞,这一观点引发了一个重要的评论.
过去的50年里,有许多艺术舞蹈根本不是来源于跳舞,而是有着完全不同的来源.
有些编创舞蹈的一个重要关注就是动作,或者说肢体、或是肌体体验本身.
另一个来源是表演——舞蹈表演,但也有其他种类的表演.
我并不想把其中任何一个排除在外!
我的重点是编创舞蹈与组织活动相关,组织活动是它的前提,这就好比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哲学,无论在构筑关注时与科学有多么紧密的联系,它都不只是"更多的科学".
它所做的乃是别的事情.
要么多一点,要么少一点,关键是,要有所不同.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写道:"'哲学'一词必然意味着它是在自然科学之上或之下,而不是与之并肩而立的东西.
")·艺术舞蹈与组织:文章中我的论断是,舞蹈,既然它是一种艺术,其目的并不在于更好地跳舞或是更好地实现作为舞者得到的组织;它的目的是要向我们展示作为舞者的自己.
这值得我们对比另一相关的观点:舞蹈编创的问题恰恰是组织的问题,但这是从专业或技术意义来理解的组织.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舞蹈,就与音乐一样,它关注的是在空间和时间上来编排组织结构.
如此想来,我们就有可能看到,舞蹈编创的原则和问题不仅会在像音乐和建筑这样的艺术里发挥作用,在商业、城市规划、布置餐桌和用餐中也同样有所表现.
这反过来又让我们想到了另一观点:舞蹈编创——可能在你看来这是娱乐业的一个分类,不过是把舞蹈呈现在舞台上供人娱乐——实际上是一个正规的、真实的研究场所,它研究的是应用于娱乐业之外的广泛的一系列观点、原则和策略,其中有些可能与工程师、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兴趣现象和问题密切相关.
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观点,对此我完全同意.
但是,值得强调的是,我所说的舞蹈编创作为一种重组织实践的概念有所不同.
舞蹈编创在重组织中的兴趣不是工程师或技师的兴趣;它的目的不是成为一种活动的主宰,也不是要把管辖这种那种组织的物理的、心理的或动态的原则表现出来.
舞蹈编创的关注要在所有这些之先,或是在所有这些之后.
它们是哲学,其目的是要把我们自己放进视野进行研究.
·马图拉纳和弗朗西斯科·瓦雷拉在《自我创生与认知:生物的实现》(AutopoiesisandCognition:TheRealizationoftheLiving)中提出了自我创生的理论.
关于自我创生对于生物学以及心学研究的意义,伊凡·汤普森的《生命中的心智》(MindinLife)里提供了更为详尽的讨论.
汤普森强调了一点,启发了我在正文里的评论:达尔文的物竞天择提供了一个解释跨越生物种群性状频率变化的理论框架;但这种理论不能解释,它并不试图解释有机体——生命的最初起源.
对于这样一个有关生命本身、有关有机体的根本解释,想来康德心里有着突出的需要:很显然,有关组织生命和它们的内在可能性,单指望自然力学原理,我们永远无法获得一个充分的知识,更不用说要得到一个解释了.
事实上,它是如此明确,以至于我们可以自信地认为,人类哪怕是有任何这样的想法来取悦自己都是荒谬的,更不要去期望某天会冒出另一个牛顿来让我们知道,即便是一根小草的源生都是来自于自然规律,无需任何设计.
这样的见解我们必须向人类予以明确地否认.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s)中说道:"哲学问题的形式是:'我找不到出路'.
"第3章天生的设计师本章的论点是技术在人类是基本的.
它们是组织的核心.
这解释了艺术对制造和技术的永恒关注,它总是在制作、做、建造和展示;但是艺术的意义永远不会被任何衡量我们能做到多好的既有标准所穷尽,哪怕是接近.
艺术摆布技术,因为技术——乔装成图画、语言本身、服装、建筑的样子——组织我们并束缚我们.
艺术不是技术,但艺术要以技术为前提,就如反讽要以直言为前提一样.
关于艺术作为创作活动,约翰·杜威在《艺术即体验》(ArtasExperience)中写道:艺术指的是一个做和制作的过程,无论是美术还是技术性艺术都是如此.
艺术包括了制陶、凿大理石、铸造青铜器、铺陈颜料、建造房子、唱歌、演奏乐器、在舞台上扮演角色、合着节拍跳舞等等.
每种艺术都要做点什么,用某种物质材料、身体或身体以外的某种东西;使用或者不使用工具;且时刻关注着某种可见、可听或可触摸的东西的生产.
杜威说,"无论是美术还是技术性艺术都是如此.
"当然,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和困惑:我们知道为什么说技术是一种做和制作的过程,技术——工程、制造——的职责就是要解决问题;它为功用服务.
但是,艺术本身为什么要与制作如此紧密地相联或者说,为什么它要像杜威列举的那样关注制造这也是本书中我为自己设置的问题.
杜威继而提供了一个线索:"人们切削、雕刻、唱歌、跳舞、做手势、铸造、描摹、绘画.
当感觉到的效果是这样一种特征,即它的性质给人的感觉是已经掌控了生产的问题时,这种做或制作就成了艺术".
·正文中我坚持认为,图画是技术,图画使用是一种组织活动.
要让这一主张变得丰满起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毕竟,图画的使用很多样;还有制作图画;然后还有,我们操作图画的方式:例如,在翻阅图录、点击网页链接时,我们怎么操作它们.
第1章中我所列举的组织活动的6个标准,在图画的情形中,除两个之外其他都能直接适用——图画需要成熟的认知;我们对它们的使用是自发的、未经操控的;图画服务于有明确用途和功能的事务;图画以及我们对它们的使用可以是快乐的源泉.
但是,第一个和第三个标准怎样根据我指出的第一个标准,组织活动应是基本的、原始的、天然的.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严肃地以为,图画使用活动是基本的吗实际上,我认为可以.
我们观看图画有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第12章和第13章中我探讨了这一话题——图画感觉直接,且不需依赖知识和学习.
用图画,我们仿佛真的能够看到它们所展示的东西;我们不需解释图画就能看到它们显示的东西,至少通常状况下不需解释.
但是,事实上,这种直接的表象是需要解释的东西,只是被最终解释偏了.
要看懂图画,并看到它们试图对我们展示的东西,需要有对语境的了解和意识.
但是标准的重点——这里指我们的主要关注——并不是强调图画使用不需要学习或是原始的、自然的,在这种意义上,它丝毫不亚于语言的使用;标准的重点是,它呈现在我们面前是可以直接感知到的;我们无需辩论或推理来确保它的清晰性.
我们可以说,图画使用、图画观赏都是习惯性的.
想到此处,值得记住的是,我在正文中也提到多次,我们使用图画至少已有3万年的历史;而且,现在看来,与我们相近的物种,如尼安德特人似乎也与我们有着同样的历史(据新近的发现;见JoaquínRodríguez-Vidal等"尼安德特人在直布罗陀留下的石刻").
至于第三个标准——组织活动有着空间和时间组织的特别模式——严格来讲,我们对图画的使用(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否具有这种组织,是一个开放性问题.
我敢保证它有.
图画制作和图画使用——与所有工具的使用一样——都要涉及在空间上以自己特别的节奏和运动模式从事活动.
要进一步研究,对此深入调查是一个挑战.
图画制作是我所说意义上的组织活动,有些轶事可作为我的论断证据:有两次艺术家为我画像,我有机会坐在他们面前,仔细地观察他们的作画过程.
两次活动和画像过程的动态都令我感到无比惊诧.
没有任何分神的东西,没有对它的沉思.
艺术家贪婪地将我置于视线内,哪怕是在他转向画面的时候.
在一种不间断的、充满活力的、来来回回地画画看看、看看画画的过程当中,我根本不是被审视,简直就像是样本一样在被品味、被处置.
在这种图画制作活动中,的确有些东西就像跳舞一样,有节奏、有动感.
它是身体的、行为的,但同时也是充满思想和智慧的.
杜威如此说道:由于对所做和所受之间关系的感知构成了理智的工作,也由于艺术家在工作过程中要受控于他对已做事情和将做事情间联系的把握,认为艺术家不能像科学研究者一样专心致志、深入透彻地思考,这种想法是荒谬的.
一个画家必须有意识地去感受自己画出的每一笔的效果,不然他就意识不到他在做什么,他的作品会向什么方向发展.
而且,他必须联系自己想要产生的整体效果,来看到他的做与受的每一个具体联系.
去体会这样一些关系就是去思考,而且是最为严谨的一种思考方式.
·关于技术和人类演化,有许多文献可参考.
我发现有些书特别有益,本章中我依赖的是HaimOfek的《第二天性:人类演化的经济根源》(SecondNature:EconomicOriginsofHumanEvolution)以及MattRidley的《理性的乐观主义者:繁荣如何发展》(TheRationalOptimist:HowProsperityEvolves).
关于这一话题,我从伦敦大学学院的遗传学家MarkG.
Tomas那里学到了很多(2007~2008年间我们同在柏林Wissenschafskolleg学院共事).
好多人认为,我们成为心理上的现代人是由于大脑的变化("大脑突变"),但他让我知道,除此之外还有另外的看法.
·关于服装的史前起源,见RalfKittler,ManfredKayser和MarkStoneking的《虱的分子演化与人类服装起源》(MolecularEvolutionofPediculushumanusandtheOriginofHumanClothing),在《黎明之前:发掘人类祖先失传的历史》(BeforetheDawn:RecoveringtheLostHistoryofOurAncestors)中,NicholasWade对此有着更为详尽的关注和见解.
另见他的"虱子讲述的故事"(WhataStoryLiceCanTell),TheNewYorkTimes,October5,2004,F1.
·关于技术及其独特的演化模式,W.
BrianArthur的《技术的本质》(TheNatureofTechnology:WhatItIsandHowItEvolves)是一部优秀的著作.
·关于销售团队的软件产品Chatter(吱吱喳喳)及其运作的信息,感谢我的朋友DeanMoses,他是销售团队的软件工程师.
·关于符号对思考的重要性:请注意,既然我们有时会以符号体系进行思考,那我们就有可能通过研究符号体系的运作来研究我们的思考.
比如,在一个叫作证明论的数理逻辑学的分支学科里,我们可以确立一种书写语言(一个"正式的体系")是完全的(即在某个特定的领域能够被用于确立所有的真理),或是可靠的(即所有的理论事实上都是正确的).
这些都是对符号本身结构的数学研究.
·工具既能延伸我们的思想也能延伸我们的身体,这是AndyClark作品的一个主题.
见他的《拓展心智:体现、行动和认知延伸》(SupersizingtheMind:Embodiment,Action,andCognitiveExtension),以及他与纽约大学哲学家戴维·查莫斯(DavidJ.
Chalmers)合作的论文"延伸的心智"(TheExtendedMind).
但是在他们讨论之前,关于心智延伸的观点早已有之.
比如,毛里斯·梅洛庞蒂在《感知现象学》(PhenomenologyofPerception)中写道:一个女人不用任何明确的计算就能让帽子上的羽毛远离任何可能损伤它的东西;她能感觉到羽毛在哪儿,就像我们知道自己的手在哪里.
如果我有开车的习惯,那么当我开进车道,不必对比车道与车保险杠的宽度,我就知道我能过去;就如我不必对比门的宽度和我身体的宽度就穿过门一样.
帽子与汽车都不再是需要通过对比其他物品才能确定其大小和体积的对象.
……盲人的手杖对他来说不再是一物件,它被感知已不再是因为它的自身;相反,手杖的最远端变成了一个敏感区域,它扩大了触摸的范围和半径,甚至已经可以与凝视相比拟.
在探索物体时,手杖的长度既不会明确地干预也不是充当一个中间介质:盲人通过物品的位置得知手杖的长度,而不是通过手杖的长度来知道物品的位置.
这里,很显然,梅洛庞蒂把手杖、车、帽子上的羽毛实际上都当作是身体的延伸部分,因此,既然延伸的身体有知觉、感受和感觉,而且能够解决问题,那它就属于心智的延伸.
梅洛庞蒂受到海德格尔在《生存与时间》(BeingandTime)中对待工具的影响.
在海德格尔看来,工具重要的是,它们并非作为我们观察、思考、评判和应用的对象出现在我们面前.
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在我们面前出现根本不是让我们看的.
我们把它们视作理所当然;我们就像依赖地面一样依赖它们;它们后退到背景之中,至少在我们认识它们、了解它们且掌握它们的时候.
工具实际上并不是对象,它们是器具.
海德格尔并不认为工具通过延伸我们的所为而延伸了我们的心智,相反,他说,它们创生了我们的世界,以一种我们在主客体模型中所无法理解的方式.
在海德格尔看来,梅洛庞蒂以及Clark和查莫斯也是一样,人与环境的界限,或者说自我与世界的界限并不是由大脑的界限来界定的(这也是我的书《跳出脑海》的主题).
在《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s)中,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也表达了极其相似的观点,他写道:当我用手杖触碰物件时,我触碰的感觉在手杖尖上,而不在握它的手上.
当有人说,"疼痛不在我手上,而在手腕,"其结果是医生会去检查手腕.
但如果我说,我感觉物体的硬度在手杖尖上或在我手上,会造成什么区别呢难道我说的意思是"这就好像是我的神经末梢长在手杖尖上一样"在何种意义上它会像这个样子——好吧,我想说的是,"我的手杖尖感觉到了硬度等.
"随之而来的是当我触碰物体时,我看的不是我的手,而是要看手杖尖;我会这样描述我的感受,"我感觉那里有一个坚硬的圆东西"——而不是说"在我的拇指、中指和食指指端,我感觉到一种压力……"如果,比如说,有人问我,"那你握手杖的指端现在有什么感觉"我可能会回答:"我不知道——我感觉那里有一个粗糙的硬物.
"我们可以看出,当维特根斯坦说我们并不是把手杖当作是一个中间介质,由此获得对对象位置的推测时,他实际提出了梅洛庞蒂心里所想的问题.
梅洛庞蒂关注的是现象:他认为我们通过手握手杖的体验从而推测出对象的位置,会大大地歪曲事物出现在手杖使用者心里的样子;如梅洛庞蒂所说,我们是通过对象的位置知道手杖在哪而不是相反.
而与梅洛庞蒂相对,如常一样,维特根斯坦关注的是,比如,关于到底是哪里感到手杖的坚硬和圆滑,要怎么说才更有道理.
维特根斯坦在其早期的作品《蓝皮书与褐皮书》(TheBlueandBrownBooks)中也曾提到过这一主题:只要我们懂得这些陈述的语法,那么如此说就是正确的:思想是我们书写的手、我们的喉、我们的大脑以及我们的心进行的一种活动.
而且,极其重要的是要意识到:由于我们对表达语法的误解,往往会导致我们以为是其中某个特别的陈述给了思想活动实在的位置.
维特根斯坦不是想否认当我们说思考是头脑的活动时,我们的正确性,而是想提醒我们,这并不意味着只有我们的大脑在实际进行思考活动,这就好比我们说只有手在实际进行思考也对一样.
第4章艺术魔圈与伊甸园本章是全书的核心.
艺术(以及哲学)不只研究、示范和展示我们自己的组织模式;它还改变我们被组织的方式;它会轮转回来重新组织我们.
之所以能做到这样,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它们给我们新的资源来思考我们所做的事;由此,让我们形成智慧以不同的方式来做这些事.
·这里我借用了加拿大科学哲学家伊恩·哈金(IanHacking)的美妙观点,他在《何为社会建构》(TheSocialConstructionofWhat)中提出了魔圈概念和魔圈效应,比如,同性恋、教授、啦啦队队长、黑人、白人、女人、男人等等,像这样的归类都能表现出哈金所称的"魔圈效应".
它们不仅被用于人身上,在他们共同特征的基础上给他们进行了归类;这种归类还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看待自己的方式.
比如,做一个异性恋的人,不只意味着你要有某种特定的行为方式或行为倾向,还意味着你要以此方式来看待自己.
有了这种看待自己的方式,那么就会有一整套相应的复杂的品质、限制以及期望和固定的想法等等,它们会反过来影响我们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倾向.
既然异性恋的人要有异性恋的表现,同性恋要有同性恋的表现,男孩要像男孩,女孩要像女孩,如此等等——既然我们甚至都明白这在语言上意味着什么——那么,这充分说明情况的确如此,因为人们认同自己属于哪个特定归类就会有意无意地做出选择去遵从这一归类应有的品质特征.
我们按照我们应有的行为方式来处事,照我们应有的装扮方式去装扮自己.
用我的方式来说就是,我们通过履行某个标签或归类的要求而生成或创造了自己.
如哈金所说:"魔圈效应表现在时时处处.
想想天才的归类让那些发现自己是天才的浪漫的人都做了些什么,他们的行为反过来对天才这个归类本身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再想想因受肥胖、超重、厌食症这些概念的影响都产生了哪些转变.
"比如,有人说厌食症是一种新奇的疾病,只见于西方国家.
人们说的没错,它的确是一种社会建构.
虽说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真实存在.
我们会依据对自己的理解而将归类实在化.
以人种为例,"黑人"和"白人"根本没有任何有意义的生物学基础,这一事实——我把它看作是一个事实——并不意味着这种区别不现实存在.
如果我被贴的标签影响了人们对待我的方式,以及我会有的选择,我可能选择什么样的配偶,我可能会居住在哪里,以及我因此最终认为,关于我自己这些有可能或有道理,那么,不用太久,我们就会制造出(或发展出、或构建出)一种以前不曾有过的实在的差别.
这类事例表明,关于身份,你无法分开哪些事实属于一阶、哪些属于二阶.
我们所属的那个类别形成了我们对事情的体验方式,因为在我们经历的事情中间就是有关我们归属的事实,以及因为我们属于哪个类别而会受到怎样对待的事实.
这不是一个有关学术兴趣的微妙的哲学问题,它能在我们生活中造成很大的差别.
来看心理学家CordeliaFine曾探讨研究过的一个问题.
研究中,一所私立大学的学生们被要求来执行一项空间推理的任务.
测试之前,一组学生填了一份表格,表格要求他们填明自己的性别.
另一组则没有被问及这样的问题,而是被要求填上自己的大学名称.
这样一来,一组被"事先设定"把自己的身份以性别来区分,而另一组则被设定为自己属于"私立大学学生".
事先设定认为是性别表现的那一组男性表现明显要优于设定自己为大学生的那些男性.
女性的结果则恰恰相反.
那些被设定认为自己的身份是大学生的一组表现远远超出那些被设定认为自己是女性的一组.
单是这些问题——男性女性学生——通过提醒学生们是哪一类人,就决定了他们在测试中的表现方式.
如果生物学是所有事情的测度标准,那么,用来划分我们属于哪类人的许多归类——男人、女人、同性恋、异性恋、黑人、白人、教授、啦啦队长——事实上都是毫无根据的.
脱离我们对那种天性的态度和信念,你无法在天性中找到它们.
而同时,能有什么比我们自身的体验更为真实呢这表明生物学并非是所有事情的测度标准.
关于隐含的偏见和固定看法的心理文献的进一步探讨,见CordeliaFine《性别的错觉》(DelusionsofGender).
在此我的讨论节选自我的"性别死了!
性别万岁!
"·动作库(motionbank)是弗西斯和ScottdeLahunta领导的弗西斯舞团组织的研究项目的名称,其目的是建立舞蹈编创作品的网上数字记录,并由此鼓励编创舞蹈的研究.
我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这一项目,在此推荐网站:www.
motionbank.
org.
是弗西斯想出了"动作库"这一名称.
说到一幅画看起来像什么,或雕塑是什么,我们记忆里都储存有很多的形象.
但是关于舞蹈是什么或它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我们却没有一个类似的形象"库".
这一项目旨在朝这一方向做出努力,(从启动一次谈话开始)提供这种需要的动作库.
·书写塑造了我们关于语言的思想和体验,这一观点是语言学家罗伊·哈里斯(RoyHarris)的一个核心关注和最初的见解.
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牛津大学上过哈里斯的课.
他的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语言创造者》(THeLanguage-Makers)和《语言神话》(TheLanguageMyth).
哈里斯的《文字的起源》(TheOriginofWriting)对本章话题有着特殊的意义.
·正文中我给出的语言教科书的大段引用选自AndrewRadford的《转换生成语法:乔姆斯基扩展标准理论的学生用书》(TransformationalSyntax:AStudent'sGuidetoChomsky'sExtendedStandardTheory)(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1)中有关语言结构的章节.
该书是我20世纪80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本科时语言学课程指定的必读书目之一.
·书写歪曲了语言原本的样子并管制了语言,而且它使得某些语言形式凌驾于其他之上,这是一个熟悉的观点.
这与规定性语法和描述性语法众所周知的区别密切相关.
规定性语法告诉你,你应该怎样说话;而描述性语法,我们被告知,只是观察人们实际是怎么讲话的.
还有一句著名的格言,出自意第绪语专家MaxWeinreich,"语言就是拥有了陆军和海军的方言.
"这通常被理解为,所有的讲话方式,在所有社群当中,就语言来讲,都是平等的,不分轩轾.
这当然很好.
毫无疑问,高雅德语只是又一种德语方言,并非天生有异于(更别说要优越于)某个小村庄里所说的方言.
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应充分认识到,一些本应是外在的因素——文字、词典、大学、电视、广播等——事实上怎样给了语言的使用者资源,使得他们实际上能够用语言对他们的生活有不同的思考,如魔圈效应的一贯情形一样,我们所处的领域预言总能实现.
对此,需要给出一个局部重点和一个更为普遍的重点.
局部重点就是写作、拼写、文体以及所有给讲话人自己的实践提供规范的语言文化机制,这是他们作为语言使用者可以利用的东西.
你对书写的关注会改变语言环境.
更普遍的重点是,对我们来说,现在再来对比语言,如它被民族、国家、大学、文字和学校、出版业、词典及所有其他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外饰所改造的样子,还是如它本初实际处于某种简单的语言核心的样子,已不再有意义.
这是本章的要点之一:我们对语言的现实体验已被书写及所有其他东西彻底塑造.
我们不可能剥离外在的因素.
我们不可能回到伊甸园.
·哲学家戴维·查莫斯使用的伊甸园的概念与我在本章中的使用关系密切.
查莫斯使用这一概念的含义主要是想找到,我们为了追寻自己知觉体验的本质而做出的最原始的努力.
他讲到,在伊甸园里,在我们没有吃智慧树的果子之前,表象和实在之间是没有差距的.
事物的实在就是它们看起来的样子.
而科学挑战了这种原始的伊甸园现象学;比如,我们后来得知,我们所看到的红色不在西红柿,而是西红柿通过光的方式,作用于我们的神经系统而造成的效果.
本章中我对伊甸园的观点进行了不同的利用.
我建议,你必须要回到伊甸园才能找到一种没受到我们应该怎样讲话的共同规范影响的语言方式.
这就是说,没有也从不曾有过一种未受语言意识形态影响的口语.
见《知觉体验》(PerceptualExperience)(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6)中查莫斯的"感知与伊甸园的堕落".
·柏拉图对诗歌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理想国》第10卷.
·更多关于口头表达和书写文化的讨论,见WalterJ.
Ong的《说话与识字:文字的技术化》(OralityandLiteracy:TheTechnologizingoftheWord).
更多关于柏拉图论诗歌,见EricA.
Havelock的《柏拉图导言》(PrefacetoPlato).
·我们并非发明文字来代表语言;我们是将已然存在的书写工具应用到讲话当中.
这是哈里斯有关书写的书中的核心论断.
·我的有关语言、文字的想法,以及本章的主题,得益于与香港大学语言学家ChristopherM.
Hutton的交流.
·感谢音乐学家LeoTreitler,我在纽约人文学院的会议上结识了他,并就贝多芬和乐谱与之进行了交流.
第5章艺术、进化论以及谜中之谜本章里,我论证到图画会改变我们观看的方式.
我的建议是,若没有图画,至少说没有赏画态度,我们所称的"审美意识"根本不可能形成.
作为一个物种,或者说作为一种文化,几万年来我们一直在创作图画.
在此背景下,我探讨了人们在广义的进化论框架里解读艺术和审美体验的尝试.
我坚持认为,进化论对艺术的这种研究极不成功.
然而,关于审美意识的进化论概念倒是有更为广阔的前景.
·在《理想国》第10卷中,柏拉图谈到了图画和镜子.
以下是相关段落,苏格拉底先问.
苏:但是现在请考虑一下,下述这种工匠你给他取个什么名称呢格劳孔:什么样的匠人苏:一种万能的匠人,他能制作一切东西——各行各业的匠人所造的各种东西.
格:你这是在说一种灵巧得实在惊人的人.
苏:请略等一等.
事实上马上你也会像我这么讲的.
须知,这同一个匠人不仅能制作一切用具,他还能制作一切植物、动物,以及他自身.
此外他还能制造地、天、诸神、天体和冥间的一切呢.
格:真是一个神奇极了的智者啊!
苏:你不信请问,你是根本不信有这种匠人吗还是认为,这种万能的工匠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可能有的,在另一种意义上说是不可能有的呢或者请问,你知不知道,你自己也能"在某种意义上"制作出所有这些东西格:在什么意义上苏:这不难,方法很多,也很快.
如果你愿意拿一面镜子到处照的话,你就能最快地做到这一点.
你就能很快地制作出太阳和天空中的一切,很快地制作出大地和你自己,以及别的动物、用具、植物和所有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些东西.
格:是的.
但这是影子,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呀!
苏:很好,你这话正好对我们的论证很有帮助.
因为我认为画家也属于这一类的制作者.
是吗格:当然是的.
苏:但是我想你会说,他的"制作"不是真的制作.
然而画家也"在某种意义上"制作一张床.
是吗格:是的,他也是制作床的影子.
·安妮·霍兰德的《服装纵览》(SeeingTroughClothes)令人兴奋,该书给了我本章的灵感.
它是西方艺术中一部关于人们对待服饰、对待着装身体的历史.
第6章专门探讨镜子,她是这样写的:"照镜子的人是在参与一项于生活中进行艺术创作的想象性活动(并不总是有意识的):他(她)的目的是把影像塑造成一幅为人所接受的图画,这种行为具有瞬间性或重复性,而且除了借助眼睛没有其他手段".
关于霍兰德观点的某些评论摘自我于她死后发表的一篇"致谢"短文:"透过安妮·霍兰德的眼睛世界看起来更美".
·如第3章中的引用一样,尼安德特人从事图画创作的证据在JoaquinRodriguez-Vidal等人的"尼安德特人在直布罗陀留下的石刻"中有所呈现.
·视觉本身属于文化的观点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史学家惠特尼·戴维斯(WhitneyDavis)研究的主题思想.
艺术史的奠基人物之一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Wofflin)曾说:"视觉本身有它的历史.
"戴维斯对此观点进行了扩展,他说,视觉有着艺术上的历史.
在沃尔夫林看来,用戴维斯的话说,"描绘风格——处于文化之中、有着独特历史印记的图画再现的创作方式——已经大大地影响了人类的视觉感知.
它们构成了我们字面所称的观察方式.
"作为这些过程的结果,视觉,用戴维斯的话表达,"继承了视觉文化(visuality)".
也就是说,它继承的视觉具有这种意义:产生新的、承担了文化意义的和增强的视觉能力(或"视觉文化",或"视觉的文化性").
戴维斯在此所说的继承,而且他强调它必须是真实的历史现象,在人类生活及个体生活发展中都有所呈现,就是他用在我一直描述的那种魔圈中的语言.
用我的方式表达就是,图画反过来改变了我们对它们展示内容的思考方式,就如写作会反过来改变我们的说话方式一样.
见沃尔夫林《艺术史的基本原理》(PrinciplesofArtHistory:TheProblemoftheDevelopmentofStyleinLaterArt)以及戴维斯的《视觉文化的一般理论》(AGeneralTheoryofVisualCulture).
戴维斯坚持认为,艺术史学家(以及视觉研究学者)没有权利猜想视觉是属于文化的,它需要证明.
这着实令人敬佩.
在戴维斯看来,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研究"继承的递归"(recursionsofsuccession),即视觉由此获得文化地位的那种机制,包括文化的和个人的(也有人际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研究视觉、继承视觉文化中间所需的"传递、递归、阻力和继承权".
他这古怪的措辞,不管怎么说,在我看来还是极受欢迎的.
戴维斯宣称,"视觉并不天生就是视觉文化".
我理解他这么说的意思是,视觉并非天生就弥漫着文化.
至此,最后这点似乎有点疑问.
我们可以承认,当然也必须承认,个体生理是人类所有视觉能力的基础,因此,可想而知,视觉总能运行,在人类(可能还包括其他动物)生活中一如既往地运行,哪怕没有成熟的绘画和充分发展的语言,至少还有它们成熟的先行者.
而这些先行者可能会以两种基本形式出现.
首先,有思想.
我同意JohnMcDowell的观点,也是康德的观点:直觉没有概念就是盲目的;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TheCritiqueofPureReason)中承认(或坚持认为):思想没有直觉就是空洞的.
人类(或动物)的感知体验需要运用理解能力.
现在,这种运用不能还原为生理能力的运用.
而且,它很有可能是共有的和文化的.
我们来到这世界上不单单要思想.
因此,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也不能单靠我们自己的知觉.
第二,还有我在第4章中所说的书者态度或画者态度.
这些都属示范态度的不同种类,也就是我们的普遍立场,在这个立场上,我们不仅要对事物的状态,还要对我们应该怎样思考、反思、看待和描述事物的状态,进行批判性地反思和评价;我们关心的是,哪些是正确的、对的、规范的、有道理的,以我们说话的方式,以我们对世界的体验.
如果我们承认书者态度的确是书写的一种原型,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不过看起来有点像是悖论),在书写出现之前早已有了书写,在图画出现之前早已有了图画,至少是这种引申意义上的书写和图画.
书面语言的实际发现和图画制作的发展并不会改变任何事情或标志一个新的世界观.
这不是一个分水岭.
这番考量的结果就是,用现象学家钟爱的一个词语来说,我们从来就已经是文化的,哪怕是在使用视觉这样的生物能力上.
用戴维斯的话说,视觉从来就是一种视觉文化.
也可能,把"视觉文化的继承"看作是一种历史现象最终会是一个错误.
如果我说的没错,它是一种史前现象.
我们需要重回伊甸园才能找到那个时段,语言还没有受到书写的改造,观看也没有受到图画的改造.
因此,我们的视觉生活像现在一样被图画改造并不是历史的偶然.
我们关注的不应当是关于它本源的故事,而应当是一个本体论的故事.
·有一位艺术史学家的历史性故事讲述方式表现了我所描述的那种对魔圈或递归的本体论敏感,他就是亚历山大·纳格尔.
在《中世纪的摩登:跨越时间的艺术》(MedievalModern:ArtoutofTime)(NewYork:TamesandHudson,2012)中,他讨论了法布里亚诺(GentiledaFabriano)的油画"在圣尼古拉斯墓旁得医治的残疾人和病人"(TheCrippledandSickCuredattheTombofSaintNicholas).
这幅油画描绘的是,在教堂后殿给人康复的石棺前,病人和残疾人在祷告、触摸和感恩;教堂的墙上有一幅镶嵌画,描绘的恰恰是同样的主题.
在某种意义上这毫不稀奇,这些朝圣者的行为是几个世纪来朝圣者的典型行为.
镶嵌画里描述的并非这一确切的场景,而是与它同属一类的场景,是更早时期来到教堂的一群不同的朝圣者.
但画中记录的不仅仅是朝圣者的例行行为,它还表现了现实中的朝圣者怎样通过遵循图画给他们树立的榜样来模仿早期朝圣者的行为.
法布里亚诺画里的朝圣者正是在遵行教堂后殿镶嵌画里树立的典范.
但据纳格尔说,油画还有别的意义.
它不仅记录了朝圣者的例行行为,还记录了艺术创作者的例行工作.
因为,油画本身创生了一个过程,在这过程中,一幅画(在此是法布里亚诺的画)是对另一幅画(描绘的、假想的镶嵌画)的回应,事实上也是对另一幅画的模仿.
纳格尔写道:"重要的是,在我们眼前的不仅仅是后殿镶嵌画中场面的再现.
它给出的是一种记录,对发生在这世上的、包括发生在艺术创作世界里的日常模仿的记录.
艺术作品以早期的艺术作品为楷模,朝圣者以早期的朝圣者为榜样.
这幅油画让我们看到这些过程的相互作用,甚至是两种过程之间的互动交流.
"法布里亚诺的油画给人带来一种眩晕和倒退感.
我们看到一幅教堂的画里画着同一座教堂,以及其他.
日常的感知生活并非以同样的方式像这样充满矛盾;但有些类似的东西在继续.
当我们看到一座实在的教堂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想法或概念的执行;它必定源自于一个设计或是一幅图画.
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看到的所有东西都在图画中,就像教堂的圣徒在教堂的画里一样,这种结论是疯狂的.
但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对现实存在的把握,尤其是我们对所见东西的把握是被图画组织起来的却一点也不疯狂.
·关于图画与文化:本章的中心观点是,图画是一种技术,它改变了我们的观看方式,就像是书写技术改变了我们的谈话方式一样.
在第12章和第13章中,我将论证图画并不真的是光学现象,它们是交际工具.
它们是用来展示的工具,而且只有在交际场景中,它们才真正有效、真正起到描绘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它们是能够改变我们观看方式的展示工具.
这使得观看以及图画都具有文化性,但并不会因此抹杀它们的本性.
通过说它们具有文化性,我是想排除这种可能:图画仅靠神经系统就能运作,无需经过思考、交流、理解或意图的作用.
因此我的解释与英国艺术史学家约翰·奥尼恩斯(JohnOnians)的立场(在他的文章"神经考古学和肖维岩洞壁画呈现的起源"中形成)并不一致.
奥尼恩斯认为,图画——甚至肖维岩洞艺术中的精致图画——都可能是产生于强烈神经反应的结果.
他写道:"一个自然的图像可能完全自然而然地产生,依赖的不过是人类神经系统组成的常规运作.
"奥尼恩斯的解释真是天才无比.
大致说来,其观点是这样的:在洞穴岩壁上看见一个熊掌印可能会自然地激发我们去做熊所做的事情(归因于"镜像神经").
然后,我们可能会从自己留下的印记获得直接的愉悦,且发现自己愿意重复去做,因为我们的视觉神经系统可塑性地适应我们自己的行为结果.
而且,在洞穴岩壁表面看见一些对我们至关重要或激发强烈感受的事物——比如野兽和猎物——的自然图像,再想起我们自己偶然留下印记的后果,我们会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去强化和阐述我们的所见,每次尝试都会产生一种更强的视觉、情感反应,导致我们做出更多行动.
"持续的活动很有可能被大脑的化学物质所引发,"奥尼恩斯写道,"而每一次对应的强化都会引起大脑神经传递要素的释放,它们驱动着对我们生存至关重要的所有行动.
"以此方式,"不需任何人教、不需指引或其他社会刺激,一种无意识的反馈过程可能由此就导致了一个高度自然的再现图像的产生.
"那么,这一解释令人瞩目,且看上去似有道理,是因为它认识到图画制作产生于做、经受、观看、感受、回应、做得更多这样一个循环过程.
我们当然可以想象,用这样一些单一的流程来解释在人或动物身上所有形式的技能和特征的形成.
比如,令我吃惊的是,照此情节发展的故事会导致自慰的发现,这貌似还真有道理.
一个人可能会不期而遇一种后果,喜欢它、重复它、越来越喜欢,然后持续下去.
但我觉得很难令人置信,这样一种从根本上来讲纯属反应的、感受的、自动的单一活动能够催生出像我们在肖维岩洞中发现的那样的图画.
如果图画是我们以此方式学会制作的刺激因素,是在神经基础上反馈过程的结果,那么,难道我们不应期待会发现乱写、乱画、草稿和实验吗我们又为什么要进入到阴暗、偏僻、难以抵达的洞穴里去制作图画奥恩尼斯说道,洞穴,在火炬的照亮之下,当然是视觉观感令人惊叹的地方.
在我看来,这么说的前提必然是:洞穴画者是观察者或审美家,他们退一步观看,凝神沉思.
但是,这种态度已经是一种赏画态度.
观察世界并欣赏它的样貌的能力——与一个人打猎、攀爬或洞穴探险时对环境所进行的视觉活动相反——是我们对图画感兴趣的表达,而不是我们不断发展的图画技术的起因.
洞穴画者深思熟虑且充满了兴趣,对此我认为不应怀疑;他们是当之无愧、地地道道的创作者;他们是专家.
奥恩尼斯在这样写时似乎留出了足够的空间:"对于手所能做的事情的记忆,当时很有可能预设了一些相关的原动系统,而这完全能够鼓励人们以后重返洞穴,带着熟悉的工具、石头和树枝、赭石和木炭,控制手的神经系统,手上已准备好要扩展或完成一个想象中的图像.
"谈到记忆和鼓励,以及想象中的图像,当然都让人想到一幅景象:这是充满思索的人们在有见识、理性地制作图像.
毫无疑问,神经系统能够让人完成这种活动,但这种活动是人而不是大脑在实施的活动.
有种观点说,我们的祖先制作图画是为了挑逗,是一种视觉自慰;与之相对,我的建议是,我们制作图画是为了展示,或思考我们所描绘的东西.
我们的目的不在于绝对的相似;我们的目的在于表达交流.
从这一观点来看,图画制作发生在洞穴中就不足为奇了.
像电影院、礼堂或画廊一样,洞穴是为一种成熟复杂的社会活动而预备的特殊场所,这种活动的复杂程度丝毫不亚于谈话,而且,没有语言和智能的交流它就不可能发生.
·图与物:2014年9月在MIT的一次会议上,当时我是听众,听到BrunoLatour的发言,他评述我们是以静物的模型来思考可见世界.
千真万确.
我们——我们的哲学家,我们的认知科学家——都把观看当作是审视一幅画,而且,我们是以静物为模型来思考我们看到的东西,思考可见世界.
令我感兴趣的是,我们不能选择以别的方式来观看事物.
我们不能选择从组织我们的结构中解放自己.
·图画会给我们施展一种力量,这一观点是布雷德坎普(HorstBredekamp)作品的主题.
他的"Bildakt"(图画作用)理论前提是这种观点:图画有,或似乎有一种功能或力量;它们会对我们发挥作用.
这样一种断言似乎太过人格化或过于强调万物有灵.
图画并不能作用于我们;我们使用图画,一个人可能会被诱使着做出反应.
但是在正文中,我与布雷德坎普的观点趋于一致.
的确,图画不是一个行动者.
但是,图画,就像语言一样,被赋予了意义与特征,它们会对我们施展巨大的影响.
图画有时会对我们说话.
这一类观点出自布雷德坎普的重要著作《图画作用理论》(TheoriederBildakt).
在布雷德坎普看来,实际上惠特尼·戴维斯也这么看,图画组织和改造我们思想的力量——它们不仅是能显示,而且会轮转回来,改变我们对它们所显示东西的思考方式的能力——使得图画本身成为奇特的工具,即使是那些在我的意义上并非艺术作品的图画.
JoergFingerhut在他的文章"扩展的意象、扩展的访问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图画与扩展思维的假说"中也提出了这一观点.
在某种意义上,我很乐于接受这一论断.
它恰恰就是我在正文中所描述的那种一阶与二阶融合的结果,而且在布雷德坎普、戴维斯、纳格尔和其他人的思想中都找到了支持,我们不再将艺术从图画技术中彻底分离出来,或将图画技术从绘画艺术中抽取出来.
在一个有图画艺术——有奇特图画——的世界里,每幅画都有成为奇特图画的风险.
但是我们不能言过其实.
报纸上政治家的照片不能承担起艺术作品的工作,它只是给你显示某样东西.
·图画组织我们,它们改变我们的观看.
这是本章的主题.
但图画改变的不单是观看,它们还再造了我们的"可看感".
图画给我们的是物,一个自立的"静物"世界.
但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图画也给了我们物理学,因为,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理解:世界是由超然的、独立于思想的、具体的实际存在物(物体)构成的,那么就不会有物理学.
这里,我与布雷德坎普作品里的主题再次不谋而合.
布雷德坎普热衷于表明图画和图画理解广泛地渗透于文化之中,而且它们非常重要,尤其是对科学.
艺术家科学从来就不只是语言或数学的科学,它总是要依赖和利用丰富的阅历、锐利的眼光和受过训练的手.
这一点,没有哪个比在伽利略的事例里表现得更为清楚了,他利用望远镜观察到的影像并在它们的基础上画出月亮的能力,让我们对天堂的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
布雷德坎普在评论伽利略的重要著作里说到,在伽利略看来,是艺术给出了哲学(从伽利略的意义上,是自然科学)的模型.
据伽利略说,为了弄明白"哲学这本书"或者,实际上是"自然这本书",你需要应用视觉艺术的标准.
见布雷德坎普,《艺术家伽利略:月亮、太阳和手》(GalileiderKünstler:DerMond,dieSonne,dieHand).
·关于进化论与艺术清楚的、有见地的探索,见斯蒂芬·戴维斯的《艺术的物种:美学、艺术和进化》(TheArtfulSpecies:Aesthetics,Art,andEvolution);另见我对该书的评论,"偶遇自然的界限".
·迪萨纳亚克关于艺术、进化、亲密感和"使与众不同"的文章值得密切关注.
尤见她的《人的审美:艺术的缘由》(HomoAestheticus:WhereArtComesFromandWhy).
·"变革性技术"一词出自AniruddhD.
Patel,他把火当作是一个典型范例.
这种技术在文化中的普遍性无需诉诸于任何有关遗传密码的观点就可以得到解释.
火如此有用,掌握火的技术会产生如此普遍和重要的回报,以至于我们不必像以往那样,还要假设有一种"火的器官"或者是一个"火的驱动力",就完全能够理解它的普世性.
见Patel的优秀著作《音乐、语言和大脑》.
·在《达尔文的危险观念:进化与生命的意义》(Darwin'sDangerousIdea:EvolutionsandtheMeaningsofLife)中,尤其是第12章,丹尼尔·丹尼特探讨了人类身形大小发生变化的文化根源,以及在文化演变的环境中选择压力的重要性.
·据说维特根斯坦曾说:"在美学中问题不是'你喜欢吗'而是'你为什么喜欢'"见《维特根斯坦的讲稿》(Wittgenstein'sLectures).
·迪萨纳亚克关于"使与众不同"的讨论及其在艺术中的核心作用,见《人的审美》第3章.
·见米勒《配对心思:性选择如何塑造了人性的进化》(TheMatingMind:HowSexualChoiceShapedtheEvolutionofHumanNature).
理查德·O.
普卢姆(RichardO.
Prum)在其近作("人类和生物艺术世界中协同进化的美学")中提出了一个极为更加合理的性选择模式.
但我关注它时已为时太晚,没能给予它应得的充分讨论.
且在此做一简要评论.
我们更为熟悉的故事是,艺术就像孔雀尾巴,它是适存性的象征.
正如我在正文中所说,这种解释把艺术的独特之处,艺术有异于其他形式的适存象征的独特之处抛在了故事之外.
普卢姆改正了这点,他坚持认为你不可能从故事中排除愉悦,而且强调我们从艺术中获得的愉悦与艺术直接且明确地密切相关.
并非因为艺术激发了一种特殊的审美感受或感觉,而是因为我们对艺术的反应——我们从艺术中获得的愉悦——通过协同演化的进程与艺术本身密切相联.
艺术是横贯于进化和文化时间长河的一个协同进化竞赛的结果.
普卢姆说,艺术是"与其自身的评价协同演化的一种交际形式".
这一观点的长处在于,它能够公平地对待美学评价中的巨大变化.
一位艺术家的作品——比如,想想安迪·沃霍尔——可以变成美的,因为这些作品可能会促成评价标准的转变,而我们当初评判这件作品恰恰也是通过这些标准.
普卢姆的解释能公正地对待正文中提到的康德的评论:喜欢某件东西是一回事,而觉得它美是另一回事.
美不只事关喜欢.
普卢姆能够容许我们的愉悦与喜好通过进化递归得到精炼打磨.
某些愉悦——比如我们从一个优雅的数学证明中可能获得的乐趣,或者从贝多芬的后期作品中获得的愉悦——只有那些立足以往、有过沟通并达成协议的人才能够体会.
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创意.
它让我们看到艺术所带来的愉悦的独特的认知特点,也就是说,评价特点.
但是这一理论网撒得太广:所有的人工制品、社会活动或技术都要受制于我们所喜欢的东西(评价反应),即便它为我们提供机会去改变和更新那些反应(协同演化).
但是艺术不只是一种活动或技术,即便它伪装成这样.
艺术总是变乱常规的事务,且将我们如常从事事务的事实展示出来.
坦白地说就是:艺术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是我们制造的东西与我们喜欢的东西之间的一个(协同演化的)合适匹配(或对话),而在于它是研究、质疑和挑战这些过程的实践.
·"拱肩"一词由史蒂芬·杰伊·古尔德和RichardC.
Lewontin引进到进化生物学文献当中.
他们用它是在"圣马可的拱肩与至善至美的典范:适者生存工程批判"之中.
在建筑上,拱肩是两个拱形之间的位置或空间.
建筑师并不制造拱肩,他们设计的是拱门,拱肩是随拱门一同出现的附加效应.
古尔德与Lewontin说,在进化中也一样.
并非所有特征都是适应性特征,因为许多特征都是真正扩大适存的特征(适应性特征)的附加效应.
拱肩的存在有着更广泛的意义,至少在古尔德和Lewontin看来.
它表明你不能把有机体看作是一组特征或一些特征的集合,其中每个都被看成是可以自立的、孤立的适应性特征.
只有以整个有机体的建筑规划为背景,特征才有意义.
对古尔德与Lewontin的有价值的批评回复,见丹尼尔·丹尼特《达尔文的危险观念》中的有关章节.
·有3本书唤起了我对华盛顿广场游行的回忆,它们是:EdwardO.
Wilson的《社会学:新的综合体》(Sociobiology:TheNewSynthesis),古尔德的《人的误测》和托马斯·内格尔的《心灵与宇宙:论新达尔文主义唯物自然观的错误》(MindandCosmos:WhytheMaterialistNeoDarwinianConceptionofNatureIsAlmostCertainlyFalse).
·托马斯·内格尔《本然的观点》(TheViewfromNowhere)表达的是一种类似有关实在的科学概念的东西.
伯纳德·威廉斯在其《笛卡尔:纯粹探索工程》(Descartes:TheProjectofPureEnquiry)和《哲学在研究伦理学时的局限》(EthicsandtheLimitsofPhilosophy)中使用"绝对的实在观"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关于普兰丁格对自然主义的批判,见他的《矛盾的真正所在:科学、宗教和自然主义》(WheretheConfictReallyLies:Science,Religion,andNaturalism).
我对他观点的批判性讨论来自于我的文章"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矛盾吗"·关于本章中对科学主义的讨论,我要感谢英国科学哲学家JohnDupré.
在《科学在研究人性时的局限》(HumanNatureandtheLimitsofScience)中,他对科学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判.
科学主义的一个表现是这样的观点:任何可以被解答的问题在科学中都能得到最好的解答;而反过来,怎样才算一个科学的解答或研究方法,它给出的常常又是一个非常狭隘的观念.
尤其是,它通常以为,正统科学必须以揭示生成现象的物理或化学机制来起到作用.
所有这些观点都在暗示,对于千差万别的可以想见的各种问题,你得到的可能是数量有限、类型相同的一系列解答.
无论在什么地方,这都意味着对人类心智能力的束缚;但是没有什么地方能比在心理学中,在人们试图解答关于心智自身的问题时,让这束缚显得更具灾难性了.
·以前我在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时的同事杰西·普林兹认为,只有强烈的情感才能解释艺术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
普林兹的论证建立在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的观点之上:理性永远不会激发或固定我们的喜好.
休谟在《人性论》(ATreatiseofHumanNature)中写道:"比起抓伤自己的手指,我宁愿毁灭全世界,这并不违背理性;对我来说,选择我的彻底毁灭,从而防止一个印第安人或是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遭受最轻微的不安,这于理性也并不矛盾.
"休谟的意思是说,要理解为什么说宁愿抓伤自己的手指而不愿毁灭世界有悖常理,我们需要去看的是感受,而不是理性.
休谟认为,只有情感,只有感受才能触动我们去行动或打造我们的喜好.
因此,以此精神,普林兹提出,如果我们想理解我们对艺术的肯定态度,如果我们想了解我们为什么喜欢它,为什么我们力求坐拥艺术,为什么我们要花大价钱去看它,我们需要去理解,艺术怎样在情感上触动我们.
因为在普林兹以及休谟看来,情感的基础是我们人类的天性(因此也是我们的生物天性),那么,普林兹的研究似乎有可能架构一个类似生物学的艺术研究.
重要的是,普林兹并没有犯迪萨纳亚克的错误.
尤其是,他并不认为,情感要是真实的、要以生物为基础,它们也就需要是文化的.
他也并不认为它们需要脱离认识或理性思维能力.
事实上,他认为,看起来与审美鉴赏关系最为密切的情感,是惊叹;而且可以认为,艺术本身的目的恰恰是要激活这样一种情感.
惊叹不像厌恶一样是一种基本的感情;而且,它是高度认知的;惊叹与吃惊、期待和好奇有着密切的联系.
普林兹也并未认为惊叹之所以是艺术重要性的关键,一定是因为惊叹本身是进化中的一种适应性变化.
他认为惊叹就是一个拱肩,随着其他认识和情感的形成,我们附带获赠的东西.
的确,惊叹,或敬畏感,是一种强有力的情感,事实上,它总是伴随着与艺术作品的审美相遇.
据说,英国君王在第一次参观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Wren)新建成的圣保罗大教堂时,仰望着那巨大的穹顶曾发出感叹:"令人敬畏,夺天之工!
"用这番话他表达的是面对艺术所产生的惊叹、敬畏和讶异.
(这故事我是听哲学家JohnRawls在课堂上讲述的,1990年他在著名的哈佛大学讲社会与政治哲学课.
)然而,我无法赞成普林兹的理论.
正如我一贯论述的,艺术的作用与那些常规的、家常的技术所发挥的作用不同.
恰当地说,艺术的目的不在于任何效应,无论是惊叹或是别的什么.
惊叹,或是我们要以强烈的感情对美的东西或者,用英国君王的话说,令人敬畏的东西做出反应的意向,是艺术的原始素材,是它需要研磨的五谷营养;它不是艺术看作理所当然的东西,而是艺术要研究和提出质疑的东西.
我的意思并不只是想说,艺术无需总是制造惊叹,尽管在我看起来这极有可能.
不,我的重点是,艺术的职责不是要制造惊叹或其他任何情感.
即便它产生这样的情感,情感效应也绝不是艺术价值的来源.
见普林兹的"传奇作品:重修艺术的浪漫主义","惊叹如何发挥作用",以及《令人惊叹的作品:艺术的心理学和本体论》(WorksofWonder:ThePsychologyandOntologyofArt).
第6章关于狂喜、运动与幽默的短笺当我们被困于组织模式时,艺术给我们释放.
这解释了为何艺术能带来狂喜.
因为狂喜恰恰是这种朝向释放的努力的代名词.
本章里还简单地讨论了为什么说运动不是艺术,虽然原则上人们也可以从运动中创作出艺术来.
·感谢霍斯特·布雷德坎普给我的建议,让我知道怎样让这里形成的理论帮助我们弄懂参与艺术时所产生的狂喜.
·感谢电视撰稿人、作家和哲学家EricKaplan与我颇有启迪的会话,使我领会到笑话和"滑稽剧"的本质.
这也形成了他与我和HubertDreyfus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论文的主题.
·"维特根斯坦曾说,一部严肃、优秀的哲学作品,可以完全由笑话构成(而又丝毫不流于轻率).
"——NormanMalcolm《维特根斯坦回忆录》(LudwigWittgenstein:AMemoir)·在《颂赞运动之美》(InPraiseofAthleticBeauty)(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6)中,HansUlrichGumbrecht捍卫了他的观点,说观看体育运动属于审美范畴完全恰当.
我的个人观点是,体育与艺术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领域.
但考虑到我的一般方法,这并不构成理由否认,我们热爱体育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们的美或令人敬畏的品质.
这样的美学品质并不只在艺术领域里才会出现.
第7章哲学之物本章中我的注意力转向到具体的艺术作品.
我的目的是要阐明艺术作品所承担的独特的哲学作用.
这些简短的讨论大多节选自过去5年来我为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网站(www.
npr.
org/13.
7)"13.
7宇宙与文化"栏目所写的文章.
其中包括:"谈同性恋、圈外人与艺术",2010年9月19日;"迷途与知返:理查德·塞拉的艺术",2011年10月21日;"威尼斯双年展上的争议对象",2013年5月31日;"这里无事可做,一切都很完美",2013年8月31日;"解读拉威尔是一个启示",2013年9月7日;"电影《魔鬼圣婴》的哲学观",2014年9月7日.
·GeoffDyer的《地带:一部关于走进房间的旅程的电影书籍》(Zona:ABookAboutaFilmAboutaJourneytoaRoom)(NewYork:Pantheon,2012)完美地展现了本章开头我提到的DVD文献片的结构.
他就是以电影的开始开篇,然后意趣盎然、见解独到、信马由缰似的随意漫谈,而又恰如其分地似乎正好赶在电影的结局收尾.
·我最早遇见理查德·塞拉的作品是1997年在纽约Dia艺术中心展出的"扭转的椭圆"(TorquedEllipses).
从那以后,我见过的他的作品组装难以计数——在纽约高古轩画廊;在洛杉矶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在纽约的Dia比肯艺术博物馆;在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
在此我的评论写的是他2013年在切尔西高古轩的展览作品:新雕塑.
·迈克尔·弗雷德评论戏剧性,后面的致谢中我将重提弗雷德.
现在仅做一下简要介绍:迈克尔·弗雷德,卓越的艺术批评家、诗人、哲学家,他创建了一种批评,在1967年发表的著名论文"艺术与物性"中,他称之为"戏剧性的"艺术.
从那以后,弗雷德在戏剧界并不被钟爱,但实际上这里存在着一种误解.
弗雷德并不(不曾)反对戏剧,他反对的是戏剧性;他断言这是劣质戏剧的一个特征.
在论文中他关注的并不是造作、生硬或浮夸卖弄(对此,狄德罗(Diderot)曾有过警告)意义上的戏剧性;尽管在后期作品中——比如,《库尔贝的现实主义》(Courbet'sRealism)——弗雷德的确也批判了这一意义的戏剧性.
不,此处利害攸关的是一个更加心理化的概念.
弗雷德批判的是作品的意义要与其心理影响密切关联这样一种观点.
一处风景可以给我们深深的触动,但它不会因此成为艺术.
同样,对弗雷德来说,艺术事业本身把艺术的职责当成构筑或调制心理影响就是一个误解.
在"艺术与物性"中,弗雷德瞄准了托尼·史密斯(TonySmith),把他当作一个戏剧性艺术家的典型例子——就是说,有些人创作的作品只是为了给我们影响,让我们觉得它(可能碰巧)很有趣或很有价值.
以我的判断——在我第一篇关于艺术的论文"艺术中的体验与实验"(ExperienceandExperimentinArt)(JournalofConsciousnessStudies7,no.
89,2000)中,我论证了这点——这可完全错判了托尼·史密斯.
(尽管对于史密斯写到他所做的某些事情,这是一个精彩的回复;后面我将再谈这一话题.
)史密斯的作品抒情、结构严谨、中规中矩,它们堪称典范,不仅研究事物,还研究思想、问题和困惑.
但理查德·塞拉的作品就不这样.
塞拉做的的确是弗雷德所批评的"教条主义者"或"戏剧主义者"所做的事:他创作的作品似是给人注射了强心针,令人震惊、恍若触电;如我老爸所说,他真的是直切你的肌肤,给你醍醐灌顶.
因此本章中我才会说,从弗雷德的意义来讲,塞拉的作品可能是戏剧性的.
要看到塞拉的戏剧性和史密斯的反戏剧性,有种方法,那就是看它们的尺度.
史密斯的雕塑尺度不等.
12英寸(约30.
5厘米)的雕塑——例如"香烟""有蛇出动"——与其15英尺(约4.
57米)大的版本完全相同.
大版有何力量与魔力,在小版上也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它与尺度无关,它与冲击无关;它要更为抒情,更为心思缜密.
而塞拉的作品不是这样.
20世纪90年代末在洛杉矶展出庞大的"扭转的椭圆"时,他们实际同时还展出了雕塑的铅制实验模型.
那就像是一些电镀小污水桶,没有丝毫奇异之处.
但那边对应的13英尺(约3.
96米)高的实物,最终却成了,如我在本章中说的那样,一个世界.
塞拉的作品就是产生心理影响的作品,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神经实验.
但重要的是,无论它是否具有戏剧性,它都并不局限于它的戏剧性.
这才是我在本章中想要说明的.
·巴内特·纽曼是我父亲的亲密朋友.
我打小就学会了关注他的作品,尽管我并不以为我们拥有他的任何一幅作品.
不管怎么说,这里的评论写的是2010~2011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抽象表现主义纽约画展.
·提诺·赛格尔因其作品在2013年威尼斯双年展上获得了金狮奖.
我有幸花了足够长的一段时间去观看他并非演出的、耐人寻味的作品.
这次双年展上,我还与他一起参加了艺术与神经科学研讨会;我对包括他在内的一小部分听众发表了关于他作品的想法.
我并不确定他对此的反应是什么.
·罗伯特·拉扎里尼是一位住在纽约的美国艺术家,他的作品是典型的哲学之物.
关于他的作品我写了一篇目录文章:"迷途与知返:在拉扎里尼作品中重返事物的意义".
·2013年我在惠特尼博物馆见到的罗伯特·欧文的"薄纱幕黑色矩形自然光",是1997年在同一地点展出的原作品的重装.
在古根海姆博物馆,詹姆斯·特瑞尔的展览同时开放,这倒成了一个有趣的对比对象.
·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上,在法国展厅展出的安利·萨拉的作品"拉威尔谜题之解"获得巨大成功.
感谢布莱克·高普尼克的引导让我去看到了它.
·见诺埃尔·卡洛尔的《恐怖的哲学》(PhilosophyofHorror)或《心的悖论》(ParadoxesoftheHeart),另外推荐他对BusterKeaton《喜剧化身》(ComedyIncarnate)的评论.
另一位探索电影哲学的杰出作家是StephenMulhall,推荐他的《论电影》(OnFilm).
在《跳出脑海》中,联系雷德利·斯科特的电影《银翼杀手》,我还探讨了Mulhall的某些观点.
第8章看你是否独具慧眼从某种意义上说,本章是第二绪论.
我重述了本书的基本观点——艺术与技术密切相联,却不是技术;艺术作品是奇特的工具;艺术与哲学息息相关.
我论证到,每件艺术作品都是在向你提出建议,让你去看懂它、领会它.
如此一来,它给你提供了一个重组织的机会,而你也由此发现自己的作为.
·舞蹈家威廉·弗西斯曾对我讲过,一次演出后的谈话中,一位发问者要冒昧地提出他的艺术理论,弗西斯冷冷地拒绝了.
他用的恰恰就是这种答复:我们不想知道!
请不要毁了它在我们心中的形象!
·本章从我的论文《神经科学在研究艺术时的局限》(ArtandtheLimitsofNeuroscience)中节选了一些素材.
·泽米尔·泽基在《内视觉:对艺术与大脑的探索》(InnerVision:AnExplorationofArtandtheBrain)中提出了他所谓神经美学的研究.
他讲到,艺术理论应该是一个大脑的理论,因为是大脑创作艺术,也是大脑感知艺术.
这一大脑创作艺术,或大脑感知艺术的观点错得如此离谱,以至于我想,我们不可能以为他是在认真地提出这一主张.
但他的意图却并不明确.
如果他所说的"大脑"指的是"活着的人",也或许是"人",那么我要说他的提法正确.
但人的理论当然要比大脑的理论包含更多内容.
·弗朗西斯·克里克与詹姆斯·沃森于1962年因为发现DNA结构而获得诺贝尔奖.
在《惊世骇俗的假说》(TheAstonishingHypothesis)中,克里克提出了脑即我的观点.
正如我在正文中所讲,与其说这是一个假说,不如说是一个流行的猜想;而且不管从哪方面讲,它都算不上惊世骇俗,因为,实际上,它就是那个我们熟悉的传统观点:你就是你里面的某个东西.
克里克提出的不过是一个唯物主义的笛卡尔思想.
对此观点的延伸批评,见《跳出脑海》.
这是一种糟糕的哲学,也是糟糕的科学.
·欲了解对神经美学真正尖锐的批评——这种批评也影响了我关于此事的想法——见约翰·海曼的"艺术与神经科学".
布莱克·高普尼克关于此话题的优秀论文《审美科学与艺术知识》(AestheticScienceandArtisticKnowledge)也令我无比景仰.
知觉反应不是我们大脑里触发的事件而是判断,这一观点由高普尼克进行了完美的阐释.
所谓的神经美学从未成功地把艺术当作一个现象放到焦点,我要感谢海曼的这一见解.
·对于体验只是大脑里被激发的反应这一观点,约翰·杜威(艺术即体验)与詹姆斯·吉布森(视觉感知的生态理论)(Boston:HoughtonMifflin,1979)提供了另外的观点.
杜威和吉布森拒绝接受苏珊·赫利所称的"输入输出图画"的观点,即知觉是从世界向大脑的输入,而行动是从大脑向世界的输出;体验、思想或意识都是由知觉和行动居间调停发生在大脑里的事.
这是她《行动中的意识》(ConsciousnessinAction)里的主要思想,这本书很重要,却也很难懂.
欲了解更多,见我的《知觉中的行动》,及HilaryPutnam的《三股线:心、身、世界》(TheTreefoldCord:Mind,Body,andWorld).
·看到某些动物使用工具,你不可能不感到震惊.
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为了把小昆虫从土丘中抽出来,大猩猩耐心地剥下树枝的外皮,把它做成一只杖.
但我们也很难忽略一个事实,人类使用工具展现出的思虑性和灵活性与在动物世界的所见有所不同.
或许这与一个事实有关:我们使用工具不只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我们使用工具还思考我们自己,即创作艺术与哲学.
·关于艺术是现代发明的论点,见LarryShiner《艺术的发明:一部文化史》(TheInventionofArt:ACulturalHistory).
·此处我提到的达·芬奇油画——《蒙娜丽莎》除外——都是在2011年冬伦敦国家美术馆"达·芬奇:米兰宫廷画师"的画展上展出的,我花了很长时间盯着它们看,思考它们.
这些画作声名远播,而且在网上很容易搜到.
这里的评论取自我给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撰稿,关于画展的回顾:"达·芬奇之手".
·利奇奥的作品在纽约弗里克收藏馆"利奇奥:文艺复兴的青铜大师(2008~2009)"的展览中展出.
这里我引用了亚历山大·纳格尔的观点,他评论利奇奥的摩西的优秀论文刊登在画展宣传册中,重印于《文艺复兴艺术的争议》(TheControversyofRenaissanceArt)(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11).
2008年我还有幸在柏林Wissenschaftskolleg学院听到了纳格尔有关此论点的会议演讲.
·摩西与磐石的故事在《圣经》中不止一次地被讲到.
这里是民数记第20章里的相关段落: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
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
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去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
"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
"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
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
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好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
"这水名叫米利巴水("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
·E.
H.
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中讨论了马萨乔的"圣三位一体"画像,公元1425~1428年(佛罗伦萨SantaMariaNovella教堂).
关于海曼对透视及其对绘画意义的研究,见他的《自然的模仿》(ImitationofNature).
·第12至第14章我专门探讨了图画.
在此我只想说明,当我使用"图画"一词时,并非指每幅图画都是艺术作品(比如,报纸广告版里的鸡的图片),也不是指每幅艺术画作都是描绘性图画[比如,弗兰克·斯特拉(FrankStella)的画作就不是描绘].
我在正文中的评论实际上都是有关图画的艺术作品(无论是绘画或是摄影).
艺术品的图画,在我的意义上,提出的正是我们常常忽略或不曾问过的关于图画本质的问题.
而这,我认为,按詹姆斯·鲍德温所言之意就是,艺术揭示的常常是被我们熟悉的答案所掩盖的问题.
非常感谢LawrenceWeschler给我的引用建议.
但是,我始终没能找到它的确切出处.
我用于第一部分题词的一版要归功于Weschler,因此我把它当作是向鲍德温的"致敬".
·罗伯特·古德诺夫(1917~2010)是美国重要的画家和雕塑家.
人称第二代抽象表现主义者,与纽约艺术圈有着紧密的联系,他是我父亲的亲密朋友,我从小看着他的作品长大.
文中所说的小雕塑是我很珍贵的一件藏品.
·艺术需要批评,许多学者都提出过这一观点.
意大利哲学家,现就职于巴黎InstitutJeanNicod学院的RobertoCasati认为,艺术可以用作交流的话题,这是它的一个决定性特征.
但是这一观点可以回溯更远,至少可追溯到康德.
他认为,我们对艺术的评价是那种可以做但必须要争论的事.
·德国数学家弗雷格(GottlobFrege)(1848~1925)写道:"不想给想法下定义,我把它称作是催生真理问题的东西.
"见他的"想法"一文,收入《数学、逻辑和哲学文集》(CollectedPapersonMathematics,Logic,andPhilosophy)中.
·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开篇写道:"没有艺术这样一种东西,有的只是艺术家而已.
"第9章艺术缘何如此枯燥艺术让我们感到枯燥并非偶然.
事实上,它能当此大事,倒是我们了解艺术本质的一个线索.
·枯燥可不是理论研究的常见话题.
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海德格尔.
在他的讲稿《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世界、有限性、孤独》(FundamentalConceptsofMetaphysics:World,Finitude,Solitude)中,他就这一话题作了探讨.
·约翰·杜威在《艺术即体验》中写道:当我们所经历的物质走完其历程趋向完满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次体验.
此时,也只有此时,它才在体验的主流中获得完整并与其他体验区别开来.
一件作品完成,结果令人满意;一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一场游戏自始至终地玩下来;无论是吃一顿饭,下一盘棋,进行一次谈话,写一本书,还是参加一场政治竞选,这样的场景是圆满的,它的结局是完成而不是中断.
这样一种体验是完整的,有着它自身独特的性质和自我满足.
这是一次体验.
·约翰·凯奇的演讲讲的是查尔斯·诺顿(CharlesEliotNorton),1988~1989年在哈佛大学所开的课程.
那是我到哈佛大学学习哲学的前一年.
我读研究生时的同学、也是亲密朋友、哲学家ErinI.
Kelly听了讲座,我的描述基本来自她的回忆.
关于此事,凯奇出版了一本书:《一至六》(IⅥ).
·乔纳森·布罗斯的《舞蹈编创者手册》(AChoreographer'sHandbook)(NewYork:Routledge,2010)是一部很美的书,可以被当作一部哲学作品来读.
取材于自己的艺术实践和多年教学经验,他借该书阐明了艺术是一种研究实践.
·在杰弗里·戴奇辞去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职位一段时间之后,我听到过他的访谈.
(据所有报道)戴奇的管理方式充满争议,因为他力主把博物馆的主旨推向流行的艺术表现形式.
第10章神经科学在研究艺术时的局限本章我主要论述了神经科学的艺术实证研究不能将其主题——艺术放到焦点进行研究.
·正文中我提到弗朗西斯科·瓦雷拉和达玛西奥,作为神经科学家,他们坚持认为,关于活生生的人或动物,应该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观念.
见参考书目,以及我与伊凡·汤普森、凯文·欧瑞根及赫尔利的作品.
·戴维·马尔的《视觉》里有一个著名的论点,通过观察单细胞来研究视觉就像是试图通过研究单根羽毛来了解鸟儿的飞行.
据马尔说,视觉,就像其他信息处理程序一样,需要在另外的层次上进行研究.
我们可以问:什么是视觉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可以问:一个人要造一台能够观看的机器,他会怎么做或者说,一台计算机会怎样观看最后我们可以问:事实上,视觉在人脑中是怎样被体现的马尔的研究,实际上是对视觉问题的应用,有人称之为心智的计算机模型,或功能主义,使得我们可以不用考虑其背后凌乱的生物基础来研究视觉.
·戴维·休伯尔(DavidHubel)与托斯坦·韦塞尔(TorstenWiesel)的论文已被收录进《大脑与视觉感知:25年的合作故事》(BrainandVisualPerception:TheStoryofa25-YearCollaboration).
关于他们研究的更多讨论,请见《跳出脑海》第7章.
·丹尼尔·丹尼特有关认知科学基础的文章,见他的《头脑风暴》(Brainstorms)和《意向立场》(TheIntentionalStance).
特拉法加广场谋杀案一例出自《意向立场》里他的论文"三种意向心理".
·"大脑、身体及世界使得意识产生"是伊凡·汤普森和弗朗西斯科·瓦雷拉文章《激进体现:神经动态和意识》(RadicalEmbodiment:NeuralDynamicsandConsciousness)的核心观点.
·丹尼特所指"笛卡尔唯物主义残余"来自《意识的解读》(ConsciousnessExplained)第11章关于"填充"的讨论.
据说每只眼睛中都有一个点,这里没有感光体,人称盲点.
但在我们的视野中,我们却注意不到有任何空白或不连贯.
有些学者认为,这必定是因大脑在后续的再现中填补了这个空白.
就是这种假设,丹尼特看作是笛卡尔主义的免费赠品.
为什么我们要认为有必要进行填充如果大脑已然知道根本没有空白,而因此还有填补的需要,那么实际进行的填充又有何益这就好像我们只能在笛卡尔的剧院里体验着在心里上演的东西.
丹尼特本人认为在大脑填充的观点之外一定有别的观点.
大脑可能只是忽略了空白的缺席.
要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见我的文章《视觉世界是一个天大的错觉吗》及《跳出脑海》第6章.
有关此话题的更多专业探讨及丹尼特的观点,见我和伊凡·汤普森以及LuizPessoa的文章:《关于填充的发现:知觉哲学和视觉科学的知觉完成导读》(FindingOutaboutFilling-In:AGuidetoPerceptualCompletionforVisualScienceandthePhilosophyofPerception).
·马尔认为,视觉是在视网膜编码信息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环境模型的过程.
这一过程分为3步:第一步,作为光线照射眼睛后部神经的结果,生成视网膜影像.
第二步,把所看见的东西形成一幅"画".
这是一个2.
5D的素描,显示的是从某个角度看到的事物;它给我们的是从这个角度能够看见的实物的表面,但没有实物被隐藏部分的信息.
最后一步是整个场景真正的3D再现.
这一步独特的地方在于,对事物的描述不会受到观看它们的具体视点的局限.
3D影像给我们呈现的,不止是事物从这里看的样子,还包括我们变换位置后它们可能看起来的样子.
是中间层次——2.
5D素描的层次——给了我们视觉意识.
我们视觉上体验到的不是视网膜影像,也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
我们真正看到的,实际上是我们纯粹的体验,是心里的图画.
在杰西·普林兹的《清醒的大脑:注意力怎样产生体验》(TheConsciousBrain:HowAttentionEngendersExperience)中,马尔的这一解释又得到了扩展和辩护.
·见帕特里克·卡瓦纳的《艺术家即神经科学家》(TheArtistasNeuroscientist).
·拉姆查德兰和赫恩斯坦关于青铜器的讨论文章发表在《艺术的科学》(TheScienceofArt)刊物上.
这让我们想到了一条格言:"所有艺术都是漫画夸张.
"(当然,从字面上讲,这并不完全正确,但我们会发现,它常常准确得令人吃惊.
)用于辨识面部特征的原则同样也适用于形体辨认的方方面面.
把漫画当作艺术看上去可能有点奇怪,但看一看印度朱罗王朝时期的青铜器——女神帕瓦蒂浑圆突出的臀和胸,你就会立即认识到,这里呈现给你的,从根本上讲就是一个女性形体的漫画夸张.
大脑里的神经元可能会再现性感、浑圆的女性体态,与棱角分明的男性形体形成对比;艺术家选择通过把这形象在一极为男一极为女的光谱序列中把女性一端推向极致,尽可能地放大女性的"神韵".
这种放大的结果,就是在男女差异的范畴内形成了一个"超级刺激".
有趣的是,在这一方面,已知最早的艺术形式常常都是各种各样的夸张;例如,史前洞穴艺术描绘的动物就像野牛和猛犸象,维纳斯著名的"丰腴"身材.
拉姆查德兰和赫恩斯坦还发现:在西方艺术中,非写实的抽象艺术的"发现"直等到毕加索的到来.
他的裸女也是被怪异地扭曲——比如,两只眼睛都在脸的一侧.
但当毕加索这么做的时候,西方艺术批评家预言,他向"超越透视法"(transcendperspective)的尝试是一种意义深远的新发现——尽管印度与非洲艺术中早在几个世纪前就预见了这种风格.
他们的直接关注是要支持这一观点:所有的艺术都旨在夸张;而且,毕加索引进扭曲的目的是要让人看到可见世界的基本特征并把它加以放大.
但是引用的篇章很怪异.
首先,他们提出,艺术品会超越时间和文化发挥作用.
毕加索被认为发现的是印度和非洲艺术家已经使用了几个世纪的技巧——通过创作实际上是漫画的东西来放大情绪反应.
但是,不管他创作的形象给观者可能造成怎样强悍的、直接的、纯粹心理的作用,(为了辩论起见,我们权且认为真有这样的作用)毕加索的影响肯定与他的风格创新有着极大的关系,他参照传统却异于传统,并由此品评他自己所在的艺术传统.
神经美学学者意图把艺术品都看作是激发器,这是一个特别直截了当的例子.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西方艺术的抽象始于毕加索,这一断言也并不准确.
)欲知对拉姆查德兰和赫恩斯坦有见地的批评,见约翰·海曼的文章《艺术与神经科学》.
·泽米尔·泽基在《内视觉》(InnerVision)中列出了他的研究.
·欲知加布里埃尔·斯塔尔的研究,见她的《感受美》(FeelingBeauty),在此她描述了她与维瑟尔和鲁宾的工作.
尤见维瑟尔、斯塔尔和鲁宾的"大脑对艺术的反应:强烈的美学体验激活大脑默认网络"(TheBrainonArt:IntenseAestheticExperienceActivatestheDefaultModeNetwork),"艺术内探:审美体验、自我和大脑默认网络"(ArtReachesWithin:AestheticExperience,theSelfandtheDefaultModeNetwork).
关于性别是否硬性关联的问题,在此我借助的是剑桥大学哲学家JohnDupré和RaeLangton2013年10月5日刊登于英国《卫报》(TheGuardian)上的才华横溢的一封信,"性别差异全都在心里".
他们引证所用的推理同样适用于审美体验的情形.
审美体验有或可能会有神经关联的事实并不能给我们理由相信,从大脑里发生了什么这一事实,我们可以了解到审美体验是什么,或我们为什么会有审美体验.
·所谓大脑默认网络的整个话题都充满了矛盾.
我想明确的是,正文中我的重点——我们不应当把审美体验看作是大脑里的反应事件——不依赖这种可能性:某些神经系统(默认网络)与相关体验的出现密切相联.
也就是说,本章中我也表明,默认网络的概念存在争议.
有些作者声称,"默认模式是一个特别的、解剖学定义的大脑系统,在个体不专注于外部环境时会优先活跃[Buckner,Andrews-Hanna和Schacter的"大脑默认网络:解剖、功能以及与疾病的相关性"(TheBrain'sDefaultNetwork:Anatomy,Function,andRelevancetoDisease)]";另有人认为情况要更为复杂.
例如,据说,有证据表明,在看电影、听演讲和策划等多种多样的面向世界的活动中,常常会出现默认网络的激活.
["为认知神经科学而明确自我"(SpecifyingtheselfforcognitiveNeuroscience)].
但正如我在正文中指出的,克里斯托弗与他的团队也给出了一个概念要点:即便我们的注意力从世界转移时,默认网络的确产生了激活,或重回它的基本速率,这也不意味着默认网络就会起到明确或塑造自我的作用.
作为主体的自我,恰恰可能因为我们参与环境的事实与方式而被明确.
·在《只是一个幸福的承诺:美在艺术世界里的地位》(OnlyaPromiseofHappiness:ThePlaceofBeautyinaWorldofArt)中,亚历山大·奈哈马把艺术以及我们对美的关注置于社群的场景中.
他以一种暗示性反康德的精神构建他的观察:不但不要求审美判断的普遍性,他反而指出,恰恰是我们审美反应的不同表明了我们的或我的群体不同于其他群体,而且如果你愿意,这也形成了我们共有的价值观和信念的核心支柱.
但是这一富有见地的观点,至少在我看来,大致还是康德思想:审美反应不是感觉或狭隘的经验;它潜在总是要共享的,可能会有争议,但在这种意义上,它是向所有人敞开的.
第11章艺术是一种哲学实践,哲学是一种美学实践本章中我论述了艺术与哲学的相似性源远流长.
艺术与哲学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同属于一个门类.
·LawrenceWeschler在网上杂志《玻璃轮胎》(glasstire.
com)中撰文说,《泉》之所以成为艺术,其关键在于杜尚将小便器的倒置安装.
因此,这样调整方向之后它所呈现的就是,至少从前面来看,是一种生物形态的三角楔形.
Weschler写道:"CarlVanVechten通过写信让GertrudeStein想到,'照片怎么使它看上去就像什么东西从麦当娜变成了菩萨'.
或者,正如我自己总是在想,有趣的是,我发现自己最近再次想到:apietà(意大利语,"圣殇",米开朗基罗的雕塑).
"·"方法与结果是同一回事":实际上,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是这样写的:"在逻辑中,过程与结果都是同样的(因此没有什么可吃惊的).
"重点是,证明的最后一行其全部意义都要依赖于把它引向证据的衍生,而且没有自立(self-understanding)的利益或价值.
逻辑不是在底线的意义上积累结果;它积累的是证据,即通向底线的路径.
维特根斯坦当然也认为,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哲学.
·杜威在《艺术即体验》(ArtasExperience)中批判了"艺术的博物馆概念":"当艺术作品被隔离了它源生的条件及其在体验中的操作时,它们周围就竖起了一堵墙,这几乎模糊了它们的普遍意义,而这正是美学理论所要处理的.
艺术被放进一个单独的领域,在这里,它与材料的联系,与所有其他形式的人的努力、经历、成就所要达到的目的的联系,都被隔裂开来.
"·柏拉图对于哲学没有价值的挑战的回答:我以为,这正是柏拉图《美诺篇》(Meno)的目的,我读美诺篇是师从GregoryVlastos之后,把它作为对哲学方法(尤其因为这是苏格拉底的实践)的一个评论.
柏拉图的问题是要解释,恰恰在它不能产生肯定知识的时候,哲学怎样成为一种有价值的东西.
·艺术是哲学,或者说,美学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哲学的特征,康德在对待这个问题时已隐含了这一观点.
他描述,美学分歧在某种程度上使它看起来令人惊讶地富有哲学性.
分歧实在且重要,但它不允许被一劳永逸地解决;没有规则来解决争议.
StanleyCavell在其代表作《论现代哲学的美学问题》[收于文集《此言何必此意》(MustWeMeanWhatWeSay)]中,也明确地表达了这个观点,并进行了完美地阐述.
第12章制作图画本章的基本论断是,图画是人工制品;它们是用来展示事物的工具.
我主张,只有在交际场景中它们才发挥作用;它们有一种修辞;它们并非"首先是视觉的".
·本章开头段落里,我的材料选自"制作者:图画是否正让我们脱离生活"宇宙与文化,2011年5月13日.
·欲深刻了解视觉理论史,见DavidC.
Lindberg的《从金迪到开普勒的视觉理论》(TheoriesofVisionfromAl-KinditoKepler),在《知觉中的行动》第2章我简要描述了这段历史.
·对史蒂芬·平克的引用来自他的《心智探奇》(HowtheMindWorks).
第13章使用模型本章我论证了,图画是一种特殊的模型.
·我首次提出图画的模型理论是在"图画呈现"里,《呈现的多样性》(VarietiesofPresence)第5章.
我论证到,我们使用图画和其他模型作为它们所描绘事物的替代或代表.
这里我利用了E.
H.
贡布里希最早提出的替代概念.
见他的论文集《木马沉思录》[MeditationsonaHobbyHorse,andOtherEssaysontheTheoryofArt(London:Phaidon,1963)]里的"木马沉思录".
在《落伍的文艺复兴》(AnachronicRenaissance)中,亚历山大·纳格尔与ChristopherS.
Wood对一个非常相近的替代观念有着不同的利用.
设想一下,一座教堂大火后被重建.
这是同一座教堂呢还是一座不同的教堂不同寻常的是,我们可以随意地说,它既是新的,又是老的;我们可以坚持把它当作一座老教堂来对待,赋予它与悠久历史相关的所有意义,即便我们非常清楚这是一座新建筑.
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我们并不是在欺骗自己,也不是在否认明显的事实,更不是依迷信行事,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事物,尤其是艺术作品,可以以此方式跨越时空,侧身不同的时代.
而使得这种"时间倒错"成为可能的,正是一种替代原则:我们让某种东西代替别的东西,并由此代表其意义的意愿、需要或能力.
同样的方式,维特根斯坦说道:就我来说,亲吻我爱人的照片可不是什么迷信.
·欲知更多关于描绘的理论,尤其是,与此解释相似的集中论述,见约翰·海曼的《客观的眼光:艺术理论中的色彩、形式与现实》(TheObjectiveEye:Color,Form,andRealityintheTheoryofArt),以及RobertHopkins的《图画,形象,体验》(Picture,Image,Experience).
·霍斯特·布雷德坎普与JohnMichaelKrois最早向我表示异议说,我在此提出的有关描绘的解释使得图画太费周折,太过深奥,对理解的要求太高,还需要对背景的了解和掌握.
他们坚持认为,图画远要比这更为直接.
你根本不需去学习观看图画.
只要你能看见妈妈,你就能看见图片里的妈妈.
我们可能会以为,你不需学习就能看见图画的这一论断很容易验证,但结果呢,你很难厘清使得我们知道怎样处理图画的是哪些不同的技能和认识.
正如正文中我讲到的,据广泛报道,有些孩子会"伸手去够"图画并试图抓住他们看到的东西.
这似乎证明,这种对图画所描绘物品的认知是因为对其图画事实缺乏相应的理解.
但是假设这不仅仅是某些孩子的失误,事情可能会更为复杂.
或许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假想游戏的一种形式,可与其他形式的假扮相比较.
假扮去吃一个并不存在的冰激凌,与被骗真的以为一个人在吃冰激凌实际并没吃可不一样.
也或许,正如JudyDeLoache和她的同事所提议的那样,这种用手对图画的探索是一种对图画为何物获得认识的方式,而事实上图画恰恰是一种特别的事物种类.
无论是何种情况,到孩子19个月大的时候,至少是据DeLoache等人说,用手探索变成了用手去指.
值得注意的是,用手指,是一种准语言交流的手势.
理解图画,与单纯的图画认知不同,它似乎伴随着一种更为普遍的认知/交流/感知的才能.
值得注意的是,据DalilaBovet和JacquesVauclair说,"已有明确的案例显示,一只经过语言训练的大猩猩有可能会分辨一件物品与它的图画的差别……它表现出了一种能力,能够(用一种符号)指示图片里呈现的物品,而不会把它们与真的物品相混淆.
"这么说,即使是人以外的动物,图画能力也与符号交际密切相关.
所有这些都与承认图画认知不是学来的相一致.
正如我在正文中所说,婴儿能"看穿"图画并不能作为图画的视觉/心理解释的证据,我拒绝接受这一解释.
Gibson认为,孩子不需学习就能看到图画,是因为图画里的信息与实际环境中呈现的信息获得方式大致相同.
我个人的观点是,图画的设计是方便用户的:它反映的并非是我们视觉能力有多强大,我们不需培训就能看到图画;相反,它反映的是图画构筑本身有多智能.
这里我借用TerrenceDeacon(在《符号物种》(TheSymbolicSpecies)当中)的一个观点,有关语言他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们之所以觉得语言容易学习,是因为我们让语言服从我们觉得容易学的方式.
图画,就像语言一样,给我们以直接和自然的错觉.
我们不需要学习就能看见图画,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图画是天然的,或说我们看见它们不是一项认知造诣.
两篇有益的文章:JudyS.
DeLoache,SophiaLPierroutsakos,DavidH.
Uttal,KarlS.
Rosengren,和AlmaGottlieb的"抓住图画本质"(GraspingtheNatureofPictures).
DalilaBovet和JacquesVauclair的"动物与人类的识图"(PictureRecognitioninAnimalsandHumans).
第14章绘画策略我们用图画来显示事物.
但我们显示事物有不同的原因和不同的场景.
因此我们应该料到图画会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我们发现事实的确如此,本章我对此做出了解释.
·关于基督圣像画,见HenryMaguire的《拜占庭的艺术与辩才》(ArtandEloquenceinByzantium)以及CharlesBarber的《人物与相像:论拜占庭圣像画的表现局限》(FigureandLikeness:OntheLimitsofRepresentationinByzantineIconoclasm)和ChristophSchonborn的《上帝的人面:基督圣像》(God'sHumanFace:TheChrist-Icon).
·我结束本章的观点是,门采尔创作的图画是关于视野本身.
ErnstMach曾试图对视野进行视觉再现——盯住正前方一个点,闭上一只眼,画出这样的所见——这一尝试闻名遐迩却完全不成功.
维特根斯坦对此的评论是,"不,你不可能画出一幅我们的视觉样态的真实图画.
"[《哲学清言》(PhilosophicalRemarks)].
关于你不能描绘观看本身,维特根斯坦说的很对.
但是,门采尔证明,你可以把我们对世界的视觉体验表现出来.
第15章空气吉他风本章和下章我研究的是音乐.
本章主要探讨流行音乐.
我非常有兴趣想去了解,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流行音乐为何如此重要、如此强大,尽管它常常并不是音乐实验,尽管它往往要受到市场的辖制.
·《粉红凯迪拉克》(PinkCadillac)收在戴夫·希基的文集《空气吉他:论艺术与民主》(AirGuitar:EssaysonArt&Democracy)中.
(LosAngeles:ArtIssuesPress,1997).
·罗杰·斯克鲁顿对于摇滚乐,尤其是对涅乐队的批评,可见于他的《音乐美学》(TheAestheticsofMusic)(Oxford:ClarendonPress,1999).
·2009年,我参加了由DenizPeters和AndreasDorschel在格拉兹组织的一个会议,会议主题是关于肢体语言与电子音乐.
在音乐里引入幻听概念的整个话题,我应该感谢他们.
·感谢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布鲁斯吉他大师PaulRishell,他让我大开眼界,领略了罗伯特·约翰逊的艺术造诣.
有段时期,我阅读了大量有关布鲁斯的书籍,对它有了相当的了解.
看过的书大部分我已忘记,但有一本一直留在记忆里,那就是RobertPalmer的《忧郁蓝调:从密西西比三角洲到芝加哥南部到全世界的一部音乐文化史》(DeepBlues:AMusicalandCulturalHistory,fromoftheMississippiDeltatoChicago'sSouthSidetotheWorld)(NewYork:Viking,1981).
·关于风格的话题,以及风格的作用——它既成就我们的感知又妨碍我们感知——感谢亚历山大·纳格尔与我进行的多次有价值的谈话(及切磋指教).
·约翰·洛克关于人的评述,见他的《人类理解论》(AnEssayConcerningHumanUnderstanding)第27章,《同一性与多样性》(OfIdentityandDiversity).
第16章音乐之声本章我提出,我们对音乐的体验是对人类行为及其组织模式的一种探索.
音乐与语言一样,绝不只是单纯的声音.
·我听到著名音乐哲学家彼得·基维的评论是他在2013年美国哲学学会上的会议发言,他讲到,音乐哲学的主要问题是去解读单纯的声音怎么会令人陶醉、引人入胜.
·对奥利弗·萨克斯的引用来自他的《音乐挚爱!
音乐与大脑的故事》(Musicophilia!
TalesofMusicandtheBrain)(NewYork:Knopf,2007).
对丹尼尔·列维廷的引用来自他的ThisIsYourBrainonMusic:TheScienceofaHumanObsession(NewYork:Dutton2006.
).
·欲知我对颜色观点的详细描述,见《知觉中的行动》第4章.
·见蔡嘉戎:《音乐表演的评判中视觉比声音更为重要》,[Proceedingsofthe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110,no.
36(2013):1458014585]在2013年8月25日的宇宙与文化栏目中,我撰文《SeeingMusicforWhatItIs》讨论了她的发现.
第17章一份极其简略却高度自以为是的美学史柏拉图对于艺术的批评,见《理想国》第10卷,以及与伊安的对话.
在《理想国》中,他写道: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肯定下来:从荷马以来所有的诗人都只是在模仿美德或自己制造的其他东西的影像,而并不掌握真相事实上,正如我们刚才说的,画家本人虽然对鞋匠的手艺一无所知,但是能画出像是鞋匠的人来,只要他自己以及那些与他同样无知但会凭形状和颜色判断事物的观众觉得像鞋匠就行了.
不是吗……因此,格劳孔啊,当你遇见赞颂荷马的人,听到他们说荷马是希腊的教育者,在管理人们生活和教育方面,我们应当学习他,我们应当按照他的教导来安排我们的全部生活,这时,你必须爱护和尊重说这种话的人.
因为他们的认识水平就这么高.
你还得对他们承认,荷马确是最高明的诗人和首屈一指的悲剧家.
但是你自己应当知道,实际上我们是只许可歌颂神明的、赞美好人的颂诗进入我们城邦的.
如果你越过了这个界限,放进了甜蜜的抒情诗和史诗,那时快乐和痛苦就要代替公认为至善之道的法律和理性原则成为你们的统治者了.
·关于悲剧与历史,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写道:从上述分析中亦可看出,诗人的职责不在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
因此,史学家与诗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用韵文写作(希罗多德的作品可以被改写成韵文,但它仍然是一种历史),而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
因此,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具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
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有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
亚里士多德如此定义悲剧: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
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模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感情得到宣泄.
这一定义(在此与柏拉图的鲜明对比也表现了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它重在强调要创作或领会一出悲剧,你需要了解和领悟多少东西.
作为一名剧作家,你既需要了解玄学还需要懂得心理学.
批评,或说此例中的诗,是一个观察人类本性与人类关注的窗口.
·海德格尔的哲学著作非常难懂.
关于器具的理论是《存在与时间》(BeingandTime)中提出的有关存在的更大理论里的一部分.
他发表的讲义题为《现象学的基本问题》(TheBasicProblemsofPhenomenology),读起来要更为易懂.
其中他写道:环绕着我们的最切近的物,我们称之为器具.
向来总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器具:用来工作的、用于旅行的、用来度量的,举凡我们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东西.
最初我们看到的就是器具整体的统一性……诸物作为器具的构成语境(比如环绕在我们周围的这些物的构成)就在我们眼下,但却不是为了让人来探究审视——仿佛我们坐在这里专为了描述这些东西……器具的构成语境起初以丝毫不起眼、不被思虑的方式出现在我们视野中,恰是我们实际环顾巡视、实际日常趋向的视野与目光.
在为人称道的"艺术作品的本源"(OntheOriginoftheWorkofArt)中,海德格尔倒是提供了某些东西,像是对艺术的理论性阐述:我们已经寻获了器具的器具存在.
然而,是如何寻获的呢不是通过对一双鞋的实物的描绘和解释,不是通过对制鞋工序的讲述,也不是通过对张三李四实际使用鞋具的观察,而只是通过对梵高的一幅画的观赏.
这幅画道出了一切.
走近这幅作品,我们就突然进入了另一个天地,其况味全然不同于我们惯常的存在.
这是海德格尔思想的一个极好表达:艺术作品,这里是梵高的画作,把通常"不起眼、不被思虑的"东西,即器具的本质(也就是说,它的器具性)带到人们的视野中.
但是他进一步阐述:艺术品首先让它揭示的东西——这里是器具的本质——成为实在;把它凸显出来.
本章中我尽量解释它的意义.
海德格尔写道:"艺术作品使我们懂得了真正的鞋子(一件器具)是什么……这作品并不像最初使人感觉到的那样,仅只为了使人更好地目睹器具是什么.
倒不如说,通过这幅作品,也只有在这幅作品中,器具的存在才专门露出了真相".
·康德关于美学的论述形成于《判断力之批判》:所以在快适方面(也就是说,单纯喜欢的东西)适用于这条原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口味.
至于美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
恰好相反,如果有一个人对自己的品味不无自负,由此以为自己有理由这样说:这个对象(我们所看到的房子,那个人穿的衣服,我们所听到的演奏、被提交评判的诗)对于我是美的.
这将非常可笑.
因为只是他所喜欢的东西,他就不必说它是美的.
有许多东西可以使他得到刺激和快意,这是没有人会来操心的事;但是如果他宣布某物是美的,那么他就在期待别人有同样的愉悦;他不仅仅是为自己,而且也在为别人下判断,因而他谈到美时好像它是物的一个属性似的.
所以他说:这个事物是美的,并不是因为例如他多次发现别人赞同他的愉悦判断,就指望别人在这方面赞同他,而是他要求别人赞同他.
如果别人做出不同的判断,他就会责备他们并否认他们有鉴赏品味,而他要求于鉴赏的就是他们应当具有这种鉴赏;就此而言我们不能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鉴赏品味.
这种说法等于说:根本就不存在任何鉴赏,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审美判断能够做得出让所有人都同意的无懈可击的断言.
在这里,重要的是我们要体会到康德并非固执己见.
他不仅仅是在坚持我们对美的判断要有客观性.
不,他的出发点是他认识到,当谈到这种判断时,我们心里所想的是这样一种东西,"它的决定基础不可能绝无主观",这事关感觉.
而他的目的是要给出一个解释,解释我们称之为审美判断现象学的东西,也就是说,美学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方式.
康德认识到,我们非常在乎审美判断;我们把它们看得很重;我们期待别人,或要求别人努力来与我们达成一致,即便这种判断属于一种主观反应.
如果你不能接受在审美判断中含有对普遍性的要求,那么,你也将无法理解现象本身.
这是康德的基本见解.
更多书籍访问:www.
j9p.
com约翰·杜威的观点可见于《艺术即体验》.
·书论题的基础.
分歧和争议的显著的亲缘关系.
感谢Cavell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它是本ProblemsofModernPhilosophy)值得称道,它也探索了审美分歧与哲学烦恼的交互作用.
他的论文《论现代哲学中的美学问题》(OnAesthetic的分歧时,对于客观性的要求,以及感觉与判断、辩论与回应这种令人当代作家中没有谁比StanleyCavell让人更清楚地看到,在面对真正·译后记你喜欢参观艺术博物馆吗见过什么印象深刻的作品它为什么给你留下印象或者,是什么触动了你是大师的作品还是它惟妙惟肖、美伦美奂或是它令你若有所思你认为它是艺术吗我们认识艺术吗看过本书后,这是我问自己的问题.
什么是艺术艺术为什么对我们重要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是本书在努力解答的问题.
站在博物馆里,面对一幅幅现代派画作,或是在街头面对一尊雕塑,我们常常会一头雾水,感慨自己不懂艺术.
即便看到那些经典的、已被奉为艺术瑰宝的作品,我们也未必能看到它的"艺术"所在.
跟随批评家的评论,我们兴许会有所感悟.
读过本书后,我坦承我是真的不懂艺术,正如我不懂哲学一样.
本书的一个核心观点便是:艺术是一种哲学实践,哲学是一种美学实践.
读了几遍我还是迷茫的,直到我把它译出来.
我不懂哲学,可据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小小哲学家,我们时不时地都会哲学一下,哲学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思考人生,思考世界,思考自己.
艺术便如哲学一样,就在我们生活的外围,它是对我们自己的思考.
《奇特的工具:艺术与人性》一书,会让我们对艺术、对哲学产生新的认识.
本书极富挑战,作者本身从事哲学研究,因此能以哲学的立场来看待艺术.
艺术与哲学的相似之处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这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它从一个全然不同的角度解读了艺术.
艺术产生于我们的一阶组织活动之中.
我们唱歌、跳舞、画画,我们谈话交流,我们观察感知世界、开车、运动、比赛……这是我们的天性,我们的生活就是由各种各样的活动组织起来,但我们常常迷失在这些组织活动里不明方向.
艺术是一种奇特的工具,它把我们自己的组织活动展示出来,是对我们自己组织的研究.
艺术是枯燥的.
正是如此,站在艺术品面前,我们往往会一无所见,打不开开关.
艺术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总是美的.
它需要在争论中被人认识.
我们的审美体验并非自然形成,它需要通过学习、通过启发,它是一种交流活动.
艺术是体验,艺术是变乱,是颠覆,是对我们人性的研究.
艺术就是把那些我们熟视无睹,理所当然的东西暴露在我们眼前,让我们去聚焦,去看见那些我们不曾看见的东西.
本书还讨论了神经生物学、进化论以及神经美学在艺术研究中的局限.
科学不能解释艺术.
艺术不是可以解释的现象,而是研究自己的工具.
一部电影,一本小说,一首诗,一幅画,一台舞剧,一支歌,一首乐曲,它们有何共同之处它们何以成为艺术如果说这些千姿百态的被称作艺术的东西确有某种同一性,那就是它们的故事.
或许看过此书后,你就知道了该怎样去欣赏艺术、怎样看待哲学.
面对一尊奇形怪状的雕塑,你若感兴趣去盯住它看,愿意用心去体验它,兴许你会突然恍然大悟.
艺术让我们做的,就是去关注它,去看懂它.
每一件艺术作品都在向我们提出挑战,看你是否独具慧眼!
看你能否看懂它!
本书也像艺术、像哲学一样,一眼望去,似乎尽收眼底,但它需要你、值得你一遍又一遍地去揣摩,去体会.
感谢李绍明老师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对我的信任,将此书交由我更多书籍访问:www.
j9p.
com2016年11月21日于烟台译者窦旭霞指正.
由于译者专业知识有限,书中难免出现疏漏和不足,敬请读者不吝阳、范明春、于玲、钟立君等老师给本书翻译提供的宝贵意见.
支持.
感谢田南阳老师帮忙校稿.
感谢姚东、于锦萍、李海波、管明生.
感谢我的家人张宏伟、浩程,朋友王琳、长红等一年来给予的无私推敲.
我深知仍难达老师的上乘译风,但所学皮毛已足以使我受用终过老师锐利的眼光,只要是他指出的问题就都值得我去精打细磨,仔细高.
感谢绍明老师的全程跟进,字字把关.
任何一个欠妥的细节都逃不来翻译,使我早先一步领略了此书的精髓,艺术修养、哲学修养得以提[1]艾米莉·狄更生(又译狄金森)(1830~1886),美国传奇诗人.
青少年时期生活单调而平静,受正规宗教教育.
从25岁开始弃绝社交,女尼般地闭门不出,在孤独中埋头写诗30年,留下诗稿1700余首;生前只发表过7首,其余的都是她去世后才出版,为世人所知,名气极大.
——译者注[2]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爱尔兰作家、诗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后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其作品及"意识流"思想对世界文坛影响巨大.
其作品结构复杂,用语奇特,极富独创性.
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尤利西斯》(1922),后期作品长篇小说《芬尼根的守灵夜》(1939),语言极为晦涩难懂.
——译者注[3]赫曼·麦尔维尔(1819~1891),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代表作有《白鲸》《水手比利·巴德》.
——译者注[4]托马斯·曼(1875~1955),德国小说家和散文家,长篇小说《魔山》作者,1929年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译者注[5]巴内特·纽曼(1905~1970),美国极简主义代表.
纽曼的作品特点就是在巨大的画面上涂抹强有力的单一色彩,中间有线条成垂直或水平方向通过画面,或者在平面背景中仅画一根或两根垂直的线条,这些孤立的线条被人们戏称为"拉链".
[6]生于1976年的英裔德国艺术家提诺·赛格尔素来以"场景"艺术、"情境"艺术出名.
在信息过剩的时代,赛格尔通过非物质的形式制造一种氛围和情境.
他创作的基本素材是人们说话的声音、语言、运动的过程和观众的参与,其间不涉及任何有形的物质,艺术家也明确提出其作品没有文字文本,没有手写的记录,没有目录图录,也没有图片,即意味着他的作品不能以任何方式来记录.
而这种创作方式使他的艺术有着转瞬即逝的特性,不是传统的行为艺术,更多的是现场的演出.
永不固化,不受物质的干扰,无形的,流动的,这就是赛格尔作品的特色.
[7]马塞尔·杜尚(1887~1968),纽约达达主义团体的核心人物.
出生于法国,1954年入美国籍.
他是20世纪实验艺术的先锋,被誉为"现代艺术的守护神".
他的出现改变了西方现代艺术的进程.
可以说,西方现代艺术,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艺术,主要是沿着杜尚的思想轨迹行进的.
因此,了解杜尚是了解西方现代艺术的关键.
[8]保罗·塞尚(1839~1906),法国著名画家,后印象主义派画家的代表人物,是印象派到立体主义派之间的重要画家,新艺术之父,现代艺术之父,现代绘画之父.
[9]马萨乔(Masaccio,1401~1428),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奠基人,被称为"现实主义开荒者".
他的壁画是人文主义一个最早的里程碑,是第一位使用透视法的画家,在他的画中首次引入了灭点.
代表作品《圣母玛利亚》《圣三位一体》《纳税银》等.
——译者注[10]尼古拉斯·普桑,17世纪法国巴洛克时期的重要画家,其作品大多取材于神话、历史和宗教故事.
《阿卡迪亚的牧人》是其重要代表作.
——译者注[11]杰克逊·波洛克(1912~1956),美国画家,抽象表现派绘画大师,也被公认为是美国现代绘画摆脱欧洲标准,在国际艺坛建立领导地位的第一功臣.
1947年开始使用"滴画法",把巨大的画布平铺于地面,用钻有小孔的盒、棒或画笔把颜料滴溅在画布上.
其创作不作事先规划,作画没有固定位置,喜欢在画布四周随意走动,以反复的无意识的动作画成复杂难辨、线条错乱的网,人称"行动绘画".
此画法构图设计没有中心,结构无法辨识,具有鲜明的抽象表现派特征.
主要作品有《秋韵:第30号》《薰衣草之雾:第1号》《大教堂》《蓝杆:第11号》等.
[12]托马斯·曼同名小说里的主人公.
[13]詹姆斯·乔伊斯小说里的主人公.
[14]约翰·凯奇(1912~1992),美国先锋派古典音乐作曲家,著名实验音乐作曲家、作家、视觉艺术家.
从1950年起,他的名声和影响开始波及全世界.
约翰·凯奇一生中最为石破天惊的作品,当然也是最著名的音乐作品当属《4分33秒》(首演于1952年),该作品为任何种类的乐器以及任何数量的演奏员而作,共3个乐章,总长度4分33秒,乐谱上没有任何音符,唯一标明的要求就是"Tacet"(沉默).
作品的含义是请观众认真聆听当时的寂静,体会在寂静之中由偶然所带来的一切声音.
这也代表了凯奇一个重要的音乐哲学观点:音乐的最基本元素不是演奏,而是聆听.
约翰·凯奇《4分33秒》的一个纪录片,现场纪录了他那次静寂无声的演出.
他走上指挥台,拿起指挥棒,然后像木头一样静止地停在那里,整个音乐厅的人都有点莫名其妙.
过了一会,他装模作样地把乐谱翻过一页,还掏出手帕擦了擦汗水,惹来人们的会心微笑.
最后,4分33秒过去,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没看表有多少秒;约翰·凯奇绅士般地致意.
有点好笑,好像发生了什么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实验,先锋,像变戏法的魔术一样暂时俘获了有点疲劳而又眼神不大好使的现代人.
[15]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1606-1669),欧洲17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也是荷兰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
画作体裁广泛,擅长肖像画、风景画、风俗画、宗教画、历史画……代表作品《木匠家庭》《夜巡》《三棵树》《浪子回头》《尼古拉·特尔普教授的解剖课》等.
[16]安迪·沃霍尔(1928~1987),被誉为20世纪艺术界最有名的人物之一,是波普艺术的倡导者和领袖,也是对波普艺术影响最大的艺术家.
他大胆尝试凸版印刷、橡皮或木料拓印、金箔技术、照片投影等各种复制技法.
玛丽莲·梦露的头像,是沃霍尔作品中一个最令人关注的母题.
在1967年所作的《玛丽莲·梦露》一画中,画家以那位不幸的好莱坞性感影星的头像,作为画面的基本元素,一排排地重复排列.
那色彩简单、整齐单调的一个个梦露头像,反映出现代商业化社会中人们无可奈何的空虚与迷惘.
[17]约翰内斯·维米尔(1632~1675),荷兰最伟大的画家之一,被看作"荷兰小画派"的代表画家.
但却被人遗忘了长达两个世纪之久.
维米尔的作品大多是风俗题材的绘画,基本上取材于市民平常的生活.
他的画整个画面温馨、舒适、宁静,给人以庄重的感受,充分表现出了荷兰市民那种对洁净环境和优雅舒适的气氛的喜好.
代表作品:《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倒牛奶的女仆》《窗前读信的少女》等.
[18]一位美籍英国画家、摄影家,同时也是一位蚀刻家、制图员和设计师.
在近30年的摄影艺术生涯中,他矢志不渝地坚持探索照相机的多种多样的工作方式和摄影作品的多种表现形式.
绘画作品代表作为《克利斯多夫·伊修伍德和唐·巴查笛》和《克拉克夫妇俩》.
[19]阿道夫·门采尔(1815~1905),德国油画家、版画家、插图画家,尤其以素描见长,是19世纪现实主义美术在德国的代表人物.
他的作品种类和题材都很广泛,多层面而深刻地表现了德国社会生活风俗,尤其是对工业生产和工人生活的描绘,为同时代的欧洲画坛所罕见,是现实主义绘画的杰出代表.
最著名的作品是《轧铁工厂》,画面展现了工厂生活一角.
在油画《腓特烈大帝及随从在霍克齐战役中》,画家力图再现战争的残酷和紧张.
打开海外主机域名商出现"Attention Required"原因和解决
最近发现一个比较怪异的事情,在访问和登录大部分国外主机商和域名商的时候都需要二次验证。常见的就是需要我们勾选判断是不是真人。以及比如在刚才要访问Namecheap检查前几天送给网友域名的账户域名是否转出的,再次登录网站的时候又需要人机验证。这里有看到"Attention Required"的提示。我们只能手工选择按钮,然后根据验证码进行选择合适的标记。这次我要选择的是船的标识,每次需要选择三个,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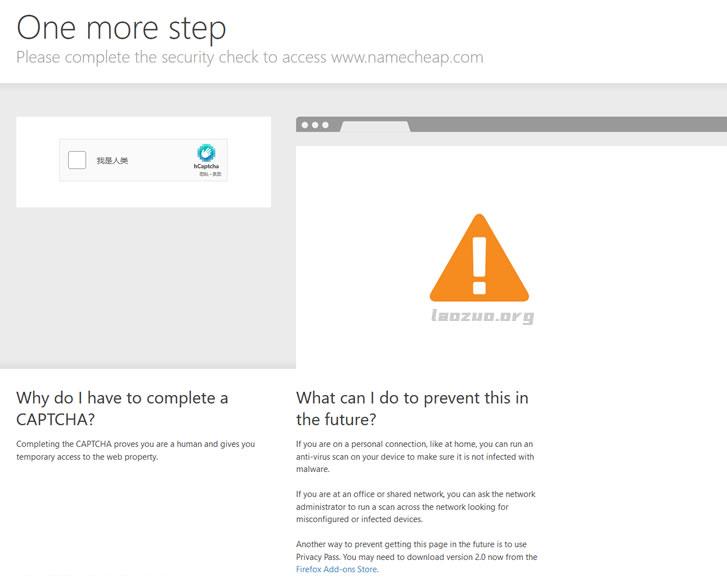
青云互联:美国洛杉矶CN2弹性云限时八折,15元/月起,可选Windows/可自定义配置
青云互联怎么样?青云互联是一家成立于2020年6月的主机服务商,致力于为用户提供高性价比稳定快速的主机托管服务,目前提供有美国免费主机、香港主机、香港服务器、美国云服务器,让您的网站高速、稳定运行。美国cn2弹性云主机限时8折起,可选1-20个IP,仅15元/月起,附8折优惠码使用!点击进入:青云互联官方网站地址青云互联优惠码:八折优惠码:ltY8sHMh (续费同价)青云互联活动方案:美国洛杉矶...

无忧云:洛阳/大连BGP云服务器38.4元/月,雅安物理机服务器315元/月起,香港荃湾CN2限时5折优惠
无忧云怎么样?无忧云是一家成立于2017年的老牌商家旗下的服务器销售品牌,现由深圳市云上无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是正规持证IDC/ISP/IRCS商家,主要销售国内、中国香港、国外服务器产品,线路有腾讯云国外线路、自营香港CN2线路等,都是中国大陆直连线路,非常适合免备案建站业务需求和各种负载较高的项目,同时国内服务器也有多个BGP以及高防节点,目前商家开启了夏日清凉补贴活动,商家的机器还是非常...

-
文件夹删不掉文件夹是文件夹删不掉怎么办?weipin唯品购,weipuvip,是诈骗网站么?充了钱之后提不出,各种套路继续充钱微信如何建群微信怎么建群?手机区号手机号码数码资源网有什么网站弄相片效果比较好的?彩信中心移动的彩信中心是?主页是?收不到彩信,怎么设置?直播加速手机上什么软件可以帮助直播加速,大神们推荐推荐qq怎么发邮件如何通过QQ发送邮件保护气球为什么会那么害怕气球创维云电视功能创维新出的4K超高清健康云电视有谁用过,功能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