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苏丹一村镇遭遇武装分子袭击超60人死亡
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议程项目5以色列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和其余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行动国际法院对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发表的咨询意见秘书长的说明1.
大会在其2003年12月8日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续会第23次会议通过的第ES-10/14号决议中决定,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九十六条第一项规定,请国际法院就以下问题紧急发表咨询意见:考虑到国际法规则和原则、包括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以及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有关决议,如秘书长报告所述,占领国以色列在包括耶路撒冷及周围地带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构筑隔离墙,有何法律后果2.
国际法院于2004年7月9日就上述问题发表咨询意见.
3.
我在2004年7月13日收到国际法院该咨询意见经正式签署和盖章的副本.
4.
特此将国际法院2004年7月9日对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发表的咨询意见以及所附的各项个别意见和声明转送大会.
国际法院2004年2004年7月9日2004年7月9日案件总表第131号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法院根据要求发表咨询意见的权限.
规约第六十五条第一款——宪章第九十六条第一项——大会要求发表咨询意见的权力——大会的活动.
导致大会通过要求发表咨询意见的第ES-10/14号决议的过程.
关于大会的行为超越宪章规定的权限的说法——宪章第十二条第一项和第二十四条——联合国在解释宪章第十二条第一项方面的做法——大会没有超越其权限.
大会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通过的发表意见的请求——根据第377A(V)号决议("联合一致共策和平")召开的会议––––该会议所定的条件——所采用的程序是否正常.
问题用语不明确的指控——该问题据称的抽象性质——该问题的政治方面——据说导致提出要求的动机和意见可能产生的影响.
法院有权提供所要求的咨询意见.
**法院有决定应否发表意见的自由斟酌权.
规约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一个有关国家不同意的意义––––不应将该问题看成是只涉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双边问题,它还是联合国直接关切的问题––––所发表的意见对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政治谈判解决可能产生的影响––––该问题只代表以巴冲突的一个方面––––法院可得到的资料和证据是否充分––––任何方面不得因自己的不当行为而获益––––所发表的意见是提供给大会,而不是提供给某个国家或实体的.
法院没有"强烈的理由"必须要使用不发表咨询意见的自由斟酌权.
**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及周围地带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所提出的问题的范围––––只请求对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修建的那部分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发表意见––––"隔离墙"一词的使用.
历史背景.
隔离墙的描述.
**适用的法律.
联合国宪章––––大会第2625(XXV)号决议––––通过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获取的任何领土均不合法––––人民处决的权利.
国际人道主义法——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所附的条例––––日内瓦第四公约对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是否适用––––人权法––––国际公民和政治权利盟约––––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盟约——儿童权利公约——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之间的关系––––人权文书在国家领土之外是否适用––––这些文书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内是否适用.
**以色列违反国际法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建立定居点––––修建隔离墙及其相关的制度在当地造成可能是永久性的既成事实––––这种情况有可能成为事实上的吞并––––修建隔离墙严重阻碍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决权,因此构成以色列不履行尊重该权利的义务的行为.
同本案有关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文书的适用规定––––财产的破坏和征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居民行动自由所受到的限制––––有关人士在行使工作、健康、教育和适当生活水平权利方面所受到的限制––––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人口的改变––––允许计及军事迫切需要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定––––人权文书内对被保证的权利作出限制和规定权利限制的条款––––不得用军事迫切需要或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需要作为修建隔离墙和有关体制的理由––––以色列违反其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文书各项适用规定所承担的某些义务.
自卫––––《宪章》第五十一条––––不得将对以色列的攻击归罪于某个国家––––以受到威胁作为修建隔离墙的理由,而这项威胁来自以色列控制的领土––––第五十一条与本案无关.
必要性––––国际惯例法––––条件––––修建隔离墙不是保护以色列利益不受所述威胁危害的唯一手段.
修建隔离墙及其相关制度违反国际法.
**以色列不履行其义务的法律后果.
以色列的国际责任––––以色列有义务履行其因修建隔离墙而未履行的国际义务––––有义务立即停止修建和拆除隔离墙、立即废除有关修建隔离墙的立法性法规和行政规章性法规或使其失效,其中有关以色列有义务为所造成的损失提供赔偿的部分除外––––以色列有义务对因修建隔离墙而受到损害的所有自然人和法人提供赔偿.
对以色列外其他国家的法律后果––––以色列没有履行的某些义务为普遍适用的义务––––所有国家有义务不承认修建隔离墙所造成的不合法局面、不协助维持修建隔离墙所造成的局面––––所有国家有义务在遵守《宪章》和国际法的同时,确保排除修建隔离墙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决权所造成的任何障碍.
––––日内瓦第四公约的所有缔约国有义务在遵守《宪章》和国际法的同时,确保以色列遵守该公约所体现的国际人道主义法––––联合国,尤其是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需要在适当计及咨询意见后,审议还需采取何种行动以停止修建隔离墙及其有关制度所造成的非法局面.
**必须从更一般的角度看待修建隔离墙的问题––––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有义务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有诚意地执行安理会一切有关决议,特别是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路线图––––有必要鼓励作出努力,以期尽早根据国际法就各项未决问题达成谈判解决办法,建立巴勒斯坦国,并使该区域所有国家都获得和平与安全保障.
咨询意见出庭者:史院长;Ranjeva副院长;法官:Guillaume、Koroma、Vereshchetin、Higgins、Parra-Aranguren、Kooijmans、Rezek、Al-Khasawneh、Buergenthal、Elaraby、Owada、Simma、Tomka;Couvreur书记官长.
关于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本法院,由上述人士组成,发表下列咨询意见:1.
联合国大会(下称"大会")在其2003年12月8日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通过的第ES-10/14号决议中列出了请本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问题.
书记处在2003年12月10日收到联合国秘书长2003年12月8日的信的传真,后来又收到该信原件.
信中正式通知本法院,大会决定提出该问题请本法院发表咨询意见.
信中附有ES-10/14号决议经检证无误的英文和法文文本.
该决议内容如下:"大会,重申其2003年10月21日ES-10/13号决议,遵照《联合国宪章》各项原则,认识到不容以武力取得领土的国际法既定原则,又认识到在尊重各民族平等权利和自决权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各国间友好关系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之一,回顾大会有关决议,包括1947年11月29日第181(II)号决议,其中将受委任统治的巴勒斯坦分为两个国家,一个是阿拉伯国家,另一个是犹太国家,又回顾大会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的各项决议,还回顾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包括1967年11月22日第242(1967)号、1973年10月22日第338(1973)号、1969年7月3日第267(1969)号、1971年9月25日第298(1971)号、1979年3月22日第446(1979)号、1979年7月20日第452(1979)号、1980年3月1日第465(1980)号、1980年6月30日第476(1980)号、1980年8月20日第478(1980)号、1994年3月18日第904(1994)号、1996年9月28日第1073(1996)号、2002年3月12日第1397(2002)号和2003年11月19日第1515(2003)号决议,重申《日内瓦第四公约》1以及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2均得适用于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回顾《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1907年海牙公约)3所附的《章程》,欢迎1999年7月15日在日内瓦召开了日内瓦第四公约缔约国会议,探讨如何采取措施,在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执行这项公约,表示支持2001年12月5日在日内瓦举行的日内瓦第四公约缔约国会议续会所通过的宣言,特别回顾联合国有关决议,其中申明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内的定居点是非法的,是妨碍和平与经济及社会发展的障碍,并回顾要求全面停止定居点活动的联合国各项决议,又回顾联合国有关决议,其中申明占领国以色列采取的旨在改变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的地位和人口组成的行动没有法律效力,因此完全无效,注意到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中东和平进程范畴内达成的协议,严重关注占领国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及周围地带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开始并继续构筑围墙,此一行为背离了1949年停战线(绿线),涉及没收和破坏巴勒斯坦土地和资源,扰乱了数以千计受保护平民的生活,而且事实上吞并了大片领土,并强调国际社会一致反对构筑此道围墙,又严重关注计划构筑的各段围墙将对巴勒斯坦平民以及解决巴以冲突和在该区域建立和平的前景产生更为严重的破坏影响,欢迎人权委员会1967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2003年9月8日的报告,4特别是有关围墙的部分,申明必须根据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有关决议,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须沿1949年停战线和平、安全地毗邻共处的解决办法的基础上停止冲突,赞赏地收到秘书长根据ES-10/13号决议提交的报告,5铭记时间的推移逐步加重了当地的困难,因为占领国以色列在构筑上述围墙的问题上继续拒绝遵守国际法,造成了有害影响和后果,决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九十六条,请求国际法院按照《法院规约》第六十五条,就以下问题紧急发表咨询意见:考虑到国际法规则和原则、包括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以及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有关决议,如秘书长报告所述,占领国以色列在包括耶路撒冷及周围地带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构筑隔离墙,有何法律后果"1联合国,《条约汇编》,第75卷,第973号.
2同上,第1125卷,第17512号.
3见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1899年和1907年海牙公约与宣言》(牛津大学出版社,1915年,纽约).
4E/CN.
4/2004/6.
5A/ES-10/248.
"信中还附有2003年11月24日秘书长根据大会第ES-10/13号决议规定编写的报告(A/ES-10/248)经检证的英文和法文文本,第ES-10/14提及了该报告.
2.
书记官长在2003年12月10日的信中,按照《规约》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通知所有有权在法院出庭的国家,本法院收到请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要求.
3.
在2003年12月11日的信中,以色列政府通知本法院其对请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要求及将依循的程序所采取的立场.
4.
本法院在2003年12月19日一项命令中决定,联合国及其会员国,按照《规约》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很可能能够就提请本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问题的所有方面提供资料,并将按照《规约》第六十六条第四款规定向本法院提交书面陈述的期限定为2004年1月30日.
有同一命令中,本法院还决定,鉴于第ES-10/14号决议以及请求信中所附的秘书长的报告,考虑到大会已给予巴勒斯坦特别观察员地位,并考虑到巴勒斯坦是要求本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國,巴勒斯坦也可在上述期限内就该问题提出书面陈述.
5.
本法院在上述命令中还决定,按照《法院规则》第一〇五条第四款规定,定于2004年2月23日起举办公开听讯会,联合国及其会员国,不论有否提出书面陈述,都可在公开听讯会上作出口头陈述和评论.
本法院在同一命令中决定,基于上述理由(见第4段),巴勒斯坦也可出席听讯会.
最后,本法院请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和巴勒斯坦,最迟于2004年2月13日通知书记处,是否有意出席上述听讯会.
书记处于2003年12月19日发信给上述实体,通知它们本法院的决定,并转送该命令的副本.
6.
本法院在对阿拉伯国家联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后来提出的要求作出裁定时决定,按照《规约》第六十六条,这两个国际组织很可能能够就提交本法院处理的问题提供资料,因此它们可在本法院2003年12月19日命令中所定时限内为此提出书面陈述,并参加听讯会.
7.
联合国秘书长根据《规约》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向本法院提供了可能有助于了解该问题的有关文件.
8.
本法院在2004年1月30日就审理本案的人员组成发出的附有理由的命令中决定,以色列政府在2003年12月31日的信中提请本法院注意的事项以及根据《法院规则》第三十四条条二款规定在2004年1月15日给院长的保密信中所提到的事项,不构成排除Elaraby法官审理本案的理由.
9.
在本法院所定时限内提出的书面陈述,按收件日期先后次序列出如下:几内亚、沙特阿拉伯、阿拉伯国家联盟、埃及、喀麦隆、俄罗斯联邦、澳大利亚、巴勒斯坦、联合国、约旦、科威特、黎巴嫩、加拿大、叙利亚、瑞士、以色列、也门、美利坚合众国、摩洛哥、印度尼西亚、伊斯兰会议组织、法国、意大利、苏丹、南非、德国、日本、挪威、联合王国、巴基斯坦、捷克共和国、希腊、爱尔兰代表本国、爱尔兰代表欧洲联盟、塞浦路斯、巴西、纳米比亚、马耳他、马来西亚、荷兰、古巴、瑞典、西班牙、比利时、帕劳、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塞内加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收到这些书面陈述后,书记处将副本送交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联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
10.
书记处特别是就口头程序组织工作的各项措施多次致函上述实体.
书记处在2004年2月20日的信中,向上述实体中已在本法院所定时限内表示有意参与上述程序者转递了听讯会的详细时间表.
11.
本法院根据《法院规则》第一〇六条规定决定,在口头程序开始后,公众可以取阅书面陈述.
12.
本法院在2004年2月23日至25日举行的听讯会期间,按下列先后次序听取了口头陈述:代表巴勒斯坦:NasserAl-Kidwa先生阁下,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StephanieKoury女士谈判支助组成员兼顾问JamesCrawford先生,S.
C.
,剑桥大学国际法Whewell讲座教授、国际法研究所成员,顾问律师GeorgesAbi-Saab先生,日内瓦国际研究所国际法教授,国际法研究所成员,顾问律师VaughanLowe先生,牛津大学Chichele讲座教授,顾问律师JeanSalmon先生,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国际法退休荣誉教授、国际法研究所成员,顾问律师代表南非:AzizPahad先生阁下,副外交部长兼代表团团长M.
R.
W.
Madlanga法官S.
C.
代表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AhmedLaraba先生,国际法教授代表沙特阿拉伯王国:FawziA.
Shobokshi先生阁下,大使,沙特阿拉伯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代表团团长代表孟加拉国:LiaquatAliChoudhury先生阁下,孟加拉国驻荷兰大使代表伯利兹:Jean-MarcSorel先生巴黎第一大学(戴昂-索邦大学)教授代表古巴:AbelardoMorenoFernández先生阁下副外交部长代表印度尼西亚:MohammadJusuf先生阁下,印度尼西亚驻荷兰大使,代表团团长代表约旦:ZeidRa'adZeidAl-Hussein大使,约旦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代表团团长ArthurWatts爵士.
K.
C.
M.
G.
,Q.
C.
,约旦政府高级法律顾问代表马达加斯加:AlfredRambeloson先生阁下,马达加斯加常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代表,代表团团长代表马来西亚:DatukSeriSyedHamidAlbar阁下,马来西亚外交部长,代表团团长代表塞内加尔:SaliouCissé先生阁下,塞内加尔驻荷兰大使,代表团团长代表苏丹:AbuelgasimA.
Idris先生阁下,苏丹驻荷兰大使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MichaelBothe先生,法学教授,法律组组长代表伊斯兰会议组织:AbdelouahedBelkeziz先生阁下,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MoniqueChemillier-Gendreau女士,巴黎第七大学(丹尼斯狄德罗大学)公共法教授,顾问***13.
当处理咨询意见请求时,本法院首先必须考虑是否有拥有发表所请求的咨询意见的管辖权,如答案为是,有什么理由本法院应拒绝行使任何这种管辖权(见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咨询意见,1966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㈠英文本第232页,第10段).
**14.
因此本法院将首先讨论是否拥有发表2003年12月8日大会请求的咨询意见的管辖权.
本法院这方面的权限依据是其《规约》第六十五条第一项,其中提到本法院"如经任何团体由《联合国宪章》授权而请求或依照《联合国宪章》而请求时,得发表咨询意见".
本法院前此已指出:"法院权限的先决条件是由根据《宪章》适当受权征求咨询意见的机关提出请求,就某一法律问题提出请求,同时除大会或安全理事会外,该项问题应产生于请求机关的活动范畴内.
"(申请复审联合国行政法庭第273号判决,咨询意见,1982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英文本第333-334页,第21段.
)15.
本法院应确定,提出咨询意见请求的必须是有此权限的机关或机构.
就本案言,本法院注意到大会征求咨询意见的授权是《宪章》第九十六条第一项,其中规定:"大会或安全理事会对于任何法律问题得请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
"16.
虽然上述规定指出,"对于任何法律问题",大会得征求咨询意见,在过去本法院有时曾就咨询意见请求这一议题与大会活动之间的关系作出过某些表示(解释与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和平条约,1950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英文本第70页;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咨询意见,1966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㈠,英文本第232和233页,第11和12段).
17.
本法院将审理本案.
本法院要指出《宪章》第十条已在《宪章》范畴内就"任何问题或事项"授予大会权限,同时第十一条第二项已具体给予大会对"任何会员国……向大会所提关于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任何问题"的权限和根据这两条规定的某些条件提出建议的权限.
如以下将解释的,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的问题是由若干会员国在为处理1997年4月25日大会第ES-10/2号决议认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而召开的大会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上向大会提出的.
*18.
在进一步审查本诉讼中提出的管辖权问题之前,本法院认为必须说明导致第ES-10/14号决议通过的情况,大会在该决议中请求发表关于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
19.
通过该决议的大会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首先是在关于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某些定居点的两项决议草案于1997年3月7日和21日被某一常任理事国投下反对票而遭安全理事会否决后召开的(分别见S/1997/199和S/PV.
3747及S/1997/241和S/PV.
3756).
其后阿拉伯集团主席在1997年3月31日的信中请求"按照题为'联合一致共策和平'的第377A㈤号决议的规定,召开大会紧急特别会议",以讨论"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和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其他地区的非法行动"(1997年3月31日卡塔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ES-10/1,1997年4月22日,).
联合国多数成员同意这项请求,大会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997年4月24日举行(见A/ES-10/1,1997年4月22日).
第二天通过了第ES-10/2决议;大会在决议中表示深信:"占领国以色列屡次违反国际法以及不遵守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有关决议和双方达成的各项协议,会破坏中东和平进程并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并谴责以色列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和其余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非法行动",特别是在该领土上建筑定居点.
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其后于暂时休会后又复会十一次(1997年7月15日、1997年11月13日、1998年3月17日、1999年2月5日、2000年10月18日、2001年12月20日、2002年5月7日、2002年8月5日、2003年9月19日、2003年10月20日和2003年12月8日).
20.
阿拉伯集团主席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在2003年10月9日的信中,要求安全理事会立即召开会议,审议"以色列……不断严重违反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并对此采取必要措施"(2003年10月9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2003年10月9日,S/2003/973).
该信附有供安理会审议的一项决议草案,其中谴责以色列偏离1949年停战线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内修建一道墙的做法是非法行为.
安全理事会在2003年10月14日举行了第4841次和4842次会议,审议题为"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的项目.
其后安理会又收到了同日几内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提出的另一决议草案,后者也谴责修建一道墙.
后一决议草案经公开辩论后付诸表决,因安理会有一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没有获得通过(S/PV.
4841和S/PV.
4842).
2003年10月15日,阿拉伯集团主席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要求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复会,审议题为"以色列在被占领东耶路撒冷及其余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内的非法行动"的项目(A/ES-10/242);这项要求得到了不结盟运动(A/ES-10/243)和联合国伊斯兰会议组织小组(A/ES-10/244)的支持.
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于2003年10月20日恢复工作.
21.
2003年10月27日,大会通过了第ES-10/13号决议,其中要求"以色列停止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包括在东耶路撒冷城内和附近建墙并拆除已建的墙,这道墙偏离1949年的停战线并且违反国际法的有关规定"(第1段).
大会在第3段中请秘书长"定期报告本决议的遵守情况,并在一个月内提交第一次报告说明〔决议〕第1段的遵守情况".
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在2003年11月24日暂时休会,印发了秘书长按照大会第ES-10/13号决议提交的报告(下称"秘书长报告"(A/ES-10/248).
22.
同时在2003年11月19日,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1515(2003)号决议,其中"赞同四方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永久性两国解决办法基于表现的路线图》".
四方由美利坚合众国、欧洲联盟、俄罗斯联邦和联合国的代表组成.
该决议"吁请当事各方同四方合作,根据《路线图》履行义务,实现两国和平、安全地毗邻共存的希望".
《路线图》和第1515(2003)号决议都未就隔离墙的修建载有任何具体规定,安全理事会未讨论过这个方面.
23.
十九天后,即2003年12月8日,经阿拉伯集团主席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并遵照第ES-10/13号决议提出新的要求后(2003年12月1日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大会主席的信,2003年12月2日,A/ES-10/249),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再度恢复工作.
在同日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请求发表本咨询意见的第ES-10/14号决议.
*24.
本法院在回顾了通过第ES-10/14号决议的先后情况后,现将说明在本诉讼过程中提出的管辖权问题.
首先,以色列指称由于安全理事会积极处理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大会请求发表咨询意见说明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根据《宪章》大会是越权的.
25.
本法院已指出这一请求发表咨询意见的议题,根据《宪章》是属于大会的权限(见上文第15-17段).
但是,《宪章》第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当安全理事会对任何争端或情势,正在执行本宪章所授予该会之职务时,大会非经安全理事会请求,对于该项争端或情势,不得提出任何建议.
"发表咨询意见的请求本身并不是大会"对于〔一项〕争端或情势"提出建议.
但在本案中的一项说法是,大会通过第ES-10/14号决议就是未遵照第十二条行事的越权行为.
因此,本法院认为最好由法院就相关文字和联合国的惯例,审查该条的意义.
26.
根据《宪章》第二十四条,安全理事会负有"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
在这方面,安理会可"在诸如其根据宪章……发出命令或指令的情况下"责成各国承担"明确的遵守义务",并可为此"以强迫行动要求各国执行"(联合国某些经费(《宪章》第十七条第二项),1962年7月20日咨询意见,1962年国际法院报告,英文本第163页).
但是,本法院要强调,第二十四条提到的是主要权限,但不必然是独有权限.
根据《宪章》第十四条,大会除其他外,有权为各种情势"建议和平调整办法"(联合国某些经费,同上,英文本第163页).
"第十四条对大会施加的唯一限制是第十二条中列出的限制,即大会非经安全理事会请求,对于安全理事会处理的同一事项,不得提出任何建议.
"(同上).
27.
关于大会的惯例,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原先对第十二条的解释和适用是,大会不得就仍属安全理事会议程事项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提出建议.
因此大会第四届会议拒绝就印度尼西亚问题建议某些措施,理由除其他外,是因安理会仍在处理这一事项(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届会议,特设政治委员会,会议简要记录,1949年9月27日至12月7日,1949年12月3日第56次会议,英文本第339页,第118段).
至于安理会方面,则有多次删除了议程中的项目,以使大会能够予以讨论(例如西班牙问题(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一年:第二编,第21号,1946年11月4日第79次会议,英文本第498页)、希腊边界事件(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年,第89号,1947年9月15日第202次会议,英文本第2404-2405页)和台湾岛(福尔摩沙)问题(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五年,第48号,1950年9月29日第506次会议,英文本第5页)).
另有大韩民国案件,安理会在1951年1月31日决定从所处理的事项清单中去除相关项目,使大会能够讨论这一事项(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六年,S/PV.
531,1951年1月31日第531次会议,英文本第11-12页,第57段).
但是,对第十二条的这种解释随着时间改变.
因此大会认为有权在1961年就刚果事项(第1955(XV)号决议和第1600(XVI)号决议)和在1963年就葡萄牙殖民地(第1913(XV)号决议)作成建议,安理会则未对这两个事项通过任何最新决议.
针对秘鲁在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提出的问题,联合国法律顾问证实大会将《宪章》第十二条的"正在执行职务"字眼解释为"目前正在执行职务"(第二十三届大会,第三委员会,第1637次会议,A/C.
3/SR.
1637,第9段).
实际上,本法院注意到随著时间的推移,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已日益平行处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同一事项(例子可参看塞浦路斯、南非、安哥拉、南罗得西亚事项,更近的例子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及索马里).
往往是安全理事会倾向于将重点放在与国际和平与安全相关的事项方面,而大会则视野更广,也考虑其人道主义、社会和经济方面.
28.
本法院认为随时间演进的公认大会做法符合《宪章》第十二条第一项.
因此,大会认为,大会采纳第ES-10/14号决议,征求本法院的咨询意见,并不违反《宪章》第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
本法院的结论是,大会提出这项请求并未超越其权限.
29.
但是有人向本法院争辩,要求发表咨询意见的这项请求并不能满足第377A㈤号决议规定的基本条件,而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是根据该决议召开,并继续行事.
在这方面的说法是,首先"安全理事会从未处理提议安理会本身应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对当前争议事项的咨询意见的决议草案",因此这一具体议题从未提交给安理会,大会不能因安理会没有任何行动而提出这种请求.
第二个说法是,在大会通过第ES-10/14号决议之前,安全理事会通过了核可"路线图"的第1515(2003)号决议,继续行使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因此大会没有资格代其行事.
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遵循的程序的效力,尤其是特别会议的"滚动性质"及其在大会召开常会的同时开会讨论请求发表咨询意见一事,也受到了质疑.
30.
本法院可回顾第377A㈤号决议,其中称:"安全理事会遇似有威胁和平、破坏和平、或侵略行为发生之时,如因常任理事国未能一致同意,而不能行使其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则大会应立即考虑此事,俾得向会员国提出集体办法之妥当建议…….
"该决议规定的程序以两项条件为前提,即因一个或多个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安理会不能行使其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和似有威胁和平、破坏和平、或发生侵略行为的情势出现.
因此本法院必须确定召开大会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的这两项条件是否已经得到满足,特别是在大会决定请求本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时候.
31.
鉴于先后发生上文第18段至第23段所述事件,本法院认为,在1997年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召开时,由于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反对票,安理会无法就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内某些以色列定居点一事作出决定;而且,如ES-10/2号决议(见上文第19段)所示,存在着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本法院还注意到,在安全理事会于2003年10月14日再次因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反对票否决了一项关于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内建造隔离墙的决议草案之后,2003年10月20日,大会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在同1997年一样的基础上重新召开(见巴勒斯坦代表和以色列代表的发言,A/ES-10/PV.
21,第2页和第5页).
本法院认为,安全理事会再次没有按照第377A(V)号决议所设想的那样采取行动.
本法院认为,2003年10月20日至2003年12月8日期间这方面的情况似乎没有发生变化,因为安理会既没有讨论隔离墙的建造问题,也没有就此通过任何决议.
因此,本法院认为,截至2003年12月8日,安理会没有重新审议2003年10月14日的反对票.
由此看来,在这一期间,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的重新召开是恰当的,它根据第377A(V)号决议处理目前本法院审理的事项也是适合的.
32.
本法院还强调,在这届紧急特别会议期间,大会可以通过属于召开特别会议要审议的主题及其权力范畴内的任何决议,包括一项征求本法院意见的决议.
就此没有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提议,要求征求意见,这在此毫不相关.
33.
现在谈及据称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程序不正常一事.
本法院认为,特别会议的"滚动式"特点,即其在1997年4月召开,随后又重新召开11次,这同大会所提请求的有效性并没有任何关联.
在这方面,本法院注意到,大会第七届紧急特别会议于1980年7月22日召开,随后重新召开4次(1982年4月20日、1982年6月25日、1982年8月16日和1982年9月24日),而大会在这些情况下通过的决议或决定的有效性从来没有引起任何争议.
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期间先前通过的任何决议的有效性也从来无人提出质疑.
34.
本法院还注意到,以色列争辩认为,在大会常会正在进行期间,重新召开第十届特别紧急会议很不妥当.
本法院认为,也许起初没有设想到大会可以同时召开紧急会议和常会,但是也没有提出联合国有任何规则因此而遭到违反,致使含有征求咨询意见此一请求的决议无效.
35.
最后,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看来是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九条(b)款的规定召开的,有关会议也是根据适用的规则召开的.
本法院在1971年6月21日关于"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276(1970)号决议继续留驻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对各国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中指出,"联合国一个妥善组成的机构根据其议事规则通过、且经其主席宣布妥当通过的决议,必须设定其为有效通过"(《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22页,第20段).
有鉴于此,本法院认为,本案件中没有任何理由推倒这一假定.
*36.
本法院现审议有关本诉讼程序中管辖权的另一个问题,即这样一个论点:大会征求的咨询意见不是针对《宪章》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和《国际法院规约》第六十五条第一款含义内的"法律问题".
据认为,对这两项规定来说,一个问题若要构成"法律问题",就必须合理地具体,因为否则本法院就不能给予答复.
对于本咨询程序中的请求,据认为,不可能相当合理肯定地确定要求本法院咨询的问题的法律含义,理由有二.
首先,据认为,关于建造隔离墙的"法律后果"问题,只允许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其中每种解释都会导致不应由本法院采取的行动.
所提问题可以首先解释为请本法院裁定建造隔离墙是非法的,然后就此非法行为的法律后果提出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据称,本法院应不答复所提问题,理由有多种多样,其中一些理由涉及管辖权,也有一些理由涉及是否适当.
关于管辖权,据认为,大会想就建造隔离墙是否合法这一十分复杂、十分敏感的问题征求本法院的看法,就应如此明确地征求意见(参见"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人员交换",咨询意见,《1925年常设国际法院案例汇编》,B辑,第10号,第17页).
据说,对这一请求还有第二种可能的解释,即本法院应推断建造隔离墙是非法的,然后就这一推定的非法行为的法律后果发表意见.
据认为,本法院也不应按这一假设答复问题,因为这一请求是以可疑假设为依据的,而且不管怎样,不确定非法行为的性质,就不可能就该非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作出判决.
其次,据认为,向本法院提出的问题不具有"法律"特征,因为问题不确切,很抽象.
特别是据称,问题中没有具体说明是要求本法院审理给"联合国大会或某些其他机构"、"联合国会员国"、"以色列"、"巴勒斯坦",还是给"以上各方面某种形式的组合或一些其他实体"带来的法律后果.
37.
关于据称大会请求的条件不清楚及其对提交给本法院的问题"法律性质"造成的影响,本法院认为,考虑到国际法各项规则和原则,包括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下称"日内瓦第四公约")及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各项决议,这一问题针对的是某一实际情况产生的法律后果.
因此,用本法院在其关于西撒哈拉的咨询意见中使用的词语来表示,大会所提问题"是从法律角度拟写的,涉及了国际法中的问题";按其性质而言,可以根据法律给予答复;而且确实也很难在法律依据以外给予答复.
本法院认为,这的确是一个具有法律特征的问题(见西撒哈拉,咨询意见,《1975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8页,第15段).
38.
本法院希望指出,问题的措辞缺乏清晰度,这并不意味着本法院没有管辖权.
相反,这种不明确将需要在解释中给予澄清,而本法院常常给予这种必要的解释澄清.
过去,常设国际法院和本法院都在某些案例中表示,关于征求咨询意见的请求的措辞或是没有准确说明要求本法院发表意见的问题("1926年12月1日《希腊-土耳其协定》(《最后议定书》第四条)的解释",咨询意见,《1928年常设国际法院案例汇编》,B辑,第16(I)号,第14-16页),或是没有应对审理中的"真正法律问题"("1951年3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同埃及的协定的解释",咨询意见,《1980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87-89页,第34-36段).
本法院在一个案例中指出,"提交给本法院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既措辞不当,又十分模糊"("申请复核联合国行政法庭第273号判决",咨询意见,《1982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348页,第46段).
因此,常常要求本法院扩大、解释甚至重新措辞所提出的问题(见上文引用的三项意见;另见Jaworzina,咨询意见,《1923年常设国际法院案例汇编》,B辑,第8号;"西南非洲问题委员会可否举行请愿人听证会问题",咨询意见,《1956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25页;"联合国某些经费(《联合国宪章》第十七条第二项)",咨询意见,《1962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57-162页).
在本案中,本法院将只能按照过去惯例从事,即"找出现行原则和规则,给予解释和应用……从而根据法律对提出的问题给予答复"("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1996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一》,第234页,第13段).
39.
在本案中,如果大会请本法院阐述建造隔离墙带来的"法律后果",使用这些术语就必然包括评估建造隔离墙是否违反国际法中某些规则和原则.
这样,本法院首先就要确定,按照预定路线建造隔离墙是否已经而且仍在违反这些规则和原则.
40.
本法院认为,争论中所称向本法院提出的问题具有的抽象性质并没有引起管辖权问题.
即便在关于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案例中,提出的是适当性问题,而非管辖问题,本法院的立场仍然是:若认为本法院不应审理用抽象语言表达的问题,这"仅仅是缺乏任何根据的说法","本法院可以就任何法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无论其是否抽象"(《1996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一》,第236页,第15段,其中提及"接纳国家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条件(《宪章》第四条)"咨询意见,《1947-1948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61页;"联合国行政法庭补偿裁决的效力",咨询意见,《1954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51页;"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276(1970)号决议继续留驻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对各国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1971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27页,第40段).
无论如何,本法院认为,就建造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向法院提出的问题不是一个抽象问题,而且将由本法院来判定给何方带来这种后果.
41.
本法院还不能接受在本诉讼程序中也曾提出的这一看法,即由于提出的问题具有"政治"特征,所以本法院没有管辖权.
从本法院就此一贯坚持的法理立场可以清楚地看出,本法院认为,法律问题也包含有政治方面,这一事实,"如同国际生活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一样,按事情的性质,不足以剥夺其'法律问题'的特征,也不足以'使本法院失去其《规约》明确赋予的权限'("申请复核联合国行政法庭第158号判决",咨询意见,《1973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72页,第14段).
无论政治方面如何,本法院都不能拒绝承认一个问题的法律特征,这种法律特征要求本法院执行一项基本的司法工作,即评估国家履行国际法规定的义务方面某些可能行为的合法性(参见"接纳国家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条件,(《宪章》第四条)",咨询意见,1948年,《1947-1948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61和第62页;"联合国大会接纳国家加入联合国的权限",咨询意见,《1950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6和第7页;"联合国某些经费(《宪章》第十七条第二项)",咨询意见,《1962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55页).
"("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1996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一》,第234页,第13段).
在其关于"1951年3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同埃及的协定的解释"的意见中,本法院甚至强调,"在政治考虑十分显著的情况下,一个国际组织尤其有必要就适用于辩论事项的法律原则征求本法院的咨询意见……"(《1980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87页,第33段》.
此外,本法院还在"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意见中申明,"可能促使提出该请求的动机的政治性质以及发表的意见可能具有的政治影响,同确立其发表意见的管辖权毫无关联"(《1996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一》,第234页,第13段).
本法院认为,目前的审理中没有任何因素会使本法院得出不同的结论.
*42.
本法院因此拥有管辖权,能够提出大会ES-10/14号决议所征求的咨询意见.
**43.
不过,目前审理中有看法认为,本法院应拒绝行使管辖权,因为大会的请求中有些具体方面使得本法院行使管辖权显得不适当,不符合本法院的司法职能.
44.
本法院以往曾多次回顾,《规约》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法院……得发表咨询意见……"应解释为是指本法院有权自行决定不提出咨询意见,既便管辖权的条件都已符合("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咨询意见,《1996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一》,第234页,第14段).
不过,本法院意识到,答复有关征求咨询意见的请求,就"表明其参与联合国的活动,原则上不应拒绝"("与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合约的解释,第一阶段,咨询意见,《1950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71页;另见"关于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享有法律程序豁免的争议",咨询意见,《1999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一》,第78和第79页,第29段等.
)鉴于作为"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宪章》第九十二条)担负的责任,本法院原则上不应拒绝提出咨询意见.
根据其一贯的法理立场,只有"紧迫原因"才应使本法院拒绝提出意见("联合国某些经费(《宪章》第十七条,第二项)",咨询意见,《1962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55页;另见"关于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享有法律程序豁免的争持",咨询意见,《1999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一》,第78和第79页,第29段等.
)本法院在运用酌处权时,从未拒绝对征求咨询意见的请求作出答复.
本法院决定不就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国家在武装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请求提出咨询意见的依据是,本法院无管辖权,而不是出于司法适当性的考虑(见《1996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一》,第235页,第14段).
只有一次本法院的前身常设国际法院认为不应答复向其提出的问题("东卡雷里亚的地位",咨询意见,《1923年常设国际法院案例汇编》,B辑,第5号),但是,其原因是"该案件非常独特的情况,其中包括,问题直接涉及一个业已存在的争端,争端的一方当事国既不是《常设法院规约》缔约国,也不是国际联盟的成员国,该国反对诉讼程序,拒绝以任何形式参加"("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1996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一》,第235和第236页,第14段).
45.
这些考虑并没有使本法院逃避责任,每当接到征求意见的请求时,参照上文所述"紧迫原因"这一标准,满意地处理行使其司法职能是否适当的问题.
因此,本法院将本着自己的法理立场,详细审析这方面提呈的每个主张.
*46.
第一个主张大致是:本法院不应对本案件行使管辖权,因为这项请求涉及以色列同巴勒斯坦间有争议的事由,对这一事由,以色列不同意行使这种管辖权.
这一看法认为,大会所提问题的标的"是以色列——巴勒斯坦关于恐怖主义、安全、边界、定居点、耶路撒冷和其他有关问题更大争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以色列强调,以色列从未同意由本法院或以任何其他强行裁定手段解决这一更大的争端;与此相反,以色列表示,各方一再表示应通过谈判解决这些问题,并有可能商定可以求助于仲裁.
以色列因此主张,本法院应拒绝发表本意见,依据之一是常设国际法院就东卡雷里亚所作裁决的先例.
47.
本法院认为,有关国家不同意本法院有争议的管辖权,这并不影响本法院拥有发表咨询意见的管辖权.
本法院在1950年的一项咨询意见中解释道:"争端当事国的同意,是本法院在诉讼案件中行使司法权的依据.
对于咨询程序而言,情况则有所不同,即便征求意见的请求涉及国家间实际未决的法律问题,也是如此,本法院的答复只具有咨询性质,因此不具约束力.
由此而见,无论是否联合国会员国,任何国家都不能阻止发表联合国认为有益于获得指点,协助其决定所采取行动的咨询意见.
本法院的咨询意见不是对国家发表的,而是对有权提出请求的机构发表的;作为'联合国机关'的本法院的答复,表明其参与联合国的活动,原则上不应拒绝.
"("与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缔结的和约的解释",第一阶段,咨询意见,《1950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71页;另见"西撒哈拉",《1975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24页,第31段).
由此可见,在这些审理过程中,本法院均未拒绝答复征求咨询意见的请求,理由是:在特定情况下,本法院没有管辖权.
然而,本法院的确在司法适当问题中,审析了某些有关国家对大会的请求表示的反对.
本法院在关于西撒哈拉的咨询意见中评述其1950年决定时解释说,它"因此……承认,不表示同意,则可能构成虽接到请求,但拒绝发表意见的理由,如果在某一特定案件中,对司法适当性的考虑应促使本法院拒绝发表意见.
"本法院接着评述道:"在某些情况下……有关国家不表示同意,可能使咨询意见的发表有悖于本法院的司法性质.
以下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当情况表明,给予答复将等同于绕过此一原则:国家未经同意,则没有义务让其争端交由司法解决.
"("西撒哈拉",《1975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25页,第32-33段).
本法院在运用这项原则审理有关西撒哈拉的请求时裁定,的确存在着法律争端,不过是在大会审理过程中出现的,涉及大会正在处理的事项;而不是在双边关系中独立出现的(同上,第25页,第34段).
48.
关于法院收到的请它提出咨询意见的请求,法院认识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对以色列修建隔离墙引起的法律后果表达了截然不同的观点,而大会请本法院对这个问题提出意见.
然而,正如法院自己所说,"几乎在每一个咨询程序中都对法律问题存在着……意见分歧"(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276(1970)号决议继续留在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对各国产生的法律后果,《1971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咨询意见,第24页,第34段).
49.
此外,法院认为,不能把大会提出这项请求的事由视为只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双边事项.
鉴于联合国对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关的问题所具有的权力和负有的责任,法院认为,隔离墙的修建,必须视为与联合国直接相关.
联合国在这个事项上的责任也源于关于巴勒斯坦的分治决议(见下文第70和71段).
大会把这种责任称为"对巴勒斯坦问题负有永久的责任,直至此问题的所有方面均按照国际正统性获得令人满意的解决为止,"(大会2002年12月3日第57/107号决议).
在联合国的体制框架内,这种责任表现为通过了许多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大会决议,以及专门设立了一些附属机构来协助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
50.
向法院提出请求的目的是,请本法院提出大会认为将有助于它适当履行职责的咨询意见.
请法院提出的咨询意见,事关联合国特别关切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涉及的范围远远超过了双边争端.
在这种情况下,法院认为,发表咨询意见并不会产生规避同意司法解决原则的结果,因此法院不能行使酌处权以此为由而拒绝发表咨询意见.
51.
现在法院谈一谈在本程序中提出的支持法院拒绝行使管辖权的又一论点.
一些参与人说,如果法院就隔离墙的合法性以及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提出咨询意见,就可能阻碍通过谈判政治解决以巴冲突.
特别是有人认为,此种咨询意见可能损害"路线图"计划(见上文第22段),路线图要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其中提及的各个不同阶段履行某些义务.
据称,请法院提出的咨询意见可能使"路线图"中设想的谈判复杂化,因此,本法院应行使酌处权,拒绝对提出的问题作出答复.
这是法院过去不得不多次考虑过的一种意见.
例如,法院在就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提出的咨询意见中说:"有人认为,法院如对此案作出答复,可能对裁军谈判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会违背联合国的利益.
法院认识到,在它可能提出的任何咨询意见中,无论作出何种结论,都将对大会关于该事项的持续辩论产生影响,并将成为有关谈判的又一个因素.
此外,咨询意见产生何种影响,是能否受到重视的问题.
法院听到有人提出相反的观点,而且没有任何明显的标准,法院可籍以认定一种评估优于另一种评估.
"(《1996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㈠,第237页,第17段;并见"西撒哈拉问题",《1995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37页,第73段).
52.
一位参与人表示,如果法院要对这项请求采取行动,无论如何都应铭记:"和平进程的两个主要方面:最终地位问题必须通过谈判解决的基本原则;在过渡期间双方必须履行安全责任,使和平进程能够取得成功".
53.
法院认识到,安全理事会第1515(2003)号决议核准的"路线图"(见上文第22段)是解决以巴冲突的谈判框架.
然而并不清楚本法院的咨询意见可能对这些谈判产生何种影响:本程序的参与人对这个问题表达了不同的观点.
法院不能把这一因素视为应拒绝行使管辖权的充分理由.
54.
还有一些参与人向法院提出,修建隔离墙只是以巴冲突的一个方面,这个问题无法在本程序中得到适当解决.
然而,法院并不认为这是拒绝对所提问题作出答复的一个理由.
法院确实认识到,隔离墙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的一部分,在法院可能提出的咨询意见中,将仔细考虑到这一情况.
同时,大会向法院提出的问题只限于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法院只有在对审议向它提出的问题有必要时才会审查其他问题.
*55.
几位程序参与人还认为,法院应该拒绝行使管辖权,因为它没有掌握作出结论所需的事实和证据.
特别是以色列提及就与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和约的解释提出的咨询意见.
以色列认为,有些事项会引起只有听取了冲突所有各方的意见后方能澄清的事实问题,因此法院不能就这些事项提出咨询意见.
以色列认为,如果法院决定提出所请求的咨询意见,将不得不对基本事实作出推测,对法律论点作出假定.
更具体地说,以色列认为,法院不能在没有进行以下调查之前就对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作出裁定:第一,调查打算通过修建隔离墙对付的安全威胁的性质和范围,以及此种对策的效果;第二,调查修建隔离墙对巴勒斯坦人的影响.
这项任务在一个有争议的案件中本已很困难,在咨询程序中就更加复杂,特别是因为只有以色列掌握很多必要资料,却它表示已决定不谈论案件的是非曲直.
以色列的结论是,法院面对在本程序中无法澄清的事实问题,应运用其酌处权,不答应关于提出咨询意见的请求.
56.
法院认为,在每一具体案例中,都必须确定它所掌握的证据是否足以提出咨询意见.
就与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和约的解释提出的咨询意见(《1950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72页),以及就西撒哈拉问题提出的咨询意见,法院都在其中清楚地表明,这些案例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本法院是否掌握了足够的资料和证据,使它能够就一切有争议的事实问题作出司法结论,法院要在符合司法特点的情况下提出咨询意见,就必须查明事实"(西撒哈拉问题,《1975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28和29页,第46段).
因此,例如在关于东卡雷利亚地位的程序中,常设国际法院决定不提出咨询意见,其理由之一是提出的问题"引起了不事先听取双方意见就无法澄清的事实问题"(与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和约的解释,《1950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72页;见东卡雷利亚的地位,常设国际法院,汇编B,第5号,第28页).
另一方面,在西撒哈拉问题咨询意见中,法院说,它已获得关于相关事实的大量书面证据(《1975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29页,第47段).
57.
在本案中,法院有秘书长的报告以及他向法院提交的大量档案材料,其中不仅有关于隔离墙走向的详细资料,并且有关于隔离墙对巴勒斯坦居民的人道主义和经济社会影响的资料.
这些档案资料包括根据特别报告员和联合国主管机构在实地视察后编写的一些报告.
秘书长还向本法院提交了一份更新其报告的书面陈述,补充报告的内容.
此外,参与程序的其他许多人都已向法院提交了书面陈述,载有与答复大会所提问题有关的资料.
法院特别注意到以色列的书面陈述.
这份陈述虽然只限于司法管辖和司法正当性,但也提出了关于其他问题的意见,包括以色列安全方面的忧虑,同时载有相关的;以色列政府就这些事项发表的许多其他文件都是公开材料.
58.
法院认为,它已具备足够的资料和证据,能够提出大会请求的咨询意见.
此外,他人可能以主观或政治方式评价和解释这些事实的情况,不能成为法院放弃司法任务的理由.
因此,本案并不缺乏有关资料,因此法院没有充分理由不提出所请求的咨询意见.
59.
一些参与人还在其书面陈述中提出了理由,认为本法院应拒绝就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提出意见,因为这种意见不会起任何实际作用.
他们认为,有的机关或机构今后的行动需要在法律上加以澄清,而法院的咨询意见应视为提供此种澄清的一个途径.
在本案中,还有人认为,大会不需要法院的咨询意见,因为大会已经宣布修建隔离墙是非法的,并已确定其法律后果,要求以色列停止修建并拆除隔离墙,另一个原因是,大会从未明确表示它打算如何使用法院的咨询意见.
60.
法院的判例清楚地表明,咨询意见的目的是向提出请求的机构提供它们在行动中必需的法律工具.
法院在关于对《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保留的咨询意见中说:"请求提供咨询意见的目的是指导联合国自己的行动".
(《1951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9页).
同样,本法院在就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276(1970)号决议继续留在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对各国产生的法律后果提出的咨询意见中说:"一个联合国机关针对自己的决定提出这项请求,它请求法院对这些决定将产生的结果和所涉问题提出法律咨询意见"(《1971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24页,第32段).
在另一案件中,法院认为,它将提出的咨询意见,将"为联合国进一步处理西撒哈拉非殖民化问题提供有关的法律意见"(西撒哈拉问题,《1975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37页,第72段).
61.
关于大会没有清楚地表明它将如何使用关于隔离墙的咨询意见的说法,法院回顾它在关于"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中提出的观点,这种观点同样适用于本程序:"某些国家说,大会没有向法院解释,它请求提供咨询意见的确切目的是什么.
然而,大会在履行职能时是否需要咨询意见,不应由法院自己决定.
大会自己有权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一项咨询意见的用途".
(《1996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㈠,第237页,第16段).
62.
因此,法院不能以其咨询意见不会有任何实际作用为理由,不答复提出的问题.
本法院不能用自己对请它提出的咨询意见是否有用所作出的评估来取代提出此种请求的机关、即大会的评估.
此外,况且法院认为大会尚未确定自己的决议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
法院的任务是全面确定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则可以从法院的裁定中得出结论.
*63.
最后,法院将谈一谈对它在本程序中提出咨询意见是否适当提出的又一个论点.
以色列说,隔离墙的目的是阻止对以色列及其居民犯下的暴力行为,而巴勒斯坦对这些行为负有责任,因此它不能请求法院对它自己的非法行为所造成的局面提出补救办法.
在这方面,以色列援引了任何人都不能获益于自己的错误行为的原则,它认为同在许多有争议的案件中一样,这项原则适用于咨询程序.
因此,以色列的结论是,诚意和"清白"原则是法院应拒绝大会请求的一个充分理由.
64.
法院认为这个理由是牵强附会的.
前面已强调过,是大会请求提出咨询意见,这项意见是向大会、而不是向任何具体国家或实体提出.
**65.
根据以上所述,本法院认定,它不仅具有就大会所提问题提出咨询意见的管辖权(见上文第42段),并且没有充分理由行使酌处权而不提供咨询意见.
***66.
法院现将答复大会在ES-10/14中提出的问题.
法院回顾,问题是这样提出的:"考虑到国际法规则和原则、包括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以及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有关决议,如秘书长报告所述,占领国以色列在包括耶路撒冷及周围地带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构筑围墙,有何法律后果"67.
如下文第82段所解释,所说的"隔离墙"("wall")是一个综合的建筑物,因此不能从有限的实物意义来理解这个用语.
然而,所使用的其他词,不论是以色列使用的"fence"一词,还是秘书长使用的"barrier"一词,如果从实物意义来理解,都是不准确的.
因此法院决定在本咨询意见内采用大会使用的用语.
法院还指出,大会的请求涉及"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地区在内的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修建隔离墙所产生的法律后果.
同样,如下文所述(见下文第79至84段),隔离墙的一部分修建在、或计划修建在以色列自己的领土上;法院认为并没有要求它审查修建这些部分的隔离墙所产生的法律后果.
68.
大会提出的问题事关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
不过为了向大会说明这些后果,法院必须首先确定修建隔离墙是否违反了国际法(见上文第39段).
因此,法院将先作出这裁定,然后再论及修建隔离墙的后果.
69.
为此,法院将首先扼要分析该领土的地位,接着叙述领土上已完成的工程或正在进行的工程.
然后,在设法裁定其是否违法之前,先说明适用的法律.
**70.
巴勒斯坦过去是奥托曼帝国的一部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国际联盟根据《盟约》第22条第4款,委托联合王国对巴勒斯坦进行"A"类委任统治,这一款规定:"原来属于土耳其帝国的某些社区已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可临时承认其作为独立国家的存在,条件是由一个受委任统治国向其提供行政咨询和协助,直至这些国家能够自立".
法院回顾,它在关于西南非洲国际地位的咨询意见中谈到委任统治问题时说,"创立委任统治制度是为了领土居民以及全人类的利益,是作为一种有国际目标的国际体制——一种神圣的文明托管.
"(《1950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32页).
关于这个问题,法院还认为,"有两项原则至关重要:不兼并原则以及[尚不能管理自己的]……人民的福祉与发展原则,构成'神圣的文明托管'"(同上,第131页).
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区的边界是通过各种文书确定的,特别是英国1922年9月16日备忘录和1928年2月20日的一项英国-外约旦条约确定了东部边界.
71.
1947年,联合王国宣布打算在1948年8月1日前全部撤出委任统治领土,后来又把这个日期提前至1948年5月15日.
同时,大会于1947年11月29日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未来治理问题的第181(II)号决议,其中"建议联合王国和联合国所有其他会员国通过并执行"决议中提出的"分治计划",把该领土分为两个独立国家,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家,并为耶路撒冷城建立一种特殊的国际制度.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国家反对这项计划,认为这项计划有失偏颇;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根据这项大会决议宣布独立,随后在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国家之间爆发武装冲突,《分治计划》未得到执行.
72.
安全理事会1948年11月16日第62(1948)号决议决定,"巴勒斯坦各区应即停战",并呼吁直接参与冲突各方设法为此目的达成协定.
根据这项决定,在联合国调停下,1949年以色列同邻国缔结了全面停战协定.
特别是1949年4月3日以色列同约旦在罗得岛签署了这样一项协定.
该协定第五条和第六条确定了以色列部队和阿拉伯部队之间的停战分界线(后来经常称为"绿线",因为在地图上用绿色标出,下称"绿线").
第三条第2款规定,"双方的任何军事或准军事部队人员……都不得为任何目的超过或跨越停战分界线……".
第六条第8款议定,不得将这些条款"解释为在任何意义上妨碍双方之间的最终政治解决办法".
这一款还规定,"《协定》第五条和第六条中确定的停战分界线是双方议定的,不妨碍今后的领土解决办法或边界线,也不妨碍任何一方提出与其有关的权利主张".
分界线须经按双方可能商定的方式批准.
73.
在1967年的武装冲突中,以色列部队占领了曾经是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的所有领土(包括绿线以东被称为西岸的领土).
74.
1967年11月22日,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第242(1967)号决议,其中强调不容许通过战争获取领土,并呼吁"以色列军队撤离其于最近冲突所占领之领土",以及"终止一切交战地位之主张或状态".
75.
自1967年以来,以色列在这些领土上采取了旨在改变耶路撒冷城地位的若干措施.
安全理事会在多次回顾"不容许以军事占领获取领土的原则"后谴责这些措施,并在1971年9月25日第298(1971)号决议中以最明确的语气申明:"以色列所采变更耶路撒冷市地位的一切立法与行政行动,包括土地及财产的征用,人口的迁移及意在合并占领地区的立法等,均一概完全无效,且不能变更此种地位".
后来,1980年7月30日以色列通过了《基本法》,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完整和统一"的首都.
安全理事会随即在1980年8月20日第478(1980)号决议中宣布,颁布《基本法》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占领国以色列改变或意图改变耶路撒冷圣城的性质和地位所采取的一切立法和行政措施和行动……都是无效的".
决议还决定,"不承认这项'基本法'和以色列根据这项法令设法改变耶路撒冷性质和地位的任何其他行动".
76.
随后,1994年10月26日以色列同约旦签署了和平条约.
这项条约确定了两国的边界线,"参照了一(a)所示的委任统治时期划定的界限……但不影响1967年在以色列军事政府控制下的任何领土的地位"(第3条第1和第2款).
一载有相关地图,并补充说,关于"1967年在以色列军事政府控制下的任何领土",所标明的线是同约旦的"行政边界线".
77.
最后,自1993年以来,以色列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了若干协定,规定了各方的各种义务.
除其他外,这些协定要求以色列将其军事当局和民事行政机构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行使的某些权利和责任移交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有些权力和责任已经移交,但由于后来发生的事件,移交的权利和责任仍然不全面,范围有限.
78.
法院认为,根据1907年10月18日《第四项海牙公约》《陆战法规和习惯条例》(下称《1907年海牙章程》)第42条体现的国际习惯法(见下文第89条),领土实际由敌对军队管理时,则将其视为被占领土,占领范围只限于已建立并实施此种管理的领土.
以色列在1967年同约旦的武装冲突中占领了绿线和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原东部边界线之间的领土.
根据国际习惯法,这些领土是被占领土,以色列在这些领土的地位是占领国.
如上文第75至77段所述,以后在这些领土上发生的事件丝毫没有改变这种情势.
所有这些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仍然是被占领土,以色列的地位仍然是占领国.
*79.
以色列主要是在这些领土上建造或计划建造秘书长报告中所述的工程.
本法院现在将依据这一报告描述这些工程.
至于该报告印发之后的事态发展,本法院将参阅秘书长为了补充报告而提交的《联合国书面陈述》(以下称"秘书长书面陈述")中所载的补充资料.
80.
秘书长报告指出,"以色列政府自1996年以来一直在考虑推行计划以阻止从西岸中部和北部渗入以色列…"(第4段).
报告称,以色列内阁在2001年7月第一次核可这样一个计划.
内阁其后于2002年4月14日通过,建造这些工程的决定,目的是在西岸三个地区筑成长达80公里的所谓"安全围栏".
2002年6月23日,以色列内阁核可在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建造"连续围栏"的第一阶段工程,从而将项目推进到下一个阶段.
2002年8月14日,内阁通过了"围栏"A阶段工程的路线,目的是在西岸北部建造一个长123公里的综合体,从杰宁以北萨利姆检查站延续至埃肯纳定居点.
B阶段工程于2002年12月核准.
这一段长约40公里,从萨利姆检查站开始沿绿线北部朝伯珊向东延展,直至约旦河谷.
此外,以色列内阁于2003年10月1日核可全部路线.
根据秘书长报告,这条路线"将沿西岸延绵720公里".
一张显示已完成及已计划部分的地图于2003年10月23日张贴在以色列国防部网站上.
根据这一地图上提供的细节,围绕几个大定居点的接连部分(C阶段)将把围绕耶路撒冷建造的"安全围栏"的西北端,与在埃肯纳建造的A阶段工程的南端连接起来.
根据同一份地图,"安全围栏"将长达115公里,从耶路撒冷附近的吉洛山定居点延伸到希伯伦东南的卡尔迈勒定居点(D阶段).
根据国防部的文件,这一段工程定于2005年完工.
最后,案件卷宗中数次提到,以色列计划在约旦河谷以西沿山建造一个"安全围栏".
81.
根据秘书长的书面陈述,这些工程的第一部分(A阶段)最终延伸150公里,于2003年7月31日宣布完工.
据报告,大约56000巴勒斯坦人将被包围在飞地以内.
在这一阶段,围绕耶路撒冷周围建造了两段围栏,共19.
5公里.
2003年11月,沿NazlatIssa-Baqaal-Sharqiya飞地以西绿线建造一段新围栏的工程开始,到2004年1月秘书长提交书面陈述时已接近完工.
根据秘书长书面陈述,B阶段工程在2004年1月仍在进行.
这样,在绿线附近或沿绿线建造,延伸至al-Mutilla村的这一段围栏的初期工程,在2004年1月已基本完工.
另外两段在这一点分叉.
其中一段于2004年1月初动工,向东延伸至约旦边境.
第二段计划从绿线延伸至Taysir村,工程基本上没有开始.
然而联合国获悉,这第二段可能不会建造.
秘书长书面陈述进一步指出,C阶段工程从埃肯纳定居点附近的A阶段终点延伸至耶路撒冷东南的Nu'man村,于2003年12月动工.
这一段分为三个阶段.
C1阶段在Rantis村和Budrus村等村落之间建造,已完成计划的40公里中的大约4公里.
C2阶段将切入西岸22公里,环绕所谓的"阿列尔突出部".
这一阶段将纳入52000名以色列定居者.
C3阶段将建造两个"堑".
其中一个为南北向,大致与目前C1阶段在Rantis村和Budrus村等村落之间的一段工程平行.
另外一个为东西向,沿着据说为正在修建的45号公路一部分的路脊延伸.
如果完成这两个坑壕的工程,将形成两个飞地,圈入24个社区的72000名巴勒斯坦人.
2003年11月还沿着耶路撒冷市边界的东南部分开始进一步的工程.
根据秘书长书面陈述,这一路线将把耶路撒冷郊区的El-Ezariya村与耶路撒冷隔开,并把附近的AbuDis一分为二.
根据秘书长书面陈述,截至2004年1月25日,大约190公里的工程已经完工,覆盖A阶段和B阶段的大部分.
C阶段的进一步工程在西岸中部若干地区和耶路撒冷已经开始.
计划在西岸南部建造的D阶段尚未开始.
以色列政府解释说,上述路线和时间表可随时修改.
例如在2004年2月就拆除了Baqaal-Sharqiya镇附近一段8公里长的工程,墙的计划长度看起来也略有缩短.
82.
根据秘书长报告和书面陈述中的描述,已经计划或完成的工程已经形成或将形成一个下述形式的综合体,其中主要包括:⑴安装有电子传感器的围栏;⑵一条坑壕(深达4米);⑶一条双车道沥青巡逻路;⑷一条与围栏平行的追踪路(一条平滑的沙路以探测脚印);⑸标明综合体周边范围的六圈带刺铁丝.
综合体宽度为50至70米,有些地方甚至宽达100米.
这些工程另可加上"深堑".
秘书长提交报告时已经完工或正在建筑的大约180公里综合体中包括约8.
5公里水泥墙.
这些水泥墙通常位于巴勒斯坦居民中心靠近或邻接以色列的地方(如盖勒吉利耶和图勒凯尔姆附近或耶路撒冷部分地区).
83.
根据秘书长的报告,在最北部,已完工或正在建筑的隔离墙基本上不偏离绿线,但大部分在被占领领土内.
在若干地方,工程为了纳入定居者偏离绿线超过7.
5公里,同时也圈入了巴勒斯坦居民区.
图勒凯尔姆以西长度为1至2公里的隔离墙似乎是在绿线以色列一方.
而另一方面,在其他地方,计划路线将向东偏离多达22公里.
在耶路撒冷,现有的工程和已计划的路线远在绿线之外,在有些情况下甚至超出以色列划定的耶路撒冷市东部边界.
84.
根据秘书长报告,在这一路线的基础上,大约975平方公里,即整个西岸的16.
6%,将处于绿线和隔离墙之间.
据说这一地区是237000巴勒斯坦人的家园.
如果整个隔离墙按计划完成,另外还有160000巴勒斯坦人将生活在几乎被完全包围的社区,即报告中所述的飞地.
按照计划路线,将近有320000以色列定居者(其中178000在东耶路撒冷)将生活在绿线和隔离墙之间的地区.
85.
最后应该指出,在建筑隔离墙的同时还建立了新的行政制度.
例如2003年10月,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命令,将西岸位于绿线和隔离墙之间的地区定为"封闭区".
除非持有以色列当局签发的许可证或身份证,否则这一地区的居民不得继续在该地区居留,非居民也不得进入该地区.
根据秘书长报告,大多数居民获得的许可证期限有限.
以色列公民、以色列永久居民以及那些根据《回籍法》有资格移民至以色列的人,可以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在封闭区继续居留或自由进出封闭区.
进出封闭区必须通过封闭区的大门,但大门不经常开放,而且开放时间较短.
**86.
本法院现在将确定与评估以色列所采取措施的合法性相关的国际法规则和原则.
这些规则和原则见诸《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几项条约、习惯国际法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通过的相关决议.
然而,以色列一向质疑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文书的某些规则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适用性.
本法院现在将审议这些问题.
87.
本法院首先回顾,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1970年10月24日,大会通过题为"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的第2625(XXV)号决议(以下称"第2625(XXV)号决议").
该决议强调,"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取得的领土不得承认为合法.
"本法院在"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尼加拉瓜诉美利坚合众国)"案的判决书中指出,纳入《宪章》的使用武力原则反映了习惯国际法(见《1986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98-101页,第187-190段);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取得的领土不合法的推论也是如此.
88.
本法院还注意到,人民自决权利原则已载入《联合国宪章》,而且在大会上述第2625(XXV)号决议中得到了重申.
该决议指出,"每一国均有义务避免对[上述决议所指的……]民族采取剥夺其自决权利的任何强制行动.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的共同第1条重申了所有人民的自决权利,并规定各缔约国有义务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促进实现这项权利和尊重这项权利.
本法院回顾,1971年它曾强调指出,"《联合国宪章》所载列的关于非自治领土的国际法"的目前发展情况,"使自决原则适用于所有[此类领土]".
本法院接着指出,"这些发展让人们很少怀疑"《国际联盟盟约》第22条第1款所述的神圣任务的最终目标,"就是所涉人民的自决……"("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276(1970)号决议继续留驻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对各国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1971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31页,第52-53段).
本法院在判例中多次提到了这项原则(同上;另见"西撒哈拉咨询意见",《1975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68页,第162段).
的确,本法院已申明,人民的自决权利今天已成为一项普遍适用的权利(见"东帝汶(葡萄牙诉澳大利亚),判决",《1995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02页,第29段).
89.
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本法院首先注意到,以色列并非载有《海牙章程》的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缔约国.
本法院指出,用《公约》的话来说,《章程》的拟定就是"修订"当时的"一般战争法规和习惯".
但是,此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认为,"《公约》订立的规则为所有文明国家所承认,并被视为战争法规和习惯的宣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1946年9月30日和10月1日,第65页).
本法院自身在审查交战方开展军事行动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咨询意见",《1996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㈠,第256页,第75段).
本法院认为,《海牙章程》的规定已经成为习惯法的一部分,事实上已经得到了参与本法院咨询程序的所有各方的承认.
本法院还注意到,根据《日内瓦第四公约》第154条,该《公约》是对《海牙章程》第二编和第三编的补充.
《章程》第三编涉及"在敌国领土内的军事当局",对本案特别相关.
90.
第二,对于《日内瓦第四公约》,参与咨询程序的各方表达了不同观点.
以色列同绝大多数其他参与方相反,反对《公约》在法律上适用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
具体而言,秘书长报告载列的题为"以色列政府的法律立场概述"的一第3段说明,以色列不同意《日内瓦第四公约》"适用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理由是"该领土在被约旦和埃及兼并之前没有被承认为主权领土",因此认为它"不是《公约》所要求的缔约国领土".
91.
本法院回顾,以色列1951年7月6日就批准了《日内瓦第四公约》,而且现在是该《公约》缔约国.
约旦自1951年5月29日以来也一直是该《公约》缔约国.
两个国家无一提出与本咨询程序相关的任何保留意见.
此外,巴勒斯坦于1982年6月7日发表声明,单方面承诺适用《日内瓦第四公约》.
瑞士作为保存国,认为这项单方面承诺是有效的.
但瑞士又认为,它"作为保存国不能确定""巴勒斯坦解放运动[1989年6月14日]以'巴勒斯坦国'的名义提出加入"除其他外《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请求是否可被视作加入文书".
92.
此外,为确定《日内瓦第四公约》的适用范围,应当回顾,1949年8月12日四公约共同第2条规定:"于和平时期应予实施之各项规定外,本公约适用于两上或两个以上缔约国间所发生之一切经过宣战的战争或任何其他武装冲突,即使其中一国不承认有战争状态.
凡在一缔约国的领土一部或全部被占领之场合,即使此项占领未遇武装抵抗,亦适用本公约.
冲突之一方虽非缔约国,其他曾签订本公约之国家于其相互关系上,仍应受本公约之拘束.
设若上述非缔约国接受并援用本公约之规定时,则缔约各国对该国之关系,亦应受本公约之拘束".
93.
以色列当局于1967年占领西岸后曾发布第3号命令,其第35条规定:"军事法庭……在司法程序方面必须适用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的规定.
如本命令与上述《公约》发生冲突,则应以《公约》为准.
"此后,以色列当局多次表示,事实上它们一般在被占领领土内适用《日内瓦第四公约》的人道主义规定.
但是,根据上文第90段概述的以色列立场,这项《公约》在法律上却不适用于被占领领土,因为根据第2条第2款,《公约》仅适用于参与武装冲突的缔约国主权范围内的领土被占领的情形.
以色列解释说,无可否认,约旦在1967年是《日内瓦第四公约》缔约国,当时以色列同约旦之间爆发了武装冲突,但它接着指出,以色列在冲突后占领的领土以前不在约旦的主权范围内.
因此它从中推论认为,《公约》在法律上不适用于被占领领土.
但是,咨询程序的绝大多数其他参与方认为,根据《日内瓦第四公约》第2条第1款,该《公约》适用于被占领领土,不管约旦在1967年之前是否对其拥有任何权利.
94.
本法院回顾,根据1969年5月23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所表述的习惯国际法,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的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
第32条规定:"为证实由适用第三十一条所得之意义起见,或遇依第三十一条作解释而……意义仍属不明或难解……或……所获结果显属荒谬或不合理时,为确定其意义起见,得使用解释之补充资料,包括条约之准备工作及缔约之情况在内.
"(见"石油平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诉美利坚合众国),初步反对意见",《1996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㈡,第812页,第23段;同样见"卡西基里/塞杜杜岛(博茨瓦纳/纳米比亚)",《1999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㈡,第1059页,第18段;以及"利吉丹岛和西巴丹岛的主权归属(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判决书",《2002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645页,第37段.
)95.
本法院注意到,根据《日内瓦第四公约》第2条第1款,《公约》在下列两项条件得到满足时就可以适用:存在武装冲突(不管是否承认有战争状态);以及冲突是在两个缔约方之间发生的.
如果满足了这两项条件,《公约》就适用,特别是在冲突期间由一个缔约方占领的任何领土内.
第2条第2款的目的并非是要排除不在一个缔约方主权范围内的领土,从而限制第1款所界定的《公约》适用范围.
其用意仅仅是要表明,即使在冲突期间实施的占领没有遇到武装抵抗,《公约》仍然适用.
这种解释反映了《日内瓦第四公约》起草人保护无论以何种方式落入占领国之手的平民的用意.
1907年《海牙章程》起草人既关注保护领土被占国的权利,也关注保护领土内的居民,而《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起草人则如《公约》第47条所表明的那样,力图确保平民在战时得到保护,而不管被占领领土的地位如何.
这种解释为《公约》的准备工作材料所证实.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下称红十字委员会)为了拟定新的日内瓦公约而召集的政府专家会议建议,公约应适用于任何武装冲突,"不管当事方是否承认其为战争状态",并适用于"在没有出现战争状态时对领土的占领情形"(《研究保护战争受害者公约的政府专家会议工作报告,1947年4月14日至26日,日内瓦》,第8页).
因此,第2条第2款的起草人在将该款写进《公约》时,其用意并非是要限制后者的适用范围.
他们仅仅是考虑到在没有发生战斗情况下的占领情形,如1939年德国对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占领.
96.
本法院还指出,《日内瓦第四公约》缔约国在1999年7月15日举行的会议上赞成这项解释.
他们发表一份声明,其中"重申《日内瓦第四公约》适用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
后来,在2001年12月5日,缔约国在特别提到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第1条的规定时,再次重申"《日内瓦第四公约》适用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
它们还提醒出席会议的缔约国、冲突各方和占领国以色列它们各自的义务.
97.
此外,本法院指出,当事方必须按照公约第142条的规定,"在任何时候均应承认和尊重"红十字委员会在涉及执行《日内瓦第四公约》方面的特殊地位.
本法院也就对公约的解释发表意见.
在2001年12月5日的一项声明中,它忆及"红十字委员会始终申明,《日内瓦第四公约》在法律上适用于以色列国自1967年以来占领的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
98.
本法院指出,大会在其许多决议中也采取相同的立场.
因此,在2001年12月10日和2003年12月9日的第56/60和第58/97号决议中,它重申"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适用于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及自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的其他阿拉伯领土".
99.
安全理事会本身在1967年6月14日第237(1967)号决议中已表明,"冲突当事国均应遵守……《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所定一切义务".
后来,1969年9月15日,安理会在第271(1969)号决议中促请,"以色列严格遵守关于军事占领之日内瓦公约及国际法之各项规定".
十年后,安全理事会审查了"以色列在1967年以来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内建立定居点的政策和做法".
在1979年3月22日第446(1979)号决议中,安全理事会认为这些定居点"都没有法律效力",并再次申明"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适用于1967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在内".
它"再次要求占领国以色列严格遵守"该公约.
1990年12月20日,安全理事会第681(1990)号决议促请"以色列政府接受……《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在法律上适用于自1967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所有领土,并严格遵守该公约的各项规定".
它还要求"上述公约的缔约国根据公约第1条的规定,确保占领国以色列尊重其按照该公约承担的各项义务".
最后,安全理事会1992年12月18日第799(1992)和1994年3月18日第904(1994)号决议重申其关于《日内瓦第四公约》适用于被占领土的立场.
100.
本法院最后指出,以色列最高法院在2004年5月30日的一项判决中也认为:"[以色列国防军]在拉法的军事行动一旦涉及平民,应适用《1907年关于陆战法规与习惯之海牙第四公约》和《1949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
"101.
有鉴于此,本法院认为,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方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时,《日内瓦第四公约》适用于任何被占领的领土.
1967年武装冲突爆发时,以色列和约旦均是该公约的缔约国.
本法院据此认为,该公约适用于在冲突之前位于绿线以东、在冲突期间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因为无需对这些领土原先的确切地位加以任何调查.
*102.
本法院正在审理的诉讼程序的参与方也对以色列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是否适用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持有不同意见.
秘书长报告一指出:"4.
以色列否认它已签署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适用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
它说,人道主义法是在诸如西岸和加沙地带这样的冲突局势中提供保护的法律,而人权条约是为了保护公民在和平时期不受本国政府的侵权行为之害.
"在该诉讼程序的其他参与方中,那些谈到该问题的参与方持相反的看法,认为这两项盟约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中适用.
103.
1991年10月3日,以色列批准了1966年12月19日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以及1989年11月20日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它是这三项文书的缔约国.
104.
为了确定这些案文是否适用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本法院将首先讨论国际人道主义法律与人权法律之间的关系问题,然后讨论人权文书是否在国家领土之外适用的问题.
105.
在1996年7月8日《关于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咨询意见》中,本法院有机会讨论与《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有关的这些问题中的第一项问题.
在那些诉讼程序中,一些国家认为,该盟约旨在保护和平时期的人权,而有关在敌对行动中非法丧生的问题是由适用于武装冲突的法律管辖"(《1996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一卷,第239页,第24段).
本法院不接受这种论据,指出:"《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提供的保护在战争时期并没有停止,除非因为该盟约第4条规定生效,根据这项规定,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某些规定可以减损.
然而,尊重生命权不属于这种规定.
原则上来说,不能任意剥夺生命的权利在敌对状态时也适用.
不过,如何界定任意剥夺生命的问题则应当由可适用的特别法加以确定,即在武装冲突中可以适用的、旨在管制敌对行动的法律.
"(同上,第240页,第25段).
106.
从较为广义的意义上来说,本法院认为,人权公约提供的保护在武装冲突中并没有停止,除非因为《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4条所述的那种减损规定造成的结果.
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律与人权法律之间的关系,因此,存在三种可能情况:某些权利可能专属于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事项:其他权利可能专属于人权法律事项:另外一些法律可能专属于国际法这两种分支的事项.
为了回答所提出的问题,本法院必须考虑到国际法的这两种分支,即人权法律和作为特别法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
107.
这两项国际盟约和《儿童权利公约》是否只适用于缔约国境内的领土,还是也可在这些领土之外适用,如果可以适用,在什么情况下适用的问题,仍有待于确定.
108.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适用的范围在该盟约第2条第1款中得到界定,该款规定:"本盟约每一缔约国承担尊重和保证涉及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享有本盟约所承认的权利,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
"这项规定可以解释为,只包括在某国境内及其属于该国管辖的个人.
它也可理解为包括那些在某国境内以及那些在该国境外但受该国管辖的个人.
因此,本法院将努力确定该案文的含义.
109.
本法院指出,尽管各国管辖权主要在该国境内,但有时也可在国家领土之外行使.
考虑到《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的目标和宗旨,似乎理所当然的是,即使情况是如此,该盟约缔约国也应有义务履行其条款.
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惯例也符合这种做法.
因此,委员会已认为,该盟约可在国家能够在外国境内行使管辖权的地方使用.
它已对乌拉圭特工人员在巴西或阿根廷开展逮捕案件(第52/79号案件LopezBurgos诉乌拉圭;第56/79号案件,LilianCelibertideCasariego诉乌拉圭)中乌拉圭采取行动的合法性作出裁决.
在乌拉圭驻德国领事馆没收护照的案件中(第106/81号案件,Montero诉乌拉圭)也作出类似的裁决.
该盟约准备资料确认委员会对该文书第2条规定的理解.
这些资料表明,在采用所选择的措辞时,该盟约起草者并不打算允许国家在其境外行使管辖权时逃避它们的义务.
他们只打算防止居住在境外的个人不会对他们的原籍国提出不属于该国而属于居住国管辖范围的权利(见人权委员会对初步案文的讨论,E/CN.
4/SR.
194,第46段;联合国大会第十届会议正式记录,,A/2929,第二部分第五章第4段(1955)).
110.
在这方面,本法院注意到以色列在给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来文中就《盟约》的可适用性问题采取的立场,并注意到委员会的意见.
以色列于1998年表示,在编写给委员会的报告时,它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就适用《盟约》而言,"被占领土内的居民是否实际上处于以色列的管辖权之下(CCPR/C/SR.
1675,第21段).
以色列采取的立场是,"《盟约》和类似文书不直接适用于被占领领土内的当前局势"(同上,第27段).
委员会在审查报告后的结论性意见中,对以色列的态度表示忧虑,并指出"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内长期存在、以色列对被占领领土未来地位持模糊态度以及以色列安全部队在领土内行使有效管辖权等情况"(CCPR/C/79/Add.
93,第10段).
2003年,针对以色列的一贯立场,即"《盟约》不适用于以色列本国领土之外,特别是西岸和加沙……",委员会得出以下结论:"在当前情况下,为了保护被占领领土内的居民,对于缔约国在这些领土上的当局或人员的所有行为,凡影响到享受《盟约》规定的权利和属于国际公法原则规定的以色列的国家责任范围之内的,适用《盟约》的规定"(CCPR/CO/78/ISR,第11段).
111.
本法院的结论认为,《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适用于一国在其领土外行使管辖权所实施的行为.
112.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没有关于其适用范围的规定.
这可能是因为该盟约所保障的权利主要是领土内的权利.
但不应排除的是,《盟约》既适用于缔约国对其拥有主权的领土,也适用于该国对其行使属地管辖权的领土.
因此,第十四条针对"在参加本盟约时尚未能在其宗主领土或其他在其管辖下的领土实施免费的、义务性的初等教育"的任何缔约国,规定了临时措施.
在这方面,宜回顾以色列在其提交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各次报告中所采取的立场.
以色列在1998年12月4日提交委员会的初次报告中提供的"统计数字表明在被占领领土内的以色列定居者享有《盟约》规定的权利".
委员会注意到,据以色列称,"同一管辖地区内的巴勒斯坦居民则没有被列入报告和被排除在《盟约》的保护之外"(E/C.
12/1/Add.
27,第8段).
委员会在这方面表示了关切.
对此,以色列在2001年10月19日提交的下一次报告中答复说,以色列"始终认为《盟约》不适用于不属于其领土主权和司法管辖的地区"(该提法受《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文字的启发).
以色列接着指出,这个立场"是以国际法在人权法与人道主义法之间牢固确立的区别为依据的".
以色列补充说:"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事件完全属于武装冲突情况下发生的事件,与人权不相关,因此委员会的使命与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事件无关"(E/1990/6/Add.
32,第5段).
鉴于这些意见,委员会再次表示关注以色列的立场,并重申"它认为《盟约》规定的缔约国义务适用于受其有效控制之下的所有领土和人口"(E/C.
12/1/Add.
90,第15段和31段).
由于上文第106段说明的原因,本法院不能接受以色列的意见.
本法院还须指出,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处于占领国以色列的属地管辖权之下,时间已超过37年.
以色列在行使在此基础上拥有的权力时,须受《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规定的约束.
此外,以色列有义务不设置任何障碍,不妨碍在已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移交权限的领域内行使这些权利.
113.
关于1989年11月20日《儿童权利公约》,根据该文书所载第2条的规定,"缔约国应尊重本公约所载列的权利,并确保其管辖范围内的每一儿童均享受此种权利……".
因此,《公约》适用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
**114.
在确定了相关的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据以回答大会所提问题、特别是就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内的可适用性作出裁定后,本法院现在将试图确定筑墙行为是否违反这些规则和原则.
*115.
在这方面,秘书长报告中题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法律立场摘要概述"的二指出,"建造隔离墙是企图违反国际法吞并该领土的行为","事实上的土地吞并干涉领土主权,因而侵犯了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利.
"提交本法院的一些书面陈述和庭审时表示的意见重申了这种意见,其中除其他外指出,"隔离墙隔断了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对之行使自决权的领土范围,构成对禁止用武力取得领土的法律原则的违反.
"在这方面特别强调指出的是,"所策划的隔离墙路线是为了通过加强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非法建立的以色列定居点,改变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人口组成".
此外还进一步指出,隔离墙是为了"减小和瓜分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对之行使自决权的领土范围".
116.
以色列方面则辩称,隔离墙的唯一目的是使其能够有效打击从西岸发动的恐怖攻击.
此外,以色列多次指出,隔离墙是一种临时措施(见秘书长报告,第29段),其中一次是由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安全理事会2003年10月14日会议上强调"[围栏]没有把领土兼并到以色列国",并且"如果是出于配合政治解决冲突的需要,以色列愿意而且能够在付出巨大代价的情况下调整或拆毁围栏"(S/PV.
4841,第9页).
2003年10月20日和12月8日,以色列常驻代表在大会上重申了这一观点.
在12月8日的会议上,他补充说:"一旦恐怖结束,就不再需要围栏.
围栏不是边界,没有政治意义.
它不以任何方式改变领土的法律地位.
"(A/ES-10/PV.
23,第5页)117.
本法院忆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均提到"不容许通过战争取得领土"这一习惯规则(见上文第74段和87段).
因此,安全理事会1967年11月22日第242(1967)号决议,在回顾该规则后,申明如下:"为履行宪章原则,必须于中东建立公正及持久和平,其中应包括实施下列两项原则:㈠以色列军队撤离其于最近冲突所占领之领土;㈡终止一切交战地位之主张或状态,尊重并承认该地区每一国家之主权、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与其在安全及公认之疆界内和平生存、不受威胁及武力行为之权利".
安理会正是本着同样的依据,数次谴责以色列为改变耶路撒冷地位而采取的措施(见上文第75段).
118.
关于人民的自决权原则,本法院指出,"巴勒斯坦人民"的存在不再是争论中的问题.
此外,在1993年9月9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与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先生的换函中,以色列已承认这种存在.
在那次通信中,巴解组织主席承认"以色列国和平、安全地存在的权利",并作出各种其他承诺.
以色列总理在复信中告知对方,鉴于这些承诺,"以色列政府决定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
《1995年9月28日以色列-巴勒斯坦关于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临时协定》也多处提到巴勒斯坦人民及其"合法权利"(序言部分第4、7、8段;第二条,第2款;第三条,第1和第3款;第二十二条,第2款).
本法院认为,这些权利包括自决权.
再者,大会也多次确认这一权利(例如,见2003年12月22日第58/163号决议).
119.
本法院注意到,按照以色列政府确定的隔离墙的路线,大约80%的生活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内的定居者被划入"封闭区"(见上文第85段).
此外,查看上文第80段所述的地图后可清楚看出,隔离墙蜿蜒路线的划定是为了将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内的绝大多数以色列定居点划进该区域.
120.
关于这些定居点,本法院注意到,《日内瓦第四公约》第四十九条第6款规定:"占领国不得将其本国平民的一部分驱逐或移送到所占领的领土.
"该条款不仅禁止诸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施的驱逐或强迫迁移居民的行为,而且禁止占领国为组织或鼓励其本国居民的一部分迁往被占领土所采取的任何措施.
在这方面,提供给本法院的资料显示,自1977年以来,以色列违反上述第四十九条第6款的规定,实行了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内建立定居点的政策并制订了种种做法.
因此,安全理事会认为,这种政策和做法"没有法律效力".
安理会还要求"占领国以色列严格遵守"《日内瓦第四公约》,并:"废除以前的措施和停止采取可能改变1967年以来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法律地位和地理性质及对其人口组成有实质影响的任何行动,尤其是不要将以色列的一部分平民迁入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1979年3月22日第446(1979)号决议).
安理会在1979年7月20日第452(1979)号和1980年3月1日第465(1980)号决议中重申了它的立场.
实际上,安理会的后一项决议将"以色列将其部分人口和新来移民移居到[被占领]领土的政策和措施"指为对《日内瓦第四公约》的"悍然违反".
本法院的结论是,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建立以色列定居点的行为违反国际法.
121.
虽然本法院注意到以色列保证建造隔离墙并不等于吞并,隔离墙是临时性的(见上文第116段),但是人们担心隔离墙的路线会预先确定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将来的边界,担心以色列可能把定居点和进出路径联成一体,本法院对这些担心不能无动于衷.
本法院认为,建造隔离墙及其附属设施造成一种完全可能成为永久性的"既成事实",在此情况下,尽管以色列对隔离墙的正式定性,但它相当于事实上的吞并.
122.
还有,本法院回顾,根据秘书长的报告,计划的隔离墙路线将把西岸16%以上的领土包括在绿线和隔离墙之间的地区内.
而生活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约80%的定居者,即320000人,加上237000名巴勒斯坦人居住在这个地区.
此外,由于建造隔离墙,另外约160000名巴勒斯坦人将居住在几乎完全封闭的社区中(见上文第84段、第85段和第119段).
换句话说,为隔离墙选择的路线实际上表明了遭到安全理事会谴责的以色列对耶路撒冷和定居点采取的非法措施(见上文第75段和第120段).
建造隔离墙还可能进一步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内的人口组成,因为这会促使巴勒斯坦人离开某些地区,下文第133段将进一步加以说明.
建造隔离墙加上以前采取的措施严重妨碍了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决权,因此,以色列违反了尊重这项权利的义务.
*123.
建造隔离墙还产生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文书有关条款方面的许多问题.
124.
关于《1907年海牙章程》,本法院回顾,第二编涉及敌对行为,特别是涉及"伤害敌人的手段、包围和轰击".
第三编涉及被占领领土内的军事当局.
现在只有第三编适用于西岸,而《海牙章程》第二编第二十三条第㈦款与此不相关.
《海牙章程》第三编中有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六条和第五十二条适用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
第四十三条规定占领者有义务"尽力采取一切措施,在可能范围内恢复和确保公共秩序和安全并且……应尊重该国现行的法律".
第四十六条补充说,私有财产必须受到"尊重"并且"不得没收".
最后,第五十二条认可占领军为满足需要可在一定限度内征用实物和劳务.
125.
《日内瓦第四公约》也区分了占领军事行动中适用的条款和整个占领期间适用的条款.
它在第六条中规定:"本公约应于第二条所述之任何冲突或占领开始时适用.
在冲突各方的领土内,本公约之适用,于军事行动全面结束时应即停止.
本公约在占领地内之适用,于军事行动全面结束后一年应即停止;惟占领国于占领期间在该国于占领地内行使政府职权之限度内,应受本公约下列各条规定之拘束:第一至十二、二十七、二十九至三十四、四十七、四十九、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九、六十一至七十七、一百四十三条.
被保护人之释放、遣返、或安置,若在上述各期限以后实现者,则在其实现之期间,彼等仍应继续享受本公约之利益.
"由于导致1967年占领西岸的军事行动早已结束,只有《日内瓦第四公约》第六条第三款提到的那些条款仍适用于被占领领土.
126.
这些条款包括《日内瓦第四公约》第四十七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和第五十九条.
根据第四十七条:"本公约所赋予在占领地内之被保护人之各项利益,均不得因占领领土之结果引起该地制度或政府之变更,或因被占领地当局与占领国所订立之协定,或因占领国兼并占领地之全部或一部,而在任何情况下或依任何方式加以剥夺".
第四十九条规定如下:"凡自占领地将被保护人个别或集体强制移送及驱逐往占领国之领土或任何其他被占领或未被占领之国家之领土,不论其动机如何,均所禁止.
但如因居民安全或迫切的军事理由,有此必要,占领国得在一定区域施行全部或部分之撤退.
上述撤退不得致使被保护人在占领地境外流离失所,但因物质原因不能避免上述流离失所则为例外.
依此被撤退之人,一旦该区域内战事停止,应立即移送回家.
凡实行此种移送或撤退之占领国,应尽最大可行的限度,保证供给适当设备以收容被保护人,该项移动应在卫生、保健、安全及营养之满足的条件下执行,并应保证同一家庭之人不相分离.
一经实行移送或撤退,应立即以其事实通知保护国.
除非因居民安全或迫切的军事理由有此必要,占领国不得将被保护人拘留于特别冒战争危险之区域.
占领国不得将其本国平民之一部分驱逐或移送至其所占领之领土.
"根据第五十二条规定:"任何契约、协定或规则均不得减损任何工人向保护国代表申请请求该国干涉之权利,不论该工人是否系属志愿,亦不论其所在地点.
在占领地内,一切以造成失业或限制工人工作机会借以引诱工人为占领国工作为目的之措施,均所禁止.
"第五十三条规定:"占领国对个别或集体属于私人,或国家,或其他公共机关,或社会或合作组织所有之动产或不动产之任何破坏均所禁止,但为军事行动所绝对必要者则为例外.
"最后,根据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如占领地全部或部分居民之给养不足时,占领国应同意救济该项居民之计划,并对该项计划使用力所能及之一切方法予以便利.
该项计划,可以由国家或公正人道主义组织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承担之,在该计划中尤应包括食物、医疗品及衣服的转运物资之供给.
各缔约国均应允许该项装运物资之自由通过并保证予以保护.
但缔约国之允许上项装运物资自由通过以运往冲突之敌方所占领之区域者,有权检查该项装运物资,规定其依指定时间与路线透过,并通过保护国,查明该项装运物资系为救济待救之居民之用而非为占领国之利益之用.
"127.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也有几项条款相关.
在深入审视这些条款之前,本法院要指出,《盟约》第四条允许缔约国在不同条件下克减该文书的一些规定.
以色列援用该条规定的克减权,于1991年10月3日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内容如下:"自从以色列国成立以来,它的生存及其公民的生命和财产一直受到持续的威胁和攻击.
这些威胁和攻击采用战争威胁、实际武装进攻和恐怖主义活动等方式,造成了人员的伤亡.
鉴于上述情况,1948年5月宣布的紧急状态一直延续至今.
这种情况构成《盟约》第四条第㈠款所指的公共紧急状态.
因此,以色列政府认为有必要根据上述第四条,完全按局势紧迫性所需的程度采取措施,包括行使逮捕和拘留权力,以保卫国家和保护生命与财产.
如果任何这些措施与《盟约》第九条的规定不一致,以色列则克减该条款规定的义务.
"本法院指出,所述克减仅涉及《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九条,而该条说明了个人自由和安全的权利并规定了适用于逮捕或拘留情况的规则.
因此,《盟约》其他条款仍然不仅适用于以色列领土,而且适用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
128.
其中必须提到第十七条第一款,该款规定如下:"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加以任意或非法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非法攻击.
"还必须提到第十二条第一款,该款规定如下:"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
"129.
除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对移动自由所给的一般性保障之外,还必须考虑到关于出入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神圣处所权利的具体保障.
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基督教神圣处所的地位源远流长,最新的有关条文规定纳入了1878年7月13日《柏林条约》第62条.
1922年7月24日给英国政府的巴勒斯坦委任统治书第13条这样规定:"与巴勒斯坦的神圣处所和宗教建筑及场址有关的所有责任,包括维护现有权利的责任和争取自由出入神圣处所及宗教建筑物或场址的权利和宗教崇拜自由、并同时保证公安和规范行为的必要条件的责任由委任统治国承担……"第13条还规定:"委任统治书中的任何条文不得视为授予……权力去干涉纯粹是穆斯林的圣迹的组织或管理,因为它们的豁免权是得到保障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会在通过关于将来的巴勒斯坦政府的第181㈡号决议时,在巴勒斯坦分治计划中用一整章来谈神圣处所及宗教建筑物或场址.
这一章的第2条规定,就神圣处所及宗教建筑物或场址而言:"与现有的权利一致,必须保障[这个阿拉伯国家、这个犹太国家]和耶路撒冷城不分国籍的所有居民和公民以及外国人自由进出、访问和过境,但须符合国家安全、公安和规范行为的需要".
在1948年发生武装冲突之后,约旦和以色列1949年签订的全面停战协定第八条规定成立特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就任何一方可能提交其处理的问题拟订双方同意的计划和安排",以期扩大《协定》的范围和改善其实施.
已经缔定了原则协议的此种问题包括"神圣处所及宗教建筑物或场址的自由出入权利".
这项承诺主要关乎在绿线以东的神圣处所及宗教建筑物或场址.
但是,有些神圣处所及宗教建筑物或场址是在绿线以西,例如"最后的晚餐房间"和在锡安山上的大卫墓.
以色列签署了全面停战协定,就是承诺——约旦也一样——保障人们自由出入这些神圣处所及宗教建筑物或场址的权利.
本法院认为以色列的这项承诺同样适用于在1967年被它控制的神圣处所及宗教建筑物或场址.
1994年以色列与约旦签订的和平条约第9条第1段以较为笼统的言辞进一步肯定了这项承诺:"每一方将让人们自由出入具有宗教和历史意义的地方场所".
130.
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它包含了几个有关条款,即:工作权利(第6和第7条);向家庭、儿童和少年提供保护和援助(第10条);适当生活水平权,包括获得足够食物、衣服和住房的权利以及"免受饥饿权"(第11条);健康权(第12条);受教育的权利(第13和第14条).
131.
最后一点,1989年11月20日《儿童权利公约》第16、24、27和28条也有类似的条款.
*132.
根据提交给本法院的信息特别是秘书长的报告,看来建造这堵墙导致了财产设施的破坏和征用,而这种情况违反了1907年海牙章程第46和第52条以及日内瓦第四公约第53条的规定.
133.
在绿线与这墙之间建一个封闭区以及建立飞地对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居民(除了以色列公民和已被同化者)的移动自由施加了很大的限制.
此种限制在城区例如卡勒基利亚飞地或耶路撒冷市及其郊区最为明显.
而其中某些地方出入的门闸少,开放的时间看来有限制而且无定时,使情况更糟糕.
例如,根据人权委员会关于自1967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的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报告,"人口4万的卡勒基利亚城完全被这堵墙围住了,居民只能在早上7时到晚上7时开放的唯一一个军事检查站通过".
(人权委员会1967年以来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约翰·杜加德依照委员会第1993/2A号决议的规定提出了题为"在包括巴勒斯坦的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人权被侵犯问题"的报告(2003年9月8日,E/CN.
4/2004/6,第9段).
农业生产方面也受到了严重影响——这是许多来源所证实的.
据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指出"被以色列占领部队没收的大约100000德南(约10000公顷)最肥沃的农地在这堵墙第一阶段的建造过程中被毁了,大量的财产消失了,特别是千万巴勒斯坦人赖以生存的私有农地、橄榄树、水井、柑橘园和温室等"(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的报告,2003年8月22日,A/58/311,第26段).
还有,1967年以来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指出,"落在墙的以色列那一边的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是该区域最肥沃的农地及最重要的一些水井"(2003年9月8日,E/CN.
4/2004/6,第9段).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粮食权利特别报告员指出,建这堵墙"把巴勒斯坦人隔离在他们的农地和水井之外,切断了他们的生计"(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让·齐格勒的报告"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特派团"增篇"食物权"(2003年10月31日,E/CN.
4/2004/10/Add.
2,第49段).
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其最新的报告中指出,这种情况已使该区域的粮食安全恶化,需要粮食援助的人据报已增加了25000人(秘书长的报告,第25段).
这已进一步导致受影响的人口越来越难于获得医疗服务、上学和利用主要的水源.
这一点已获得若干不同的消息来源所证实.
因此,秘书长的报告这样概括地指出:"据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指出,迄今这堵墙已隔离了30个地方的医疗服务、隔离了22个地方的学校、隔离了8个地方的主要水源、隔离了3个地方的电力网.
"(秘书长的报告,第23段).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1967年以来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说,"在墙与绿线之间的巴勒斯坦人实际上已同土地、工作地点、学校诊所和其他社会服务隔离开.
"(2003年9月8日,E/CN.
4/2004/6,第9段).
特别是在水资源问题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指出:"以色列通过建造这堵墙还将有效地并吞西边含水层的大部分(这个西岸的水资源51%来自这个含水层)(2003年10月31日,E/CN.
4/2004/10/Add.
2,第51段).
同样,在医疗服务方面,据指出,自卡勒基利亚镇被围起来之后,该镇的一家联合国医院的工作量减少了40%(秘书长的报告,第24段).
根据提供给联合国的报告显示,卡勒基利亚有大约600家店和企业倒闭,6000至8000人离开了该区域(2003年9月8日,E/CN.
4/2004/6,第10段;2003年10月31日,E/CN.
4/2004/10/Add.
2,第51段).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还指出,"在这个围栏/围墙把社区隔离它们的土地和水资源的情况下,在没有其他生计的情况下,许多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将被迫离开.
"(2003年10月31日,E/CN.
4/2004/10/Add.
2,第51段)还有,建造这堵墙将剥夺数量相当多的巴勒斯坦人"选择居住地的自由".
不过,还有一点,在本法院认为,由于数量相当多的巴勒斯坦人已因这堵墙及其相关的制度而被迫离开某些地区——随着这堵墙继续扩建,加上上文第120段提到的以色列新建的移民点,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人口构成将会改变.
134.
总而言之,本法院的意见认为建造这堵墙以及其相关的制度阻碍了被占领领土居民(除了以色列公民和已同化者)的移动自由——这是《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12条第1款所保障的,也阻碍了受影响的人行使工作、获得医疗服务、接受教育和拥有适当生活水平权的权利——这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郑重宣布的.
最后一点,由于建造这堵墙以及其相关的制度促成了上文第122和第133段所提到的人口组成的变化,这已违反了日内瓦第四公约第49条第6款以及上文第120段提到的安全理事会决议.
135.
不过,本法院愿意指出,适用的国际人道主义法有条款容许在某种情况下考虑到军事紧急状况.
1907年海牙章程第46条和日内瓦第四公约第47条都没有容许任何这类特殊条件.
至于日内瓦第四公约第49条第1款禁止的强制转移人口和递解出境,该条第2款则规定在"人民的安全或绝对的军事理由需要"的情况下允许例外.
不过,这项例外不适用于该条第6款——它禁止占领国把自己的部分平民人口流放或转移到其占领的土地.
至于有关破坏个人财产的第53条,该条规定在"军事行动必须作出此种破坏的情况下"允许例外.
本法院认为这些条文所考虑的那些军事紧急状况,即使在占领所用的军事行动总体上已结束的情况下仍可援引.
不过,本法院面前的材料不能使它信服,即以色列违反日内瓦第四公约第53条进行的破坏是其军事行动所绝对必要的.
136.
本法院进一步指出,一些人权公约,特别是《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载有缔约国在各种情况下可援引用以克减其所承担的某些公约义务的规定.
但是,在这一方面,本法院回顾,以色列根据《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四条给联合国秘书长的通知函仅涉及该盟约有关人身自由和安全的第九条(见上文第127段);所以,以色列必须遵守该文书的所有其他规定.
此外,本法院注意到,人权公约的某些规定含有限制这些规定给予的权利的条款.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十七条没有此类条款.
另一方面,该文书的条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对该条保障的迁徙自由"除法律所规定并为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需且与本盟约所承认的其他权利不抵触的限制外,应不受任何其他限制.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第四条载有下列一条通则:"本盟约缔约各国承认,在对各国依据本盟约而规定的这些权利的享有方面,国家对此等权利只能加以同这些权利的性质不相违背而且只是为了促进民主社会中的总的福利的目的的法律所确定的限制.
"本法院认为,《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限制,从该款本身的规定来看,是对第一款所载迁徙自由的例外.
此外,此类限制仅服务于许可目的是不够的;它们还必须是达到这些目的所需要的.
如人权委员会所说的那样,它们"必须符合相称原则"以及"必须是可能实现期望结果的同类手段中干涉程度最低的手段"(CCPR/C/21/REV.
1/Add.
9,第27号一般性意见第14段).
根据已掌握的资料,本法院裁定本案没有满足这些条件.
本法院进一步指出,因以色列修筑隔离墙而对生活在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享有其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造成的限制没有满足《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第四条规定的条件,也就是说实行这些限制必须"只是为了促进民主社会中的总的福利的目的".
137.
总之,根据已掌握的资料,本法院并不相信以色列为隔离墙所选择的特定路线是实现其安全目标所需要的.
沿所选择路线修建的隔离墙及其相关制度严重侵害了生活在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上的巴勒斯坦的几项权利,以军事紧急状态或以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需要来对这一路线造成的侵权行为进行辩解是站不住脚的.
因此,修建这一隔离墙是构成以色列对其在适用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文书下所承担的多项义务的违反.
138.
因此,本法院断定,修建隔离墙是一项不符合以色列应遵守的多项国际法律义务的行为.
但是,秘书长报告的一说,以色列认为:"建造隔离墙符合《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其固有的自卫权利以及安全理事会第1368(2001)和1373(2001)号决议".
更具体地说,2003年10月20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大称,"隔离墙是一项完全符合载于《宪章》第五十一条中的各国自卫权的措施";他继续说,所提及的安全理事会决议,"明确承认各国有权在对恐怖主义袭击进行自卫时使用武力",因此当然也承认了为此目的采用非武力措施的权利(A/ES-10/PV.
21,第5页).
139.
《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
"所以,《宪章》第五十一条承认在一国对另一国进行武力攻击的情况下存在自卫之自然权利.
但是,以色列并未称对它的攻击可归责于一个外国.
本法院还注意到,以色列对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行使控制,正如以色列自己所说,它认为成为修建隔离墙的原因的威胁来自领土内部而不是领土外部.
这一情况与安全理事会第1368(2001)号和1373(2001)号决议所考虑的情况不同,因此,以色列无论如何不能援引这些决议来支持它正在行使自卫权利的主张.
所以,本法院断定,《宪章》第五十一条在本案中不具相关性.
140.
但是,本法院审议了以色列是否可以危急情况为由排除修建隔离墙行为的不法性.
在这一方面,本法院必须注意到,本案所涉及的一些公约含有对保障权利的限制条款或克减规定(见上文第135和136段).
由于这些条约本身的条款中已对此类考虑作出了规定,可以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就这些条约而言,是否可援引习惯国际法所承认的危急情况,作为排除正受到挑战的措施或决定的不法性的理由.
然而,本法院不需审议这一问题.
正如本法院在有关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案(匈牙利/斯洛伐克)中指出的那样:"危急情况是习惯国际法承认的一项理由","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得到接受";危急情况"只有在某些严格规定的条件下才可以援引,必须以积累的方式满足这些条件;至于这些条件已否得到满足,不能只由所涉国家作出判断"(《1997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p.
40,第51段).
本法院以国际法委员会使用的说法阐明了其中的一项条件,该说法目前的案文要求受到挑战的行为"是该国保护基本利益,对抗某项严重迫切危险的唯一办法"(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的第二十五条;又见关于国家国际责任的条款草案的前第三十三条,英文文本措辞略有不同).
鉴于所掌握的资料,本法院不相信,沿所选择的路线修建隔离墙是以色列保护其利益,对抗严重迫切危险的唯一办法,而以色列却援引此点为修建该隔离墙辩解.
141.
实际情况依然是,以色列必须面对针对其平民的许多不分清红皂白的致命暴力活动.
它有权,也的确有责任作出反应,以保护其公民的生命.
但是,所采取的措施仍然必须符合适用的国际法.
142.
总之,本法院认为,鉴于上文第122和第137段的考虑,以色列不能以自卫权或危急情况为由排除修建隔离墙的不法性.
因此,本法院裁定,隔离墙的修建及其相关制度违反国际法.
***143.
本法院已断定,以色列因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包括在东耶路撒冷城及其周围的修建隔离墙及实施相关制度,违反了它所承担的多项国际义务(见上文第114至137段),本法院现在必须审查这些违法行为的后果,以便答复大会提出的问题.
**144.
本法院诉讼程序的许多参与者在其书面和口头意见中坚决主张,以色列非法修建隔离墙不仅对以色列本身,而且对其他国家和对联合国都具有法律后果;以色列方面,在其书面陈述中未就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提出任何论证.
145.
关于对以色列的法律后果,有人坚决主张,以色列,首先,有法律义务立刻停止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修建隔离墙,从而终止这种非法状况,并作出不再重犯的适当保证和保障.
有人认为,第二,以色列有法律义务对非法行为引起的损失进行赔偿.
认为此类赔偿首先应采取恢复原状的形式,即拆除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已建的那部分隔离墙,废除与修建隔离墙有关的法案,归还为此目的征用或没收的财产;赔偿还应包括对那些住家或农业用地被毁坏的人进行适当补偿.
有人还进一步坚决主张,以色列继续有责任遵守它因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以及相关的制度而违反的所有国际法义务.
也有人认为,根据《日内瓦第四公约》,以色列有义务搜寻和向法院起诉被指控实施或下令实施规划、修建和使用隔离墙等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人员.
146.
至于对以色列之外其他国家的法律后果,有人向法院主张,所有国家都有义务不承认因隔离墙的修建而导致的非法状况,不提供任何帮助或援助来维护这种状况,并有义务进行合作,以结束这种受到指控的违法行为并确保为此进行赔偿.
诉讼程序的某些参与者还主张,《日内瓦第四公约》缔约国有义务采取措施确保该公约得到遵守,并主张,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修建并维持隔离墙的行为严重违反了该公约,因此公约缔约国有义务起诉或引渡这些违法活动的行为人.
他们进一步指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应审议以色列公然和蓄意违反国际法规范和原则的行为,尤其是……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制止此类违法行为",他们还指出,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必须对法院提出的咨询意见给予应有的重视.
**147.
由于法院已经得出结论认为,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包括在东耶路撒冷及其周围修建隔离墙的行为以及与其相关的制度违背了以色列的各项国际义务,因此,该国应负的责任是由国际法确定的.
148.
法院现将研究以色列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所造成的法律后果,区别对以色列的法律后果和对其他国家的法律后果,并酌情研究对联合国造成的法律后果.
法院将首先研究这些违法行为对以色列造成的法律后果.
*149.
法院指出,以色列首先应当履行它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修建隔离墙的行为所违背的各项国际义务(见上文第114至137段).
因此,以色列必须履行尊重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利的义务以及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规定其应承担的义务.
另外,以色列必须确保其自1967年战争以来控制的圣地的进出自由(见上文第129段).
150.
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的行为引发了以色列的一些国际义务,法院认为,以色列还有义务不再违背这些国际义务.
一个国家若对一项国际不法行为负有责任,则该国家有义务结束这一行为,这一点在一般国际法中早有明确规定,法院也多次确认这一义务(《1986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49页,在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案(尼加拉瓜诉美利坚合众国)判决书,实质问题;《1980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44页,第95段,美国驻德黑兰外交和领事人员案判决书;《1951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82页,阿亚·德拉托雷案判决书).
151.
因此,以色列有义务停止其正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包括在东耶路撒冷及其周围进行的隔离墙修建工程.
另外,法院了解到(见上文第143段),隔离墙的修建及与其有关的制度导致以色列对其国际义务的违反,因此要结束此类违反义务的行为,以色列就必须立即拆除隔离墙位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部分,包括在东耶路撒冷及其周围的部分.
为修建隔离墙及建立与其有关的制度而通过的所有法规,都必需立即撤销或宣告无效,除非在规定向巴勒斯坦人口进行补偿或其他形式的赔偿后,这些法规仍然与以色列遵守下文153段中所述的各项义务有关.
152.
另外,鉴于除了其他后果之外,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修建隔离墙的行为还导致住家、商业以及农业用地被征用或毁坏,法院进一步裁定,以色列有义务向所有遭受损失的有关自然人和法人进行赔偿.
法院回顾,常设国际法院曾就习惯法中赔偿的基本形式作出如下规定:"一项非法行为的实际概念中所包含的基本原则(似乎是由国际惯例,特别是由仲裁法院各项决定确立的原则)是,赔偿必须尽量消除非法行为的一切后果,并尽可能将有关情况恢复到假定这一行为没有发生的状态.
可归还实物,在不可能归还实物时,亦可赔款,赔款数额相当于实物补偿的数额;对实物归还或赔款未覆盖的损失,亦可以做出必要补偿——应依据这些原则来确定一项违背国际法的行为的补偿数额.
"(《1928年常设国际法院案例汇编》,A辑,第17号,第47页,第13号判决书,Chorzow工厂案,实质问题).
153.
因此,以色列有义务退还土地、果园、橄榄园,以及归还为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而从任何自然人或法人手中攫取的其他不动资产.
若无法归还实物,以色列有义务赔偿有关人员所遭受的损失.
法院认为,以色列还有义务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规则,对所有因隔离墙的修建而遭受任何形式的物质的自然人或法人进行补偿.
*154.
法院现将审议因以色列修建隔离墙而引发的国际不法行为对其他国家造成的法律后果.
155.
法院认为,以色列所违背的各项义务包括某些普遍义务.
正如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些义务从本质上说"涉及所有的国家",而且"鉴于所涉权利的重要性,可以说这些权利的保护在法律上同所有国家都有关"(《1970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32页,第33段,巴塞罗那电车、电灯及电力有限公司案,第二阶段,判决书).
以色列所违反的普遍义务是,尊重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义务以及以色列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应遵守的某些义务.
156.
至于这些义务中的第一条,法院已经指出(上文第88段),在东帝汶案中,法院认为,"从《宪章》及联合国惯例中演变而来的人民自决权具有普遍性质"的说法是无懈可击的"(《1995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02页,第29段).
法院还要回顾,根据上文已经提到的大会第2625(二十五)号决议的规定(见上文第88段):"每一国均有义务依照宪章规定,以共同及个别行动,促进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及自决权原则之实现,并协助联合国履行宪章所赋关于实施此项原则之责任…".
157.
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法院回顾,在其关于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中,法院表示,"在武装冲突中适用的许多人道主义法规则也是在对人的尊重以及'人道考虑因素'方面的根本规则……","这些规则是不容违背的国际习惯法原则,因此,无论是否批准了载有这些规则的各项公约,所有国家都应当遵守"这些规则((《1996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㈠,第257页,第79段).
法院认为,这些规则包含了一些实质上具有普遍性的义务.
158.
法院还要强调,《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一条是日内瓦四公约中共同的一条,此条规定,"各缔约国承诺在一切情况下尊重本公约并保证本公约之被尊重.
"法院根据该规定认为,该公约的每个缔约国,无论是否是某冲突的一方,都有义务确保有关文书中的各项规定得到遵守.
159.
鉴于所涉权利和义务的性质和重要性,法院认为,所有国家都有义务不承认因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包括在东耶路撒冷及其周围修建隔离墙而导致的非法状况.
各国还有义务不为维护这一修建行为所致局势而提供帮助或者援助.
所有各国在遵守《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的同时,应确保终止任何通过修建隔离墙而对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决权造成阻碍的行为.
另外,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第四公约》的缔约国都有义务在遵守《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的同时,确保以色列遵守该公约所包含的国际人道主义法.
160.
最后,本法院认为,联合国,尤其是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应该考虑须采取何种进一步行动,终止修建隔离墙及相关制度所造成的非法状况,对本咨询意见给予应有的考虑.
***161.
本法院,致力于维护《联合国宪章》阐明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及和平解决争端,强调急迫需要整个联合国加倍努力,迅速结束继续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从而在该地区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62.
本法院得出结论,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违反国际法,并陈述了此非法行为所导致的法律后果.
本法院认为自己有义务补充说明,必须将修建隔离墙置于更广的背景之下.
1947年,大会通过第181㈡号决议,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终止.
从那时以来,在这块先前的委任统治领土上,武装冲突、滥用暴力和镇压措施接连不断.
本法院强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有义务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则.
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一项首要目的就是保护平民的生命.
各方都有非法行动,都出过单方面决定,而本法院认为,只有本着诚意,执行安全理事会各项有关决议,特别是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才能结束这种可悲的局面.
安全理事会第1515(2003)号决议核准的"路线图"就是最近为启动谈判实现这个目的而作出的努力.
本法院认为有义务提请大会,即本咨询意见的接受者,注意必须鼓励这些努力,以根据国际法,尽快促成谈判解决各项未决问题,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同以色列及其他邻国毗邻共处,而该区域所有国家都有安全和保障.
***163.
出于这些理由,本法院,⑴一致,载定国际法院有管辖权给予所要求的咨询意见;⑵以十四票对一票,决定应允对咨询意见的请求;赞成:院长史久镛;副院长兰杰瓦;法官纪尧姆、科罗马、韦列谢京、希金斯、帕拉-阿朗古伦、科艾曼斯、雷塞克、哈苏奈、埃拉拉比、小和田、西马、通卡;反对:法官比尔根塔尔;⑶以下列方式答复大会提出的问题:A.
以十四票对一票,占领国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地区,正在修建的隔离墙及其相关制度违反国际法;赞成:院长史久镛;副院长兰杰瓦;法官纪尧姆、科罗马、韦列谢京、希金斯、帕拉-阿朗古伦、科艾曼斯、雷塞克、哈苏奈、埃拉拉比、小和田、西马、通卡;反对:法官比尔根塔尔;B.
以十四票对一票,以色列有义务终止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根据本咨询意见第151段,以色列有义务立即停止正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地区在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修建的隔离墙工程,立即拆除在上述地区已经修建的隔离墙,并立即撤消与其相关的所有立法和管制行为或使其无效;赞成:院长史久镛;副院长兰杰瓦;法官纪尧姆、科罗马、韦列谢京、希金斯、帕拉-阿朗古伦、科艾曼斯、雷塞克、哈苏奈、埃拉拉比、小和田、西马、通卡;反对:法官比尔根塔尔;C.
以十四票对一票,以色列有义务赔偿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地区在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造成的一切损失;赞成:院长史久镛;副院长兰杰瓦;法官纪尧姆、科罗马、韦列谢京、希金斯、帕拉-阿朗古伦、科艾曼斯、雷塞克、哈苏奈、埃拉拉比、小和田、西马、通卡;反对:法官比尔根塔尔;D.
以十三票对一票,所有国家均有义务不承认修建隔离墙造成的非法状况,不为维持修建隔离墙造成的状况提供帮助或援助;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第四公约》所有缔约国还有义务,在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前提下,确保以色列遵守该公约所体现的国际人道主义法;赞成:院长史久镛;副院长兰杰瓦;法官纪尧姆,科罗马,韦列谢京,希金斯,帕拉-阿朗古伦,雷塞克,哈苏奈、埃拉拉比、小和田、西马、通卡;反对:法官科艾曼斯,比尔根塔尔;E.
以十四票对一票,联合国,尤其是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应该考虑须采取何种进一步行动,终止修建隔离墙及相关制度所造成的非法状况,对本咨询意见给予应有的考虑.
赞成:院长史久镛;副院长兰杰瓦;法官纪尧姆、科罗马、韦列谢京、希金斯、帕拉-阿朗古伦、科艾曼斯、雷塞克、哈苏奈、埃拉拉比、小和田、西马、通卡;反对:法官比尔根塔尔.
本咨询意见于2004年7月9日在海牙和平宫以法文和英文拟就,以法文本为准,一式两份,其中一份在本法院存档,另一份转交联合国秘书长.
院长史久镛(签名)书记官长菲利普·库弗勒(签名)法官科罗马、希金斯、科艾曼斯和哈苏奈另有个别意见附于本法院咨询意见;法官比尔根塔尔有一声明附于本法院咨询意见;法官埃拉拉比和小和田另有个别意见附于本法院咨询意见.
史久镛(草签)库弗勒(草签)科罗马法官的个别意见建造隔离墙和吞并––––法院管辖权的有效性––––法院在咨询程序中的职能––––依据适用法律作出的裁定––––裁定的普遍适用性––––尊重人道主义法––––大会的作用.
1.
我同意本法院的裁定,即占领国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及附近地区在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建造隔离墙以及相关制度均属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但是,我认为还有必要强调以下各点.
2.
首先,占领国以色列通过建造隔离墙吞并了一部分被其占领的领土,违背了不得使用武力获取领土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本法院确认巴勒斯坦领土为被占领土,因此以色列无权在那里从事属于主权性质的活动,因为这将改变这些被占领土的性质.
占领的本质属于临时性,而且应当有利于占领国人民的利益以及占领国的军事需要.
因此,任何改变占领性质的行为,例如建造隔离墙,均属非法.
3.
对提交给本法院的问题,即占领国在被占领土上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在发生违反这些义务的情况下国际法能够提供的补救措施,会有各种不同的法律意见和看法,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认为,这个问题显然属于法律问题,属于本法院咨询管辖范围,因此,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九十六条——本法院与大会在法律问题上的职能合作)、《国际法院规约》(第六十五条——酌处权和第六十八条——参照诉讼程序)、《国际法院规则》(第一百零二条,第二款——参照诉讼程序)以及本法院已经解决的判例,关于本法院无权就这类问题作出裁决的反对意见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以司法适宜性为由提出的反对意见也无效,本法院从其权限和司法公平性的角度对司法适宜性问题给予了充分考虑.
在这方面,向法院提出的问题既不是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本身,也不是冲突的解决方案,而是在被占领土上建造隔离墙带来的法律后果.
换言之,现行法律是否允许某占领国单方面改变被占领土的性质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法律问题,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可从法律角度作出回答,而且不一定需要具备双边争端裁定的特点;上述问题是要求解释适用法律,法院正是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
因此,本法院在这个问题上行使咨询管辖权是适宜的.
由此可见,本法院咨询意见是以法院司法管辖权为坚实的司法基础.
4.
本法院在这类程序中的职能是,确认正在处理的问题的相应法律并且适用该法律.
为了作出裁定,本法院适用了与巴勒斯坦领土有关的国际占领法律的相关规定.
经适用这些规定,本法院认为这些领土属于被占领土,因此不得随意吞并;任何这类吞并都等于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和平背道而驰.
根据占领制度,占领国分割或者分治被占领土均属非法.
另外,根据当代国际法,每个国家都有义务不采取任何旨在局部或者全部破坏任何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行动.
5.
本法院还认为国际法确立并承认的自决权适用于该领土以及巴勒斯坦人民.
因此,行使这种权利使巴勒斯坦人民有权按照第181㈡号决议最初设想并经后来确认的办法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
本法院认为,在巴勒斯坦领土建造隔离墙将妨碍实现上述权利,因此,是侵犯上述权利的行为.
6.
关于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本法院公正地作出裁决,这两项规章制度均适用于被占领土;以色列作为占领国有义务尊重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
因此,本法院认为在被占领土建造隔离墙违反了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
为了制止这种违反行为,本法院理所当然地要求立即停止建造隔离墙,并且为建造隔离墙造成破坏支付赔偿费.
7.
以下裁定同样重要:整个国际社会对作为前委任统治地的巴勒斯坦人民负有义务,国际社会代表巴勒斯坦人民承担"神圣任务",不应承认建造隔离墙给该领土的地位带来的任何单方面变化.
8.
本法院的裁定以具有权威性的国际法规则为依据,具有普遍适用性.
本法院的回应是对提交给它的问题作出权威性答复.
鉴于这些规定对所有国家都有约束力,遵守这些规定关系到所有国家的利益,因此所有国家都应服从上述各项裁定.
9.
同样重要的是,呼吁冲突各方在不断发生的敌对行动中尊重人道主义法.
长期占领引发抵抗,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冲突各方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
10.
通过作出上述裁定,本法院发挥了作为国际合法性最高仲裁人和防止非法行为保障机构的作用.
现在就看联合国大会如何根据《宪章》履行其责任,以应有的尊重和严肃态度对待本咨询意见,目的不是为了互相指责,而是为了恰当地利用这些裁定,公正、和平地解决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
这场冲突不仅旷日持久,而且给直接卷入冲突各方造成了巨大的苦难,破坏了整个国际关系.
阿卜杜勒·科罗马(签名)希金斯法官的个别意见法院未处理的有关酌处权问题––––持平的咨询意见所缺乏的因素––––对《海牙章程》第四十六和第五十二条以及对《日内瓦第四公约》第四十九和第五十三条的违反––––不赞同关于自决、自卫和普遍义务原则的咨询意见中的某些段落––––所依赖的事实材料的局限性.
1.
我赞同本法院关于其对本案管辖权的咨询意见,并认为第14至42段对就这一点提出的各种相反论点作出了正确的回答.
2.
酌处权和适当性问题则要困难得多.
尽管我最后对发表咨询意见的决定投了赞成票,但我的确认为事情并不象本法院所说的那么明确.
显而易见的是(特别是从向本法院提出请求的措辞来看),寻求咨询意见者曾试图把关于隔离墙的咨询意见同本法院对纳米比亚一案发表的咨询意见(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276(1970)号决议继续留驻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对各国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1971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2页)相比.
基于以下几种理由,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
首先,1971年在请求对某些行为的法律后果发表意见之时,已对西南非洲问题发表一系列法院咨询意见,阐明了南非应承担的法律义务(西南非洲的国际地位,咨询意见,《1950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28页;与西南非洲领土的报告和请愿书有关的问题的表决程序,咨询意见,《1955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67页;西南非洲问题委员会可否举行请愿人听证会问题,咨询意见,《1956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23页).
此外,作为受委任统治国的一切法律义务由西南非洲承担.
作为纳米比亚人民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在1971年也没有承担任何法律义务,更谈不上未履行的义务.
3.
在本案中,事先对合法性作出宣示的是大会,而不是本法院.
而且,与纳米比亚1971年的情况相比,更大的棘手问题(隔离墙可以被视为其中的一个因素)不能被看作是这样一个问题:只有一个当事方业已被法院归类为法定违法者;唯有该当事方应采取行动,恢复具有合法性的局面;而且从法律义务的角度来看,另一"当事方"没有任何其他事情需要做.
从这件事的漫长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而且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第1515(2002)号决议也都证明了这一点.
4.
为了证明这个不当的类比——因为这一类比不仅在酌处权的法律问题方面有所帮助,而且还起到更广泛的作用——法律顾问告知本法院,"这个问题……是一个国家即以色列与联合国之间的问题.
"(例如,见CR2004/3,第62页,第31段).
当然,拿纳米比亚一案作比较,并且否认除以色列与联合国之间以外存在任何争端,还可以避免必须符合本法院所阐明的、本法院在两国之间发生争端时考虑应否发表咨询意见的标准.
但是,正如以下所说明的那样,这是无法避免的.
5.
此外,在纳米比亚一案的咨询意见中,大会就其必须对正在处理的事项所作决定的后果征求法律咨询.
大会此时是拥有结束一项国际联盟委任统治的权力的机关.
委任统治如期结束.
但是,大会决议在大多数情况下仅是建议而已.
安全理事会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根据《宪章》第七章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决议,却又不是对委任统治负责的机关.
这个难题是要求本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症结所在.
在这一点上,与本案也没有任何真正的可比性.
6.
这样,我们就处在不同的法律领域——在所熟知的领域中,争端发生在两个当事方之间,但这一事实本身并不意味着某些条件如得到满足,本法院则不应行使其管辖权.
7.
自1948年以来,以色列一直处于争端之中,先是与阿拉伯邻国(及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近年来又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之间发生争端.
以色列就这一问题提出的书面看法(7.
4-7.
7)以及秘书长的报告都是这一现实情况的佐证,而后者提及了"每一方"的"简要法律立场".
尽管巴勒斯坦还不是一个独立国家,本法院认为其具有特殊地位,可以允许其应邀参与这些诉讼程序.
因此,两个国际行动者之间存在着争端,而且咨询意见请求与争端的一个因素有关.
8.
这本身并不说明本法院应以适当性为由拒绝行使管辖权.
对于本法院审查酌处权问题而言,这只是个起点.
一系列咨询意见案例说明了应如何适当解读1923年"东卡雷利亚地位"一案咨询意见(《常设国际法院案例汇编》,B辑,第5号)的原则.
通过"联合国某些经费"一案(《宪章》第17条第2项)的咨询意见(《1962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51页)、"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276(1970)号决议继续留驻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对各国的法律后果"一案的咨询意见,(《1971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2页)、以及最显而易见的"西撒哈拉"一案的咨询意见,(《1975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2页),"东卡雷利亚地位"一案的判决理由得到了解释.
在这些案例中,"西撒哈拉"一案提供了最相关的指南,因为该案涉及两个国际行动者之间的争端,而本法院本身没有对此发表若干咨询意见(参照纳米比亚一案的咨询意见,该意见是在此前三个有关合法性的咨询意见的背景下发表的).
9.
本法院并未在"西撒哈拉"一案中表明,咨询意见中的同意解决冲突原则对身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各方而言现已丧失了一切相关性.
本法院只是说,"东卡雷利亚地位"一案的判决理由所依据的具体因素并不存在.
不过,在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法律利益成为咨询意见的主题时,必须对其他因素予以考虑,以确定发表这一意见是否具有适当性.
10.
的确,在"西撒哈拉"一案中,法院引述了经常被引用的"与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和约的解释,第一阶段"一案咨询意见中的法官意见,即向联合国机关提供的意见"代表着其对本组织活动的参与,而且在原则上不应予以拒绝"(《1950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71页),但法院又接着重申:"假如在某个案例的具体情况下,对司法适当性的考虑迫使本法院拒绝发表咨询意见,那么,未表示同意可以构成拒绝发表所要求意见的理由.
简言之,对于认识到发表意见的适当性而不是对本法院的管辖权而言,有关国家的同意仍然具有相关性.
因此,在某些情况下,由于有关国家没有表示同意,可能致使发表咨询意见不符合法院的司法特性.
"(西撒哈拉,咨询意见,《1975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25页,第32至33段).
11.
那么,在西撒哈拉一案中有哪些条件被认为可以使本法院甚至在争端牵涉到联合国会员国的情况下发表咨询意见一种条件就是:联合国会员国:"不能合理地反对大会行使其处理非自治领土的非殖民化问题的权利,并要求就有关行使这些权利的问题发表咨询意见(同上,第24页,第30段).
尽管大会没有在行使委任统治监督机构(例如纳米比亚的情况)或使非自治领土实现非殖民化的机构的权力(例如西撒哈拉的情况),但本法院在第48至50段中正确地陈述了联合国对这一争端的长期、特殊的机构兴趣,而修建隔离墙现在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12.
然而,另有一个条件有待满足,本法院在"西撒哈拉"一案对此作出阐述.
本法院表示,法院感到满意的是:"大会的目的不是通过请求发表咨询意见的方式,向本法院提交一项争端或法律争议,以便大会日后可以凭借本法院咨询意见,行使其和平解决这一争端或争议的权力或职能.
请求出于完全不同的目的:从本法院获得一项大会认为有助于其适当行使领土非殖民化职能的咨询意见"(西撒哈拉,咨询意见,《1975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26-27页,第39段).
在本案中,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请求并不是为了获得关于大会非殖民化职责的咨询,而是日后根据本法院的咨询意见,行使对争端或争议的权力.
许多参与者在本案口头辩论阶段坦率地强调了这一目的.
13.
本法院在其咨询意见中有关适当性的部分根本没有涉及到这一点.
更确切地说,本法院对这一事项简直是未置一词,从而避免提到上文引述的字句,并避免就这些词句对本案的适用作出任何答复.
就此而言,正因其不置一词,这项咨询意见实质上修订了而不是运用了现有判例法.
14.
就适当性问题而言,另有一个问题一直令我感到关切.
以色列-巴勒斯坦间冲突的法律、历史和政治都十分复杂.
一个法院被要求对一个多面性冲突的一个因素作出宣示,同时又不得审视其他因素,这本身令人难堪.
前因后果在法律裁定中通常具有重要性.
然而,鉴于大会的请求是希望对人道主义法发表咨询意见,这一请求所带来的义务是绝对的(这些义务本身的限制性规定除外).
这是人道主义法的基石,而且那些参与冲突的各方始终知道,冲突是以我们对未来的希望为代价,因此,无论冲突是如何挑起的,他们交战时都必须"有所节制",并且遵照国际法行事.
尽管就人道主义法的义务而言,这一因素削减了前因后果的相关性,但事实上,前因后果对于法院决定处理的其他国际法问题仍然具有重要性.
然而,由于问题的提法,无法对这一前因后果加以考虑.
15.
法院在提到"建造隔离墙只不过是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一个方面"这一现实时指出,"本法院的确知道隔离墙是一个大问题的一部分,不论提供什么样的意见,它都会认真考虑这个情况"(第54段).
16.
事实上,它从来没有这样做.
意见的其他部分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
此外,我发现法院在第71-76段中描述的"历史"既不平衡也不令人满意.
17.
在被要求就一大问题中的一个因素提出意见时,法院应当如何做显而易见,这不意味着"答复"这些比较大的法律问题.
法院回避我们可能称之为"永久地位"的问题,以及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以往众多争议评论是非是很明智和准确的.
法院面临进退两难的窘境,因此就必须提出平衡的意见,回顾各方应承担的义务.
18.
我遗憾地指出,我不认为本意见达到了这个目的.
当然,法院在第162段中指出"各方都采取了非法行动,作出了单方面的决定",并强调指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有义务严格认真地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则.
"但我认为,还需要做大量工作,避免因被请来考虑"整个大问题的一部分"而引发的不平衡,然后"认真考虑"实际情况.
应在主文的范围内呼吁双方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律采取行动.
不这样做就严重违反了法院遵循《威胁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合法性的主文》(国际法院报告,1996年(I),咨询意见第266页)执行条款F的途径.
此外,法院应提出在这个"大问题"上对双方的要求.
这样做并不难,从安全理事会第242号决议到第1515号决议,根本要求始终未变,这就是以色列有存在、被承认、享有安全的权利,巴勒斯坦人民享有领土权利,自决和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
安全理事会第1515号决议设想从总的方面到细节方面确保这些长期义务.
可以预料的悲剧是,在一方采取行动之前,另一方绝不会为实现这个目的而采取行动.
法院决定,应当行使其司法管辖权,应利用咨询意见案中的范围或余地,提醒双方根据国际法,他们不仅有实质性义务,而且还有同时向前推进的程序性义务.
此外,我认为,为了达成平衡的意见,后一个因素似乎应出现在主文中.
19.
我认为,法院还应当借此机会最明确地说明,令人遗憾的是,现在明显需要的是重申、甚至是在国际律师中重申保护平民仍然是人道主义法不可逾越的义务,不仅对占领者是如此,对寻求从被占领中解放出来者也同样如此.
20.
我极度犹豫后终于投票赞成主文第(2)分段.
我最终投赞成票是因为我对法院在第44-64段中提到的所有看法都表示同意.
我对它选择不写的方面表示遗憾.
**21.
主文第(3)(A)分段编拟的方法没有把法院据此达成结论意见的各种理由分开来.
我投票赞成这段是因为我也认为,在被占领领土及其关联制度上修建的隔离墙违反了人道主义法.
但是我不同意法院在达成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决定之前采用的其他几个台阶,同样也不同意其处理资料来源的做法.
22.
大会提出的问题请法院考虑国际法规则和原则,包括《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和安全理事会以及大会的相关决议"(大会第ES-10/14号决议).
人们本来期望,一旦法院认定《日内瓦第四公约》适用,则人道主义法律就应成为本《意见》的核心.
23.
大会第ES-10/13号决议认定隔离墙违背人道主义法,但却没有具体说明违背了哪一条和为什么这么说.
巴勒斯坦告知大会,它认为违反了《日内瓦第四公约》第33、53、55和64条和《海牙章程》第52条.
其他与会者援引《海牙章程》第23(g)、46、50和52条,以及《日内瓦第四公约》第27、47、50、55、56和59条.
特别报告员认为,隔离墙违反《海牙章程》第23(g)和46条以及《日内瓦第四公约》第47、49、50、53和55条.
人们可能期望,咨询意见可能载有详尽的分析,并提到案文,大部头的学术文章以及由法院决定哪些事实是正确的情况.
这种措施可能是采取了传统的做法,把咨询意见作为阐述和发展国际法的机会.
24.
也许为了平衡,不但应说明以色列违背了哪些条款,而且还要说明它没有违背哪一条.
但是法院一旦决定适用其中哪些条款,就只提及以色列违背的那些条款.
此外,意见的结构没有分别讨论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我认为这使人们很难理解法院确定的理由.
主文第(3)(A)分段的语言很笼统,但是也不应当忽略法院认定只违反了《日内瓦第四公约》第49条(第120段)、《海牙章程》第46和52条以及《日内瓦第四公约》第53条(第132段).
我同意这些认定.
25.
经过对国际人道主义法进行一份轻描淡写地叙述之后,法院转向人权法.
我同意法院关于人权法在被占领领土上具有重要性的结论.
我还赞同第134段中对《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12条所作的结论.
26.
与此同时,还应当指出,有一些常设条约机构,它们的职能是仔细审查各《盟约》缔约国的行为.
的确,法院对《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的答复既提到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相关管辖权,也提到该委员会对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上的义务所作的结论意见.
27.
迄今为止,考虑到实现这类权利的方案要求,《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的情况甚至更为蹊跷,法院所能做的只不过是用一句话说明,隔离墙及其关联制度"妨碍有关人员行使工作、健康、受教育和享受如《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所宣布的适当的生活条件的权利"(第134段).
对这两个《盟约》来说,人们可能希望了解要求法院就缔约国遵守这些义务的情况提出咨询意见是否适当,遵守盟约情况又由为此目的设立的条约机构负责进行极为详细的监督.
大会没有提出任何更笼统地先例,因为很多很多缔约国不遵守根据这两项盟约所应承担的义务,因此请法院研究以色列在这方面的行为,这也许难以成为一个理由.
28.
法院为了决定主文第(3)(A)分段中的一般性决定,也必须依赖所谓以色列违反自决法的结论.
法院同意关于隔离墙及其相关地域风险在法律上确有问题,"建筑隔离墙、与以前采取的措施严重妨碍了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决的权利,因此破坏了以色列尊重这种权利的义务.
"(第122段)对我来说,这似乎不合逻辑.
29.
关于"超越殖民主义的自决"有很多理论教义和实践做法.
《1970年联合国友好关系宣言》(大会第2625(XXV)号决议)也谈到自决于适用于人们受到"外来征服、统治和剥削的情况.
"大会在考虑阿富汗和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情况下通过了很多涉及后者的决议(例如1974年大会第3236(XXIX)号决议(巴勒斯坦);1987年大会第2144(XXV)(阿富汗)号决议).
人权事务委员会一贯支持这种殖民后时代的民族自决观.
30.
法院第一次在没有任何法律分析的情况下,无保留地通过了第二种看法.
我支持所援引的原则,但我对这项原则是否适用于本案感到困惑.
自决是"所有人民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权利"(《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第一(1)条.
正如咨询意见所指出的(第118段),为了自决的目的,现在人们已承认巴勒斯坦人为"人民".
但对我来说,这似乎与法院认定是隔离墙"严重妨碍行使这一权利".
真实的方案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显然无法和/或不愿意并行向前迈进,确保必要的条件:在以色列从阿拉伯被占领领土上撤出时,巴勒斯坦人提供必要的条件,让以色列感这样做是安全的.
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即使从未建造过隔离墙,巴勒斯坦人也依然不能行使自决的权利.
我认为,让法院认定隔离墙(而不是"大问题",超越了请法庭提供意见的范畴)严重妨碍实现自决,既不现实也不实际.
31.
如果从领土的角度来看的话,这项裁定也同样不更具说服力.
正如本法院在第121段中指出的,这堵墙本身在目前不构成实际的并吞.
"人民"必须在自己的领土上行使自决权.
不论最后谈判议定了什么样的边界,正如这个咨询意见第78段所说的,毫无疑义的,以色列是占领了巴勒斯坦人的领土.
这个领土被占领的事实,不会因为现在建了一堵墙穿过它而增加一分或减少一分.
要结束这种状态,双方必须同时接受国际法给予它们的责任.
32.
本法院在解决了适用的法律问题并予以应用之后,审视了对可能的违反情况是否有可能的但书、例外和辩护.
33.
我不完全同意法院就自卫法问题所说的一切.
法院在第139段援引了《联合国宪章》第51条,然后接着说"因此《联合国宪章》第51条承认在一国对另一国进行武装攻击时存在固有的自卫权利".
恕我直言,第51条没有一点规定只有在国家发起武装攻击的时候才可以用自卫的手段.
这个但书只不过是本法院在尼加拉瓜境内发生的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所作的这样的裁定(尼加拉瓜讼美利坚合众国,实质问题、法院判决、1986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4页)的副产品.
法院在那一次认为,如果非正规军是由一国所派或是为了其利益而派出的,并且如果这些活动"的规模和影响之大,就象是由正规的武装部队进行的,会定性为军事行动",则可构成武装攻击(同上,第103页,第195段).
虽然我接受——我也必须接受——必须视此为目前的法律的表白,但是我维持我已经在其他地方表达过的对此论点的所有保留(罗莎琳·希金斯著,《问题与过程:国际法和我们是怎样应用国际法的》,第250-251页)(R.
Higgins,ProblemsandProcess:InternationalLawandHowWeUseIt).
34.
本法院的论点是,由于武力的使用源自被占领领土,因此那不是"一国对另一国"的武装攻击.
我认为这个论点没有说服力.
我不能明白本法院这样的观点,即如果攻击源自占领国占领的领土(这个领土是法院曾裁决没有被并吞的,则当然是以色列"以外"的领土),则占领国失去保卫自己国内的平民百姓的权利.
此外,巴勒斯坦可以因够不上一个国际实体而不邀请其来参加这些诉讼程序和受益于人道主义法,但却不因为够不上一个国际实体而不适用禁止对他国进行武装攻击的法律.
这是不公平的那种形式主义.
问题肯定是派人和派人群去对付以色列平民的责任谁属以及此种行动累积的严重性.
35.
不过,到头来,这些保留没有使我投票反对答复第(3)(A)分段,理由有二:第一,我仍然未能信服的是,非强制性的措施(例如建墙)按照平常理解的《宪章》第51条属于自卫范围;第二,即使正确地说那是自卫行为,那也需要提出这是必要和恰如其分的理由.
虽然这堵墙看来是减少了对以色列平民的攻击,但所选的墙的建筑路线为与这些攻击没有相干的巴勒斯坦人造成的困难,其必要性和是否恰如其分并没有加以解释.
36.
这份答复的后部分讲的是本法院的裁定的法律后果.
37.
我对答复的第(3)(D)分段投了赞成票,但我与法院不同,我不认为已确定的违反国际法事件的指定后果与普遍义务的概念有任何关系(参看这个咨询意见第154-159段).
本法院在巴塞罗那BarcelonaTraction,LightandPowerCompany,Limited有限公司一案第二阶段的著名判词(判决,《1970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32页第33段)常常被援引,次数多得不得了.
遗憾的是,本咨询意见也这样做——在第155段.
当年的那个判词是针对十分具体的司法诉讼地位问题.
正如国际法委员会在对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的评注(A/56/10,英文本第278页)中正确地指出的,有些权利,由于其重要性,"予以保护对所有国家来说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这与在一个案件中把重大的义务强加于第三方无关.
38.
第三方不要承认或协助非法的状况是不言而喻的,不需要援引不确定的"普遍义务".
根据《宪章》第24和第25条,安全理事会如裁定一种状况非法,其"决定就对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有约束力,它们就有义务接受及执行这些决定"(南非不管安全理事会第276(1970)号决议继续留在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对各国造成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1971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53页第115段).
联合国会员国不得承认南非在纳米比亚的非法存在的义务,以及不得给予支持和援助的义务,其依据绝对不是"普遍义务".
相反,本法院强调指出:"联合国的主管机关对一种非法状况作出了有约束力的裁定之后,这种状况不能继续下去而没有后果"(同上,第117段).
本法院已经在一个争议性的案件中裁定,它如裁定一项行为非法,就"有法律后果,即结束非法状况"(HayadelaTorre,判决,《1951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82页).
虽然在本案里,裁定非法的是本法院,而不是联合国的机关;而虽然这项裁定是以咨询意见的形式作出的,不是在一个诉讼案件中作出,但是,本法院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意味着它的法律后果与裁定一种行为或状况非法是一样的.
联合国会员国不得给予承认和援助的义务的依据不是建立在普遍义务的概念上.
39.
最后一点,对违反人道主义的事援引(第157段)"普遍义务"性质看来是同样不相干.
这些不得违反的原则一般是有约束力的,因为它们是切切实实的习惯国际法.
而日内瓦第四公约第1条规定"缔约国承诺在所有情况下尊重本公约及确保本公约得到尊重",虽然本法院看来将其视为与"普遍义务原则"有关,但其实只是几乎获得普世批准的这个多边公约的一个条款而已.
1949年日内瓦外交会议的最后记录没有对该项规定作出有用的解释;有关的评注认为"确保公约得到尊重"超越一国自己领土上的立法行动和其他行动.
它指出"如果一个缔约国没有履行其义务,则其他缔约国(中立国、盟国或敌国)可以也应当努力使它恢复对该公约的尊重.
该公约提供的保护制度要正确运转,事实上要求各缔约国不应当仅仅满足于自己适用公约的条款,而应当尽其所能确保该公约所立足的人道主义原则在全世界适用.
"(1949年8月12日的日内瓦四公约:评注,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第四公约(Pictet版)第16页)人们将注意到这份答复第(3)(D)分段谨慎地指出任何此种行动都应当符合《宪章》和国际法.
40.
最后,我想补充一点,即虽然在这件事情上,本法院的确收到了许多信息,但由以色列直接提供的则仅是一小部分.
本法院处理此事主要根据2002年4月14日至2003年11月20日期间的秘书长的报告和其后的联合国书面陈述(见第79段).
法院有没有利用在公开领域中的其他资料,这一点不清楚.
有用的资料事实上可在诸如以下的文件中找到:现任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和以色列的有关答复(E/CN.
4/2004/6/Add.
1);"以色列的隔离墙对其穿越的西岸社区的影响:给人道主义和紧急情况政策小组的最新报告,这堵墙的建造、出入以及其在人道主义方面的影响,2004年3月".
不管怎样,本法院的法律裁定的性质明显地是一般性的,对海牙规则或日内瓦第四公约具体条文怎样适用于该墙某些段落讲的很少.
不过我还是投票赞成答复的第(3)(A)分段,因为西岸的部分人口肯定受到重大的不良影响,这是不能以这些公约的军事上必要条款作为理由的;而以色列也没有向联合国或本法院解释它的合法安全需要只能够通过其现在选定的隔离墙路线才能满足.
罗莎琳·希金斯(签名)科艾曼斯法官的个别意见对执行部分第(3)(D)段投反对票的理由——请求提供咨询意见的背景——需要给予均衡的对待——管辖权问题——《宪章》第十二条第二项和大会第377A(V)号决议——司法适当性问题——请求的目的——实质问题——自决——相称性——自卫——法律后果——其他国家的义务——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家责任条款的第41条——不承认的责任——弃权的责任——确保尊重人道主义法的责任——四项《日内瓦公约》的共同第1条.
一.
介绍性发言1.
除了对关于国家承担的法律后果的第(3)(D)段外,我对《咨询意见》执行部分各段都投赞成票.
我投反对票有几个理由,在目前阶段我只是简要提一下这些理由,因为我在对《咨询意见》各个部分提出评论时将会提到这些理由.
我的动机可以摘述如下:第一:大会提出的请求没有使得法院必须确定各国因法院的裁定而需承担的义务.
在这方面,拿纳米比亚案中的《咨询意见》来作类比是不恰当的.
在该案中,关于国家承担的法律后果问题是请求的核心问题,而且从逻辑上来说也是这样,因为它以安全理事会的一项决定为前提.
法院认为该项决议,特别是其执行部分中涉及"所有国家"的第5段,"对于本《咨询意见》的目的是极为关键的"(虽有安全理事会第276(1970)号决议,各国对南非在纳米比亚(西南非洲)的继续存在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1971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51段,第108段).
本案不存在类似的情况.
在本案中,不是请求法院对联合国的一个政治机关作出的决定引起的法律后果提出意见,而是请求法院对一个成员国采取的行动引起的法律后果提出意见.
虽然一旦认定该行动是非法的,也不妨碍法院审议第三国所承担的后果问题,但是,这样一来,法院的结论将完全取决于其推理,而不是取决于该项请求的必然逻辑.
但是,我认为,正是这项推理不够说服力(见下文第39-49段),这是我投反对票的第二项动机.
第三,我认为,法院在本答复第(3)(D)段中所作的结论相当软弱无力;除了法院裁定国家有义务"在维持由于建造[隔离墙]而造成的局势方面不提供支援或援助"(我同意这项裁定)外,我很难想象可以预期各国在实际情况下应做什么或不应做什么.
我认为,一个司法机构的裁定应对当事方的行为有直接的影响.
执行部分第(3)(D)段第一部分或最后一部分都不能满足这项请求.
2.
虽然我大体上同意法院的《意见》,但对于一些问题,我对法院的推理有保留.
我将遵照该《意见》的逻辑顺序提出我的评论:(a)管辖权问题;(b)司法适当性问题;(c)实质问题;(d)法律后果.
在提出评论之前,我想就该请求的背景说几句话.
二.
请求咨询意见的背景3.
在《意见》第54段,法院(就司法适当性)指出,大家知道隔离墙问题是更大的问题的一部分,但是,这不能作为它拒绝回答所提问题的理由.
法院还说,它将会认真顾及这个更大的背景.
我完全同意法院在该段所说的观点,包括法院认为,无论如何它可以只限于审查为审议向它提出的问题所需的其他问题.
4.
我认为,法院可以而且应该在其意见中更加明确注意到该请求的一般背景.
几十年来,巴勒斯坦内和周围的局势不仅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几乎是不断的威胁,而且还是人类的悲剧,在很大方面是巨大到难以想象的地步.
象巴勒斯坦人那样的社会如何能够对暴力的受害者往往是无辜男子、妇女和儿童这样一个局势熟视无睹和生活在这样的局势中象以色列人那样的社会如何能对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对政治对手的攻击转向无辜平民、男子、妇女和儿童的局势熟视无睹和生活在这样的局势中5.
以色列解释说,建造隔离墙是提供保护免受后一种一般被认为是国际罪行的行为的伤害所必要的.
为了杀害而蓄意和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平民是恐怖主义的核心要素,国际社会对此行为已经毫无条件地加以谴责,而不论其动机如何.
每一个国家,包括以色列,都有权甚至责任(如法院在第141段所说的那样)对这类行动作出回应,以保护自己公民的生命,尽管这样做的手段的选择受到国际法的规范和规则所限制.
在本案中,以色列没有尊重这些限制,而法院令人信服地证明以色列没有尊重国际法的这些规范和规则.
我对这项结论没有意见,同样的,我也对下列结论没有意见,即沿着所选择的路径建造隔离墙的行动大大增加了生活在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的苦难.
6.
在第122段中,法院认为,建造隔离墙以及早些时候采取的措施严重地妨碍巴勒斯坦人行使其自决权利,因此构成以色列违反其尊重该权利的义务.
我质疑该裁定的后一部分是对的(见下文第32段),但是,毫无疑问,一个把巴勒斯坦人隔离成两部分的建筑物的存在本身使得他们的自决权利更加难以实现,虽然我们必须承认,这项权利的实现更多地是取决于政治协定而不是当地的局势.
但是,同样正确的是,正如2002年7月16日中东四方声明所说的,恐怖分子的行为本身"对巴勒斯坦人民希望有一个更好的未来的合法愿望造成极大的损害".
该声明接着说:"必须不让恐怖分子毁灭整个区域以及一个团结一致的国际社会的希望,即希望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获得真正的和平与安全.
"(MWP2004/38,Add.
,Annex10).
7.
法院限制自己只报告导致目前的人类悲剧的一些历史事实.
从真正需要些什么东西来回答大会的请求这一观点来说,这样做也许是对的.
但是,它的结果是,第70至78段所列的历史梗概却是两维的.
我会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这个例子与本案毫无关系.
8.
法院在给出其历史梗概之前说,法院将对领土的状况做一个简要的分析,它开始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委任统治权的建立.
但是,它丝毫没有提到西岸从1949年《全面停战协定》的缔结到1967年以色列的占领期间的状况,虽然众所周知,约旦把西岸置于其主权范围内,而这项直到1988年才取消的主权请求只得到三个国家的承认.
9.
我不能理解忽略这项客观历史事实的理由,因为我认为,约旦对西岸的主权请求只会增强赞成从以色列在1967年6月占领时刻起适用《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论点.
以色列政府声称,由于西岸在1967年战争之前不在约旦的主权范围内,因此《日内瓦第四公约》在法律上不适用于西岸.
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么这种论点就已经站不住脚,因为冲突一方声称属于它的并在它的控制下的领土一旦被冲突另一方所占领,按照定义,就是《日内瓦第四公约》意义下缔约国的占领领土(斜体是后加的),而以色列和约旦都是该公约的缔约国.
这一点当时也为以色列当局所承认,以色列占领后颁发的命令就是证明,而且《意见》第93段也提到这项命令.
10.
法院对西岸从1949年到1967年期间的状况保持沉默造成了奇怪的结果,即读者只能从言外之意才能了解到西岸当时是在约旦控制之下(第73和129段提到以色列和约旦之间的停火线(绿线)),而《意见》从来就没有向他们明确说明西岸已经置于约旦当局的控制下.
法院如果提到这一点,也绝不会被迫就该当局的合法性或正当性作出评论,因此,这种做法就更加令人困惑不解了.
11.
以色列外交部副主任兼法律顾问在1月29日给法院书记官长的信中说,"以色列相信并预期法院会超越该请求的范围而研究与此事项有关的更为广阔的问题"(MWP2004/38,附信).
在这方面,有人说ES-10/14号决议对以色列公民受到的恐怖袭击"绝对保持缄默",从而"反映了提出请求的机关怀有极大的偏见和不公道".
因此,以色列请求法院不要提出意见.
12.
我认为,法院在决定它回应一项提出咨询意见的请求是否适当的问题时,法院可以只限于研究在这项请求前进行的为了解有关问题所需的政治辩论.
这类辩论毫无例外都是非常激烈的,但如法院在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案件中所说的:"一旦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请求就一项法律问题提出咨询意见,法院在确定它是否有任何迫不得已的理由拒绝提出这类意见时,不会去理会该请求的本源或其政治历史,也不会去理会该项通过的决议的表决情况"(《1996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I),第237页,第16段.
)但是,法院不是在真空中运作的、它是联合国的一个主要司法机关,必须在更大的政治背景下来履行其职务和责任.
不能预期它会在一个政治机关的请求下提供法律意见而不充分考虑到这项请求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
13.
虽然法院肯定已经考虑到以色列提出的论点并以体谅的方式处理了这些论点,我认为,目前的《意见》本来是能够更加令人满意地反映所有生活在该区域的人的利益的.
《意见》中有好几处提到恐怖行为时措辞相当模糊,我认为,这样的提法是不够充分的.
咨询意见是要提请联合国的一个政治机关注意的,而且肯定会对政治进程有影响.
因此该意见必须在其整个推理中直至其执行部分都应反映所有有关者的合法利益和责任,而不是只在结论段落(第162段)中向他们提及.
三.
管辖权问题14.
我完全赞同本法院的看法,即ES-10/14号决议的通过不是越权行为,因为它没有违反《宪章》第12条第1项的规定;它也具备了联合一致共策和平决议(第377A(V)号决议)所定的须召开紧急特别会议的基本条件.
15.
然而,我却怀疑是否在叙述联合国政治机关有关对《宪章》第12条第1项的解释的实践时能够不考虑联合一致共策和平决议对这项解释的影响.
本法院在《意见》中把第377A(V)号决议当作另外一个项目,而且单单连同其程序要件一起讨论.
我认为,这项决议还可产生更加敏感的影响,即它影响到关于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内各自职权范围间关系的解释;它必然已加快了对载于第12条第1项内的条件的解释的发展,此项条件就是,当安全理事会对于任何争端或情势,正在执行职务时,大会对于该项争端或情势,不得提出任何建议(着重号是附加的).
16.
在学说上也承认这种影响.
"'维持和平联盟'决议的表决免不了会对第12条第1项的限制的范围产生影响,…….
"(PhilippeManin之语,载于J.
P.
Cot,《联合国宪章》,第2版,1981年,第298页;亦见E.
deWet,《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所拥有的第七章内的权力》,2004年,第46页.
)在实际上惯例上,联合一致共策和平决议的通过有助于形成以下的解释,即如果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票阻止了安全理事会作出决定,则后者不再应被认为是在执行其属于第12条第1项含意内的职务.
事实上如果发生当安全理事会就一项关于构筑隔离墙问题的决议进行表决时有国家投了否决票,则此项事实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可据以获致一项结论,即安全理事会因而并未在执行关于构筑隔离墙问题的其《宪章》下的职务.
因此,在本案中,认定ES-10/14号决议未违反《宪章》第12条第1项的结论同第377A(V)号决议对关于该项条文的解释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17.
下述的事实已证明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在第377A(V)号决议所必备的程序要件方面也都接受这类的实践,那就是,安理会的成员没有一个认为于2003年10月20日重新召开大会紧急特别会议有违《宪章》条款,或者认为要求以色列应停止构筑隔离墙并拆除已构筑的隔离墙的决议的通过因此就构成了越权行为.
在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此项决议(ES-10/13号决议)是由欧洲联盟主席当作一项折衷办法提出来的,而且是在关于同一主题的一项决议草案在安理会中被否决之后不到一个星期内提出的,当时欧洲联盟成员国在安全理事会中正占有两席常任理事国席位和两席非常任理事国席位.
18.
我要补充的是,我赞同本法院的意见,即认为已经发展出了一种惯例,让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能够同时一并处理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同一事项.
但是,我怀疑大会是否能够合法地通过具有ES-10/13号决议(它无疑是第12条第1项含义下的建议)性质的决议而不论是在大会常会上为之或是在大会紧急特别会议上为之,如果安全理事会已审议了关于构筑隔离墙的具体问题但却尚未作出决定.
四.
司法正当问题19.
我必须承认,在关于如果遵循大会的请求,是否在司法上系属妥当一事上,我的看法是相当犹豫的.
20.
我的犹豫不定主要关涉到关于本法院是否会因为发表了所请求的咨询意见而达成了正当的政治目的,从而有损本法院促进全球安全和尊重法治的能力的问题.
必须承认,本件意见不论其内容如何,都必然将会成为本已热烈进行的政治辩论的一部分材料.
这个问题的适切性特别可证诸当事四方中有三方(美国、俄罗斯联邦和欧洲联盟在表决ES-10/14号决议时都投了弃权票而且似乎不太热衷于看到本法院是因为担心咨询意见可能会抵触政治和平进程而遵循大会决议的请求.
因为相关的局势是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持续性危局和引起巨大的人类苦难的根源,所以,这种担心必须受到重视.
21.
我虽然承认,关于可能的政治化的危险是实际存在的,但是,我却归结出一个看法,即这个危险不会因为拒不发表咨询意见而被抵销.
大会在构思要求发表咨询意见的请求时本应考虑到此项危险.
一旦决定提出此项请求,这就使本法院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一个行动者,不论它是否会发表咨询意见.
正如同发表了咨询意见一样,如果不发表它,也会同样使本法院走向政治化.
本法院只有将它的工作严格限于其司法职能,它才能够尽量减少会损及它在坚持尊重法治原则的可信度方面的危险.
22.
我的犹豫不决还涉及大会的请求的目的问题.
请问,大会提出该项请求的目的是什么在这点上,ES-10/14号决议序言部分最后一段似乎提供了某些进一步的信息,其内容如下:"铭记时间的推移逐步加重了当地的困难,因为占领国以色列在构筑上述隔离墙的问题上继续拒绝遵守国际法,造成了有害影响和后果……"大会显然认定有必要迅速采取行动以终止这些有害的影响和后果;因此,它需要本法院的看法.
但是,问题依然存在:针对什么事项的看法为什么要一个司法机关对一项已被认定为不符合国际法而且行为者已被要求终止其此项不法的造墙行为并拆除已造的隔离墙(ES-10/13号决议)的问题发表意见23.
本件请求令人回想起Petrén法官在纳米比亚案中所观察到的两难情况.
他认为在该案中请求发表咨询意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从本法院获得一种答复,可据以导致各国因而有义务应对南非的压力……"他认为这倒转了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和主要政治机关之间角色的自然分配,因为请求本法院发表意见的议题并不是为求据以推知政治后果的法律问题,其情况正好相反(《1971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28页).
24.
本法院在本件意见中答复了一种论点,即认为大会并未明确指出它将如何利用关于隔离墙的咨询意见,并且在就此提及核武器案时指出,"大会在履行职能时是否需要咨询意见,不应由本法院自己决定.
大会自己有权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一项咨询意见的用途.
"(第61段).
本法院还宣称,本法院"不能用自己对请求它提出的咨询意见是否有用所作出的评估来取代提出此种请求的机关、即大会的评估"(第62段).
25.
我不认为这个答复完全令人满意.
在用本法院对咨询意见的效用的评估取代请求发表它的机关的同样的评估与从司法观点分析该项请求的目的为何之间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
后者系属单纯的必要举措,目的是为了查明本法院作为一个司法机关能够宣示什么.
客气地说,从这个观点视之,该请求的措词非常奇特.
就实际事实而言,本法院已作了这种分析;然而,《咨询意见》第39段却宣称,使用建造隔离墙所带来的"法律后果"的术语"就必然包括评估建造隔离墙是否违反国际法中某些规则和原则".
我赞同这个说法,因为"必然"二字涉及本法院的司法职责,而非因为"必然"二字涉及请求文件中的措词.
兹引用Dillard法官在纳米比亚案中曾说过的话:"虽然这些[政治]机关认为适宜请求发表咨询意见,但它们必须预期本法院在行事时一定会严格遵循其司法职能.
这项职能禁止它未经任何调查即接受本身可规范此项职能所生之法律后果的性质和范围的法律结论.
如果请求发表咨询意见的决议在法律上系属中立性质者,则另当别论……"(《1971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51页,着重号是附加的.
)26.
本案中的请求绝非"在法律上系属中立性质者".
因此,如果从司法正当的观点视之,本法院为了便于发表意见,就有义务重新审议请求文件的内容,以期维持其司法尊严.
本法院已经这样做了,但是,我却认为它应当自动这样做而且不应假设大会"必然"应假设的那样;显然大会并未这样假设.
27.
我要补充的是,在司法正当问题的另一些方面上,我都赞同本法院的看法.
特别是本法院断定大会的议题不应被视为"只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间的一项双边问题"(第49段);我认为这项断定的措词很适当,因为在关涉到存在双边争端的问题上,它避免了"这个/或那个"式的两难情况.
可能会同时存在着有组织的国际社会有正当理由加以关切的局势和有关该同一局势的双边争端.
后者的存在不应使有组织的社会的机关丧失构成性文书所赋予的职能.
在本案中,联合国长期以来一直都介入巴勒斯坦问题,而且正如同本法院所指出的,请求文件内载的主题也是联合国十分关注的(第50段).
因此,本法院如发表意见,绝不会损及同时亦存在的双边争端的司法解决上的同意原则.
该双边争端不应当与请求文件的主题毫无关系;但是,只有在无法概括叙明的极为特殊的情况下,该争端的存在才能被视为可构成本法院拒不答复请求的理由.
在这点上,我发现,《意见》第47段内所载纯属间接性质的推理的得自西撒哈拉案咨询意见的引证文句用处并不大.
28.
如果鉴于联合国长期以来一直都介入巴勒斯坦问题,所以所提出的请求是合法的,那么,以色列辩称本法院未取得大都由作为争端一方的以色列掌握的必要的证据材料的辩解就无法成立.
本法院必须尊重以色列选择不讨论案情实质的立场,但是,本法院本身却有责任评估已有的资料是否足以使本法院能够发表所请求的意见.
此外,虽然以色列已决定不讨论案情实质实在令人遗憾,但本法院却已正确地断定它可以根据现有的资料发表咨询意见.
五.
实质问题29.
我赞同法院的意见,认为1907年《海牙章程》、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1966年《公民及政治权利盟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盟约》以及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均适用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而以色列修建隔离墙并制订相关的制度,违反了这些公约中每一项公约的一些条款为其规定的义务.
我认为法院在这方面的推论无可指摘,但我感到遗憾的是,法院第137段中的裁定概要没有列出遭到违反的各项条约的规定.
30.
法院没有就领土权利和永久地位问题表明立场.
它注意到以色列当局在各种场合发表声明,称"围栏"只是一种临时办法,并不构成边界,没有改变领土的法律地位.
我对此类保证表示欢迎,因为它们可被视作以色列方面对法律承诺的确认,但我同法院一样,对修建隔离墙造成既成事实表示关切.
因而更必须加快解决所有领土问题和永久地位问题的政治进程的步伐.
31.
自决——我认为,法院也应把自决问题留给这一政治进程处理.
我完全确认自决权是当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让巴勒斯坦人民实现这一权利是解决以巴冲突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
如《路线图》等文件所述,这一政治进程压倒一切的目标,就是"导致一个独立、民主和可行的巴勒斯坦国家的出现,与以色列及其他邻国在和平、安全的环境中共存.
"(《秘书长档案材料》,第70号).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对这一目标均表示认同;为此,双方本着善意都有义务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有损于这一共同利益的行动.
32.
因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属于比修建隔离墙更宽广的问题范围之内,也必须在这一更宽广的问题范围内加以实现.
我乐意赞成法院的意见,认为隔离墙及其相关制度妨碍了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决权,即便仅仅因为隔离墙有形地隔开了有权享有这一权利的人民.
但按定义来看,并非阻碍行使权利的每一种行为都违反了这项权利,或违反了尊重权利的义务,但法院在第122段中似乎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正如2002年7月16日四方声明所述,恐怖主义袭击活动(以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未能加以阻止)同样极大地损害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愿望,为此严重妨碍了自决权的实现.
这是否也违反了这项权利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违反者又是谁呢我认为,法院如不在法律上作进一步分析,就不应得出结论,认为以色列违反了它尊重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义务.
33.
就此,我认为《咨询意见》第88段提到法院以前的说法并不太具启迪作用.
在"纳米比亚"一案中,法院使用具体用语,提到委任统治下的居民与委任统治制度组织文书中所提的委任统治国之间的关系.
在"东帝汶"一案中,法院称殖民地情势下的人民的自决权是普遍适用的权利,因此是适用于所有人的权利.
但是,法院却没有提到如何将这一"权利"转化成作为非殖民国的国家应履行的义务.
我要再重复一下这个问题:阻碍行使自决权的行动是否都是违反了尊重这一权利的义务是否仅在情况较严重时才算违反中止妨碍行为是否就恢复了这项权利,或者仅中止了违反行为34.
相称性——法院裁定,在适用的人道主义法和人权公约的限制条款中规定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而且以色列不能把军事上的迫切需要或者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方面的要求当作以色列采取措施的正当理由(第135-137段).
我同意这一裁定,但认为隔离墙的修建还应受相称性原则的检验,特别是因为军事需要和相称性概念已经在国际人道主义法中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而且我认为,即使能认为修建隔离墙和制订相关制度作为用来保护以色列公民合法权利的措施具有正当理由,这些措施也不会通过相称性原则的检验,这一点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为修建隔离墙选定的路线以及随之对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居民造成的令人担忧的后果,与以色列力图保护的利益明显不相称,而且以色列最高法院在最近的裁定中也确认了这一点.
35.
自卫——以色列把它根据《宪章》第五十一条享有的固有的自卫权,当作修建隔离墙的理由.
在这方面,它援用了是安全理事会在2001年9月11日对美国境内的目标发生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之后通过的第1368(2001)号和第1373(2001)号决议.
法院在就这一论点作出答复时,首先指出,第五十一条确认在一国对另一国发动武装进攻时存在固有的自卫权(第139段).
这一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作为就以色列的论点作出的答复,它虽应予以应有的尊重,却不相干.
第1368号和第1373号决议确认了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而没有一处提到一国的武装进攻.
安全理事会称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授权安理会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而未对国际恐怖主义行为作出进一步限制.
它实际在第1373号决议中作出有关规定时,没有将恐怖主义行为归于具体的一个国家.
这是这些决议中全新的特点.
这一新特点并未因第五十一条的用词而受到排斥,因为它以先发生武装进攻作为行使固有的自卫权的条件,而没有说这一武装进攻必须来自另一个国家,即使50多年来这种解释已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接受.
这一新特点的法律影响迄今尚未得到评估,但无疑是自卫概念的新的处理方式.
令人遗憾的是,法院没有考虑到这一新特点.
36.
我认为,对驳回以色列关于它只是在行使自卫权的主张具有决定意义的论点载于第139段第二部分.
《宪章》所载的自卫权属于国际法规则,因此与国际现象有关.
第1368号和第1373号决议提到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因此,它们对也是受害国的国家控制的领土内所产生的恐怖主义行为没有直接影响.
而且以色列没有说这些行为产生于其他地方.
因此,法院正确地认定,这一局势不同于第1368号和第1373号决议所述的情况,因而以色列不能援用《宪章》第五十一条.
六.
法律后果37.
我投票赞成执行部分第3段(B)、(C)和(E)分段.
我同意本法院对以色列违背依照国际法应承担的义务对以色列本国和联合国所造成的后果的裁定(第149至153段和第160段).
不过,由于我投票反对执行部分第3段(D)分段,我将在后面的意见中以比我在介绍性评述中所作说明更加详细的方式,解释我不同意的理由.
38.
大会请求本法院具体说明建造隔离墙的法律后果.
如果大会提出这项请求的目的是认为本法院提供的意见可以协助其正当行使职能(第50段),那么,合理的做法是,《咨询意见》中应有一个段落是针对大会提出的.
同样合理的是,这一段落也应针对安全理事会而提出,因为这两个机关有着共同或平行的责任.
既然本法院已经认定,建造隔离墙及相关管理制度构成以色列违背依照国际法应承担的义务,本法院详细说明以色列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就也是合理的.
39.
毫无疑问,本法院有权这么做,但即使有许多法官竭力主张本法院这么做(第146页),这项请求本身却并没有要求(甚至连暗示也没有)确定其他国家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在这方面,本情况与"纳米比亚案"完全不同.
该案的问题只集中于国家应承担的法律后果,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请求标的是安全理事会的一项决定.
由于明确使用与"纳米比亚案"类似点的措辞是不够的,因此要在本案中确定其他国家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必须有一个特别的理由.
40.
《咨询意见》第155至158段所述的理由是:以色列违背的义务包括一些普遍义务.
必须承认,我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国家违背了一项普遍义务,就必定会给第三国带来义务.
我勉强能够找到的一种解释是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第41条的条文.
该条写道:"1.
各国应进行合作,通过合法手段制止第40条含义范围内的任何严重违背义务行为.
(第40条论述了对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所产生义务的严重违背行为.
)2.
任何国家均不得承认第40条含义范围内的严重违背义务行为所造成的局势为合法,也不应提供协助或援助以维持这种局势.
"第41条第3款是一项保留条款,与本案无关.
41.
我不会谈论普遍义务能否等同于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所产生的义务这个棘手的问题.
在这方面,我提及国际法委员会在其《条款》第三章开头部分的有益评注.
为便于论证,我先假定违背此类义务的行为都有同样的后果.
42.
第41条第1款明确提到合作的义务.
正如评注第3段所述:"面对严重违背行为,所要求的是所有国家联合和协调努力,抵消这些违背行为的效果.
"而第2段提到"在主管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框架内的合作".
因此,第41段第1款并没有提到严重违背行为给第三国带来的个别义务.
该款所述的内容,已经列入本法院的裁定执行部分第3段(E)分段,而不是第3段(D)分段.
43.
但是,第41条第2款明确提到不得承认严重违背行为所造成的情况为合法的义务,正如执行部分第3段(D)分段所述的一样.
国际法委员会在评注中提到,非法状况——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以合法权利要求,通常是对领土的权利要求的形式出现.
它举了下列例子:"试图通过否认自决权取得对领土的主权";日本吞并满洲国和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权利要求;罗得西亚单方面独立宣言,以及在南非建立班图斯坦.
换言之,所有上述这些例子都提到,正式或准正式颁布意在造成普遍效果的公告所产生的局势.
在此类案件中,我可以同意不承认的义务.
44.
然而,我很难理解,不承认非法行为的义务指的是什么.
为了遵守这项义务,执行部分第3段(D)分段此部分内容涉及的各个对象应该做些什么鉴于有144个国家明确谴责建造隔离墙为非法行为(ES-10/13号决议),这个问题就更加切中肯綮了.
而那些弃权或投票反对的国家(以色列除外),也不是因为认为建造隔离墙合法才这样做.
因此,我认为,不承认的义务是一项没有实质内容的义务.
45.
这一论点不适用于第41条第2款提到的第二项义务,即不提供协助或援助以维持严重违背行为所造成的状况.
因此,我完全支持执行部分第3段(D)分段此部分的内容.
此外,我也赞成在推理中、甚至在执行部分中添加一个句子,提醒各国注意向建造隔离墙的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重要性.
(本法院在"纳米比亚案"的《咨询意见》中列入了一个论述范围不同但内容类似的句子,见《1971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56页,第125段.
)46.
最后,我难以同意本法院关于《日内瓦第四公约》缔约国有义务保证以色列遵守该公约所包含之人道主义法的裁定(第159段,执行部分第3段(D)分段,最后一节).
在这方面,本法院以《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的第一条为依据,该条写道:"各缔约国承诺在一切情况下尊重本公约并保证本公约之被尊重.
"(强调后加.
)47.
本法院没有说明,它有何依据断定该条给未参与冲突的第三国强加了义务.
"筹备工作材料"并不支持此项结论.
按照透彻研究共同第一条之起源和进一步发展的卡尔斯霍芬教授的看法,该条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居民作为整体对条约的尊重,这与论述内部冲突的共同第三条密切相关.
(卡尔斯霍芬著:"TheUndertakingtoRespectandEnsureRespectinallCircumstances:FromTinySeedtoRipeningFruit",《国际人道主义法年鉴》,1999年,第二卷,第3至61页).
他从"筹备工作材料"中得出的结论是:"我在外交会议的记录中发现,政府代表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有人会在'保证尊重'这个句子中读出缔约国除了保证其人民'在一切情况下'尊重《四公约》义务之外应承担的任何承诺.
"(同上,第28页.
)48.
如今确凿无疑的是,早在很久以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在其对《1949年公约》的(非权威)评注中采取立场认为,共同第一条包含了所有缔约国应保证《公约》被其他缔约国尊重的义务.
同样确凿的是,通过《1977年附加议定书》的外交会议已在《第一议定书》中纳入共同第一条.
但是,该会议从来没有讨论该条对第三国的推定影响.
49.
本法院在"尼加拉瓜案"中对共同第一条的引用也不是没有助益.
本法院在未解释其条款的情况下评论说,"这一义务并非仅来自《四公约》本身,还来自《四公约》只具体提到的人道主义法的一般性原则.
"本法院继续说,"美国因此有义务不鼓励参与尼加拉瓜冲突的个人或团体"违反共同第三条("在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采取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尼加拉瓜诉美利坚合众国),判决书,《1986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14页,第220段).
但是,这项不采取行动的义务完全不同于保证遵守法律的积极义务.
50.
我绝不赞成对共同第一条的狭义解释,这种解释可能在1949年就已经考虑过.
但我只是不明白,本法院在《咨询意见》中给予该条的适用范围,是不是象实在法的陈述一样正确.
鉴于本法院没有在推理时提供任何论据,我觉得不能支持其判决.
此外,我看不到由于有了这项义务,个别国家除外交行动外,还可以采取哪一类积极行动.
51.
鉴于所有这些理由,我不得不投票反对第3段(D)分段.
彼得·科艾曼斯(签名)哈苏奈法官的个别意见同意咨询意见——大体上同意所作的推论——个别意见只是为了阐明一些显著要点——被占领领土的地位以连贯一致的法律意见为根据——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决议——《日内瓦第四公约》缔约国的意见——红十字委员会的立场——国家的立场——以色列承认《日内瓦第四公约》的适用性——以色列法庭的最近的裁决——本法院不满足于仅仅重申这种结论——本法院根据对《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解释独立作出类似的结论——本法院认为没有理由要确定被占领领土的先前的法律地位——明智的裁决没有必要也不会影响目前的地位——领土为无主地的情况除外——情况不会如此——概念不足令人置信,对当今世界也不适用——与属于委任统治地的领土不符——不兼并原则和居民福利原则于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期结束后继续采用——直到实现自决权为止——实现该项权利的当前障碍是以色列的持久占领——绿线最初是停战线——1967年战争前以色列法学家试图给予绿线较高的重要地位——无论当前局势如何,绿线是判断以色列占领情况的一个起点——对绿线地位提出质疑既有利亦有弊——本法院要求开展谈判的做法是对的——谈判是手段而不是最终目标——谈判应以法律为依据——应以放弃不利于谈判结果的既成事实来反映谈判的诚意.
1.
我同意本法院的裁定,大体上也同意其所作的推论.
咨询意见中有些显著要点应予阐明,我特别是因为这些要点而附上本意见书.
目前在以色列占领下的领土的国际法律地位2.
可以说在国际法中甚少提议得到近乎普遍的接受而且是以长久、固定和充实的法律意见为依据的,例如其中的一项提议是:以色列在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和加沙的巴勒斯坦领土内的驻留是属于军事占领,所以应遵守有关军事占领的适用的国际法律制度.
3.
为支持这一论点,不妨引述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一致通过或以绝大多数票数通过的大量决议,包括安理会各项具约束力的决定和其他决议,这些决议虽不具约束力,但产生法律效果,也是国际社会法律意见的一个可靠的记录.
在所有这些决议中,有关领土一成不变地被称为被占领领土;作为占领国以色列在这些领土的驻留以及它遵守或不遵守其对领土及其居民的义务均以人道主义法的保护规范为客观尺度予以判断.
4.
《日内瓦第四公约》缔约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保留它们的一致意见,即该公约",指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第四公约》,"在法律上适用于被占领领土".
5.
这也包括对以色列友好的国家在内的国家个别或集体所持的立场.
有关记录表明了这一点,如法国在其《书面说明》中所述:"以色列最初承认《日内瓦第四公约》的适用性:根据1967年6月7日占领当局发表的第1号令第35条,'军事法庭……必须适用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有关司法程序的条款.
若本令与所述公约发生抵触,应以公约为准……'"(P.
5.
)6.
最近以色列最高法院确认《日内瓦第四公约》对这些领土适用.
7.
"国际社会法律意见的一贯记录不能搁置一旁或置之不理",本法院已注意到这一点,不仅将法律意见重述一遍,而且主要根据对《公约》文本(第86-101段)的解释就《日内瓦第四公约》在法律上的适用性作出类似结论.
第101段申述如下:"最后,本法院认为在两个或三个争端国之间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下《日内瓦第四公约》可在任何被占领领土适用.
1967年武装冲突爆发时,以色列与约旦均为《日内瓦第四公约》的缔约国.
因此本法院认为《公约》适用于冲突前位于以色列与约旦所设的1949年停战分界线(绿线)以东并在冲突时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
对这些领土的先前的确切地位进行任何质询是没有必要的.
"8.
本法院避开了对这些领土的先前确切地位进行质询的做法,这是明智之举,这不仅是因为为了确定被占领领土的现有地位并申明《日内瓦第四公约》对其适用的目的进行这样的质询实在是没有必要的,而且因为这些领土的先前的地位对其作为被占领领土的现有地位并无任何影响,除非这些领土在被以色列占领时是属于无主地.
对于这一点不会有人认真提出反驳,因为这个不可令人置信的概念除了不符合作为前委任统治地的领土的地位之外,确实对当代没有任何适用性.
关于此点,本法院宣布了"两项据认为极具重要意义的原则:不兼并原则和促进[尚无能力管理自己]的民族的福利和发展的原则构成'文明世界的一种神圣的托管关系'"(西南非洲的国际地位,咨询意见,国际法院1950年报告,第131页).
9.
无论约旦对西岸的所有权有何法律依据,约旦提出的理由多半是:它的所有权是完全有效并得到国际承认的,并会指出它已断绝与这些领土的法律联系以利巴勒斯坦人自决,但客观事实仍然是:阻止实现该项自决权的因素是以色列的长久军事占领及其在地面制造既成事实的政策.
在这方面应当记得,不兼并原则并非于委任统治期结束后就不再生效,而是直至得到实现为止.
绿线的重要意义10.
当初绿线确实只是在一项协定中确立的停战线,协定明文规定其条款"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得被解释为当事方之间达成的最终政治解决办法","《协定》第五和第六条所订的停战分界线是由当事方商定的,不损及未来的领土解决或分界线,也不损及任一方对领土提出的权利主张"(咨询意见,第72段).
11.
以色列知名法学家于1967年战争前提出的论据是:《全面停战协定》是特殊的协定,事实上全面停战协定不仅是停战协定,而且未经安全理事会同意,不能予以更改.
这种论据不无讽刺意味.
无论停战线现今有何真正的重要意义,有两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1)引述阿瑟·瓦兹爵士的话,绿线"是判断以色列对非以色列领土的占领程度的一个起点"(CR2004/3,第64页).
这句话没有暗示绿线将成为永久的边界.
(2)试图贬低绿线的意义必然有利也有弊.
如果以色列对他国所有权提出质疑,就应想到他国也会对它的所有权及其所涉及的在分治决议范围外的领土提出质疑,确保安全的最终办法是使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法律关系稳定下来,而不是建造隔离墙.
谈判的作用12.
本法院提到圣地的悲惨状况.
"除非诚意执行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决议,特别是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这种状况才会结束.
安全理事会第1515(2003)号决议核准的路线图是为此目的开展谈判的最新努力.
"(咨询意见,第162段.
)13.
提倡者主张为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开展诚意谈判,这样做并无不妥之处.
应当记得,谈判确实促成了和平协定,这些都是正当有理的计划,受过时间的考验.
但任何人都不要忘记,谈判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其本身不能取代这个目的.
经谈判后国际义务包括对所有国家适用的义务的履行均不得受条件限制.
此外,有关路线图的问题,当考虑接受该项努力的条件时,相互义务和对等义务的产生是否需要一致意见确实是值得怀疑的.
即使如此,如果不想这些谈判产生非原则性的解决办法,就必须以法律为根据,诚意的谈判必须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即避免在地面制造既成事实,例如建造隔离墙,建造隔离墙只会损及谈判的结果.
奥恩·哈苏奈(签名)比尔根塔尔法官的声明1.
我认为法院本应行使自由裁量权,拒绝提出所请求的咨询意见,因此,我对法院决定受理此案有异议.
我对答复中其余各项投了反对票,但这并不是说,我认为以色列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修建隔离墙,从国际法角度看没有严重问题.
我认为以色列的做法是有严重问题的.
而且咨询意见中的许多看法,我是同意的.
不过,我不得不对法院就实质问题所作的裁定投反对票,因为法院并不具备作出这一全盘裁决所必需的事实依据;因此,法院本应拒绝受理这一案件.
我是以法院对"西撒哈拉"一案的意见为指南得出这一结论的.
在"西撒哈拉"案件中,法院强调,法院是否决定行使自由裁量权,对请它提出咨询意见的申请采取行动,要看"法院是否具备充足的信息和证据,使它能够就一切有争议的事实问题得出司法结论,而法院要根据与其司法特性相符的条件提出一种意见,就必须查明事实"(《1975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西撒哈拉案咨询意见》,第28-29页,第46段).
我认为,本案缺乏必要的信息和证据,使法院就实质问题作出的裁定没有说服力.
2.
法院认为,国际人道主义法,包括《日内瓦第四公约》和国际人权法,适用于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以色列必须忠实地遵守这些法律.
我同意这一结论.
我承认,隔离墙给生活在这一领土内的许多巴勒斯坦人造成了可悲的痛苦.
在这方面,我同意,防范恐怖主义所用的手段必须符合国际法各项有关规则,受恐怖主义之害的国家不得采用国际法禁止的措施反恐自卫.
3.
如能对所有相关事实进行彻底分析,作出的裁决很可能是,以色列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修建的隔离墙,几段甚至各段都违反国际法(见下文第10段),这是很有可能的,而且我准备作这种假定.
但是,考虑到以色列本土一直并继续反复遭受来自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的致命恐怖袭击,在不具备或不设法查明与以色列合法自卫权、军事必要性和安全需要有直接关系的一切有关事实,便对整个隔离墙得出结论,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
对于跨绿线发动的这些攻击的性质及其对以色列和以色列人民的影响,法院从未真正认真地加以审视.
联合国提供给法院的卷宗几乎没有触及这个问题,而法院的裁决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这些卷宗为依据的.
我不是说,进行这样的审视后,以色列就可以摆脱关于它正在修建的隔离墙部分或全部违反国际法的指控,而只是说,不经过这样的审视,作出的裁决在法律上没有可靠的依据.
我认为,法院如果能考虑到这些因素,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人道主义需要会更有利,因为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法院的咨询意见就会有可信度,而我认为,现在的意见缺乏可信度.
4.
这一点适用于法院的全盘结论,即整个隔离墙,只要修建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就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另一项裁定,即隔离墙的修建"严重妨碍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决权,因此这样做违背了以色列必须尊重这项权利的义务"(第122段).
我同意,巴勒斯坦人民享有自决权,而且有权得到充分保护.
然而,假设但未必同意这项权利与受理的案件相关而且受到了侵犯,但以色列的自卫权如果可以适用并合法援引,就必然会解除这方面的不法性.
见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第21条,其中规定:"如果某一行为是依照《联合国宪章》采取的合法自卫措施,则解除该国这项行为的不法性.
"5.
我认为,以色列的自卫权与本案是否相关,必须审视以色列本土遭受跨绿线致命恐怖袭击的性质和规模、以及就此种袭击而言,整个或部分隔离墙的修建是否必要,是否相称.
从法律角度看,在巴勒斯坦领土上修建的几段隔离墙经得起这种检验,而另几段隔离墙则经不起这种检验.
但不论得出哪种结论,都必须从各段具体的隔离墙、其防护需要和相关的地形考虑出发审视与这个问题有关的事实.
鉴于法院并没有掌握这些事实,它不得不得出了在我看来靠不住的结论,即合法或固有的自卫权对本案无关.
法院对此事的结论是:"《宪章》第五十一条……确认,一国在受到另一国武力攻击时,享有自卫的自然权利.
但以色列并未声称对它的袭击为一外国所为.
法院还指出,以色列对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实行控制,并如以色列自己所说,它认为促使它修建隔离墙的威胁来自领土之内,而非领土之外.
因此,案情与安全理事会第1368(2001)号和第1373(2001)号决议所针对的情况不同,因此以色列无论如何不能援引这些决议证明它关于行使自卫权的论点.
所以,法院的结论是,《宪章》第五十一条与本案无关.
"(第139段)6.
在这一结论中有两个原则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姑且不论法院为本案之目的是否不应而且实际上并未将巴勒斯坦比作一个国家的问题,《联合国宪章》在申明固有的自卫权时,并未将一国对另一国的武装攻击定为行使这项权利的前提.
《宪章》第五十一条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
此外,在法院援引的决议中,安全理事会表明,"国际恐怖主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并"再次申明《联合国宪章》所确认并经第1368(2001)号决议重申的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安全理事会第1373(2001)号决议.
)在2001年9月11日对美国发动的袭击仅一天后通过的第1368(2001)号决议中,安全理事会援引自卫权,号召国际社会打击恐怖主义.
在这两项决议中,安全理事会都没有规定这些决议仅适用于国家主体发动的恐怖袭击,决议中也没有隐含这种意思.
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
(见托马斯·弗朗克,"恐怖主义与自卫权",《美国国际法学报》,第95卷,2001年,第839-840页).
第二,以色列主张,对于跨绿线对其领土发动的恐怖袭击,以色列有权自卫,而且它这样做是在行使固有的自卫权.
在评估这项主张是否合法时,以色列对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实行控制的论点,不论"控制"概念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毫不相干,因为以色列受到来自该领土的袭击;袭击并非来自领土之外的论点,也不相干.
这是因为,只要法院接受绿线是以色列与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的分界线,只要作为袭击发源地的领土不是以色列本土的组成部分,上述论点就不相干.
因此,以色列遭到来自绿线另一侧的攻击,就可以对这种攻击行使自卫权,只要它所采取的措施在其他方面符合合法行使自卫权的要求.
要作出判断,或者说要确定以色列修建的隔离墙能否整个或部分经得起这种检验,就必须分析与必要性或相称性有关的一切相关事实.
法院对待自卫权的形式主义做法,使它得以回避本案的核心问题.
7.
法院裁定隔离墙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最后总结说:"总而言之,法院从掌握的材料看,并不信服以色列为隔离墙选定的走向是出于达到安全目标的必要性.
隔离墙、隔离墙的走向、以及与隔离墙有关的制度,严重侵害了在以色列占领的领土内居住的巴勒斯坦人的多项权利;因隔离墙的走向而侵害权利的行为,以军事上紧迫需要或国家安全或公共治安需要为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因此,以色列修建隔离墙,违反了它根据有关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文书承担的各种义务.
"(第137段)法院广泛引述了有关法律规定,作为此种结论的论据,并提出了隔离墙在某些区段造成痛苦的有关证据.
但法院在得出这一结论时,并未列举任何事实或证据,具体驳斥以色列关于修建隔离墙是出于军事紧迫需要或国家安全需要的主张.
法院的确表示,它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参阅了联合国秘书长提供的事实摘要和联合国其他报告.
但法院几乎没有触及秘书长报告后附的以色列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摘要,这同样是事实;而以色列的立场摘要与法院声称依赖的材料相抵触或对此种材料投下了疑云.
相反,法院所做的,无非是叙述隔离墙造成的伤害,并讨论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文书的各种规定,然后得出结论说,这项法律遭到了违反.
其中所缺少的,恰恰是审视事实,而通过审视事实,可能会发现,出于军事紧迫需要、国家安全或公共治安需要的论点,为何无法为整个隔离墙或者几段隔离墙的走向辩护.
法院说,它"不信服",但并未说明它为何不信服.
正因为如此,法院的这些结论不令人信服.
8.
诚然,法院援引的某些国际人道主义法不承认基于军事紧迫需要的例外情形.
因此,《海牙规则》第46条规定,私有财产必须得到尊重,不得加以没收.
在联合国秘书长报告一所载以色列政府法律立场摘要(A/ES/10/248,第8段)中,秘书长报告了以色列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其中一部分是:"以色列政府的论点是:土地的所有权并没有改变;对土地的使用、作物收成或土地受到的破坏给予了补偿;居民可以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要求停止或改变隔离墙的修建;而且居民身份没有变化.
"法院没有谈到这些论点.
虽然以色列的这些呈件对本案未必有决定性作用,但法院应加以处理,而且这些呈件事关以色列的另一项主张,即隔离墙是临时性结构.
法院注意到了这一主张,认为这是"以色列作出的保证"(第121段).
9.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四十九条第6款也不允许存在以军事或安全紧迫需要为理由的例外情形.
该款规定,"占领国不得将其本国平民之一部分驱逐或移送至其所占领之领土".
我同意,这项规定适用于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定居点的存在违反了第四十九条第6款.
据此,以色列为保护定居点正在修建的几段隔离墙自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此外,鉴于这几段隔离墙造成的飞地内和飞地周围受影响的巴勒斯坦居民显然遭受巨大苦难,我十分怀疑隔离墙在这方面能符合相称性的要求,因此无法视其为合法的自卫措施.
10.
最后谈一下我关于法院应行使自由裁量权拒绝受理这一案件的立场.
关于这一点,可以说法院缺乏与以色列修建隔离墙有关的许多相关事实,因为以色列未能提出此种事实,因此法院有理由几乎完全依赖提交给法院的联合国报告.
如果法院处理的不是请它提出咨询意见的申请,而是受理每个当事方都有责任证明其主张的争议案件,那么这种说法是成立的.
但这并不是适用于咨询意见程序的规则,因为在咨询意见程序中没有当事方.
一旦法院确认无需以色列同意此种程序,因为这一案件并不是针对以色列的,以色列不是案件的当事方,因此以色列在法律上没有义务参加程序或提交证据证明其关于隔离墙为合法的主张.
虽然对于以色列不提交必要的资料是否明智我自有看法,但这不是由我决定的问题.
但实际上以色列没有这种义务.
因此,法院不能从以色列不提供证据的角度得出任何不利于以色列的结论,也不能自己不充分调查问题,就设定法院掌握的信息和证据足以成为其全盘法律结论中每项结论的依据.
托马斯·比尔根塔尔(签名)埃拉拉比法官的个别意见联合国责任的性质和范围——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国际法律地位——历史调查——交战占领法,包括长期占领的现有状况、军事上的必要原则、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违反以及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利的普遍适用.
我想在开头就表示我完全地、毫无保留地赞同本法院的裁决和结论.
不过,我认为有必要行使规约第57条所赋的权利,附加我的个别意见,缕述咨询意见所载一些历史和法律方面的问题.
我不得不颇为勉强地从咨询意见第8段说起.
我认为,如拉克斯法官在《在尼加拉瓜境内对该国进行的军事和半军事活动(尼加拉瓜控告美利坚合众国)案的判决》的个别意见中所说的"每一位法官——这一点无需强调——有义务不偏不倚、客观、超然、公平无私和不带偏见.
"(《国际法院1986年报告》英文本第158页).
在这个咨询意见的整个考虑过程中,我尽量做到依照这项明智的准则行事,因为它涵盖的范围较每位法官依《国际法院规约》第20条所作的庄严宣告为广.
在这一个别意见中,我将讨论三个相关的要点:㈠联合国责任的性质和范围;㈡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国际法律地位;㈢军事占领法.
一.
联合国责任的性质和范围1.
必须强调的第一点是,有必要讲清楚联合国对巴勒斯坦的历史和法律责任性质和广泛的范围.
确实,本法院在下述主张中提到这种特别责任:"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源自巴勒斯坦的委托管理和分治决议……这项责任的表现在于通过许多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决议以及成立几个专门协助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附属机构.
"(咨询意见,第49段)我认为应在此强调的是五十年来在执行这项特别责任方面没有妥为顾及法律规则,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是其主要工作,但联合国从来没有一个机构请国际法院就其各自管辖范围内事项的复杂法律问题予以澄清.
过去基于政治权宜作出了各项影响深远的决定,但没有妥为顾及法律方面的要求.
就算在通过各项决定时,原想贯彻始终加以实施的意愿不久便烟消云散.
联合国各主管机构,包括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在内,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迄今有些决议的全部或部分仍未获执行.
联合国的特别责任源自1947年11月29日大会第118(II)号决议(下称分治决议).
在分治决议通过以前,在各主管的附属机构曾多次考虑关于请求提供咨询意见的建议,但始终没有通过任何请求建议.
这一事实本身赋予大会第十届特别紧急会议续会第23次会议通过的大会第ES-10/14(A/ES-10/L.
16)号决议所载的关于提供咨询意见的请求以相当大的重要性.
该项请求确实是联合国审议巴勒斯坦问题的一个里程碑.
在此至少应简单地回顾一下以往为征求国际法院的意见所作尝试的历史记录.
巴勒斯坦问题特设委员会第二小组委员会1947年的报告认识到必须澄清一些法律问题.
该报告第38段说:"本小组委员会仔细审查了叙利亚和埃及代表团所提出的法律问题,经过考虑的意见已收录在本报告.
不过,毫无疑问请最高国际法庭就这些棘手而复杂的法律和宪法问题提出咨询意见各方都认为是有利的和较符合要求的.
"(第A/AC.
14/32和Add.
1号文件,1947年11月11日,第38段)"棘手而复杂的法律和宪法问题"围绕着:"大会是否有权就特别委员会多数和少数成员提议的解决办法中的一个提出建议;联合国的任一会员国或会员国的任何集团未征得巴勒斯坦人民同意是否有权限执行任何所提议的解决办法"(同上,第37段)几个这类的提议得到审议.
结果没有通过任何提议.
在分治决议付诸表决前约两个星期,第二小组委员会的报告认识到:"拒绝将这个问题提交国际法院征求咨询意见等于供认大会决心作出某种取向的建议,而其理由并非这些建议符合国际正义和公平的原则,而是大多数代表想以某种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不论该问题的是非曲直,也不问当事各方的法律义务为何.
这种态度决无助于提高联合国的威信……"(同上,第40段)这些要求阐明澄清法律问题的合乎逻辑推理的清晰论点被置若罔闻,而在法律问题未予澄清的情形下,匆匆地付诸表决,在这方面,应当回顾分治决议完全赞同将"有关该决议规定的适用或解释的任何争端"提交国际法院.
"应当应当事双方中任一方的请求"提交国际法院.
用不着说,这一途径从来没有使用过.
因此,第10/14号决议所载的大会请求提供咨询意见是一个联合国机构首次就巴勒斯坦的任何方面征询国际法院.
本咨询意见作为一个里程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一定会增加它的法律价值.
二.
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国际法律地位2.
1我认为巴勒斯坦人民领土的国际法律地位(本咨询意见第70至71段)应予更全面的处理,对于大会所提出的这个问题.
进行一项历史调查是适切的,因为一方面可为了解巴勒斯坦领土的法律地位提供背景,另方面可突出大会特别和持续的责任.
若非与当前事件有关,这项调查似乎是学术性研究而已.
不过,现今是过去事件之总和所决定的,若要对今后有公平合理的关注对过去事件绝不能无精确了解.
特别是过往避开法律规则的一致作法已发生不只一次了.
出发点,即法律术语中的所谓关键日是国际联盟对大不列颠的委托管理.
如巴勒斯坦委托管理序言所说,联合王国承诺"代表国际联盟行使管理"委托管理必须根据《国际联盟公约》来思量.
受托管理国的主要责任之一是协助有关领土人民尽早实现自治和独立,该《公约》第22条第1款规定"此等人民的福利和发展构成人类文明的神圣信托".
该《公约》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主权和完全独立所施加的唯一限制是受托管理国的临时托管.
巴勒斯坦属于《国际联盟公约》第22条第4款之下A类委托管理的范围,该款规定:"以前属于土耳其帝国的若干社区已发展到了这样的阶段:可临时确认它们作为独立国家存在,但须由受托管理国提供行政咨询和援助,直至它们能够自己站立为止.
"依凭常识,一般的期望是当提供行政咨询和援助的阶段完毕,委托管理终了时,巴勒斯坦从该日起即为独立,因为《国际联盟公约》在法律上已承认它是一个临时独立的国家.
此外,该《公约》就以前属于土耳其帝国的社区与其他领土作一明确区分.
关于后者,它责成受托管理国全面管理巴勒斯坦领土,而不限于提供行政咨询和援助.
这些不同的安排可解释为该《公约》进一步确认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前土耳其领土的特别地区.
论及事实,巴勒斯坦问题特设委员会第二小组委员会提出的报告更加清楚明白地显示巴勒斯坦的地位.
该报告提出以下的结论:"巴勒斯坦人民自治的条件已经成熟,各方面都同意应尽早让他们独立.
此外,上述也涵蕴了大会没有权限建议除承认巴勒斯坦独立以外的任何解决办法,更加没有权限强制执行除此以外的任何解决办法.
"(A/AC.
14/32和Add.
1,1947年11月11日,第18段)该小组委员会还提出以下意见:"可回顾在《国际联盟公约》第22条之下设立A类委托管理,诸如巴勒斯坦的委托管理的目的是在于规定受托管理国的临时管理,而受托管理国的主要责任之一是协助受托管理领土人民尽早实现全面的自治和独立.
一般同意目前在巴勒斯坦这个阶段已到来,不仅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而且受托管理国自己也同意委托管理应予结束,对巴勒斯坦独立应予承认.
"(同上,第15段)2.
2.
法院于1950年(西南非洲的国际地位,咨询意见)和1971年(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276(1970)号决议继续留驻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对各国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审议了委任统治地的法律性质,并为如何界定前委任统治地的法律地位制定了概念宗旨和法律参数.
法院法官的意见强调了国际社会的特殊责任.
应当注意的是,关于委任统治制度的构建,法庭认为:"有两项原则被视为是至高无上的:不得吞并原则和这些人民的福利和发展构成'文明之神圣任务'的原则"(《1950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31页;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明).
法院在1950年阐明的这两项基本原则适用于还没有获得独立的所有前委任统治地.
直到今天它们对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仍然有效.
该领土不得遭到武力吞并,而作为"文明之神圣任务",巴勒斯坦人民的前途是联合国的直接责任和关注.
2.
3.
应当铭记,规定委任统治的巴勒斯坦领土分治的大会1947年11月29日第181(II)号决议除别的以外,要求采取下列步骤:㈠1948年8月1日以前结束委任统治;㈡建立两个独立国家,一为阿拉伯国和一为犹太国;㈢从分治决议通过起到"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和犹太国"的这段期间"应为过渡时期".
1948年5月14日,犹太国宣布独立.
以色列宣布这是"根据[以色列的]天赋权利和历史权利"和基于"联合国大会决议的权威".
巴勒斯坦阿拉伯国的独立迄今尚未实现.
在建立两个国家之前"应有一段过渡时期"是由大会在其职权范围内决定的,因为具有法律效力和产生了法律后果,对所有会员国都应具有法律约束力.
此一结论得到法院判例的支持.
法院在纳米比亚一案中认为,一旦大会宣布委任统治结束,"'南非即无权管理该领土'……这并非对事实的认定,而是制定一种法定情况.
因为作出下列假定将是不正确的,即:由于大会原则上被赋予的是提出建议的权力,它就不得对在其职权范围内的特定案例通过作出决定或附有执行计划的决议(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276(1970)号决议继续留驻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对各国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1971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50页,第105段.
)此外,法院此前在某些经费一案中认为,大会根据第十八条对"重要问题"作出的决定,"具有处置效力"(联合国的某些经费(《宪章》第十七条第2项),咨询意见,《1962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63页).
因此,经大会"在其职权范围内"通过的大会决议具有法律效力早就在法院的判例中得到充分确认.
据此,它认为,下两项结论看来是绝对必要的:(a)联合国有义务着手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这项事实使得大会的特殊法定责任在这项目标实现之前不得终止;(b)分治决议中提到的过渡时期成为委任统治的法律联结点.
过渡时期这个概念把委任统治所阐明的各项责任维持到现今,这是政治现实,而非法律拟制,得到了法院法官意见的支持,特别是关于前委任统治地是"文明之神圣任务"和"不得遭到吞并".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各个方面的一系列决议提供了确凿的证明,证实过渡时期这一概念得到了普遍赞同,尽管没有明白写出来.
2.
4.
必须审视关于尊重被占领领土领土完整和撤出该领土的以色列约定承诺,否则就无法充分体会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法律地位.
撤退和领土完整的强制命令是以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作为基础.
该决议普遍被视为是公正、可行和全面解决的基础.
第242号决议是一项涉及多方面的决议,论及阿拉伯-以色列争议的各个方面.
我仅着重指出第242号决议有关领土的方面:该决议载有界定1967年被占领领土的范围及地位和确认该被占领土必须"解除占领"的两项基本原则:第242号决议强调,不准许以战争获取领土,从而禁止吞并1967年征服所占领的领土.
它要求以色列部队撤出在冲突中占领的领土.
1973年10月22日,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338(1973)号决议,其中重申必须执行第242号决议的"所有部分"(1973年10月22日S/RES/338,第2段).
继第242号决议之后,以色列又作出了关于终止以色列军事占领,同时维护西岸和加沙地带领土完整的若干承诺:(a)1978年7月17日《戴维营协议》,其中以色列同意,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42号决议的所有部分构成和平解决与其邻邦冲突的基础.
(b)1993年9月13日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签署的《奥斯陆协定》,这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一项双边协定.
《奥斯陆协定》第四条规定"双方视西岸和加沙地带为单一的领土单位,在过渡时期将维护其完整性".
(c)1995年9月28日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签署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关于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临时协定》,其中重申在过渡时期尊重该领土完整和地位的承诺.
此外,第三十一条第(7)款规定"在永久地位谈判获得成果之前,任一方不得启动或采取将改变西岸和加沙地带地位的任何步骤".
据此,以色列承诺履行下列义务:㈠依照第242号决议撤出;㈡尊重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领土完整;和㈢不采取将改变西岸和加沙地带地位的任何步骤.
这些承诺是约定的,对以色列具有法律约束力.
2.
5.
然而,尽管国际上普遍禁止吞并被占领领土、法院法官关于前委任统治地法律性质的意见和明确违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承诺,以色列总理在2004年4月14日致函美国总统.
该函随附的一份《脱离接触计划》不得不被诠释为反映以色列吞并巴勒斯坦领土意图、具有权威性的文件.
《脱离接触计划》规定:"在西岸,显然有些地区将成为以色列国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城市、市镇和乡村、保安地区和设施,以及以色列特别关注的其他地方".
关于撤出和尊重西岸和加沙地带完整和地位的明确承诺在法律上禁止以色列侵犯或改变巴勒斯坦领土的国际法律地位.
构筑围墙、连同其选定的路线和相关的法规必须参照《脱离接触计划》来理解.
如果假定构筑围墙的构想旨在吞并巴勒斯坦领土,在西岸"将成为以色列国一部分"的"城市、市镇和乡村",这是不会错的.
以色列总理的信件是在提出咨询意见之前两个多月送出的.
法院对确定围墙的特性达成了正确结论,它认为:"围墙的构筑及其相关法规创造了在当地很可能变为永久存在的"既成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以色列对该围墙的官方说法如何,都不啻是事实上的吞并"(咨询意见,第121页).
它认为,此一定论应当已经反映在答复内,并申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不得遭到吞并.
我认为,提到以色列总理函件及其的言下之意和强调该函意图作出的宣示都违背了以色列的义务和同国际法背道而驰,也将是适当的.
三.
交战国占领法大会请本法院就"占领国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构筑隔离墙有何法律后果"紧急发表咨询意见(A/RES/ES-10/14(A/ES-10/L.
16)).
这一请求的重点围绕着交战国占领法问题.
如前所述,我赞同咨询意见中的理由陈述和结论.
但是,我感到不得不对下列几点进行强调和阐述:(a)延长占领;(b)军事需要的范围和限制;(c)严重破坏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以及(d)自决权.
3.
1.
《宪章》第二条第四款所载的禁止使用武力无疑是20世纪出现的最重要的原则.
它被普遍认为一条绝对法原则,是一条不允许任何减损的强制性规范.
本法院在第87段回顾了《关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该宣言对第二条第四项提供了一致同意的解释.
该宣言"强调'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取得之领土不得承认为合法.
'"(咨询意见第87段).
非法行为不能产生法律权利(侵权行为不得产生权利)这条一般原则是国际法广泛承认的.
以色列占领已持续近40年.
占领,无论其期限有多长,都会造成无数的有关人、法律和政治的问题.
在解决延长的交战国占领问题上,国际法寻求"在冲突结束前的原地待命".
没有人会低估延长的占领期间会产生的固有困难.
延长占领会损伤适用的规则,但是,无论占领期限多长,交战国占领法必须得到完全尊重.
克里斯托弗·格林伍德教授提供了正确的法律分析,我对他的分析表示赞同.
他写道:"然而,没有任何情况表明,国际法仅仅因为一个占领国占领的时间长,更不用提因为没有一套似可取代有关规定的法典而允许一个占领国无视条例或公约的规定;没有情况表明,国际社会愿意将无限行动权委托给占领者.
"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均遭到难以描述的痛苦.
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均有权生活在和平与安全中.
安全理事会第242号决议确认"该地区每一国家……在安全及公认之疆界内和平生存、不受威胁及武力之行为"的权利(S/Res/242(1967),第一条㈡段).
这些是神圣的对等权利,它们引起神圣的法律义务.
保证和享受安全权利适用于巴勒斯坦人,也适用于以色列人.
一方不能以另一方为代价而获得安全.
同样,权利和义务是对应的,双方有对等义务,严格认真尊重和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则,尊重平民的权利、尊严和财产.
双方有法律义务,按照保护平民人口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相同标准来衡量其行为.
本法院在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案件中非常明确地裁定,"构成人道主义法体系的各项文书的主要原则如下.
第一项原则的目的是保护平民和平民目标,并规定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的区别;各国绝不可把平民作为攻击的目标,因此绝不得使用不能辨别平民目标和军事目标的武器.
根据第二项原则,禁止对战斗人员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因此禁止使用对他们造成这种伤害或不必要地加重他们痛苦的武器.
根据第二项原则,各国并非毫无限制可以自由选择使用武器.
"(咨询意见,1996年国际法院判例汇编㈠,第257页,第78段).
占领遭到武装抵抗这一情况不能用作无视被占领领土内的基本人权的借口.
纵观历史,占领总是一直遭到武装抵抗.
暴力滋生暴力.
这一恶性循环同样严重地影响着占领者和被占领者的每一行动和每一反应.
理查德·福尔克教授和伯恩斯·韦斯顿教授当贴切地捕捉了这种困境,他们写道:"占领者面临的对其安全的威胁……主要和特别是最近阶段产生的,这是长期公然未能限制占领者和结束其占领恢复居民的主权权利造成的.
以色列占领实质性地侵犯了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占领本身就是一个威胁领土行政当局安全的燃烧剂,从而导致越来越多地依靠残暴做法来恢复稳定,结果对巴勒斯坦人的挑衅更大.
实际上,以色列占领政权本身的非法性引起了一个抵抗和镇压的上升式螺旋,在这些条件下,所有对道德和原因的考虑都确认人民固有的抵抗权利.
这种抵抗权利是主权特征和确保对居民的人道主义保护的优先地位引起的基本法律权利所隐含的法律必然结果.
"我衷心赞成福尔克教授和韦斯顿教授所表达的观点,双方违反人道主义法的基本规则源于"以色列占领政权本身的非法性".
占领是一种非法和临时状况,是整个问题核心所在.
唯一可行的结束严重侵犯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办法是结束占领.
安全理事会一再呼吁结束占领.
1980年6月30日,安全理事会重申"绝对必须停止以色列自1967年以来对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的继续占领"(S/Res/476(1980)).
尽管有着这一响亮的呼吁,但巴勒斯坦人民仍然在高压手段的长期占领下日夜受折磨.
3.
2.
本法院在第135段中驳回了可援引军事需要原则作为修建隔离墙的理由的论点.
本法院裁定:"不过,本法院面前的材料不能使它信服,即以色列违反《日内瓦第四公约》第53条进行的破坏是其军事行动所绝对必要的".
(《咨询意见》,第135段.
)我完全同意这一裁定.
如果以色列已经证明本国可以查明没有其他替代方法可以保卫自身安全,则把军事需要和军事急迫要求作为修建隔离墙的理由似可商榷.
本法院指出,以色列未能表明这一点.
以色列认为,修建隔离墙是一种安全措施.
另一种观点认为,可以把军事需要原则作为与修建隔离墙过程同时出现的无正当理由的破坏和拆除行动的理由.
对此两种观点必须加以区分.
军事需要如果适用,仅仅延伸至前者而非后者.
在建设隔离墙及其相关制度过程中给平民住户造成的巨大损害和伤害,显然是国际人道主义法所禁止的.
在修建隔离墙的同时毁坏家园、拆除基础设施及剥夺土地、果园和橄榄园,是无法以任何借口开脱的.
100000多名平民非战斗平民已经遭到不幸,变得无家可归.
交战占领法中载有一些条款,使占领国拥有有限的军事需要和安全余地.
这是一个事实.
和一般准则的每个例外情况下一样,对此必须以严格的方式加以解释,以便保持基本的人道主义考虑.
秘书长于2003年11月24日向大会报告说,他承认"以色列有权利也有义务保护其人民免受恐怖主义袭击.
然而,履行这种义务的方式不应违反国际法.
"(A/ES-10/248,第30段.
)本法院的判例是连贯一致的.
在1948年"科孚海峡"案中,本法院认为人道主义法规则的核心和结构是"人类的基本考虑,在和平期间比战争期间更加迫切"("科孚海峡"案,初步反对意见,《判决书》,1948年,《1947年-1948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22页).
在关于"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一案中,本法院裁定:"所有国家均须遵守这些基本规则,无论他们是否已批准载有这些规则的公约,因为这些规则构成不得违反的习惯国际法的原则"("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1996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㈠,第257页,第79段).
总之,我得出的结论与MichaelSchmitt教授的一样,即:"军事需要在这一事例内起到的作用是禁止军事上不必要的行为;这是一项限制原则,而不是授权原则.
在法律意义上,军事需要不能成为任何行为的理由.
"本法院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本法院裁定:"鉴于它所掌握的资料,本法院不相信,沿所选择的路线修建隔离墙是以色列保护其利益,对抗严重迫切危险的唯一办法,而以色列却援引此点为修建该隔离墙辩解.
"(《咨询意见》,第140段.
)3.
3.
此外应该回顾,两名特别报告员JohnDugard和让·齐格勒宣读的报告明白无误地表明,以色列作为占领国犯下了严重违法行为.
我认为,与修建隔离墙有关的附带措施中侵犯平民非战斗人员权利的行为的模式和程度,都属于"无军事上之必要而以非法与暴乱之方式对财产之大规模的破坏与征收"(《日内瓦四公约》,第147条).
在向平民提供保护方面,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则自缔结各项日内瓦公约和议定书以来已经逐步发展.
我提出观点认为,本法院通过把修建隔离墙过程中犯下的毁坏行为定为严重违法行为,将能够促进战时法规则的发展.
3.
4.
本法院突出强调了自决权在我们当今世界中的至关重要性,并在第88段中裁定:"的确,本法院曾申明,人民的自决权利今天已成为一项普遍适用的权利(见东帝汶案(葡萄牙诉澳大利亚),判决书,《1995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02页,第29段).
"此外本法院指出,为隔离墙选定的路线及采取的措施"严重妨碍了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治的权利,因此,以色列违反了它尊重这项权利的义务"(《咨询意见》,第122段).
我完全支持这一仅限于推理的具有法律权威的判词.
我认为,严重妨碍巴勒斯坦人民行使普遍适用的权利的措施给所有国家带来的法律后果应该列入本法院的答复.
结论我现在准备提出最后意见.
这是对未来的思考.
本法院在第162段中作出了评述.
法院认为:"只有本着诚意执行安全理事会各项有关决议,特别是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才能结束这种可悲的局面"(《咨询意见》,第162段).
本法院这一裁定反映了国际社会长期以来未能实现的一个崇高目标.
自1967年11月22日以来,所有努力的目的都是确保执行获得一致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
在长达37年的时间里,对安全理事会第242号决议既有赞誉,也有诋毁.
但诋毁者和支持者都同意,该决议条款中的平衡是建立可行及公正和平的唯一可接受的基础.
安全理事会在1973年武装冲突之后通过了第338(1973)号决议,呼吁各方在停火后立即开始"执行第242(1967)号决议所有各部分"(此处有所强调).
这些决议产生的义务是非常重要的结果义务.
这些义务是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的义务,其中每一方的义务构成另一方义务的存在理由.
把这种结果义务转变为简单的手段义务,从而使之局限于谈判过程,这在法律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
任何篡改这类庄严的义务的企图都不会有助于实现以稳固的法律和正义根基为基础的结果.
建立安全理事会第242号决议提出的"公正、持久的和平",需要双方充分履行各自的义务.
《咨询意见》作为有关巴勒斯坦问题意义深远的司法行政的第一次切实表现,应该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希望这将为指导及指引中止已久的对公正和平的追求提供推动力.
纳比勒·埃拉拉比(签名)小和田法官的个别意见咨询程序中行使管辖权的司法适当性问题,是本法院依职权必要时应审查的一个因素.
——在请求标的上存在双边争端,重要之处并非阻碍本法院行使管辖权,而是应予考虑的一个因素,以确定本法院如何处理请求标的,而不触及处理当事国争端本身的问题.
——对于与双边争端明显相关的案件,本法院处理行使司法适当性的问题,不仅针对是否应允提出咨询意见的请求这个问题,而且要考虑到如何行使管辖权,以确保司法公正性,包括任命专案法官问题——注重司法公正,必须在评估事实和法律两方面,都公正对待标的所涉双方的立场——谴责双方令人痛心地相互无休止针对无辜平民滥用暴力,应该成为本法院咨询意见的一个重要部分.
1.
我同意本法院咨询意见中关于先决问题(管辖权和司法适当性)和所涉实质问题案情核心的许多论点.
然而,我不仅对咨询意见的某些具体要点有不同意见,而且对本法院处理此案的方式,也有一些严重保留.
我承认,本案情节有非常和独特之处,并不完全属于本法院的职责,本法院如此处理此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我感到有义务阐明我的立场,指出本法院处理本案方式上有问题的一些方面.
2.
在关于管辖权和行使这种管辖权的司法适当性等先决问题上,本法院得出的结论主要基于书面和口头审理程序参加者所作的陈述.
第24至67段阐述了本法院得出这些结论的理由.
对这些理由本身,我本人并无重大不同意见.
然而,我认为,管辖权问题,特别是司法适当性问题,是本法院依职权必要时应审查的问题,目的是不仅确保在法律方面正确,而且确保本法院作为对具体案件行使管辖权的司法机构,在司法政策上也是适当的.
这就意味着,本法院必须深入研究与案件审理相关的本案特殊情节的各个方面,必要时超出参加者辩论的范围.
至少这是我的想法.
本案中这些方面之一是咨询意见请求标的存在双边争端的影响.
3.
最初的《常设国际法院规约》对于咨询管辖权并无明文规定.
只有《国际联盟盟约》第14条规定"法庭对行政院或大会提交的任何争端或问题,也可提供咨询意见".
正是这项规定,后来成为常设国际法院履行咨询职能的法律依据.
4.
虽然从国际联盟缔造者的意图看,这项规定的主旨似乎并不完全清楚,也不一致,但是,从《盟约》立法史可以清楚地看出,从一开始,常设法院咨询职能的目的,就在于协助和平解决提交国际联盟行政院的具体争端,特别是在《盟约》第12条至第16条规定的程序方面.
5.
1922年常设法院成立后起草《法庭规则》时,有四条(第71条至第74条)专门规定咨询程序.
这四条确认了新法庭咨询职能的"司法特性",并为以后将咨询更充分地纳入诉讼程序铺平了道路.
确实,1927年9月2日任命的[常设国际法院]委员会的报告做了如下陈述:"《规约》并未提到咨询意见,而完全由本法院处理有关咨询意见的程序.
本法院在行使这一权力时,慎重而审慎地将咨询程序纳入其诉讼程序,产生的结果充分证明这一行动是合理的.
国际法院今天作为法庭享有如此声誉,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大量的咨询工作以及处理咨询工作采取的司法方式.
实际上,在当事国发生争执的情况下,诉讼案件与咨询案件的差别微不足道.
主要差别是案件提交本法院的方式,事实上甚至这种差别也会消失,例如突尼斯案件.
所以,认为咨询意见不具有约束力,理论上如此,实际上并非如此.
"(《常设国际法院案例汇编》,E辑,第4号,第76页)6.
事实上,在"东卡瑞立亚地位"一案,常设法院拒绝行使管辖权提出所要求的咨询意见(《常设国际法院案例汇编》,B辑,第5号),决定的主要理由恰恰是这一点.
提交法院的具体问题是"[1920年]《芬兰和俄罗斯和平条约》第10条和第11条和所附关于东卡瑞立亚自治的《俄罗斯代表团声明》"是否"构成具有国际性质的保证,使俄罗斯对芬兰承担了履行其中各项规定的义务"(同上,第6页).
换言之,芬兰要求国际联盟受理的事项,其背景是芬兰与俄罗斯之间的争端.
行政院在决议中表示"如果两个有关当事国同意,愿意审议该问题,以得出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同上,第23页).
然而,爱沙尼亚政府请求俄罗斯"同意依照《盟约》第17条将问题提交行政院"(同上,第24页),遭俄罗斯政府拒绝,芬兰政府再次将问题提交行政院,正是出于这些情况,行政院才决定请求提出有关咨询意见.
7.
在这种背景下,常设法院做了如下陈述,澄清其立场:"如果请求提出咨询意见的问题,与形成国家间未决争端事由的问题有关联,是否可以不经当事国同意,将其提交本法院,对此已经做了一些讨论.
本案没有必要再讨论这个问题.
"(《常设国际法院案例汇编》,B辑,第5号,第27页;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明)在阐明这一观点后,常设法院继续说:"可以从上文得出结论,请求本法院提出的意见与芬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实际争端有关联.
由于俄罗斯不是国际联盟成员,根据《盟约》第17条,此案属于这样的案件……接受《盟约》的国际联盟成员,承担的义务源于有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这个部分的条款.
对于不是国际联盟成员的国家,情况则完全不同.
这些国家不受《盟约》约束.
因此,这些国家与国际联盟成员之间的争端,只有经其同意,才能提出依照《盟约》规定的办法解决.
然而,俄罗斯从未表示同意.
"(同上,第27页至第28页;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明)从这段文字可以清楚地看出,常设法院拒绝在东卡瑞立亚案件行使管辖权,其主要理由不是存在涉及请求标的当事国之间的争端,而是争端的一个当事国不同意"依照《盟约》规定的办法解决".
8.
当国际法院作为国际常设法院的制度继任者重新组建并且作为主要司法机关纳入联合国系统时,新的《国际法院规约》并没有对它的职能或这方面的构成作出大幅度变动.
从那时以来,本法院按照其前任——国际常设法院在上述国际联盟时代制定的路线,履行了本法院第二位但同样重要的职能——咨询职能.
9.
鉴于这种背景,并根据本法院成立以来在对咨询程序的管辖权和实施咨询程序的适当性问题上多年积累的判例法,我认为,本法院对本案的结论是正确的,即双边争端的存在不应阻止本法院按请求提出咨询意见.
10.
虽然存在双边争端不应阻止本法院作为司法适当性问题对咨询程序行使管辖权,但是我认为,存在双边争端应当作为本法院确定对咨询程序行使管辖权的程度和方式时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在这方面,我认为本法院对目前和过去的咨询意见案例的类比过于轻率,特别是关于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276(1970)号决议的规定继续在纳米比亚(西南非洲)留驻对各国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案例.
鉴于本案的复杂性,我认为,采用这种把过去先例产生的原则自动适用到目前情况的方式没有很充分的理由.
11.
尤其在纳米比亚案例中,构成请求提供咨询意见依据的争论要点是,"不顾安全理事会第276(1970)号决议,……南非继续在纳米比亚留驻……所产生的法律后果".
尽管提出请求所用的语言相类似,但是那项请求的依据同目前请求的依据大不相同.
在纳米比亚案例中,对于联合国采取行动,终止南非对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联合国请本法院对这项行动的法律意义及其对南非在这块领土上的地位的法律影响提出咨询意见.
如果存在法律争议或争端,那恰恰是联合国和有关国家间的法律争议或争端.
相比之下,目前情况的争议之处主要在于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对巴勒斯坦采取行动造成的状况.
不可否认,本案与这种情况直接相关双方存在根本的法律争议或争端,同时,本法院正确地指出,由于联合国的合法利益理所当然地牵涉其中,它也涉及联合国和以色列之间的问题.
12.
这当然不是说本法院应为此拒绝对本案行使管辖权.
然而,这的确意味着应该审查司法适当性问题,同时考虑到这种现实,并基于更恰当案例的法理.
我认为与本案最接近的可能是西撒哈拉问题咨询意见,这指的是该案有关各方之间明显存在根本的法律争议或争端.
然而,即使这项案例也不是一项完全可比的先例,本法院也无法从中得出结论.
在西撒哈拉案中,本法院表示:"大会的目的不是以请求提供咨询意见的方式向本法院提交一项争端或法律争议,以便大会将来可以根据本法院的意见,为和平解决争端或争议而行使权力和职能.
请求的目的完全不同:要从本法院获得大会认为有助于适当行使该领土非殖民化职能的意见".
(《1975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26页和第27页,第39段;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明)在本案中,可以推想,大会要求提供咨询意见的目的,似乎不是本节两个实例中的后者,而是前者.
13.
因此,我承认本案双方存在根本的法律争议或争端这个不可否认的方面,并明确牢记这个方面,但是我要表明,本法院行使其无疑拥有的管辖权,其司法适当性的严格检验,这不是在于这项要求是否同存在具体法律争议或争端有关,而是在于"作出答复的作用是规避这样的原则,即一国没有义务不经其同意允许其争端提交司法解决"(《1975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25页,第33段;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明).
换句话说,司法适当性的重要标准归根结底应在于,本法院确保以咨询意见形式答复所请求的主题,不应等同于对目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毫无疑问存在的根本性的具体双边争端问题作出裁定.
14.
上面的推理使我得出下列两个结论.
一,本案涉及考虑双边争端的方面.
不应阻碍本法院行使管辖权.
二,不过,这个事实会对本法院处理本案的整个程序产生某些重要影响,就是说,在目前的咨询程序中,本法院应当着重提出请求机关——大会履行关于该问题的职能时所需要和有用的客观法律裁定,而不是对双方争端的主题作出裁决.
15.
应当回顾,即使本法院决定履行其咨询职能时,也一贯声明其立场,即应当切实遵守"其各项司法特征的要求".
因此,本法院在西撒哈拉案中宣布:"《规约》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本法院提供咨询意见的权力,该款相当宽容,根据这项规定,这种权力具有酌处性.
象常设国际法院一样,国际法院行使这种酌处权时一直遵循一项原则,即作为司法机关,必须在提供咨询意见时切实遵守其各项司法特征的要求"(西撒哈拉问题咨询意见,《1975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21页,第23段;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明).
16.
对于作为司法机关的本法院,其中一项要求是,在有关各方立场和利益有分歧的情况下,保持咨询程序中司法的公正性.
换句话说,必须强调,本法院在咨询问题上的酌处权并不限于是否应允一项要求,它还包括咨询程序问题.
这项要求对于本案特别重要,因为我们接受上文阐述的不可否认的事实,即本案的确与根本性具体法律争议或争端相关,尽管我自己的结论是,本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是适当的.
17.
《国际法院规约》第六十八条规定"法院执行关于咨询意见之职务时,并应参照本规约关于诉讼案件各条款之规定,但以法院认为该项条款可以适用之范围为限".
《国际法院规则》第四部分(第一百零二条至一百零九条)阐明了《规约》的这项规定.
在目前情况下特别相关的是第一百零二条第三款,其中规定"当请求对两国或多国实际存在的法律问题提出咨询意见时,应适用《规约》第三十一条以及本《规则》中关于适用该条款的规定".
18.
在纳米比亚案例中,南非根据这项规定,申请任命一名专案法官,参加该案的审理.
本法院在1971年1月29日的命令中决定拒绝这项申请(《1971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2页),但是,在这一点上的反对意见十分雄辩(同上,第308页;第324页).
相比之下,本法院在西撒哈拉案中采取了不同立场.
在答复摩洛哥关于根据《法院规则》第八十九条(即目前的第一百零三条)任命一名专案法官的请求时,本法院认为摩洛哥有权在诉讼中选择一名专案法官.
(而毛里塔尼亚提出的类似请求被拒绝.
)(《1975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6页).
19.
如果一国的请求书声称"咨询意见的请求是就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间实际上悬而未决的法律问题提出的",任命一名专案法官的程序即予启动(《法院规则》,第102条).
我认为,鉴于上述先例,在本案中具有特殊地位的以色列本应有理由请求选择一名专案法官.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以色列没有选择这样做.
如果它这样做了,法院在司法过程中必须维持公平的任务会大大得到帮助.
不用说,这样做会使情况复杂化,因为,为《法院规约》的目的,争端的另一当事方巴勒斯坦是一个不被承认为国家的实体.
如果一个直接相关当事方能够任命一名专案法官,而另一方却不能,会发生什么情况.
从这个角度可以对司法过程的公正性提出异议.
我不是要对这个棘手的假设问题提出自己的结论,但我希望指出的是,这个因素是本案的一个重要方面,法院在决定根据本案的特殊情况,法院是否应行使和如何行使其管辖权的司法正当性问题时应可加以考虑.
20.
尽管如此,惯例是,即使在诉讼案件中,一个当事方缺席本身并不剥夺法院的审理管辖权(《法院规约》,第五十三条),但法院必须维持其作为法院在司法方面的公平性.
因此,就应证明和适用的法律问题而言,法院在关于"渔业管辖权"的案件中这样说:"本法院……作为一个国际司法机构,被认为已对国际法作出司法认知,因此,和任何其他案件一样,必须在《法院规约》第五十三条下的案件中主动考虑可能与解决争端相关的所有国际法规则.
既然法院本身有义务根据特定案情确定和适用相关法律,就不能责成任何当事国确定或证明国际法规则,因为法律属于法院的司法知识范围.
"(《1974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81页,第18段.
)就应澄清的事实的问题而言,法院在"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实质问题)"一案中说:"[本法院]原则上没有义务只考虑当事国正式提交的资料(参考"巴西贷款",《常设国际法院案例汇编》,A辑,第20/21号,第124页;"核试验",《1974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263-264页,第31、32段)"(《1986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25页,第30段).
法院还说:"本法院……因此实现了平衡.
一方面,法院应该知道当事国双方的看法,无论这些看法的表达形式如何.
此外,正如本法院在1974年指出的,在一个当事国不出庭的情况下,'本法院特别有义务确信它已掌握所有可获得的事实'("核试验",《1974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263页,第31段;第468页,第32段).
另一方面,法院必须强调争端当事国的平等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是法院的基本原则.
"(《1986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25-26页,第31段).
21.
本法院的基本立场所依据的这顶原则既应适用于诉讼程序,也应适用于咨询程序.
的确,甚至可以争辩:这项原则更适用于咨询程序,因为咨询程序不同于诉讼程序,从法律上无论如何不能说,"缺席当事国放弃驳斥对方的事实指控的机会("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尼加拉瓜诉美利坚合众国)",《1986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25页,第30段).
在咨询程序中,任何国家,无论是多么相关的当事方,都没有义务到本法院陈述其论点.
22.
就这个与本案有关的事实和信息问题而言,正如咨询意见所说毫无疑问的是:"法院有秘书长的报告以及他向法院提交的大量档案材料,其中不仅有关于隔离墙走向的详细资料,并且有关于隔离墙对巴勒斯坦居民的人道主义和经济社会影响的资料"(咨询意见,第57段).
法院的确有大量资料,特别是关于建造隔离墙的人道主义和社会经济影响的资料.
其真实性和可靠性没有受到质疑.
不过,似乎欠缺的是解释以色列方面的情况的资料,特别是实际计划和实施的隔离墙建造工程为什么是必要和恰当的.
23.
我认为,情况好像就是这样,尽管法院断言,"以色列的书面陈述虽然只限于管辖权和司法适当性问题,但也提出了关于其他问题的意见,包括以色列在安全方面的忧虑,同时载有相关的"(咨询意见,第57段).
事实上,咨询意见本身对以色列关于这个问题的论点所作出的评论好像证实了我的看法.
以色列争辩说,隔离墙的唯一目的,是使之能够有效地打击从西岸发动的恐怖袭击,或者像秘书长的报告所说,"阻止从西岸中部和北部渗入以色列"(咨询意见,第80段).
但是,法院在咨询意见第137段中只是说"根据已掌握的资料,[它]并不相信,以色列为隔离墙所选择的特定路线是实现其安全目标所需要的"(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明).
我认为明显的是,法院在此实际上承认没有以色列方面关于这点的详尽资料,而不是根据以色列可能就这点提供的资料驳回以色列的论点.
在咨询意见第140段中,法院也仅根据"其面前的资料"表示不相信"沿所选择的路线修建隔离墙是以色列保护其利益,对抗严重迫切危险的唯一办法,而以色列却援引此点为修建该隔离墙辩解".
24.
我提出这点的目的不是要质疑这些论断的事实准确性,或对根据法院现有文件和资料得出的结论提出异议.
事实上,似乎有理由得出总体结论:在程序中提供和取得的大量证据证实,修建隔离墙造成严重的政治、社会、经济和人道主义影响,构成违反以色列为缔约国的各项国际文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的行为.
此外,这些影响之巨大程度使我同意接受这样的论点:不可能以任何"军事迫切需要"的理由,作为根据严格的相称性条件排除该行为的不法性的合理依据,即使是在有已证明事实的支持的情况下.
25.
不过,这不是要点.
重要的是,上面节录的咨询意见证明了我的看法,即法院一旦决定对本案行使管辖权,就应十分小心,不仅要确保结果客观公平,而且要保证法院被视为在整个程序中保持公平,无论我们最后会得出什么结论.
26.
提交给本法院征求其咨询意见的问题是关于"以色列建造隔离墙造成何种法律后果"(大会第A/ES-10/L.
16号决议)这个具体问题,只涉及以色列建造隔离墙这个具体行动.
不过,不言而喻的是,以色列建造隔离墙并非发生在真空中,这是围绕着由来已久的中东和平问题的整个局势的一个部分,甚至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
27.
这当然不能改变以下事实:关于征求咨询意见的要求侧重的是一个具体问题;本法院应当处理这个具体问题,而且只处理这个问题,而不是将处理范围扩大到与中东和平有关的更大问题上,包括与所涉领土的"永久性地位"有关的问题.
但是,为了全面了解建造隔离墙这个具体问题的客观真相,由于此案含有直接卷入的双方之间争端所包括的因素,为了确保此案的司法公正,看来极为重要的是,本法院在审查交给其处理的这个具体问题时,平衡地考虑到构成建造隔离墙的整个背景的全局情况.
28.
实现中东和平的一个无可争议的前提是,必须由以下这两项并行的原则构成实现和平的基础:"以色列军队撤出[1967年]冲突期间占领的领土"和"终止一切交战地位之主张或状态,尊重并承认该地区每一国家之主权、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及其在安全及公认之疆界内和平生存、不受威胁及武力行为之权利".
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用如此众多的措辞将这两项原则神圣化.
安全理事会第1515(2003)号决议核准的"路线图"是在上述原则基础上向前迈进的蓝图.
29.
如果本法院认为建造隔离墙阻碍而且不利于上述原则的实现,从而违背了这项原则,特别是就"不容许通过战争取得领土"这一惯例而言(咨询意见,第117段),那就应当坦言直说.
与此同时,本法院应当提醒联合国大会,这项原则的表达方式来自上述两套并行的原则,在实现中东和平过程中无论如何必须同时并举地实现这两项原则.
30.
如上文所述,以色列争辩说,隔离墙唯一的目的是使以色列能够有效地打击来自西岸的恐怖主义袭击.
对此,本法院只说"根据收到的材料来看,本法院不认为沿所选择的路线修建隔离墙是以色列保护其利益和预防风险的唯一办法,而以色列以此为修建隔离墙辩解.
"(咨询意见第140段).
本法院当然知道,所提供的材料中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阐述,而没有这样的材料,本法院无法以其他方式对上述局势作出反应.
另外,或许可以接受的是,以色列的上述辩解,即使就动机而言确实如其所说,也不能构成其所实际拟定和实施的建造隔离墙工程的充分理由.
本法院雄辩地证明,建造隔离墙依然是以色列方面的违约行为,特别是违反了《关于陆战法规和习惯之海牙章程》》以及《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第四公约》,除非能够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排除这一行为的非法性.
但是,重要的一点是,本法院本来可以自行作出深入的努力,依据事实和法律确认上述辩解的有效性,全面、客观地介绍建造隔离墙问题,并且在此基础上,评估以色列的辩解之词的是非曲直.
31.
我认为在这方面重要的是,应当审查双方相互对平民百姓滥用暴力的问题.
不必细说当事双方诉诸暴力这种悲剧行为的因果关系问题,也不必细说是否应当指责对以色列平民百姓采用携弹自杀爆炸方式的巴勒斯坦人的所谓恐怖主义袭击构成了建造隔离墙充分理由,我认为无可争议的是,双方对对方平民百姓滥用暴力的这种悲剧循环应受到谴责,应将其作为绝对不可接受的行为予以摈弃.
尽管实际上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地作为提交给本法院的具体问题的一个部分提出,但我认为,在处理建造隔离墙问题时,强调这个因素,将其作为法院意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顺理成章的.
我认为从本法院应当以平衡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的角度来说,这点格外有意义.
- 以色列苏丹一村镇遭遇武装分子袭击超60人死亡相关文档
- 渗滤苏丹一村镇遭遇武装分子袭击超60人死亡
- 回答苏丹一村镇遭遇武装分子袭击超60人死亡
- 烧伤苏丹一村镇遭遇武装分子袭击超60人死亡
- 一人苏丹一村镇遭遇武装分子袭击超60人死亡
- 瑞士苏丹一村镇遭遇武装分子袭击超60人死亡
- 的是苏丹一村镇遭遇武装分子袭击超60人死亡
PQS彼得巧 年中低至38折提供台湾彰化HiNet线路VPS主机 200M带宽
在六月初的时候有介绍过一次来自中国台湾的PQS彼得巧商家(在这里)。商家的特点是有提供台湾彰化HiNet线路VPS主机,起步带宽200M,从带宽速率看是不错的,不过价格也比较贵原价需要300多一个月,是不是很贵?当然懂的人可能会有需要。这次年中促销期间,商家也有提供一定的优惠。比如月付七折,年付达到38折,不过年付价格确实总价格比较高的。第一、商家优惠活动年付三八折优惠:PQS2021-618-C...

OneTechCloud香港/日本/美国CN2 GIA月付9折季付8折,可选原生IP或高防VPS
OneTechCloud(易科云)是一家主打CN2等高端线路的VPS主机商家,成立于2019年,提供的产品包括VPS主机和独立服务器租用等,数据中心可选美国洛杉矶、中国香港、日本等,有CN2 GIA线路、AS9929、高防、原生IP等。目前商家针对全场VPS主机提供月付9折,季付8折优惠码,优惠后香港VPS最低季付64元起(≈21.3元/月),美国洛杉矶CN2 GIA线路+20Gbps防御型VPS...

TabbyCloud周年庆&七夕节活动 美國INAP 香港CN2
TabbyCloud迎来一周岁的生日啦!在这一年里,感谢您包容我们的不足和缺点,在您的理解与建议下我们也在不断改变与成长。为庆祝TabbyCloud运营一周年和七夕节,TabbyCloud推出以下活动。TabbyCloud周年庆&七夕节活动官方网站:https://tabbycloud.com/香港CN2: https://tabbycloud.com/cart.php?gid=16购买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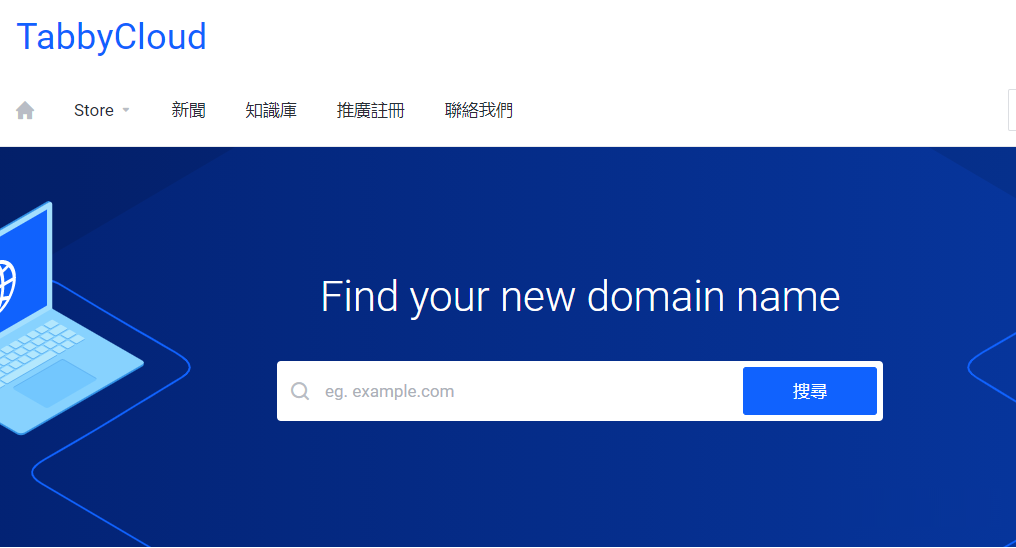
-
德国iphone禁售令苹果手机禁售了 我想问问 这两天刚买的8p现在禁售了 我是赔手里了还是没啥事 是幸运的还是倒霉的支付宝账户是什么支付宝账户是什么?北京大学cuteftp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待遇怎么样啊,电话营销的网站方案设计网站文案策划怎么写显示隐藏文件手机怎么打开隐藏文件夹搜索引擎教程如何利用搜索引擎获取有效的信息?shopex分销王商派的分销王怎么样?听说ShopEx还是大牌子?chmod文件夹linux chmod,如何把一个文件夹及其子文件夹里的文件、文件夹都设为777盛大通行证盛大通行证什么样